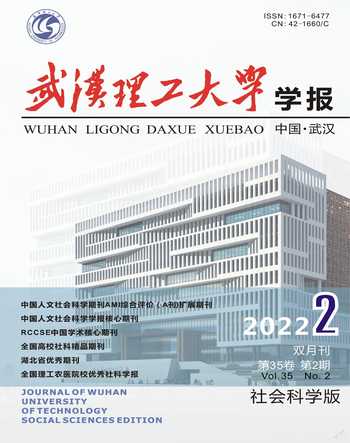论董监高责任追究的制度形态构建
2022-05-30罗艺源
罗艺源

摘要: 公司经营不规范、财务管理混乱、法人独立性欠缺、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等问题致公司破产,董监高对其实施的导致企业破产的行为应负个人责任。《企业破产法》第125条虽对此作出了规定,但未厘清对公司高管的具体问责路径,存在诉权行使主体范围不明、财产保全措施缺位等问题,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从诉权架构的视角,对董监高导致企业破产的个人责任的追究机制进一步细化,将对董监高个人责任的追究作为管理人的职责加以明确,同时赋予债权人会议和个别债权人在特定条件下提起诉讼的权利,并与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相衔接,以确保破产法框架下追究董监高个人责任的秩序与实效。
关键词: 债权人会议; 民事责任追究机制; 诉权制度; 个人破产制度
中图分类号: DF12; DF411.91文献标识码: A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2.02.014
一、 问题的提出
公司①进入破产程序(包括破产清算、重整程序与和解程序)后,债权人尤其是普通债权受偿比例较低是我国破产实务中的普遍现象②。目前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严重失范的现象,民营公司经营不规范、财务管理混乱、法人独立性欠缺、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问题极为突出。因此,管理人不能完整接管到公司财务资料的情况较为普遍,这使得案件的审理难度加大,债权人能够受偿的比例进一步降低[1]。要改善这类状况,必须规范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公司管理层的经营行为。因此在破产法中明确董监高的责任、厘清追究董监高个人责任的路径成为提高债权人清偿比例、促进良好公司治理实践与文化的形成的重要途径[2]48。
对此,我国《企业破产法》对债务人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作为债务人的公司有隐匿资产、逃避债务等欺诈行为,其法定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债权人也有权在法定期间内通过破产管理人请求法院宣告其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另一种是债务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违反忠实勤勉义务,对导致公司破产的行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25条所规定的民事责任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形,较之前者较为抽象③。我国《破产法》虽然规定董监高导致公司破产须负民事责任,但却并未厘清追究这类民事责任的具体路径,因而即使需要追究公司董监高个人破产责任的情形在破产案件中普遍存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却十分鲜见④。
利益平衡是破产法的立法基石,破产责任追究作为破产程序的一环,同样需要权衡多方利益。若在破产法中对公司董监高课以沉重的个人责任,使董监高的职业风险增高,最终必将导致经营活动的萎缩,有碍于公司的拓展,甚至进而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挫伤其及时申请破产的意愿[3]。且我国尚未颁布个人破产制度,若要求公司的董监高对巨额的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债务人必将长时间为沉重的债务所困。反之,如果将董监高对公司破产承担个人责任的要件设置过于严格,则有滋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更容易出现法人人格滥用、公司资产不当流失的问题,有碍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4]。这亟待我们审视破产法的立法目标,权衡各方利益,规划出妥善追究公司董监高个人破产责任的路径和限度。
二、 破产法语境下董监高对公司与债权人承担个人责任的法理基础
《企业破产法》第125条实际上是公司法上的董监高民事责任在破产法上的延伸,有学者指出这条规定“具有典型的公司法上的民事性格,完全依赖于公司法的相关实体规定”,是对公司法缺乏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的补充[5]。《公司法》中关于“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的规定可作为《企业破产法》第125条中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然而,公司法中,由于股东是公司财产的实际所有者,是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人;董事是公司的代理人,基于这种委托代理模式,董事对公司和股东承担信义义务。但在公司法与破产法语境下这样的信义义务悄然发生了改变。
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股东(剩余索取权人)和债权人(优先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公司正常经营状态下,股东是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人,公司的董事会只对股东负责而不对债权人负责。只要不存在支付不能的情况,公司法基于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允许管理层采取冒险行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股东回报也随之最大化)。然而随着公司债|股比例(杠杆率)的增长,一旦公司陷入资不抵债时,二者的冲突就达到了极致[6]。公司法中对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基本安排是公司的收入必须优先偿付债权人,只有在公司清偿债务获得盈余时,股东方能获得利润分配[7]。加上作为现代公司法律基石之一的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的配合,当公司的经营状况出现恶化之后,公司高管就有了以牺牲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经营活动的动机,公司高管往往不是选择采取措施减少债权人的损失,而是选择隐瞒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继续经营,试图摆脱危机维持公司的存在,此时的高管人员并不愿意积极地进入破产程序。此时由于延迟申请破产,公司的资产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债权人受偿的比例进一步降低。公司董监高与债权人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债权人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很难及时了解,此时公司董监高如果仅对股东尽到忠实勤勉的义务而不考虑债权人的利益而采取冒险的经营活动,债权人也难以及时通过破产申请来保护自身的利益。鉴于这样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表明公司财务恶化将导致董事信义义务受益人由股东向债权人转化,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公司法哲学的新变化”[8]。
在公司经营状况恶化,甚至财务上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时,公司高管忠實、勤勉义务的对象由股东转向债权人,虽对债权人不负有直接、独立、持续性的信义义务,但是却负有间接义务。当公司缺乏偿付能力而破产时,债务人取代了公司股东成为公司发展与增值的最终受益人[9]。因此在公司财务上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时,高管忠实、勤勉义务的内容增加了确保作为债权人债权的一般担保的公司财产整体价值不得不当减损的注意义务。公司高管此时不应当采取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并且必须密切注意公司的营运状况,及时向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提出破产申请提案,否则应当对公司破产向公司和债权人承担个人责任⑤。
三、 董监高民事赔偿责任的追究程序
(一) 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范围
1.破产管理人
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人由股东变为债权人,管理人接管了破产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作为破产财团的代表⑥,管理人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追回债务人财产,增加债权人获得财产的机会,使全体债权人获得最大限度的受偿。因此,追究債务人董监高的民事责任成为破产管理人当然的职责之一。破产程序庞杂繁复,同时包含经济事务和法律纠纷,并且还有期限与效率的要求,这些因素在客观上为破产管理人设定了较高的资格准入门槛。另外,破产法还强调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公正地保护债务人、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因此破产管理人必须同时具备独立性、中立性和专业性三方面的特点[10]。基于上述原因,同时出于效率性要求,比较法上很多国家都将破产管理人作为追究责任之诉的诉讼主体⑦。即使有数个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破产管理人通常也具有优先提起诉讼的权利,其他主体必须在破产管理人明确拒绝提起诉讼之后方有权提起诉讼。
2.由债权人会议选出的债权人代表
管理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了公司破产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德国、美国等采用了将公司董监高民事责任的追究主体范围限制在管理人这样一个单一的主体内的做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管理人队伍的专业素质高,债权人完全有理由期待由法院选任并监督的管理人能够公平诚实地执行职务。由管理人负责追偿符合公平性与效率性的双重要求。
然而,相较于德国、美国等破产法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而言,目前我国管理人制度的建设显得较为落后,在专业性方面不足以满足实践上的需求。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任方式不够合理。我国指定管理人主要是采用随机摇珠的方式,但实践表明,随机方式往往导致案件的复杂程度与管理人能力以及执业水平不匹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制定管理人的规定》,在符合有关情形时,法院可以依照债权人会议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更换管理人,但管理人能力不足却并未作为更换管理人的充分理由列入。是否对债务人的董监高提起诉讼需要管理人基于自身的专业能力作出判断,这对管理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果管理人的专业能力不足,其作出的判断则难以使债权人信服,此时将提起诉讼的权利独占性地赋予管理人似乎有欠公平。二是我国管理人的职业风险防范机制尚未建立,监督尚不完善,新的情况又不断涌现,实务处理经验还有待进一步总结[11]。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管理人怠于履行职责甚至和利益相关者勾结的情况也屡见不鲜,难以保证管理人能够尽职尽责对公司董监高的民事责任进行追究。即使债权人会议有权请求法院更换管理人,但在我国破产管理人队伍整体素质不强的现状下,也无法确保债权人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甚至会进一步增加破产程序的成本。因此,使管理人独占提起诉讼的权利既难以保证公平性也不符合效率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虽然从理论上来说由管理人进行追责是最合理也最高效的选择,但是我国破产管理人队伍专业素质不足的现状,决定了想单一地依靠破产管理人实现追究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的董监高的民事责任是难以遂愿的。当然,其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在于规范管理人的执业道德、提高管理人的执业能力并且完善对管理人的监督,然而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实现,现实条件的不完备不应成为牺牲债权人利益的理由和高管滥用经营权力的保护伞。基于我国破产管理人队伍尚不完善的现状,对于管理人作出不对债务人的高管进行追究的决定,应当赋予债权人一定的救济途径。
我国《破产法》规定管理人的职责之一就是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并且向债权人会议报告职务执行情况。追究公司董事或高管的个人责任属于管理人的职权,无论决定是否提起诉讼都应当向债权人会议进行报告。如果债权人会议召开时未能及时做出决定,也应在决定作出后及时向债权人委员会报告⑧。如果管理人决定不提出诉讼或没有提出并在一定期限内债权人催告无效的情况下,债权人委员会认为有提起诉讼的必要的,可以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债权人会议表决认为有必要提起诉讼的,可以选任一名或数名债权人代表提起诉讼。
3.个别债权人
债权人会议的表决结果是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方能通过决议。并且提起诉讼所追回的赔偿款项或有关财物是由全体债权人共同分配。这样的规则显然不利于激发个别债权人提起诉讼的积极性,且极易诱发多数债权人“搭便车”现象,即债权人对于管理人作出不对公司董事等人予以追究的决定是否出于勤勉尽责的态度不主动发问[12]。出于以上原因和专业性的限制,为了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允许个别债权人在向管理人或债权人委员会先后申请被否决的情况下,可以行使债权人代表诉讼,其性质类似于公司法上的股东代表诉讼。为了防止滥诉和破产财产的不当减少,法院可以要求提起诉讼的债权人交纳相应的担保并承担诉讼费用。
4.股东无权提起诉讼
我国《破产法》规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条件相较于清算与和解程序而言较为宽松,并不要求必须达到资不抵债的财务状况,以期促进陷入财务危机的公司及时寻求帮助,重新恢复正常的营运状态。因此,有学者认为只要100%减资或无偿出售全部股份的重整计划尚未被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得到法院认可,股东权就不会消灭。股东完全可以期待在重整成功之后从剩余财产中获得分配,因此,此时的股东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13]。
诚然,在公司没有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时,股东权利并不必然消失,股东在重整程序中仍然可能有一席之地。但重整成功中股东地位较债权人来说更为“劣后”,在重整计划中除非出现符合适用“新价值原则”的情况⑨外,股东在全部组别的债权人得到清偿前不允许得到任何的清偿。因此重整程序中的股东相较于债权人来说追究董事等人造成公司破产的个人责任的动力更小,股东可以通过向管理人或债权人会议申请的程序来追偿。并且由于此诉讼的共益性,诉讼费用将通过破产财产来清偿,如果在重整程序中赋予股东诉权,股东可能会为了追求细微的清偿可能性而发生滥诉的情况,造成用以清偿债权人的破产财产进一步减少。并且诉讼使得破产程序的时间更长,增加的破产成本将威胁到债权人本就不高的受偿比例。因此,在重整程序中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并无必要。
(二) 追究程序的简易化
我国目前破产实践中存在着“案多人少”的情况,司法资源极为紧缺。为使破产程序尽快结束,债权人能够尽早得到清偿,探索更简单、高效的裁判方法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必然需求。构成日本破产制度的《破产法》、《会社更生法》、《民事再生法》均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役员责任查定制度”的简易程序,以求迅速地追究董事的责任⑩。查定制度是一種将狭义的审查手续与诉讼手段(异议诉讼)结合的一种制度,前者能够迅速地实现申请者的损害赔偿请求,后者又赋予了当事者提出异议的权利。这种制度是法院单方口头或书面讯问的方式进行的一种损害赔偿责任的审核,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出一种更加迅速简洁的责任追究机制。笔者认为,比起直接诉讼的方式,这种简单的责任追究机制与我国目前司法资源紧张的情况更为相宜。尤其是对于大量存在的企业主逃废债以及公司账册不全、不清之类的情况,应当通过便捷高效的程序来处理。
这种简易的责任追究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降低破产成本,更重要的意义体现在重整程序中。重整程序的管理模式分为两种:一种由管理人主导,被称为管理人模式;另一种由债务人主导,被称为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DIP模式)。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是指在重整期间经由债务人申请和法院批准,由债务人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经营和管理财产。即使有法院和管理人的双重监督,这种管理模式也具有极高的道德风险。但此模式也具有管理人模式不具有的优势,由诚实的债务人自行主导重整程序能有效提高重整成功率并降低重整成本。因此,是否在破产案件中采用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需要法院的谨慎判断。因此,简易的责任追究程度在重整程序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大企业适用重整程序的正当性依据。日本破产实务中,役员责任查定制度在大型企业的再生案件中得到广泛利用[14]148。
这种审查制度也并不排斥诉讼程序的运用,对于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仍然可以采取诉讼的方式进行。在日本的司法实务中,对董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有可能不采用查定前置主义,而是直接采用直接诉讼的方式实现[15],因此我国对于经营者对公司破产承担个人责任可以采用以审查为主、诉讼为辅的双轨并行的责任追究机制。
四、 利益平衡理念下董监高责任追究的保障制度
(一) 对董监高个人财产的保全措施
执行难是我国当下破产诉讼乃至整个民事诉讼中的一大难题,追究公司董事或高管造成公司破产的个人诉讼也同样如此,如果胜诉之后发现董事和高管个人名下的财产远不足以支付损害赔偿的数额,不但债权人受到的损害无法得到弥补,其受偿比例甚至会因为支付相关的诉讼费用而进一步降低,会大大挫伤债权人追责的积极性。由于民事责任具有任意性的属性,即受害人可以放弃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因此,忠实勤勉的管理人也可能会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选择不追究公司董监高的责任。
然而追究董监高导致公司破产的行为的个人责任这项制度的最优效果并不是在个案中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在惩戒董事或高管个人,而是激励公司董事理性行事,避免产生上述责任。即激励董事和高管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之时积极寻求援助和救济,而不是无视公司困境继续延续经营而损害债权人利益[2]48。如果民事责任的追究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那么即使有资格限制和相关的刑罚规定的辅助,也不利于形成对债权人权利高效而有力的保护,更无益于促进公司治理实践的优化和防范道德风险。
前文论述了董事与高管的责任追究之诉原则上首先需要管理人自行决定提起;或在请求管理人被拒绝后由债权人提起诉讼。那么法院通常在诉讼提起后才能依申请或依职权作出对董事或高管个人财产的保全裁定。然而我国破产法规定了管理人的指定时间在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时,从提出破产申请到法院裁定受理之时期间可以长达15或22天之久。在此期间内,可能受到追责的董事和高管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转移、藏匿自己名下的财产。
因此,我国破产制度中有必要借鉴比较法上的规定,在认为必要或紧急的情况下,法院收到破产申请的同时可以依职权或者因利益相关人的申请对公司董事或高管的个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尽可能地避免董监高对其个人财产的不当转移和藏匿。
(二) 董监高破产责任的限制与免除
1.企业破产程序中董监高损害赔偿责任的减免
随着破产法的完善,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向破产公司的董监高提出相应的赔偿主张,公司董监高的职业责任风险将随之增大。公司董监高时常面临承担巨额损害赔偿的风险,一旦为法院所认定,可能会瞬间失去其全部财产。并且,由于我国目前破产法中个人破产制度的缺位,只要债务人所背负的债权未因时效而消灭,那么破产债务人一生都必须背负清偿债务的责任[14]110,这使得公司董监高在职业中风险与收益之间形成极大落差,造成遏制公司管理队伍的经营活力,经营效率低下、经济活动萎缩的局面。因此,比较法上,不同国家从数额和程序选择上对此做出了责任减免的规定。
比较法上企业破产程序中对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破产责任的限制与免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对损害赔偿的数额进行减免,最典型的是日本法的规定,日本《商法典》在2001年修订时,受经济产业界的压力,对代表董事和普通董事因违反法令或公司章程而发生的损害赔偿金额作了有条件的限制,代表董事的最高赔偿数额为其从公司获得报酬的6倍,普通董事为4倍,独立董事为2倍。二是禁止对重整程序中的公司董监高的破产责任进行追究,以法国法为例:法国于2005年新修订的《商法典》对破产制度有不少重大的调整,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修改之处就在于:一旦企业开始了重整程序,对企业的经营者责任的追究也就相应被禁止了[4]127|157。这些规定显然是受到美国联邦《破产法典》第11章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积重难返的公司经营者摒弃顾虑,更加积极地使公司及时进入重整程序,尽可能使公司能够焕发新生重新回到正常的市场经济中。这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在法律中的体现,符合现代破产法鼓励企业采用重整程序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有学者也认为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25条中所称的“企业破产”,应当以我国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清算”为限[16]199。司法实务中也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认为我国《破产法》第125条只适用于清算程序而不适用于重整程序。
然而这类责任减免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这也是美国联邦《破产法典》广受诟病的地方,即重整程序往往遭到滥用;同时,对损害赔偿数额的限制往往也会引起企业董监高的注意。免责的主要副作用是使公司管理层压力相对减轻,使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乐于求助于破产法庭,美国破产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甚至屡创新高的原因也就在此[17]。对此,美国参议院查理斯·格雷斯勒在参议院辩论会上提出“破产法的基本宗旨在于为那些有能力清偿债务的人施加一些压力”[18]。而破产民事责任确立的目的就是通过使有过错的违法责任人赔偿损失,以填补债权人因违法责任人的行为而受到的损害[19]。因此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中小企业公司经营管理失范以及通过破产逃废债十分严重和破产公司普通债权人受偿比例极其低下的情况,对董监高破产责任减免规定的创设不宜操之过急,我国董监高的个人责任应该得到强化而不是进一步减弱。对董监高的职业风险的转移和分散不应以牺牲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可以通过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来实现。并且,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出台指日可待,公司的高管人员除了董事责任保险之外,也能在个人破产制度中受到更完善的保护。
2.个人破产制度中董监高损害赔偿责任的减免
社会的发展需要每个人都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通过充分而健全的竞争,深度挖掘社会潜在的经济活力。然而竞争存在的地方就必然出现经济上的失败者。当公司的董监高成为经济上的失败者,其背负的债务往往数额巨大,如果不允许个人破产制度予以保护,沉重的债务将会成为这类人群一生无法摆脱的负担,债务人也会间接地成为社会的负担。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目的之一就是使这类“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摆脱债务的沉重枷锁,为债务人保留一定的谋生财产,提供这类债务人以必须的保护和全新的开始。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必须注意公司董监高破产与普通消费者破产的区别,个人破产法应在保护规则上对二者予以区别。
个人破产制度中为陷入破产境地的董监高提供保护的规则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破产免责制度,另一项就是自由财产制度。破产免责制度设立的目的就在于给予“诚实却不幸”的债务人以全新的生活和今后努力奋斗的崭新空间,而不用受到既存债务的过大压力[20]1044。这样的免责存在着重要的正当理由:其一,使无力清偿的债务人从被债务埋葬的重压中得到解救是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其二,使债务人摆脱债务缠身的境遇,重新进入社会生产,而不是沦为政府和社会的负担和救济对象的做法也能使得社会全体间接获益[20]1044。然而,免责程序如果能够轻易获得,则不免会被滥用,宽泛的免责条件容易导致债务人的信用低下和道德危险。过于偏重对债务人的保护会使债权人对破产法失去信任感,有损法律的公正与权威。因此出于惩戒主义的传统和“合同必须严守”的契约精神,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免责条件,例如德国法规定债务人必须将6年内的工资收入中的可扣押部分交付受托人用于分配给债权人。日本司法实务中也出现附条件免责或部分免责的情况。即使是对债务人格外友好的美国《破产法典》也将个人破产分为清算型的第7章和重整型的第13章程序。法律原则上允许债务人自愿选择使用的程序,然而对于未来可能拥有相对稳定收入、有相对强清偿能力的债务人申请适用全部免责的第7章程序的,法院可以驳回其申请[2]48。与普通消费者不同,公司的董监高通常具备符合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其未来清偿债权人的能力相对较强,因此破产法不能简单地允许破产的董监高获得全部免责,而应当为其免责设置一定的条件,要求其用一定比例的未来收入清偿破产债权,达到一定清偿比例后,对余下债务予以免除,保障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平衡。
除了破产免责制度之外,另一项为董监高提供破产保护的制度是自由财产(英美法上又称豁免财产)制度。自由财产制度是个人破产制度立法中的另一项重要制度,使债务人能够保留一定的财产而免受债权人的追索,以保障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个人破产制度,因此必然也没有相应的自由财产制度,但适当救济无力偿债的个人债务人的理念在现行法律法规中也并非毫无体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5条的规定。该规定表明:当个人债务人成为被执行对象时,允许债务人保留特定的财产,这类财产不能成为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的对象。从该项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民事执行制度中为债务人保留财产的标准是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为准,这样的标准仅仅只為债务人提供生存的保障,而无法为债务人及时以劳动获得收入而开始新的生活提供适当的激励。正如Local Loan案中,美国Sutherland大法官所述:从自由的本旨出发,个人为自己以及所扶养人的需要而劳动营生的权利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项具体的财产权利,甚至可以说,比任何一项具体的财产权利都更加重要。因为这仅与私人利益相关,还涉及到极大的公共利益。对于债务人而言,毫无收入与所有收入都归债权人所有的结果都是穷困潦倒,并无多大差异。如果不予以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后新取得的财产予以必要的保护就会使个人破产法保护债务人的立法目的落空[20]1045。因此,破产程序开始后的新收入尤其是劳动收入的归属问题对于破产债务人东山再起至为重要。
对于债务人于破产程序开始后取得的财产的归属历来在学说上存在着固定主义与膨胀主义之争。膨胀主义倾向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规定破产程序中新取得的财产属于破产财产。固定主义更倾向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固定主义下破产人在破产程序中新取得的财产应该属于自由财产。膨胀主义与固定主义各有其理论依据:前者能够让债权人在最大的限度内获得清偿,避免破产债务人再次实施破产程序,但同时也打击了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后尽早开始新的生活的积极性;后者能及早给予破产人全新开始的机会,促使债务人积极寻找谋生的新出路,但债权人的受偿比例更低。但是,通过对比较法上相关法律制度作宏观的分析,虽然在司法实务中还是有不同的保护倾向,但无论采纳何种立法偏向都能基本做到双方的利益平衡,相关的配套制度都能对这种立法偏向起到一定的矫正作用。以德国为例:虽然将破产程序开始后新取得的财产作为可以分配清偿的破产财产,但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50条规定了对劳动收入的特殊保护。这种保护不仅包括债务人自身,还考虑到了被扶养人对于债务人产生的负担,采取了阶梯式的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同时,德国还规定了几种特殊的收入不可以被扣押执行:(1)加班工资一半的金额;(2)圣诞节工资;(3)结婚补贴和生育补贴;(4)教育费用、研究补贴等。由此可见,德国在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的同时,注重对债务人的劳动(包括教育、研究之类的脑力劳动)积极性给予鼓励,保护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的生存权,并且对于结婚生子这类消费需求较大的重大事项也很宽容,缓解了膨胀主义的立法偏向造成的消极影响。与德国相反,日本采用的是固定主义的模式,似乎采取偏重债务人保护的立场。为了缓和这种矛盾,日本《民事执行法》规定:将债务人的劳动收入的1/4作为破产财产进行分配,并且债务人作为自由财产保留的工资每月不可以超过33万日元。对养老金等财产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债权人的受偿比例,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立法上无论是膨胀主义或是固定主义都只是对一国破产财产范围制度的立法例的大致概括。如前文所述,典型的破产法立法国家中几乎不存在纯粹采用固定主义或者膨胀主义立法例的情况了。两种立法例在运行的过程中通过与其他规定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的不足,使破产法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得到平衡。相比较而言,笔者倾向于在我国立法上采用膨胀主义的立法模式,即偏重对债权人的保护。这是因为我国的现状仍然是债权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护,这种状况在目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在债务人陷入破产的境地时,其所拥有的财产的价值往往已经很小,甚至可能出现“无产可破”的情况。破产法的最重要的功能首先应该是使破产债权人得到公平有序的清偿,如果允许将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新取得的财产用于分配可以增加债权人的受偿比例,增加债权人对破产法的信任,也使债务人在经济生活中更加审慎。同时也必须辅以相关的配套制度来弥补膨胀主义不利,避免债务人的劳动的积极性受到打击,鼓励破产债务人的劳动力重新投入市场。所以,为了鼓励债务人生活重建的积极性,对于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因劳动所取得的报酬应保留一部分作为债务人的自由财产。
关于保留比例,笔者认为应当对超过债务人生活地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收入不予保留,少于當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全额保留,对于两个标准的差额的部分依比例予以保留,并依其所扶养的人数进行阶梯式计算。居民消费水平是指居民在物质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过程中,对满足人们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按照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保留债务人的劳动报酬标准是鼓励破产债务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高水平的生活,允许债务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达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摆脱贫困的窘境,符合鼓励其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目的。超过的部分应当用于清偿债权人,提高债权人的受偿比例。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下限标准则是为了保障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的生存权,不挫伤债务人劳动的积极性。
五、 结语
董监高个人责任问题是连接公司法和破产法两大部门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与破产法的公平与效率休戚相关,但我国破产法对其具体的追究机制却缺乏具体设计。追究破产公司董监高导致公司破产的个人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债权人更高的受偿率,但这并不是设计这项制度的最终目的。其最优效果并不在于惩戒董事个人,而是激励公司的董事理性行事以尽力避免个人责任的产生[2]48。这样的制度可以促使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之际积极地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同时尽可能避免债权人的债权受到进一步的损害。破产法中凝结着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破产法规则需要将不同的价值取向内化其中,对公司董监高课以个人责任以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同时,也必须对社会公共利益予以考虑。对公司董监高课以重责会对社会经济活力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除了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之外,破产法也必须对债务人的董监高予以适当的救济。考虑到我国司法实务中债权人受偿率较低的情况,董监高的责任减免与保护应当在即将出台的个人破产法中进行具体设计。
注释:
①我国《企业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包含了我国境内所有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研究对象主要为公司制企业。
②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为例,破产案件中普通债权平均清偿率仅为4.5%。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白皮书(2007-2017)》,载《中国破产审判的司法进路与裁判思维》,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③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25条规定:破产案件中债务人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④笔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截至2019年10月6日,提到《破产法》第125条的裁判文书仅有8份。
⑤由于我国《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申请权人不包括董事会和监事会,因此无权直接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因此应当在必要的时机向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提出议案。
⑥破产财团代表说目前为日本法学界的通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大批学者主张此说,美国破产法则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我国因立法中尚未采用财团法人以及破产财团的概念,因此难以直接主张此说,但此说较之其他例如代理说、职务说都更为合理。参见王欣新主编的《破产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页。
⑦德国《破产法》第92条规定:破产程序开始前后,因属于破产财团的财产的不当减少使破产债权人受到共同损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破产期间内只能由破产管理人行使。英国《破产法》第212条第1项规定:失当行为申请权人由管理人、官方接管人、债权人或责任分摊人申请。法国《商法典》第L651|3第1款规定有权提出申请的人包括清算人或检察院。
⑧参见我国《企业破产法》第23、25、68、69条。
⑨新价值原则为绝对顺位规则的例外,即重整程序中顺位较低的组别通过新的出资来参与分配,因为新出资对于重整成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允许低顺位的组别通过新价值出资为申请前债权或股权留存财产。参见查尔斯·J.泰步著《美国破产法新论(下)》,韩长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版,第1288|1302页。
⑩參见日本《破产法》177|181条、《民事再生法》142|147条、《会社更生法》40、99|103条、《会社法》545|858条.
佐藤鉄男.会社整理·特別清算における会社の取締役等の責任追及.判タ866号,1995第422|424页;谷口安平.損害賠償の査定.金判1086号(2000)第103|105页;石井教文再建手続における役員の地位と責任.高木新二郎,伊藤眞.講座倒産の法システム第3巻,2010年第206|212页。转引自金澤大祐的《取締役の第三者に対する責任と役員責任査定制度の交錯》一文(《法务研究》2018年第15期).
参见《企业破产法》第10条、第13条。由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情形下,提出申请到法院裁定受理最长可达15天,由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情形下,甚至最长可达22天。
日本《破产法》第177条规定:法院在决定受理破产案件时,在认为必要或紧急的场合,可以依破产管财人的申请或是法院依职权对被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法人的理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监察人员等人的个人财产进行保全。在申请时,如果状况紧急的,法院也可以依申请对上述人员的个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
布井千博的《日本における会社取缔役の责任と株主诉讼》一文,参见黄来纪、布井千博、鞠卫峰主编的《中日公司法比较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集第373页);山口幸代的《取缔役の责任の减免》一文,参见田边光政等的《最新会社法をめぐる理论と实务》(新日本法规出版社株式会社2003年第309页)。转引自甘培忠、赵文贵的《论破产法上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追究》,参见《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第115|116页。
《法国商法典》规定:按照第L651|2规定宣告的处罚,不能作为和解(交易)的标的。由此可以看出,法国法通过免除经营者民事责任的规定来鼓励经营者及时对陷入危机中的企业进行重整。
参见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9民终71号,奚振析等诉万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出台已经“破冰”。《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中已经明确提出要“研究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立法工作”。2019年7月,国家发改委会同13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也明确提出要分步推进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附条件免责是指破产债务人需要将其未来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逐步清偿债权人,只有数额达到债务总额的1/10之后,才能获得免责。部分免责是指法院只许可免除债务的一部分(通常为80%),其余不予免责的债务必须继续清偿。参见山本和彦的《日本倒产处理法入门》一书(金春等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5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一)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
(二)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必需的生活费用依照该标准确定;
(三)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物品;
(四)未公开的发明或者未发表的著作;
(五)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用于身体缺陷所必需的辅助工具、医疗物品;
(六)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的物品;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部门名义同外国、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协定性质的文件中规定免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八)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Pfndungsschutz für Arbeitseinkommen
本表中的金额数据自2007年1月22日公布,适用至2009年6月30日止。
类似于年终奖,但是不可以超过劳动的月工资的一半,最高不得超过500欧元。
日本一些法院在实务中采取的是1/2的标准。
举例而言:月收入20万日元的破产者要拿出5万日元归入破产财团;月收入44万元的破产者要拿出万日元归入破产财团;月收入50万日元的破产者可保留的收入也只有33万日元,要将17万日元归入破产财团。
[参考文献]
[1]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破产审判调研报告(2013-2017):中国破产审判的司法进路与裁判思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91.
[2]韦斯特布鲁克,布斯,保勒斯,拉贾克.商事破产全球视野下的比较分析[M].王之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3]近藤光男.最新日本公司法:第7版[M].梁爽,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303.
[4]張子弦.フランスの企業倒産手続における経営者責任[J].北大法学論集,2017,67(5):127|157.
[5]甘培忠,赵文贵.论破产法上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追究[J].政法论坛,2008(2):115|116.
[6]Laura Lin.Shift of Fiduciary Duty upon Corporate Insolvency:Proper Scope of DirectorsDuty to Creditors[Z].46 Vand.L.Rev.1485,1489 (1993).
[7]趙秉志.法学新论:北师大法学院教师法学论文荟萃(上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519.
[8]陈鸣.董事信义义务转化的法律构造:以美国判例法为研究中心[J].比较法研究,2017(5):59|73.
[9]王保树.中国商法年刊2012[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119.
[10]顾功耘,吴弘.商法学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29|330.
[11]广州市两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实践和破产机制调研报告(2006-2016年):中国破产审判的司法进路与裁判思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98.
[12]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法律前沿问题研究:第1辑[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82.
[13]刘颖.日本破产重整程序中的股东代表诉讼[J].政治与法律,2012(2):41|42.
[14]山本和彦.日本倒产处理法入门[M].金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5]金澤大祐.取締役の第三者に対する責任と役員責任査定制度の交錯[J].法务研究,2018(15):125|137.
[16]李永军.破产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17]程春华.破产救济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81.
[18]范键.商事法律报告:第1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332.
[19]付翠英.简论破产民事责任[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1):21|22.
[20]泰步.美国破产法新论[M].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文格)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of the Directors,Supervisors
and Senior Managers:Right of Action Based Framework
LUO Yi|yuan
(School of Law and Business,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205,Hubei,China)
Abstract:In case of company bankruptcy due to such problems as non|standard operation,disordered financial management,lack of legal person independence,and confusion between the companys property and the shareholders personal property,directors,supervisors,senior managers should b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leading to the bankruptcy of the enterprise.Although Article 125 of The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provides for this,it does not clarify the specific accountability path for the companys senior executives.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unclear scope of the subject exercising the right of action,the absence of property preservation measures,and the lack of operability in judicial practice.Therefo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igation right structure,the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for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directors,superviso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leading to enterprise bankruptcy is further refined,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directors,superviso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is defined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nager.At the same time,the creditors meeting and individual creditors are given the right to initiate litigation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 bankruptcy system,so as to ensure the order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directors,superviso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ankruptcy law.
Key words:creditors meeting; civil liability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litigation right system; personal bankruptcy system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Promote the Legal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N Dao|gui1, YU Lin|ying1, ZHAO Mei|rong2
(1.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2.Shayang County Peoples Government Office,Jingmen 448200,Hubei,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has advanced in twists and turns and achieved leapfrog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three time no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1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historical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hinas legal construction has developed in twists and turns.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the legal work was restored and valued,and the idea of “rule of law” was gradually formed.After the 1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developed innovatively in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governance,and the rule of law became the basic strategy of state governance.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further deepened,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has taken shape,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has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It shows that the CPC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rule of law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management.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drawing experience from it,we need to integrate the Party leadership with law|based governance,uphold and improve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reate a favorable atmosphere in which the law is respected,observed,and applied,and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historical 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