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近鹧鸪声
2022-05-30陈位洲
陈位洲
他在家里已经住了三天。这样的日子难得有过。
村里人夸他,说他懂事,孝顺。他听了谦逊地笑笑。
其实,在家这几天,他还有别的想法。他十分怀念那种美妙的啼鸣。夏日炎炎,南风吹拂,那啼鸣高亢、激越,穿越山坡、田野和树林,一声一声,伴他入梦。
他期待着重温这种美好。
“你说的是鹧鸪吧?早绝种了!”母亲说。
“没有。上一次回家时,我还听见过呢!”他说。
“尽想好事,也不看是什么年头儿了!”母亲笑他。
母亲说得也是。村边的树林草丛里,只有低吟浅唱的小雀鸟,要不就是上蹿下跳的小松鼠,哪还有什么鹧鸪!
他还很小的时候就不同了。那时,斑鸠在树林里咕咕叫,乌鸦站在高高的椰子树上聒噪。大中午,村子对面的山坡上就会传来鹧鸪的啼鸣;黄昏降临,村边田坎的刺竹丛里,白面鸡又开始叫个不停。那时候,树林里很生动,绿得迷人,空气很清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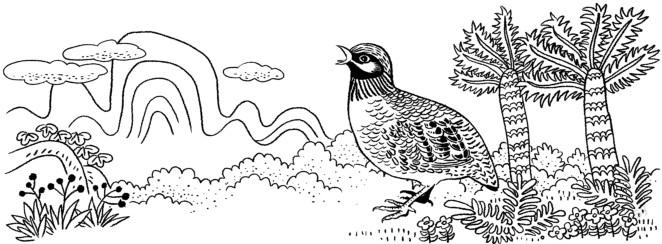
后来,椰子树上没了乌鸦的聒噪。不久,鹧鸪渐渐地就没了踪影,白面鸡也销声匿迹了。
“几十年没听见鹧鸪叫了。”母亲说。
可是,他确信自己听见了鹧鸪的啼鸣,就在几个月前。但他不想与母亲争辩,便不再说什么。
那次是清明节,他回家给父亲扫墓。离家返城时,刚走出村口不远,突然从对面的山坡上传来鹧鸪的啼鸣,婉转悠扬。他驻足聆听,沉浸在一种山水入怀的陶醉中,十分享受。
久违了,鹧鸪!
他当时一激动,就想,下次回家,一定多住几天。
村子周边,不是野树林就是橡胶槟榔园子,全为绿色所覆盖,看上去郁郁葱葱,十分养眼。天变得更蓝,山变得更青。村道铺上了水泥,村巷硬化,庄户人家建起了小楼。环境变好了,可他觉得好像少了什么。
那一声鹧鸪啼鸣让他感到欣慰。他觉得失去的美好又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回来了。
可是,已经是回到老家的第三天了,对面的山坡上仍然没有动静,期待中的啼鸣一次也没听见。他心有不甘。他要到那边去走一趟,希望能够撞上好运。
他记得小时候山坡上有大片的芒萁草。芒萁草烧火旺,还耐烧,村里人常割来做柴火。他跟随母亲到山坡上,母亲忙着割草,他则在一边玩耍。突然,“噗”的一声,吓他一跳,草丛里就有一团东西倏地飞起,闪电一般,很快又消失在不远处的草丛里,只留下一道五彩斑斓的影子。他问母亲那是什么。母亲说是鹧鸪。他恳求母亲捉一只。母亲笑了,摸摸他的头,说:“妈要有那本事就好了!”
山坡上现在更多的是树。树林里,芒萁草还在,这里一簇,那里一簇,零零散散,不像过去那样密密匝匝连成大片。空气中一丝风也没有,树叶耷拉着像在打瞌睡,正午的阳光筛落,闷热异常。他在树林里绕着芒萁草走来走去,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鹧鸪会藏在哪儿呢?环顾周围的树林草丛,他揣摩着,这里那里扔了几块小石头,又扯起嗓子“哇哇哇”大喊几声,可除了听到自己的回声,别的什么动静都没有。
也许母亲说得对,鹧鸪早绝种了。清明节听见那次,不过是自己心心念念而产生的幻觉。
他一脸沮丧,就像不小心弄丢了什么宝贝,再也寻不回来了。
进家门时,母亲正在屋里与邻巷的桂嫂闲聊。
“刚才哪儿去了?”母亲说。
“村边随便走走。”他说。
“大中午也不歇着,看把你晒的!”母亲嗔怪。
“媽,我想明天就走。”
“不是说再住两天吗?”
正说着话,隐约听见一声啼鸣,像鹧鸪在叫。他喜出望外,冲出门去,凝神谛听。
“瓜熟了,哥哥——瓜熟了,哥哥——”
这下他听真切了,是鹧鸪在叫,一声又一声,从对面的山坡上传过来。他两眼放光,像眼尖的孩子替大人寻回了失物一样兴奋:“妈,您听,是鹧鸪在叫!”
母亲不吭声。
他又看向桂嫂:“桂嫂,您听见了吗?”
桂嫂点点头。
“妈,桂嫂也听见了。这下您该相信了吧!”
“我耳朵不聋。”母亲说,“但那不是鹧鸪,是录音机!”
“录音机?”他不明白。
母亲说:“你还记得桂嫂家那位大舅吗?”
他想起来了。那个“络腮胡子”,沉默寡言,目光阴沉,背一杆鸟铳、一个缀满羽毛的竹篓,手拎鸟笼,鸟笼里是一只鹧鸪媒。村里人说,那是个能人,以鹧鸪媒的叫声引来山上的鹧鸪,枪一响,从不失手。
母亲说:“过去是用鹧鸪媒,现在省事了,用录音机。”
“哦——”
他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十分失望。
山坡上的啼鸣还在继续,但不再美妙迷人。他不清楚山上究竟还有没有鹧鸪,若还有,那就赶快逃离吧,逃得越远越好!
他决计明天一早就返城。
[责任编辑 吴万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