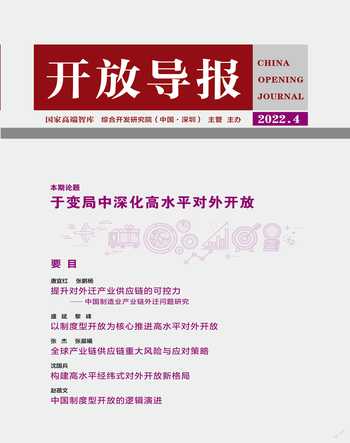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推进更高水平开放
2022-05-30陈淑梅王瓅苑
陈淑梅 王瓅苑
[摘要]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对外开放总体经历了从选择性对外开放、全方位对外开放,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演变进程。制度型开放聚焦于加速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国内制度安排与国际高标准对接、融合、创新,既对外部机制表达一定程度的制度约束,又促进国内制度改革,具有双向性、诱致性和正外部性特征,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目标。目前,我国制度型开放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扩大市场、完善机制、统一规则、促进公平,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基础支撑。标准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要将标准制度型开放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对标对表发达经济体高标准,完善与国际兼容的标准体系,通过制度输出参与全球治理,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
[关键词] 全国统一大市场 标准 制度型开放 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2)04-004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贸易体系变革的前瞻性研究(20BJL047)。
[作者简介] 陈淑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标准化与经济治理;王瓅苑,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一体化与地区治理。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如何稳步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成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必须直面的重要时代命题。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冲击,国际环境愈加复杂严峻且急剧变化,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不仅要保持既有的广度,而且要达到必要的高度和深度,这就需要利用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契机,从全面融入到参与引领经济全球化,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得益于党领导的对外开放。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国内外环境变化息息相关,总体路径上经历了从选择性对外开放、全方位对外开放,到《“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演变进程。
(一)选择性开放阶段(1978—2000年)
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末,我国对外开放从局部范围尝试逐步过渡到全面展开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选择性试办经济特区,开展进出口贸易,扩大市场准入吸引外资,逐步探索对外开放。党的十二大将对外开放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①。在对外开放的初步实践中,我党逐步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资源要素错配严重,国内市场发育很不健全,经济激励缺乏,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与外汇严重短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借鉴国际经验,顺应国内经济发展大势,我国逐渐引“活水”入市场,带动了市场经济变革。由此,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努力发挥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逐步成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下的“世界工厂”。
总结这一阶段的开放成效,对外开放增强了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在外部全球化国际环境作用下,中国利用内部优势造就了“三来一补”的“引进来”选择性对外开放的国内市场环境。通过外部刺激内部生产力,虽然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但驱动了国内市场加速追赶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外资为主导、代工制造、加工贸易为依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二)全方位开放阶段(2001—2013年)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对外开放从全面展开逐渐进入全方位开放阶段。在贸易、投资、金融等不同领域,无论是基于规则,还是基于结果,开放度均不断提升。以贸易开放为例,关税税率是最明显的貿易调节手段,因而是贸易开放度测度最常采用的方法之一。自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认真履行承诺,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截至2010年,货物降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达到并超过了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2003年首次超过50%达到51.9%,2006年超过64%。除此之外,我国还逐步清除与多边贸易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进入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的新阶段。入世后的法律法规调整,是我国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之后第一次系统性的、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其意义超越了简单履行国际义务,为此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开始了从制度学习到制度模仿的过程,不断调整、接受、融入国际规则。从局部地区和有限产业的对外开放,走向全域性和所有产业的对外开放,这是我国融入全球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在GDP总量上连续赶超西方七大工业强国(G7)的历史阶段。
概述这一阶段的开放成效,中国从内部市场争取与全球市场的匹配转为内外部环境在国际经贸规则接轨过程中初步互动。通过制度学习,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适应和学习国际标准,遵守国际准则,并将国际规则灵活运用于国内改革,以此“倒逼”国内的制度改革,实现与国际制度“接轨”。
(三)高水平开放阶段(2014年至今)
2014年开始,我国从全方位开放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表明我国开放由扩量向提质发展。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此后,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每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十四五”规划纲要》更进一步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十二篇),并设置专章对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部署(第四十章)。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国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必然选择。仍以贸易开放为例,入世20年以来,我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7.4%,对外贸易依存度由2006年的64.2%下降至2019年的31.8%。国内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从劳动力数量红利逐渐转变为数量及质量优势并存,伴随着国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创新动能明显不足,部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美国不仅主动挑起了对华经贸摩擦,而且逐步升级至科技战,企图在多个领域与中国脱钩,将中国划出全球多边、双边贸易体系。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让全球经济复苏更显乏力。
世界各国要达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均要求从一种“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转型为一种“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中国也不例外,进一步扩大开放不能囿限于外国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市场准入与扩大开放,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涉及国内制度改革,实现与国际制度“接轨”,还需要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制度型开放则是必然的选择。
二、以制度型开放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制度型开放的时代诠释
“制度型开放”是2018年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开放的新表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做了重点强调,《“十四五”规划纲要》部署了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的相关工作,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大目标。“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因此成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的我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工作之一。
纵观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特别是实施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体,在经济腾飞的早期阶段,往往基于自身的发展需要,相对独立地制定与对外开放相关的各类制度体系。然而,随着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对其他经济体外溢效应的增强,各经济体均强调提升自身制度体系和其他国家制度体系的相容性,制度型开放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语境下,制度型开放的内涵、路径和效用等有着中国的独特注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在《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思路研究》中从历史、现实、国际、国内四个维度将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界定为,“在具有较强外溢效应的相关体制机制领域将本国相关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高标准规则进行对标对表,在此基础上实施一系列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措施”。从本质来看,制度型开放是从“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的拓展、延伸和深化,是对新一轮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调整和完善,是具引领作用的先进制度安排。从实践路径而言,充分运用自由贸易区战略,有效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等平台,有助于推动制度型开放,在开放倒逼改革中推动规则等制度体系的优化。从参与全球治理的效用来看,我国既通过制度学习实现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对标,也通过制度供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改革。
总而言之,制度型开放专注于加速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国內制度安排与国际高标准的对接、融合、创新,既对外部机制表达一定程度的制度约束,又以开放促进国内制度改革。通过对已有实践路径的不断优化,提升国内循环的起点和国际分工水平,推动制度输出,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取主动权、争取话语权,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推动由商品等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二)制度型开放与对外开放
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重点。40多年来,在开放条件下,借助于融入外部全球化环境的机遇,中国通过降低关税、引进外资等措施实行“渐进式”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今后的高质量发展,也应当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面对当下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在“边境开放”中降低关税措施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境内开放”的非关税措施亟须提上日程。《“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具体目标: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以制度型开放为目标。从国内环境看,“边境开放”到“境内开放”将市场开放深入至内陆地区,推动关税措施到非关税措施开放,畅通国内大循环,这一过程要加快国内制度变革,作出相应制度安排,以有效应对外部对国内制度、政策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击。从国际环境看,通过深化规则、制度改革,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衔接国际高标准规则,融入国际大循环,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首先,有着双向性特征的制度型开放能够通过规则制度协调统一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在国内国际规则对接方面具有双向协调特征,意味着既有国内制度向外开放,又接受国际制度向内输入。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管理和规制境内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更加强调规则等制度标准的统一和兼容。制度型开放无论是从领域的广延性需求角度看,还是从程度的深化性需求角度看,都更加具有协同、兼容乃至一致的内在特性,能够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其次,具有诱致性特征的制度型开放可以通过促进国内制度改革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将制度创新机制引入到本国,而这些被引入的制度创新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诱致性制度创新,以及通过对外贸易将市场竞争激励、信息等引入本地,加快地区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外溢,进而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制度输入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形成与国际经贸活动中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规则和制度体系,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再次,拥有正外部性特征的制度型开放足以通过推动国际规则变革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输出将国内已经制度化的规则体系,通过输出的方式将其变为国际通行规则,构建更加公平和合法的国际贸易制度规则,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有助于发挥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也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三、建设统一大市场推动制度型开放
3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①。文件明确了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的具体要求,这与通过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相契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又可以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我国由大到强的统一市场将从市场规模、市场取向、规则统一和环境竞争等方面推动制度型开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让制度型开放更有底气、更加灵活、更具竞争力。
(一)孕育超大规模市场,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外溢空间
中国具有地缘辽阔、人口众多的天然禀赋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国民人均收入、消费能力逐渐提高,已具备形成大规模市场的必然条件。但一直以来,我国地区发展并不均衡,由于一些地方保护、相互竞争的关系,存在一些隐性的、隐蔽的、歧视性的政策壁垒,这就阻碍了要素资源、商品服务的流通,致使市场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有效运用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精细化分工,从而扩大需求、刺激生产,更加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使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得到更大范围的开放,更好发挥本土市场效应,为制度型开放孕育畅通的超大规模市场,推进经济的高质量运行。
(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制度型开放提供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尤其作为超越型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事关重大,需要正确处理,政府管控过度限制或是过度放松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缺少政府“有形之手”的方向指引、路线设置,市场极易产生混乱。在经过40多年的磨合期后,市场已经形成一定的运行规则,调节能力逐步完善。而中国具有天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功能,在统筹管理与发展的任务时,容易出现过度调控引起政策的不稳定。地方政府采取主导型产业政策形成了“行政区经济”现象,对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造成了显性或隐性障碍,既限制了市场规模,又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
只有突出市场取向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各种阻碍,废除旧机制,建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才能为制度型开放提供更加自由的市场环境,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
(三)建立统一市场规则,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制度供给
从建构主义视角看,我国天然拥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认同感,更容易形成统一的制度规则。但长期以来,国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规则,这其中有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如对经济特区的支持力度、开放力度、区域倾斜政策明显优于内陆城市等;有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的原因,如地方政府过度注重权力的使用以及腐败问题,权力的应用对制度完善形成了一定的阻礙;也有大型国企或强势企业垄断的因素,其资源高度集中,拥有规则的顶端优势。经济持续增长发展需要适当的制度平台,缺乏一套市场主体共同接受的游戏规则,既压制了国内市场活力,又无法提供对外制度型开放的制度基础。
必须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形成统一的国家标准的深度基础,应充分运用统一标准这一数据化量度,推动建设国家标准和规范,以及统一的市场规则,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进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建设高水平商品和服务市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政策,对标国际出口标准,在国际标准化领域占据有利地位,以高质量标准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制度基础。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以优质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推进高水平开放。
(四)优化竞争环境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制度创新环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是没有市场自由和市场竞争,也不是没有发展竞争,而是缺少平等竞争,缺少自由竞争中的公平环境和条件。地方政府有时出于保护本地企业等原因,限制产品进口或其他地方企业、外资企业投资,形成经济歧视和市场准入障碍,也制约了内部间或内外部公平竞争带来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
平等的竞争要对国内市场开放,也要对外资开放,才能产生虹吸效应,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企业的垄断效应,给予企业同等竞争地位,打造自由平等的经营环境,激发企业不断创新的动能,创造更优质的商品服务,提升商品和服务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走出去”和“引进来”。要将国内市场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使国内市场既成为内部的向心力,又形成外部辐射源,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创新的动力,持续为对外开放赋能。
总的来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统一规则,促进公平竞争,刺激创新,推动政府功能转型,发挥市场能动性,增强制度透明度,既是制度型开放推进国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也向外部世界提供制度供给,为处于不确定性动态变化中的世界注入新的活力。
四、将标准制度型开放作为推动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
制度型开放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诸多方面。其中,标准制度型开放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阵地。伴随标准的国际化,标准将成为制度型开放的载体,顺应标准制度型开放的国际趋势,我国标准制度型开放将能够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标准成为制度型开放的载体
对内,“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①。对外,标准能够提升产业质量技术基础,有助于抓住产业顶端优势,帮助国家抢占全球产业链竞争话语权,在全球市场形成竞争优势。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能够助力高技术创新,可以促进我国高水平开放。因此,标准是消除贸易壁垒、强化贸易便利的有效手段,是制度型开放联通国内外可量化的重要载体。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贸易规则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了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再到当前高标准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的转变,由各国产品和行业标准、技术法规的差异,以及合格评定的差异或重复而引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逐渐成为主要贸易壁垒。全球高质量贸易协定已将国际经贸规则的主题转向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包括标准一致化、竞争一致化和监管一致化。作为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治理与贸易规则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既成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重要依据,也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已经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实施了19个自贸协定,关税的影响和保护正在逐渐减小,包括标准在内的非关税措施的作用越发显得重要。更高水平开放是其中一些自贸协定升级的一大特色,其中不断创新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可以支撑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在自由贸易试验区里先行先试“中国标准”,推动“中国标准”成为制度型开放的载体,再以标准的“软联通”打造国际经济合作的“硬机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推动不断由商品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促进国内国际双标准,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二)标准制度型开放的国际趋势
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不定期发布标准化战略,不断促进在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发声,加强其在标准领域的主导地位。以欧盟为例,其技术标准化不仅是经济一体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一体化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欧盟的标准化有其内生性的动力,更有其外推性的作用。由于制度的非中性特征,在国际关系中几乎不存在完全客观、没有任何价值取向的制度。欧洲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不仅包含技术内容,还包括欧盟核心的民主价值观和利益,以及绿色和社会原则等。2022年2月,欧盟发布新的《欧盟标准化战略》,明确提出“通过制定全球标准,欧盟输出其价值观,同时为欧盟公司提供重要的先发优势”。欧盟区域标准显然已经成为维护其核心利益和输出价值观的重要制度型工具。
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标准制度型开放中的联盟化趋势日趋明显。美国与欧盟于2021年6月成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从当年9月在匹兹堡召开首次会议到2022年5月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美欧选择在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加强合作,旨在牢牢抓住高新技术的标准制定权,企图通过制定技术和行业标准,进一步占据在全球贸易、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双方表示要加紧制定尖端技术规则,以对抗“非市场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计划创建美国—欧盟战略标准化信息(SSI)机制,以实现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信息共享。
(三)推动我国标准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标准化工作历经机制化建设、入世合规化、标准化改革等不同发展阶段,于2021年首次发布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大幅提升标准化水平、显著增强标准化开放程度等发展目标。依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总体要求,基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时代背景,通过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建议从标准国际化跃升、标准体系健全、标准认证衔接等方面推动标准制度型开放。
1. 高效实施标准国际化跃升工程
标准国际化对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贸易至关重要,更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抓手。要实现标准国际化,除了目前已经采取的将中国标准直接转化为国际标准,以及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再转化成中国标准,我国还需加大力气,实现让中国标准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标准。为促进标准制度型开放,对于国际上已经成熟的国际标准我国要加大采标力度,提升转化率,这不仅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益,也有助于消除贸易壁垒。对国际上尚未形成国际标准的要加大研究,充分运用我国作为WTO成员的话语平台,既严格保证我国的标准、技术法规制定和实施符合相关要求,也要充分把握对其他成员的标准、技术法规进行评议的机会,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及时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积极融入国际标准制修工作。在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将我国优势规则向国际推广,促进生成国际规则,有效帮助我国企业在面对国际竞争时应对新型贸易壁垒,实现中国标准“走出去”,引领国际标准制定。
2. 尽快健全结构优化、先进合理、国际兼容的标准体系
加速形成由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和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共同构成的新型标准体系。我国目前仍处于政府单一供给标准体系,企业对标准化工作认识不到位,标准制定多为满足产品出口对象国要求而动能不足。我国部分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拥有制定国际标准的能力,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主观能动性,有效运用国外合作企业或机构的标准动态捕捉能力,官方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交流活动,加快推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
3. 促进标准认证衔接,破除内外贸一体化制度性障碍
2021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59号)。2022年5月9日,商务部等14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的通知》(商建函〔2022〕114号)。实现内外贸一体化需要加速推进“同线同标同质”,也就是按照相同标准、相同质量要求在同一生产企业生产既能满足境外特定目标市场要求又可內销的产品。既要加强标准内部协调,提高标准技术水平,积极开展国内国际标准转化,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加快提质升级,也要通过采用国际标准,补齐国内标准短板,提升对外竞争力。
4. 深入拓展标准化国际合作,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
依据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到2025年,标准化工作由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标准化开放程度将显著增强。要提升标准化对外开放水平,就必须深化标准化交流合作,强化贸易便利化标准支撑,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随着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稳步拓展,我国将深入开拓包括标准化在内的国际合作,持续优化规则和标准制定的透明度和国际化环境,将包括标准化在内的经验与世界分享。
五、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制度学习、制度互动、制度竞争到制度供给的不同阶段。从一开始的学习和适应国际规则、国际标准等,到逐渐接受和对标国际标准与国际规则;从被动卷入到主动介入,引致了与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之争和标准之战。制度型开放是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制度型开放不仅体现在开放的水平上,也意味着开放领域更加扩大,意味着开放要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对接。制度型开放必将促进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与创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会建立统一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标准是制度型开放的载体,对内需要政府引导、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动,对外需要深化标准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标准制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制度型开放需要以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环境,以标准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制度型开放迈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利于加快对外开放进程,助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参考文献]
[1] 陈淑梅.“上海标准”推动制度型开放[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4-19.
[2] 陈淑梅.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技术标准化[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3] 戴翔,张二震.“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制度型开放[J].国际经贸探索,2019,35(10):4-15.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思路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2):125-135+148.
[5] 刘彬,陈伟光.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J].国际论坛,2022,24(1):62-77+157-158.
[6] 刘志彪.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基石[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4):6-13.
[7] 盛斌.中国、CPTPP和国际经贸新规则[J].中国经济评论,2021(4):92-96.
[8] 徐秀军.从中国视角看未来世界经济秩序[J].国际政治科学,2016,1(1):90-117.
[9] 姚树洁.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逻辑及战略路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16-27.
[10] 张二震,戴翔.更高水平开放的内涵、逻辑及路径[J].开放导报,2021(1):7-14.
Promoting Higher Level of Open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hen Shumei, Wang Li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Academy of Global Governance & Area Studies,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generally gone through an evolution process from selectiv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ll-rou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a higher level of opening up. Institutional opening focuses on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domest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uch as rules, management, and standards with international high standards. It not only expresses a certain degree of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external mechanisms, but also promotes domestic institutional reforms. It is bidirectional, inductive and positive. The externality feature is a new goal of a higher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t present, Chinas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xplorati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an expand the market, improve the mechanism, unify rules, promote fairness, and provide basic support for institutional opening. Standard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tandard and institutional opening the focus of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benchmark the high standards of developed economies, improve a standard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world,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output to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o spread more Chinese voices and inject more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Key word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tandard;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High-Level Opening-Up
(收稿日期:2022-06-20 責任编辑:罗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