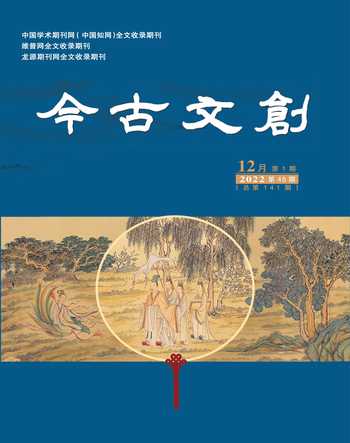记忆的力量
2022-05-30林巧
【摘要】 记忆是《宠儿》的核心主题之一,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对记忆的思考引发读者的关注和深思。主人公赛丝在故事的最后是在回忆起往昔团结氛围的社区里的黑人群体的帮助下,才摆脱了宠儿走出困境的。由此表明了记忆的力量,也象征着黑人个体应在黑人群体的框架中去回忆,通过集体记忆的力量才能走出困境,回归到凝聚生命力的社区。
【关键词】记忆;集体记忆;美国黑人;《宠儿》;托妮·莫里森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45-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45.005
《宠儿》是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的第五部作品。从《宠儿》开始,莫里森开始转向关注黑人的过去,对百年来黑人历史做一番梳理,对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观照和反思,关注黑人共同的命运及凝聚力的呈现。《宠儿》的面世便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评论家们高度评价这部小说,称它是“一部历史,字字是惊雷,句句是闪电”,认为它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不读这部作品就“无法理解美国文学”。《宠儿》在美国文坛建立了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地位,无论是其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手法都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和评论家的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对《宠儿》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而1988年莫里森凭借该书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93年更凭借该书和《所罗门之歌》《爵士乐》等作品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故事取材于1856年逃亡黑奴玛格丽特·加纳杀死自己孩子,以使他们从此免受奴隶制残害的真实事件。小说主人公赛丝从南方奴隶主庄园“甜蜜之家”逃到俄亥俄州,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被奴隶主带走,她亲手扼住了自己女儿的喉咙。莫里森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展现了往昔黑人奴隶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揭露了奴隶制对黑人身心的摧残。
“记忆”一直是托妮·莫里森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她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之一。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邀请读者一起进入被排斥、被隐藏、被遗忘的历史情境。“《宠儿》不仅碎片式展现了各人物独有的个人记忆,同时从不同角度勾勒出黑人社群有关自身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1]53小说里莫里森对过去事件的挖掘与回忆成为摆脱困境和重塑自身的契机,呈现了黑人集体对于过去奴隶身份的摆脱并建立自信的积极姿态。
“集体记忆”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概念。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指出,“集体回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2]68他指出,集体记忆可以用于建构过去,是个体置于在集体的社会框架里进行的回忆。而记忆是人们在经历时代的变换后,留存在身体和心灵里标志性的、带有集体色彩的个人元素。在《宠儿》中,莫里森直面历史,以赛丝弑婴事件呈现了黑人在奴隶制下的悲惨记忆来传承黑人历史上玛格丽特·加纳杀子的真实记忆,激活了黑人群体的集体记忆,展现了奴隶制下黑人群体的悲惨与苦难。
一、痛苦不堪的过去:黑人血与泪的奴隶记忆
哈布瓦赫指出,“每一个个体心灵后面都拖着一长串记忆。”[2]70在奴隶制时期下的黑人,任打任骂的奴隶身份成为他们血与泪的奴隶记忆。莫里森将《宠儿》的时间背景设置在美国内战结束后,这一时期南方黑人们虽然免去了奴隶制的压迫,但曾经沦为奴隶的记忆仍鲜明生动。小说中对饱受奴隶制摧残的赛丝来说,往昔的奴隶生活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的奴隶记忆折磨着她,久久不能散去。
哈瓦布赫在谈论童年记忆时说道:“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2]82记忆是一种重复行为。自人出生有记忆开始,在不同时期,各个阶段的记忆是不同的。赛丝作为黑人奴隶的孩子,她从一出生开始,记忆就是痛苦不堪的。赛丝拥有少得可怜的与自己母亲的回忆,而这些回忆也不是温暖的、充满母爱的。“她从来没为我梳过头,也没干过别的。”[3]71赛丝从小缺少母爱的关怀。而当赛丝的妈妈来接她并告知她通过自己身体上的记号来辨认自己时,赛丝天真地想烙上同样的记号,来让妈妈也认得出自己。这是孩子对母爱的需求,是相互记忆的渴望,可回應赛丝的却是一个耳光。在赛丝母亲的眼里,烙上记号便是沦为奴隶低人一等的表现。她不愿赛丝也过上自己悲惨痛苦的生活,便以一记耳光来打醒赛丝。由于赛丝童年的记忆,当她面对“学校老师”的追赶时,她迫不得已下意识地做出了与她母亲类似的行为,即杀死自己女儿的过激行为,这其实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沦为奴隶的悲惨下场。这一行为虽出于母爱之名,但赛丝余生却被这一行为留下的记忆缠绕痛苦不已。
在赛丝被带到“甜蜜之家”后,她短暂地过了几年幸福生活。可当奴隶主更换之后,“学校老师”管理的“甜蜜之家”不再甜蜜。赛丝及其他黑奴被赋予动物属性,被呵斥、侮辱、鞭打。赛丝自己的奶水被无情地夺走、被强行地当作动物来衡量,她的后背被鞭打地伤痕累累。当她千辛万苦地逃离“甜蜜之家”后,杀死自己女儿的行为又使她深受折磨。保罗·D的到来使她回忆起以前的奴隶生活,也了解到丈夫黑尔目睹自己被凌辱却无动于衷的真相,由此她不断地从现在出发去追溯、挖掘过去血与泪的个人记忆。赛丝自己也清楚,记忆是不会消散的。“有些东西去了,一去不回头。有些东西却偏偏留下来……有些东西你会忘记。有些东西你永远也忘不了……不仅留在我重现的记忆里,而且就存在于这世界上。”[3]42
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存在,个体记忆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张隆溪在论述记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时说道:“记忆是事实和人生经历在我们头脑和心灵上留下的印记。记忆是追叙历史的依据,无论个人的历史还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都有赖于我们个体或集体的记忆。”[4]67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是相关联的。个人记忆既是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也是集体记忆的依据之一。在赛丝痛苦的个人奴隶记忆中,隐含了历史,也隐含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黑人群体具有的特殊记忆。哈瓦布赫认为,个体思想汇入到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之中,是群体共有的思想总体的一部分。在集体的意义上,个人思想和个人记忆在集体和社会的框架中去整理、回忆、集合。以赛丝为代表的黑人奴隶,在当时历史下经历的痛楚是无法述说的,由此也映射到当时奴隶制下,美国黑人群体身份背后的辛酸与痛苦。
二、难以割舍的苦难:124号的家庭记忆
哈瓦布赫在《论集体记忆》中写道:“群体自身也具有记忆的能力,比如说家庭以及其他任何集体群体,都是有记忆的。”[2]95这里他所说的群体记忆,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说法。实际上,家庭记忆是由家庭群体里各个成员的意识记忆中生发出来的。当家庭成员都生活在一起,居住在同一个空间里时,集体里的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忆家庭共同的过去经历。《宠儿》里生活在124号房子里的每一个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忆起弑婴事件的记忆。莫里森在《宠儿》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了124号房子的存在,而124号房子在小说中也成为一个家庭集体的空间,房子里的每个人都拥有着关于过去的苦难记忆。“一百二十四号充斥着恶意。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房子里的女人们清楚,孩子们也清楚。”[3]3被母亲杀害的婴儿的灵魂萦绕在124号房子里,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恶意与悲伤。
在小说一开始,赛丝的两个儿子,因受不了婴儿鬼魂在房子里作祟,而选择在十三岁那年相继离家出走。贝比·萨格斯在病榻上躺着,“悬在生活的龌龊与死者的刻毒之间,她对生或死都提不起兴致,更不用说两个出逃的孩子的恐惧心理了。”[3]4赛丝对于自己杀死女儿的记忆格外清晰。除了记得自己别无选择杀死女儿的记忆之外,赛丝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交换了身体来获得女儿墓碑刻字的事情。保罗·D的到来使赛丝回忆起更多关于“甜蜜之家”的事情,而宠儿化身的到来,使得赛丝提及了更多伤痛的过去。“过去的一起都是痛苦,或者遗忘。她和贝比·萨格斯心照不宣地认为它苦不堪言。”[3]68
丹芙始终铭记着有关赛丝弑婴的家族记忆。[1]54作为赛丝的女儿,母亲亲手杀死自己姐姐的记忆一直萦绕着丹芙,使她产生“她每天晚上割下我的头”[3]239的幻觉。这表现出丹芙出于家庭记忆对赛丝的恐惧。虽然她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的囚禁折磨,“但是死去的姐姐的幽灵,母亲苦难的过去,一家几代人漂泊离散的历史,将她幽禁在蓝石路124号狭小的空间中,将她笼罩在家族充满苦难和屈辱的记忆中,将她本应鲜活灿烂的少女生命扭曲成被母亲和死去姐姐的怨恨主体占据的躯壳。”[5]104 痛苦的家庭记忆使得丹芙从小生活在孤独和安静之中。
124号房子里的家庭记忆,使得宠儿化作鬼魂时将赛丝一家人囚禁于孤独的境地,对过往的苦难记忆久久不能忘怀。而当宠儿化作肉身来到124号家里时,赛丝和丹芙由于过去记忆的连续,保持着对宠儿的愧疚,最终被控制和吞噬。哈瓦布赫也认为,“家庭成员不断交流着彼此的印象和观点,这会加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纽带,而一旦他们试图要斩断这条纽带时,他们便会感到这条纽带竟是如此坚韧。”[1]96《宠儿》中124号房子里虽充斥着以往悲伤苦难的家庭记忆,但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保持着对过去的连续感。124号房子由此有了象征意义,充斥着美国黑人被压迫、被割断的苦痛回忆,也凝聚了支撑和联系着的集体力量。
三、维系生命的力量:黑人群体社区记忆
莫里森从《宠儿》开始,小说写作转向黑人的过去历史,对百年来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观照和反思。《宠儿》结尾中赛丝母女在黑人群体的帮助下,回归到了黑人社群,呈现了黑人群体的社会责任感。由于奴隶制和种族问题,黑人群体在早期历史中成为孤独的流散者,因此黑人群体聚集的社区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空间不足以支撑美国黑人的生存,对于被割断和亲人与家园联系的黑人个体来说,社区成为极其重要的空间,它给予离散的黑人个体以维持生命的集体力量,是对家庭空间的有力补充。”[6]109
在小说中,贝比·萨格斯可以称为黑人社区里的领袖人物,她像黑人牧师一样帮助黑人群体团结在一起,劝告他们找回自我、热爱生活。“在莫里森的小说中,歌唱、讲故事和玩笑以及社区的滋养和疗伤,都是寻求形成和维持黑人集体的活动。”[7]55贝比·萨格斯固定举办“林间空地”的仪式,利用社区的集体力量,促进黑人群体的向上发展。黑人群体通过在草地上赤着脚跳舞、用和声给舞蹈伴奏,释放了自己的身体来获得身心自由,得到治愈的力量。黑人群体“通过集体的心理疗法治愈社区人们过去所经历的创伤。共同的痛苦经历使他们走到一起,集体的力量使他们走出过去,重建新的自我。”[6]135
当“学校教师”试图抓走赛丝和她的孩子们时,奴隶制的入侵使赛丝做出了绝望的过激行为,也使得124号房子陷入了与辛辛那提社区对立和隔绝的境地:弑婴后的18年里,赛丝的两个儿子相继逃走;贝比·萨格斯困于床上死去;赛丝活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丹芙整日关在家里,足不出户。当保罗·D来到124号时,家中的鬼魂被驱走,可之后却化作宠儿的肉身,吞噬着赛丝的生命。此时,124号与社区之间陷入僵局。
正如杰瑟(Nancy Jesser)所说,当家与社区之间变得僵硬的时候,从这个空间到那个空间,虽不是不可能但却很困难的时候,这些空间就失去了它们改变社会的力量。由于蓄奴制、殖民化以及渗透于美国历史任一时刻的种族歧视的存在,如果说所有的家庭都受困于暴力和创伤,是有道理的。正是莫里森对这种广泛存在的困扰的坚持使《宠儿》成为一个考察家庭空间多难历史的有用场所。[8]326《宠儿》中,带领124号打破这种僵局,重获生机的是赛丝的女儿丹芙。她走出了自己的世界,跨出家门,走向社区。由于丹芙主动向琼斯女士诉说了家里断粮的情况,社区里的人们也主动将食物放到124号门前,帮助赛丝一家度过饥饿的困境。而宠儿的离开也是由于丹芙去找工作,告知实情,社区里的人們才了解到真相。以黑人群体驱鬼结尾,在邻居们汇集到124号房子门口时,宠儿永远地消失了。黑人个体势单力薄,在历史背景下被歧视、被虐待,如果想要改变弱势群体的地位,黑人就必须团结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去争取自由和解放,去获得平等的地位。
当女人们结伴去124号房子驱逐宠儿时,“所有三十个人相偕来到一百二十四号的时候,她们第一眼看见的不是坐在台阶上的丹芙,而是她们自己。更年轻,更强壮,简直像躺在草丛中睡觉的小姑娘” [3]299,集体的力量使得她们觉得自己更加强壮、更加有力量。而这个场景对赛丝来说,“仿佛是‘林间空地来到了她身边,带着它全部的热量和渐渐沸腾的树叶;女人们的歌声则在寻觅着恰切的和声,那个基调,那个密码,那种打破语义的声音”[3]303。赛丝回忆起了“林间空地”,这是社区群体黑人集体的美好回忆,女人们的歌声“震撼了赛丝”,使得“她像受洗者接受洗礼那样颤抖起来”。宠儿被赶走后,女人们集体的力量也传递给赛丝力量,使得她清醒起来,由此重获生机。
四、结语
“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文学在不断接受记忆邀约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参与人类记忆的重构。”[9]59莫里森在小说《宠儿》中,通过对以赛丝为代表的黑人奴隶记忆的描写,124号家庭记忆的书写,最终回归到黑人群体社区记忆,表明集体记忆的力量使得赛丝一家最终打破与社区的僵局,摆脱了宠儿的吞噬,重获生机。出于黑人作家的认同感与责任感,莫里森打破了沉默与僵局,将过往黑人的苦难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表明黑人要想摆脱过去苦难的历史境地,必须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去面对历史,塑造全新的民族形象。
参考文献:
[1]王丰裕.“记”与“忘”:莫里森《宠儿》中记忆的伦理观照[J].外国语文研究,2021,7(03):52-61.
[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4-45.
[3]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4]张隆溪.记忆、历史、文学[J].外国文学,2008,(01):
65-69+127.
[5]黄丽娟,陶家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的黑人代际间创伤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11,33(02):100-105.
[6]赵宏维.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Robert B.Stepto,A Home Elsewhere:Reading African American Classics in the Age of Obam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55.
[8]Nancy,Jesser.Violence,Home,and Community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3,no.2(1999):325–45.
[9]洪治綱.文学:记忆的邀约与重构[J].文艺争鸣,2010,(01):56-59.
作者简介:
林巧,女,汉族,四川绵阳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