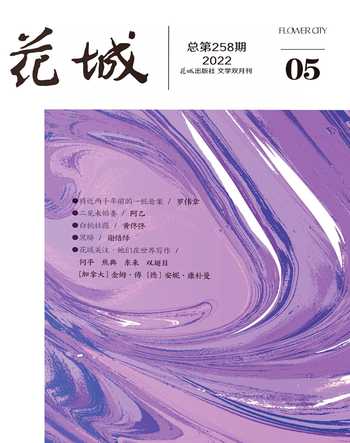在火之上
2022-05-30李晓君
李晓君
一
我在墙根下捡起一枚瓷片:青花釉里红,图案残缺的美依然楚楚动人。我举着瓷片对着夕阳,光线仿佛能刺破这半透明薄片,芙蓉花在夕照中变得血红。青花是这个城市的别名。现今流散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青花瓷,大都来自这个城市。来自皇帝、督陶官、艺匠、工人、农民、商人等社会各阶层构成的庞大体系。人们喜爱这种叫瓷的物件。为此以最优质的原料、发达的水系交通、严密的分工,以积淀数千年的审美:书法、绘画、雕塑的菁华,来保障它的完美无缺。为使每一件瓷具有独一性,除了将完好的成品送到皇宫,它“孪生”的 “兄弟姐妹”,就此粉碎,在地下堆积成时间和艺术的碎片。
一件瓷的诞生,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有经验的师傅来保证它工艺上的极致。日积月累,除了沉淀出精湛的技艺之外,它也形成了一种生活形态,一种精神上的严苛和专注。当它们汇集到一起,以一件瓷的面目出现,所有背后的艰辛、汗水、喜悦,都消失不见。人们甘心地为一件物所奴役,里面包含着一种怎样的意义——仿佛是瓷而不是人进入了历史。人们以举国之力生产瓷器,用“疯狂”来形容都不过分。哪怕王朝更替,瓷,缔结起的生产制度、运行机制、生产组织体系依然牢不可破。
在这城市烟囱林立的年代,与国家工业生产机制相适应,在灰色工装、像章、毛巾、瓷缸、铝制饭盒、自行车、广播……大行其道的年代,暗红色建筑大面积地在这丘陵起伏的城市矗立起來,高耸入云的烟囱,取代了20世纪以前的传统手工作坊的建筑形式。它们呈现出一种工业社会锐利的风度,以工厂和工人为符号的文化景观,进入历史。它强势进入视野,甚至让人们淡忘了它以前的面目。甚至,瓷作为艺术品的功能也在褪减,而以平实的工业品出现。一种生活方式、生产景观、工人群体形象(劳模、技术能手等)在这个体系中开始上升。
在短短数十年间,这片曾被官窑和民窑作坊盘踞上千年的丘陵地上,被成片的几何形状建筑物所分割。巨大的烟囱在红色土壤地上投下暗蓝色阴影,坡面、墙体以及暗红色建筑在阳光下,被光线切割成边缘锋利、线条干净、面积巨大的光面与暗影:这是欧洲立体主义绘画,或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绘画在赣北大地的移植。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在大风的午后,它旋即又被刮得干干净净。瓦蓝的天空下,翠绿的松柏林、落羽杉林、香樟树林,在猩红的土地上望不到尽头:千余年来,它源源不断地为瓷窑作坊提供燃料,但旺盛的生命力似乎永不枯竭。阴郁、深沉的丝柏,热烈、燃烧的枫树,明亮、温柔的银杏,它们杂陈在以松树、香樟、茶树为主体的原生林、次生林之间,就像瓷器上的青花釉里红:斑斓、凝固。一座座暗红色建筑在大地上凸起,就像红壤在一种不可知力量的驱使下,向空中塑形。林木退去后,阴影的面积变得无比阔大,如同水流无声地漫过层积着无尽的破碎的瓷片堆积的大地……它们拥有着与时代相称的名字:建国、人民、新华、宇宙、东风、艺术、光明、红星、红旗、为民……这些名字,伴随着遥远的年代的歌声、露天电影般幻梦的画面、泉水般的爱情,以及一种理想主义的狂热情绪,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二
邓希平,是个青年知识女性,一个即将入职轻工部研究所的大学生。这个城市,除了部研究所,还有省研究所,以及其他瓷研究机构。她23岁,灰色衬衣上别着“武汉大学”的校徽,大眼睛,齐耳短发,背着军绿色书包,安静但也不无疲倦地坐在一辆白色救护车里,她已经坐了三天两夜的车,到达这个看起来偏远的小城——难以想象,曾经,以瓷为媒,这里是世界关注的中心。另一个来自湖南大学的毕业生,也坐在车里,他与她一样,依照国家分配,从事陶瓷研究工作。那是1965年盛夏。她从武汉出发,坐船渡过长江,转道南昌,又坐长途班车向这个她从未涉足的城市进发。焦热的风,从窗外吹入,却不能减少一毫车内的闷热。尽管疲倦,那窗外新鲜的一切还是让她的眼睛得到片刻满足:肌肉暴胀的红壤被汽车压成一道一道,松柏和香樟面带严肃的表情,昌江像一条深情的缎带在群山间环绕。视线中,隐约可以看到成片的建筑,和那怪异的密集的烟囱,仿佛那是一个战场……
这个城市,拥有着深厚的移民文化传统,所谓“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现在,成千上万个她,接续了这样一个传统。传统七十二道工序形成的五行八作,对应着新社会瓷业所属机构。她的专业是研究颜色釉。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希望从德国获得精密仪器制造技术来发展工业。德方提出了对等条件:他们需要颜色釉技术。以前,几大家族颜色釉技术传承,以古老的方式:父传子续、口耳相传。仿如禅宗,不立文字。老师傅们能熟练地完成颜色釉的各流程。她这样年轻大学生的任务,就是跟着他们,观察、分析、记录,形成可行性的报告——将传统技艺,转化为工业社会标准的研究性文本。
月亮升起在部所两层办公楼和宿舍的上空。丘陵地上的月亮,庞大、圆润、柔和……如一枚瓷片镶嵌在靛蓝、神秘的夜空。月亮,对于一个从未离开家乡的人来说,它像一条小溪、一朵野花、一声牛哞一样自然。对于成千上万个邓希平们来说,月亮是一种距离、一种思恋、一种不可触碰的伤感。月亮升起在暗红色建筑的顶上,她暗自神伤了一小会儿,很快便被另一种仿佛激昂、阔大、带有金属味儿的情绪所鼓舞,于是,她从仰望月亮的黯淡中很快便回到了室内。
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2500家私营陶瓷作坊,经过联营、公私合营,变为16家制瓷社和15家画瓷社。它们构成了建国、人民、新华……俗称“十大瓷厂”的雏形。这些名字脱胎于此,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启。为了不混淆各厂生产的瓷,它们必须拥有一个“身份”,即底款标记代号。分为英文字母和数字两种:红星-A、宇宙-B、人民-C、艺术-D、建国-E……以及×××陶瓷厂-01、浮南陶瓷厂-02、文艺瓷厂-03、民政局社会福利瓷厂-04、陶瓷加工厂-05……
瓷的工业属性和时代烙印,让这泥与火经过艺术再造的物件,赋予了与周围的建筑、人群、广播歌曲、空气中喧哗的激情相似的表情。那些依附于白瓷的松竹梅、牡丹、西番莲、菊花、牵牛花等植物,龙凤、鹤、鹿、鸳鸯、绶带鸟等动物,鬼谷子下山、昭君出塞、周亚夫屯军细柳营等故事,以及火珠、犀角、法螺、方胜等杂宝大面积地消失。与时代主题相匹配的画面、场景,被画工描绘在瓷盘、瓷瓶上,既是生活的对应物,一种提炼和升华,也是一种审美和欣赏。它们与暗红色建筑几何形状的轮廓,互为表里,光大了一种新生活的热度和理想。在国庆的游行队伍中,“十大瓷厂”的工人们,唱着昂扬的歌曲,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兴奋的满足感。他们在人们羡慕的眼神中,内心沉淀着一个词:“吃香。”仿佛那是一块甜蜜的永不融化的糖。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主宰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在消费、娱乐、恋爱、交往、郊游等日常生活的伦理和细节中获得一种自尊、自豪和由衷的幸福。这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社会及经济地位的上升所带来的。
现在,这些遗迹般的建筑,躺在夕照里,让你看到时光凝固的状态。同时又启示你,时间正在无情流逝。这些建筑:几何形状屋顶、平整墙面,圆形、高耸的烟囱,就像欧洲新浪潮电影或者“新小说”中常见到的场景。曾经灯火通明、浓烟滚滚的建筑变得冰冷、无声。人们离去又返回。过去的宇宙瓷厂,现在叫陶溪川——一座文化创意园,大型建筑综合体。对应着这个消费时代的趣味、心理体验,一种包豪斯风格的展示……
四
这里寂静无人。几辆小车:别克君威、长城皮卡、路虎极光……泊在车位上。现在是6月,湿闷的天气温度节节攀升,从山壑、昌江吹来的风,被弥漫着瓷土味儿、草叶味儿、尘埃味儿和金属味儿的气息所稀释。门楼是仿古的翘角、琉璃双层凤楼。门楼中间一块牌匾,上书“皇窑”两字。这里平时也是一个对外供游客观览的去处。疫情席卷了全球,是造成它空寂的原因。这个大型宅院,有假山、水榭、垂柳、花荫、游廊、荷池……是上演《游园惊梦》的绝佳处。现在,只有场景道具孤单地呈现在那里,像一个空的舞台,没有演员,也没有观众,像一个幻境。
这个城市,手工制瓷作为一种产业、一种文明,已延续了千年。试想一下,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靠一种产业支撑千年并且还在延续下去?我被自己的发问吓了一跳。目光仿佛看到室外: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灭唐,建立后梁,五代十国割据形成。这个城市当时还叫新平镇,南河两岸的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锣山、盈田、月光山、石虎湾、湘湖、寿安、枫树山,以及城内的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坳……都发掘出窑址。元代在此设立“瓷局”,因“唯匠得免死”法令,战争中俘虏的工匠成为“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的参与者。元代青花瓷技艺短时间内在这里达到登峰造极、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画青花艺人的艺术修养、文化水平、绘画功夫,非一般匠人所及,纹样生动、优美,人物生气勃勃、变化多端,昆虫鱼儿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那段时期,一批来自磁州窑和吉州窑的绘瓷名匠,以及当时知名的文人画家,甚至来自阿拉伯的细密画师……参与了这段艺术史的构建。至正十二年,城镇被红巾军攻克,在农民军与元军的厮杀中,瓷局瓦解。为元王朝生产御器的能工巧匠和被垄断的优质瓷土,流散民间,为民窑的繁盛创造了条件。当新中国成立,国营瓷厂收买、整合民间作坊,这里是另一番情景:那由机械、矩形房子、工人占据的大地,蚁动的人群热火朝天,歌声响遏行云,生活的热情始终保持在滚烫的刻度……在成为旧照片中消逝的风景的另一个年代,劲风吹彻,生活的喧哗与骚动又开始变奏,“十大瓷厂”成为追忆……
这座花园的主人是个80余岁的老翁,身材挺拔,样貌朴素,神态沉实温和。这个园林看起来并没有完工——虽然它建于十余年前,但一些零星冒出的想法,又转变成现实的行动,因此,一些小工程依然在这个空间里进行。这位有经验的老者,一边娴熟地调度,一边满足我对瓷的好奇,带我从楼上回到庭院,穿过几道回廊,来到烧制车间,看新出窑的一些小件:绘着植物花卉的摆件、茶具。他一件一件仔细地过手,嘴里发出遗憾:颜色烧灰了。在一堆成品中他没有找到一件满意的。我很震惊,像他这样级别的艺人,还不能保证出窑的质量,对于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他恢复了柴窑烧制,以保持瓷的温润、古雅。这与电、气烧制的瓷不尽相同。他以做仿古瓷而出名:元青花和洪武、永乐、宣德青花,备受海内外收藏界重视。——他收藏的古瓷片难以计数,一头扎进去,仔细研究,鉴定,成为一马当先的民窑的研究者。专家说他,从事青花断代研究,在国内属于先行者。耿宝昌记得:1973年在故宫博物院保管部陶瓷组,这个高高瘦瘦、一口乡音很重的普通话、带有几分“土气”的年轻人,一连十余天,孜孜不倦研究古瓷片的情景;更记得1981年某天风雨大作,他一身水淋淋赶去火车站为离赣的他送行……他着迷仿古瓷仿佛出自本性,在整日对配料、纹饰、图案的研究中忘了忧乐。他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其专业知识、修养、文笔和鉴定功夫为从事仿古瓷绘制增添了羽翼。曾经他是陶瓷研究机构中的一员,见证了“十大国营瓷厂”的兴衰,也目睹了传统陶瓷技艺的流失……后来毅然下海。如果说这座城市依然能够为世人所夸耀,那一定是沉淀在一代代瓷工手中千锤百炼、登峰造极的传统技艺。他从很年轻时就打定主意,要将这传统技艺学到自己身上。
五
一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陶瓷部落”,开办在某社区街道。这个新文艺群体,由相对固定的20余个外地瓷画爱好者组成:有的是科班毕业,有的是停薪留职干部,有的是来自农村的手艺人,有的是待业青年,还有的身份不明……他们称自己为“创客”。这是一间简陋的一室一厅,墙上挂着风格无法统一、难以命名的瓷画:大漠飞沙的驼队、仕女图、寿翁图、虫鱼、荷塘月色、边塞风情、古桥牧歌、百婴图、秋山览胜、模仿艾轩油画的藏女……不一而足。仅从题材和形式来看,与市场上的其他瓷绘别无二致。无法命名,正是这个手工业城市的,最大之谜。
我参观了一个叫菁菁的女孩的工作室。这是一个卖场二楼仅有几平方米的小间。因疫情的原因,整个市场非常冷清。更别说这位置欠佳的二楼了。菁菁擅长工笔花卉,兼画人物:这是相对传统的题材和技法。她来自一个有戏曲传统、民间尚保存数百座明清古戏台的邻县。一个高中毕业的乡村姑娘、一个孩子的母亲。她热爱瓷绘,拜了一些师父,更多的是自学。她整个的人和作品都透露出一種认真、朴素、纤丽的味道。坦率地说,我是外行,无法置喙。她的作品我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在我的审美系统里,似乎没有将传统工笔花卉、人物放置进去。她为工作室的局促而不安。我知道,每年有数万人(也许还不止)从全国各地到这里画瓷、作瓷。不少功成名就的油画家、国画家、艺术院校教授,各行各业的爱好者,甚至海外华人、欧美日韩陶艺家,加入这队伍中来。他们在城区甚至郊外的村庄,形成了一个个创作群体,以部落的方式,重构了一种生活形态。菁菁所在的这个组织,就是其中一个,只是更年轻一些、草根一些,也更艰辛一些。她拿出一块四开纸大小的瓷板,让我在上面写字:似乎具有一眼看透我内心正跃跃欲试的洞察力。这个城市我来过多次,心里始终有一种想加入画瓷队伍的冲动。我身边就有数个这样的朋友,离开供职的单位,在这里过上了一种抟土、捏陶、画瓷的生活,成为暗红色建筑空间内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手艺人……
我写了一首王维的诗《山居秋暝》。脑袋里只想到这首诗。因为生涩,无法把控釉料,字写得歪歪斜斜,留出近半的空白。菁菁说,正适合她画两支花卉来补白。我回到居住的城市不久,收到菁菁微信发来的图片:几朵牡丹摇曳在那字的一边。再过一些时日,瓷板已经烧好,寄到我的住处了。我原以为,自己只是这个城市的观察者。我多次来到这里,感到它如此个性鲜明,但又如此难以命名。现在,一块瓷板将我与它链接在一起。
六
一个奇异的空间:一楼罩着玻璃的展柜里,铺着层层叠叠的瓷片,一朵朵幽蓝的火焰在破碎的瓷片上舞蹈;这凝固、无法被时光湮没的火焰,与穴居时代红色泥壁上的图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个无名氏在巨大的时空里留下的谜语,使瓷片具有永恒与消逝的双重意味——它们,像那瓷窑——龙窑、葫芦窑、马蹄窑、色窑、蛋形窑内赤红烈焰尖头的部分——那抹微蓝,蟒蛇的芯子、蓝色的尖叫、冰冷的奇异之花、泥与火的刺青、黑夜的徽章、亡者的邮戳……我们目睹这穿越了层层厚土、重见天日的图案,它们如新雨洗涤过般簇新,釉色明净、靓丽,在碎裂的瓷的边缘露出残缺的亭榭、枝蔓、祥云、异兽……这是一个来自京城艺术家的工作室,兼具博物馆与家居的功能。
这座时间博物馆,让人感叹一个人日积月累的功夫,可以达到的深度。主人清癯、黑瘦,鸭舌帽下眸子精光,疲倦的皱纹在眼角细密而松弛地流淌,不厌其烦地述说——使得那些艺术概念、艺术事件、艺术史实,化作空中飘舞的尘埃……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奇观,我们经由他带领,踏上曲折的楼梯上到二楼,右边的悬空如高山崖壁,等待主人的创意将它填满,上楼的感觉如同登山,回头所见风景陡峭而幽深;二楼是片开阔、壮丽的空间,一派万马奔腾的气象,远看如一匹匹大小、错落、颜色不一的瓷马在虚拟的草原、风中奔跑,又像一朵朵云,一团团烈焰,在漆黑的空间里舞蹈;在第二层瓷的景观中,是举着硕大鹿角的动物(有着浑圆的、金属管道意味的长腿和紧致的腰身),齐刷刷地在视野中出现,如同一片明亮的、白色的森林……我内心的震撼无法言语。仿佛置身在一个符号的国度,一个可以多重阐释的当代艺术的公共空间。我的情绪被唤醒——对瓷和这个城市的认识,大大拓展。此前暗红色建筑浅表的忧伤,变得遥远而陌生。仿佛这城市远不是那停滞的国营瓷厂给人造成的陈旧、衰败的错觉;从内部看,它生长着无限当代精神的可能,超前于时代的趣味,是一种活力与创造力的表现。
七
聚光灯下,这个嘴上留着胡子、身材颀长的男子,与身边的白瓷瓶站在一起。这件器物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文君瓶。脱胎于梅瓶,文雅如君子。德化白瓷。瓶子造型修长、大方、沉静、稳重。一个物件有着这么鲜明的人格属性!这件作品,将成为一个世界性运动会的国礼,展现在各国要人和运动员面前。
他在世界各地拥有粉丝。作为一个将传统技艺与当代艺术相融合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标签,同时难以定论。在他主持的一个国家级展览中,这个城市迎来了属于瓷的荣光,大型展馆内,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以鲜活的想象力,拓展着陶瓷艺术的边界……这是一场瓷的盛宴。是千年窑火,在暗红色建筑内不熄的明证。“匠从八方来”——从这里走出的瓷的亲戚们,表兄表弟,有着陌生的面孔,甚至不少喝过洋墨水,讲着ABC,欢欢喜喜回到故地。有些观念超前、形式先锋、面目生疏者,却也使部分人不适和难以接受,在热烈的氛围中潜涌着争议……
他始终沉默,没有回应。他并非出生于这个城市——但它自有种魔力,吸引瓷艺家、爱好者殊途同归。它自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时间博物馆。瓷是载体,是时间的碎片,是民间遗书,是社会结构的表现,是组织形态的结晶,是文化遗产,也是争议甚至冲突的产物……瓷是一种不死的器物,也是一个未亡的魂灵。它是深埋在红壤之下的高岭土,与上升的火焰的纠缠,是无数双手的轻抚与托举。
不熄的窑火,照彻了它的过往,使每一个细节熠熠生辉。而阴郁的丝柏林、墨绿的香樟林和纵横的丘陵地形成的屏障,也遮挡了部分人的视野,形成一种定见。瓷,从来不曾被一种定论所塑造:本质上它是时代工艺、哲学、审美的产物,是人们头脑中创造出来的形象、符号、情感寄托。它可以是很温和的,如“文君瓶”典雅大方,也可以是尖锐忧伤,甚至粗粝狂暴的——如变形的角鹿,甚至是著名的杜尚的观念性的“泉”。瓷,来自泥土的包容和火焰的幻境,可以塑造千千万万,承载最新最前沿的思想和审美——甚至它也可以回到过去,回到狮子穿花、双鸟栖枝、海水奔马,回到牡丹、芍药、菊花,回到螭、鱼、蟹,回到八仙朝圣、鬼谷子下山、萧何月下追韩信——但最终,它还是要回到当下的欢乐忧伤。
八
瓷,这朵开在历史深处的花,闪烁着白亮、低哑的微光。它带着人类童年古老的记忆,带着从穴居走向城邦、方国的跳跃性转折——从砍削石块,开始塑泥成陶,由陶到瓷,推进的不仅是时间,也是演进的文化。层层瓷片堆积在暗红色建筑下面,形成了朝代分明的文化岩层。这泥与火的艺术,携带着城市的集体记忆——跨越了时间,也跨越了空间。过去的“十大瓷廠”,现在的陶溪川,正生长出新的业态和技艺。
陶溪川还保留着一根高耸的烟囱——像一棵树,在大地上兀自矗立,不再吞吐灰色的颗粒与烟雾,而仅仅是时间的道具,国营瓷厂的记忆样本。过去,这个城市烟囱林立,其景象殊异而可怖。照片无法留下更早的记忆,比如昌江两边上千座作坊,被满载瓷器的舟船壅塞的江道。每一件幸存下来的瓷器都是珍贵的,它保有时间和工艺的完整性——而数倍于它们的瓷片,则碎裂在城市的泥层中,无法计数。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建筑在瓷片上的城市,有着微冷的光泽、靠想象拼贴的图案、温润如玉的颜色和坚硬的品质。
一座座暗红色建筑,矩形、盒形,它们安放在大地上。既是时间的截片,也是城市独有的符号。
瓷是有灵魂的物件,凝视它就是凝视鲜活的生命和依然生长的传奇。
责任编辑 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