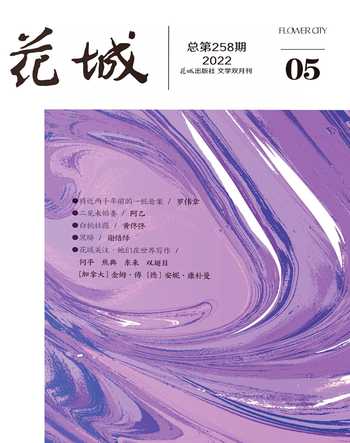遗落在窗台的烟斗
2022-05-30马必文
马必文
2013年,在湘南一个灰暗冬日的晌午,阴沉而雾蒙的天空,吹着丝丝湿冷的北风,父亲去世了。
父亲走的那一天,我没有哭,但胸闷得比哭还难受。痛失第一个至亲,让我真正体会到人世间生离死别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父亲临走前,我回乡一趟,在病榻前守候了两昼夜。此前,父亲已在病床上躺了十多天,生命已处于枯萎状态。每到晚上,他不断地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呻吟着。父亲在日常生活中不招人嫌,但到了这个地步实是不得已。除了生理方面的痛楚之外,可能还有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此刻,一阵寒风吹来,村子里的狗叫声此起彼伏,让寒夜更陡生出毛骨悚然感。为了给父亲壮胆,我告诉他如果可以减轻痛苦和恐惧,您就大声喊出来吧。有了我的体恤,父亲再也不用顾忌,呻吟的节奏变得更加频密。
知道父亲来日无多,故我想先回广州,准备些钱为父亲办后事。临别那天,父亲回光返照般微微地点着头,随后主动地把偏瘫后尚带余温的还能活动的左手,从被窝中伸了出来,抖动着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自我成人后,父子之间何曾有过此举。此刻,我强烈地预感到,父亲真要走了。父亲一直是个寡言少语、不善交际的人。以前在家,我们父子俩可以一直呆坐在冬日的炉火边,一句话都不说,沉闷得似乎可使房间里的空气凝固起来。我隐隐地觉得,这是我和父亲之间的最后一次告别。
我回到广州后的第二天上午便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父亲走了!回想几天前,躺在床上的父亲,日夜间或掐着手指,初时我以为他是在消磨难熬的时光,后来才领悟到是在算时辰。他要选一个好日子、好时辰上路,这样才有利于子孙兴旺发达。生前,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必须讲究点。据说走的那天上午,父亲因不能言语而不断地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开始家人不明其意,他很着急,后来干脆拉着长孙的手放在他头上,家人才知道他要理发了。平日里,他就比较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于是家人匆忙从镇上请来了理发师。在理发的过程中,先帮他点了一支烟,喂了一碗稀饭,随后又点了一支烟。头发一理完,他便断气了。走得如此安详、如此井井有条,完全靠生存意志在支撑。他走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似乎对后人为他后面旅程的安排充满了信心。父亲生前就是一个不叽歪、不讲名堂的人,以这种方式告别,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
三年后母亲去世时,我哭得像个刚出生的婴儿。父亲走时,我却心如止水。甚至在主持告别仪式期间,还叫了三五知己玩“三打哈”的扑克游戏。我知道父亲不会怪罪的。因为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错,父亲从不打自己的小孩,气极时也是语言上吓唬一下。有时见我们兄弟几个围在炉火边打闹,被母亲数落时,他最多也是附和着嘿嘿一笑了之。他一辈子都活在通达与宽容中。
平日里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会经常想念他们,尤其是每当清明或是中元节来临时,思念会变得无以复加。2020年的清明节,由于疫情的缘故,我没有照例回乡祭坟。在偶读儿子的习作《故乡的小屋》时,一个沉重的话题映入了我的眼帘:
生离死别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爷爷、奶奶的离世,曾使得一大家人两度聚到一起。生活的磨难使各人除了基本的寒暄外,却再也没有过多的话可说。于我而言亦然,故乡的小屋似乎早已把发生于此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透过被风吹雨打撕裂的玻璃窗户,一眼便能望见,当年我送给爷爷的那根烟斗,被层层尘埃包围着,仿佛岁月静好般地匍匐在窗台上。
儿子的描述,唤起了我对点滴往事的追忆。
父亲或喜或忧,一辈子基本上是在袅袅轻烟中度过的。抽烟是中国乡村庄稼汉的主要休闲和人际交流方式,成年男人基本上都会。我不知道父亲啥时候学会抽烟的。但是他学会之后,不同时期所用的不同烟具,或许暗含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别样的心路历程。
卷煙
20世纪30年代初出生的父亲,如果不是因为出身问题,或许也可以在体制内混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重庆刚解放时,诸多学校招考,父亲在巷道中窝了十多个昼夜,终于以“城市失学失业青年”的名义报了名,然后又顺利地考上了重庆公安学校,兴奋地读了一段时间。由于该职业对从业人员的政治背景要求特别严格,在政审时以“阶级出身异常复杂”为由,被清理出来,只好灰溜溜地回乡归田了。从此,生活让他真正懂得了生活。
在过苦日子时,父亲是抽喇叭筒,即用纸卷着来抽。纸是随机找来的,大凡是书、作业本或者废旧的报纸之类。把它们撕下来,在卷烟的过程中,在嘴唇上沾些口水,把纸弄湿,这样便于把纸严丝缝合,抽起来才不会散架。以至于我读小学、中学的课本或是作业本,不是被父亲撕来卷烟用,就是供家人上厕所用,早已杳无踪迹。父亲抽烟时,经常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像哲人般在思考着深邃的哲学问题。其实,父亲没有读过几箩筐书,但我总觉得父亲在抽闷烟时,还是有些心思。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的日子特别难熬。他的人生路向,便是随着寒暑易节、春种秋收的四季更迭而起伏。乡下的农活名目繁多得像一堆没有规则的土豆,让人心烦意乱。他也只好一如既往地像沙漠中的骆驼,踏着皇天后土负重前行。
在深灰的冷冬,湘南大地常常是白雪皑皑,山野里那些熟悉的风景几乎被白雪全覆盖了。母亲每天照例都得早起。她像个独角戏演员,一会儿骂鸡、一会儿训狗,弄得鸡飞狗跳的,使得寒冷的农家院落陡然间充满了生机。这时候父亲在母亲的吆喝声中极不情愿地起来了。他无惧寒冷,独自一个人搬一条长方凳坐到门口,用火柴点着卷烟,便哧哧地抽起来。寒冷的空气中都飘着旱烟的味道。父亲虽然基本上不接话,但该干的活,还得去。沉默中,父亲扔掉残存的烟尾巴后,望着桌上母亲早已准备好的一荤一素的两碗热菜,一个人端起碗低着头便默然地吃起来。吃完再点一支烟,随后便担着箩筐去20公里外的山坳挑煤。每次挑一百斤,一个月约去三趟,只为了省下用拖拉机运煤的钱。
当布谷鸟叫春时,大地也渐渐从淅淅沥沥的春雨中苏醒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此刻,父亲便变得更忙了。经常见他咕噜咕噜地喝一碗母亲酿的糯米酒之后,便红着像猴子屁股的脸,担着黑而发臭的粪肥,摇摇晃晃地在田埂上行走着。为了不滑到水田中去,他双脚的趾甲紧紧地夹着松软潮湿的泥土,每走一步似乎要在泥土中打一个螺丝钉,以便把自己的脚紧紧地固定在地面。富有弹性的扁担,合着父亲踽踽独行的脚步,一路叽咕叽咕地响个不停,被春露打湿了的裤管不时摩擦出声音。当春雨把田土泡软之后,父亲和他的“四类分子”同类,便要对村里几百亩水田进行翻耕。每当母亲要我去给正在田间劳作中的父亲送饭时,只见他扎紧裤腿、闷着头、扶着铁犁,举着鞭儿吆喝着,不断地抽打着牛背,驱赶着牛一拐一拐地行进着。
每当夏天“双抢”季节来临的时候,红彤彤的太阳把大地照得像火苗在燃烧。流经村前的小溪,水草沿溪而生,鱼儿在水中溜达,野鸟在水上嬉戏,村鸭在溪中放歌。但对父亲来说,该季节却并非人间好时节。因为每到农忙季节,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斗地主”便成了“极左”路线下惯常性的政治运动。主角基本上是我的长辈们。每当运动来临时,生产队长的口哨吹得特别急促而高昂,晚上全体村民瞬间就会被集聚在村口的泥坪里。会场中间,早已有几个戴着白色高帽的人,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我大伯因为是长子,在他们兄弟之间,出身带来的原罪,若要被处罚,便主要由他来承受。因此,凡有批斗,他必在场。二伯,陪伴得多些。父亲在其兄弟间居第四,政治气候特别严时,才出场。三伯因为参加过革命,就没有划入被斗的阵线。叔叔,因土改时还不够划成分的年龄,所有这些政治运动几乎与他无关。不过,每当运动来临时,他都会偷偷地躲在人群中,神情低落地当着看客。村干部带头喊口号,村民们就会附和着,哧哧地从喉管里挤出一点声音来。时光在压抑中慢慢流逝着。
拼命干农活还不打紧,偶尔挨斗也可以承受,但经常有些事让父亲更堵心。在集体所有制年代,牛是集体财产,是生产队重要的生产力。若是生产队的母牛长大了能生出娃来,那真是添喜的大事!但是,每当母牛发情时,派谁去外地赶公牛来交配,却是一件棘手的烦心事。因为,干这档事,往往是村子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所为,所以,谁都不愿意被贴上这一标签。但有一次,生产队长毫无商量地把任务交给了父亲。父亲闷闷不乐、满脸阴沉地从家里拿根竹棍子,气呼呼地出发了。一路上尽管他不断地吸着烟,但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等把公牛赶来时,已是日上三竿。约莫半个小时后,生产队长如释重负般,勒令父亲继续把公牛赶回去。父亲依旧阴沉着脸,二话不说,狠狠地吸着烟,高高地举起鞭子,把公牛重重地抽了几鞭,顺着逼仄泥泞的山路,再次往伍家湾方向走。
秋天来临时,农人开心的事除了收割作物,便是干鱼塘。那时候,生产队部分鱼塘由村民承包。如果鱼塘经营得好,相应可以增加一笔收入。我们家也承包过十多年鱼塘,每当忙完田间活之后,父亲时常会顶着夕阳的余晖,叼着一根烟,用粪箕担着水淋淋的、沉甸甸的青草,摇摇晃晃地往自家的鱼塘奔去。到鱼塘边时,父亲会把裤脚卷起来,跳到水中,然后依次把青草在鱼塘撒开。此刻,只见碧波荡漾的水面,鱼儿欢快地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父亲的嘴角会不由自主地露出开心的微笑。成长中的鱼儿兴许会给东家带来几十、百把元不等的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一个六口之家的油盐酱醋等零花钱,基本上够用了。若是遇上鱼发病的年景,就倒霉透顶,一年白忙乎了。往往夏秋之交是鱼最易发病的时节,一旦鱼犯病死去,母亲便一大早到鱼塘边守候着,把死了鱼逐条捞上来,回家煮熟烘干给我们解馋。即便是瘟死的鱼或鸡,用红辣椒加酸豆角爆炒,味道也好极了。但如果鱼死得太多,父亲便满脸黑沉,卷着裤腿呆坐在鱼塘坎上,哧哧地把烟抽个不停,任母亲如何骂老天不开眼,他不会接一句话,一家人的心情都是灰暗的。
不过干鱼塘时,却给我留下过温馨的回忆。我们家几度承包的后山塘,是村子里的一口大塘,窝在山坳里,离家较远,常担心鱼被偷。有一年深秋干塘,由于当天水抽不完,父亲只好带着我和哥守夜。鱼塘四周除了秋收后的田野,便是杂草丛生的坟山。晚上,我们在坟堆之间的缓坡处,铺上稻草,三人同盖一张用白布染黑的被子,将就着睡。父亲为了克服我们的恐惧心理,睡前,他用手在我们兄弟俩额头上分别轻轻地扫了一下。然后告诉我们,即便有鬼也不敢近身了。我们也不知道父亲使的是什么魔法。由于稻草铺得太薄,睡在稻草铺上,树根隐隐地刺着背部,初时弄得我很不舒服,不斷地翻滚着。父亲见状立刻翻身起来,叫我侧睡在一边,然后他点了一支烟,通过烟火的微光,硬是把地上的树根拔得一干二净。其实,只要他把稻草再铺厚些就能解决了。此时,秋露慢慢升起来了,父亲怕我受凉,便搂着我睡,尽管我被夹在两人中间,还是感觉有些冷。于是,父亲便蜷缩着身子,尽量用被子把我捂得严实些。此刻,他身上几乎没有被子,寒露使他冷得有些受不了,于是便又起来抱了一捆稻草,把自己包裹着。他还是担心我受凉,于是再次把我搂得更紧了。此刻,一种被呵护着的温暖感在我周身弥漫着。记得那晚的夜色真好,到了后半夜,秋风萧瑟、繁星满天,像极了鲁迅笔下曾经描写过的场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那一夜,我睡得特别沉、特别香!
那年月,尽管生活很艰辛,可是父亲的人生基调始终是乐观的。每当逢年过节时,无论生活遇到多大的风浪,他都会坚守人生的礼仪。对祖宗的祭祀从不含糊。饭前他都会在堂屋的神坛前,焚香烧纸,口中念念有词,显得非常虔诚。我曾问他:天上真有神灵菩萨保佑我们?他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他曾对我说:有一年夏天的夜晚,暴风雨像山崩海啸般,屋后的泥石流把堂屋中设置神坛的后墙冲塌了,然而神坛却没有随之倒地,还是巍然屹立在堂屋的中央。凌晨起来时,家人见状,无不称奇。后来,每念起此事,父亲不断地念叨着:我们的祖先还是管事的!
竹管烟斗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进入了新天地。父亲就像春天来临时,卸掉了冬日整天穿在身上的沉重的破棉袄般轻松。于是,他自制了一杆竹管烟斗,经常把它别在裤腰带上。每次抽烟之前,他要用细小的树枝把烟孔掏空,然后再把烟丝捏成一团摁进去。抽的过程中,随着烟孔火光的增大,丝丝浓烟不断地从嘴里、鼻孔里飘出来,抽不了几口,烟丝便全化成了灰烬。父亲似乎觉得还不过瘾,便把烟孔朝鞋底或是找个质地硬的地方狠狠地敲几下,以便让烟灰抖搂出来。随即又塞进烟丝,由于烟孔还是滚烫的,烟丝便很快点燃了,父亲从容地抽着,终于觉得过瘾了。于是,再把烟管交给坐在他旁边,嗓子痒了很久的平辈兄弟。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聊些乡村趣事。乡村不缺新闻素材,种田人也是善于挖掘的。他们对时政新闻显得更为关注。诸如何时给“四类分子”“摘帽”,父亲和他的兄弟一旦聚集时,便会念叨着。他们可不想把这顶帽子带进棺材中去,这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自从“摘帽”以后,父亲的笑容显得更舒展了。他可以从容地根据自己的节奏从事农活,再也不用担心生产队长来派活监工了。忙完农活之后,背靠着稻草,坐在松软潮湿的田坎上,慢悠悠地抽上一管,真是惬意极了!望着微风过后起伏的稻浪,便在内心盘算着,丰收在望,那些陈年老账,可望一笔勾销了。家中稍有余粮,父亲便开启了属于他的宏大伟业——建房子。
那时候,在乡村建房子,是一件复杂而系统的困难工程。从打砖、烧砖、烧石灰、烧瓦、扛树等到兴建,整一条流水线,基本上没有钱去雇工,大凡是靠自家劳力和换工来完成。能不让人挣的钱,绝不给别人机会。为了节省买杉树的运输成本,他经常是凌晨3点钟起床,带着家人和左亲右戚,到50公里外的井冈山南麓去扛杉树。来回要两三天时间,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天黑走路怕撞见鬼,父亲便告诉我们招数:出发前,用手在自己额头上把头发往后扫三下,鬼就不敢近身了。在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哪里会怕鬼呢。怕蛇倒是真的。父亲同样自有驱蛇的办法:要我们每人拿一根竹棍,凡是遇到茅草丛生的路段,便用竹棍噼噼啪啪敲打着,蛇听到响声便会溜走。到达大山深处的目的地时,已是夜深人静、皓月当空,四外虫声唧唧。我们一路奔波,疲倦至极,再好的景致,也无心欣赏,稍作洗漱,倒头便睡。第二天天未亮,便扛着树往回赶。由于负重而回,所以更辛苦。汗水把每个人的衣服浸染得像一张张斑驳的地图。我一个未满18岁的少年,干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力不从心。父亲一路上叮嘱我,走路不要太快,要学会省力;不要轻易用山涧的水洗脚,洗多了容易得风湿病。他不时往前赶,然后折回来帮我扛。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走就是十多个小时。我累得真想把树扔掉径直回家,但望着前面父亲佝偻着的背影,像一个旋转乏力、左右摇摆的陀螺在盘旋而行进时,只好咬紧牙关亦步亦趋地追赶着。
劳作消歇时,无论是躺在田埂还是山冈上,望着白云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飘来荡去,一种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的冲动,在我的心底鼓浪而来。父亲对我的成长没有任何期许,但他穷且益坚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前行。一有机会上学,我便发奋苦读。從小学到高中,基本上是在半耕半读中度过的,靠自己在农田里抓鱼卖钱换学费。父亲在农活歇下来心情好时,见我背着黄色帆布书包去上学,偶尔会冒出一句:“读书要发狠呀!”经过寒窗苦读,终于鲤鱼跃龙门,我考上大学的消息让父亲感觉似乎是喜从天降。从此,父亲的担子一下减轻了不少。
在我读大学的过程中,父亲每学期都会用书信同我交流着,无非是告诉我家里六畜兴旺,要我安心读书;要与同学搞好关系,千万不要取笑别人;借了钱一定要还,大家都不容易等之类。然后,便会附寄二三十元钱。大学毕业之后,我在井冈山南麓大山深处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了三年书。那时候,乡村中学教师的工资和社会地位都不尽人意。而我乡下老家搞冶炼之风兴盛,涌现出了一大批暴发户。受此影响,我萌生了弃教从商的念头。有一次父亲见我回家休假,便搬条木板凳和我面对面坐着,装了一管烟,边抽边温和地说了几句:“读了这么多年书,还去做生意。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况且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当年,你爷爷在世的时候,我们家大业大,现在剩下了什么呢?”父亲寥寥数语把我点醒之后,从此我再也不三心二意了。面对人生困局,便横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考研改变命运!于是,便在石溪河边的乡村中学,潜心山林、不与人往、不谈婚娶,经过几年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中举”了。
喜讯一到,我便归乡了。见父亲挽着裤脚,打着赤脚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表现出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但还是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激荡。他用哆嗦的手装了一管烟,然后用力地抽着,不但节奏加快了,而且发出了更为欢快的哧哧声!
牛角烟斗
历史进入新阶段之后,父亲已到了生命的晚秋。晚年的父亲抽烟,最后改用牛角制的短烟斗了。那是我儿子五岁那年,随他妈去泰山旅游,出于孝心,花了5元钱给爷爷买的。孙子的这份孝心,让爷爷喜不自胜。父亲对这管烟斗,偏爱有加。每次抽完烟之后,他再不像对待竹烟管那样,用力肆意在鞋底或是在硬物上猛敲了,而是用牙签小心翼翼地在烟孔中拨弄着。一边修饰烟斗,一边流露出一副幸福满满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揣进衣兜里,形影不离,生怕有闪失,因为这是他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儿子出生时,父母亲都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本应该在乡下安度晚年。但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他们还是努力支撑着进城来为我们带小孩。乡下人进城,最难处理的是婆媳关系,但我们一家人相处得其乐融融,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节俭习惯,进城后丝毫都未改变,能省的钱几乎省到了极致。父亲从乡下带来的烟丝没有了,便叫母亲去菜市场旁边的小巷买。想喝酒了便叫母亲酿。但是由于城里很难找到合适的酒药,酿出来的酒没有乡下的口感好,难以满足父亲的酒瘾,于是我不时就会给他买些廉价的低端白酒。平时父亲感觉累时,即便没到吃饭时间,也会倒上一小杯抿几口。看他闭着眼睛喝酒那副满足的样子,我既欣慰又内疚。觉得父母这么大年龄了,还让他们来带小孩真辛苦,而我连买几瓶像样酒的能力都没有。但是,父亲在生活方面从不对我提任何要求。他和母亲经常私下嘀咕:这一辈子还能到城里来见见世面,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同以前在乡下吃过的苦相比,干这点活,那叫什么苦呢。我听后,暗自流泪。
为带好孙子,父母亲没少费心,分工合作得很默契。时常是父亲带孙子去外面玩,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爷孙俩一到外面,也顾不得体面,经常席地而坐玩起石头来。父亲就地取材,用零碎的红砖块,教孙子在水泥地上写字。当年我办公的地方与居家的院落仅一墙之隔,有时趁休息的片刻,溜出来看他们玩耍时,儿子便会得意地用刚从爷爷那里学会的土话同我交流。玩累了,便要爷爷背回家。我们家住在没有电梯的八楼。儿子两岁多时,本来可以慢慢爬上去,但天性偷懒,执意要爷爷背上楼。爷爷只好咬紧牙关,气喘吁吁地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为了舒缓爬楼的艰辛,爷爷一边爬,一边“喂呷!喂呷!”地喊着号子。儿子便在背上模仿着,爷爷喊一句,他也喊一句,让爷爷心里乐滋滋的。一背回家,爷爷便像泰山登顶般惬意,急匆匆地装上一锅烟,不声不响地躲进厕所,独自慢悠悠地抽起来。以至于儿子经常给我们告状:爷爷又躲在厕所抽烟!弄得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后来,父亲便干脆躲在门外去抽了。我觉得过意不去,便给父亲解围,告诉他在自己家里不必拘束,想在哪儿抽就在哪儿抽,但是他自律意识很强。尽管孙子不断地告状,但爷爷总是乐滋滋的。待我儿子上幼儿园时,父母顿时感觉清闲多了。父亲说,没有孙子在家的日子,像坐牢般,便不想再待了,执意要回乡下去。我们再三挽留,都没有办法。
回乡以后,父母亲都已年逾古稀。为了让其生活不过于单调,我鼓励父亲同村人打俗称“跑胡子”的纸牌。同时,每年回去我会瞒着母亲拿两三百块钱给父亲。父亲如获至宝,把钱偷偷地藏在贴身所穿衣服的口袋中,不至于让母亲发现后被剥夺。若是赢了三五块钱,父亲就会大声在母亲面前声张,输了就闷不吭声了。小赌怡情,也是天伦之乐。但是,他们还是想重操农活。除了养鸡种菜,每年还养一头猪。每次回乡探亲,见父亲步履蹒跚、气喘吁吁地担着猪潲,往屋后山坳上的猪圈爬时,母亲便拿着猪勺跟在后面,不断地提醒着父亲:慢点走,小心看路,别摔倒了。见他们如此辛苦,我让他们别养猪了。可父亲却说:这点活累不着人,干惯了农活的人,哪里清闲得下来?母亲则在一旁帮腔,养猪是累点,但是等你们拖家带口回家过年时,家里杀年猪,年就过得热闹些。趁着还能动,能做就做点。其实,还是想通过自食其力为我们减轻负担。
父亲和母亲先后走了,兄弟们迫于生计,四散着外出打工,整个家庭便解体了。每次回乡,踏进家门,便感觉整座房舍空寂了。尤其是父母亲终老的两间房,因长年无人居住,缺少了烟火气,显得潮湿而阴暗,了无生机。长年放在厨房兼客厅的炉灶,也因主人的离去而被弃之墙角。他们曾经睡过的、暗红的油漆脱落后显得有些斑驳的、只剩下空架子的两张简易木床,四处布满了尘埃。我长时间驻足在父母的卧室,望着那两张空荡荡的床架,深情地回忆着旧日温馨而美好的时光。如今,这一切都如烟而逝了。
在父母亲谢世均满三年之后,按照乡俗,我又对他们安葬在一起的两座坟,用钢筋水泥大理石进行了修葺围蔽。尤其是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周边的山茶花、杜鹃花,在竞相绽放着,仿佛春天在这里长驻。在山花的簇拥中,父母亲可以安然地拥抱着春天长眠了。
我把遗落在窗台的那根烟斗,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