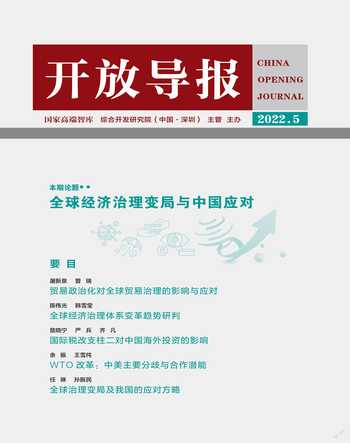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趋势研判
2022-05-30陈伟光韩雪莹
陈伟光 韩雪莹
[摘要] 在外生冲击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冷战后最大幅度的调整和结构性重塑。通过分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演进,可以看出,外生冲击是体系演变的破坏性力量,引起国家行为体内部观念、权力和利益结构的改变,而基于结构性变化国家行为体的大国博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俄乌冲突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裂变为“准平行体系”。为避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分裂,中国应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反对单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及“金砖+”合作机制建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
[关键词] 外生冲击 大国博弈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F1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2)05-001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制度型开放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研究(20&ZD06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重大研究专项招标项目(GD22ZDZ01-15);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智库课题专项:广州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及发展路径研究 (2022GZZK01);广东省市场监管局项目:市场监管领域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研究——以广东为例(GDDA2022GK-055)。
[作者简介] 陈伟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全球经济治理;韩雪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洋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
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迎来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也形成了与此相对应的多边主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两者的互动和相互作用成就了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一般而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互为因果关系,全球经济治理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对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治理过程,表现为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风险、问题和挑战的化解、解决和应对,全球经济治理是经济全球化得以有序运行的前提。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间,国际格局加速演进,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和世界多极化趋势越发明显,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重大外部冲击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推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也给本就处在逆风中的经济全球化和动荡中的全球经济治理以重创。可以判断的是,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不断走弱,以此替代的是多元化、慢速化、区域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再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演进将从过去缓速的、低烈度的渐变过渡到快速的、高烈度的突变,世界将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塑。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的方向何在?国际社会的政界和学界对此做出了分析和判断。一是分裂论(李晓,2018),即国家间在竞争规则、竞争理念、全球共识等方面正在发生重大分裂。二是碎片化论(陈伟光、刘彬,2022),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体系呈现明显的碎片化趋势,数字技术、新冠肺炎疫情和大国竞争等外部冲击和影响,进一步撕裂了原本碎片化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三是脱钩论(卢江 等,2022),认为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主观发起脱钩”还是拜登政府的“选择性脱钩”,外生冲击加强了与“脱钩”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动力。四是平行体系论(张宇燕 等,2020),认为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治理可能产生两套平行的体系,形成两个“异质”的“全球化”动力之源。上述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走向的判断,只是方向性的预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的未来图景如何,并没有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
接下来的问题是,引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的外部动力和内在因素是什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演变的动力机制何在?事实上,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和重塑的动因的探索,学界也作出了一系列分析,包括权力转移推动论(孙伊然,2021)、中美战略竞争决定论和相对收益决定论(吴心伯,2020)、外部冲击论(鞠国华,2009)、国内民粹推动论(蔡拓,2017)等。本文综合借鉴上述观点,寻找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演变的动力源及传导机制,分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未来趋势和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演进
全球經济治理体系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体制系统,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行为体协调全球经济的各类国家集团、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总和,广义上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组建的各类多边、区域和双边机制、协定,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依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本质是制度体系。从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的历史来看,二战以来的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制度先行,即主导国和主要国家先谈判构筑和设计出一个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制度框架,以此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为此后的经济全球化运行确立了多边制度规范。但这个体系并非稳定不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变革、调整。
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衰期(20世纪40—70年代)
二战结束后,基于经济大萧条的教训和战后重建的需要,美国主导建立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体系,在国际金融领域逐步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该治理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银行(WB)。在国际贸易领域,成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应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一度是“最稳定的货币体系,也是真实经济各项指标最好的时期”。超国家国际经济组织的成立,也表明全球制度化文明进一步发展。当然,这种“金字塔”式的国际货币制度,主要反映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相继爆发,加之石油危机的冲击,美债高居不下,国际收支失衡,美元大幅贬值,美元危机开始显现。同时,日本、西欧在体系内开始崛起,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弱,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各国开始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制。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三大政府间的多边组织仍一直保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2. 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兴起期(20世纪70—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冲击资源供给,西方世界的宏观经济从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供给乏力,西方世界陷入了高通胀与低增长并存的“滞胀”困境。面对“滞胀”危机的冲击,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英美两国共同发起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运动,从而使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消除“滞胀”危机的法宝。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转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进超级全球化的重要手段。由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三大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打着经济援助的旗号,诱使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进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新自由主义导向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开始兴起。
3. 冷战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复杂演变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应当说,冷战时期西方主导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治理体系是一个西方世界的治理体系。但苏联没有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主导了另一个体系,即以卢布结算的经济合作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体系。因此严格来说,冷战时期全球治理体系是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线、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经贸关系关联微弱的两个平行的“半球治理”体系。当然,这两个体系实力和规模不完全对称,有不少国家游离在这两个相对立的体系之外。
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结束,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两大阵营不再对峙,美国处于“一超独霸”地位。人类进入高密度发展的超级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推动的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扩张,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纷纷加入这一体系,货物贸易活跃,人员流动频繁,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不断上升,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的局面,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促进了G20的成立,这一新的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框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一直被控制在区域层面,但此次危机使G7国家意识到要在亚洲金融危机事件上采取共同行动,并改革既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酿成了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受到自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冲击,对以G7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G20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级峰会。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重大转变,实现了全球经济治理核心体系的重大变革。
上述分析表明,重大事件的冲击,往往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转折拐点,主要国家行为体观念、权力和利益结构变化构成了体系演进的内部张力。
二、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变革的外部冲击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相对稳定的,遵循路径依赖规律,某一时期形成的制度一般不会突然出现断裂式的变迁。但外部冲击,即带来冲击的、偶然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战争、经济危机、科技革命、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等,会引发国际制度的急剧变化。重要历史事件被称为“关键节点”,通过打破制度均衡,引发制度的突发性剧变,进而实现制度加速变迁。形成关键节点的原因和条件的累计时间越长,矛盾的爆发性就越强,这一节点就越重要。外部冲击打破制度的路径依赖,打破了制度均衡,打断了制度的持续性,发生断裂现象。实现制度变迁的动力,一是来源于制度机制的缺失或失灵,即原有机制的制度功能丧失,无法发挥自身作用。二是推行制度的主体、制度的制定者、反对者和之前的制度匹配发生变化。三是结构的断裂,如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出现问题、国家政权迭代等。
在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上,外部冲击事件改变了制度主体,也引发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博弈后的冲突结果逐步凝固为新的制度安排。外生性动力来源涉及国际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相关因素,包括无法预料的事件、战争、金融动荡等。这些因素通过挑战现存制度对危机的应对能力和适应能力、威胁现存制度的合法性等方式,变革现有体系制度。
當前,全球经济治理处于通胀和经济下行并行、地缘政治危机的叠加期,即便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惯性得以维持,在路径依赖的轨道上继续前行,但“脱钩”与“筑墙”的频繁化引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重塑期。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俄乌冲突、科技革命在内的持续外部冲击,使得经济全球化边际效益递减,边际社会成本递增,主权国家的地位强势回归,各国治理形式的偏好分化,多边治理难以取得进展或突破。
1.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
自2020年至今在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百年来最严重、最持久的公共卫生外部事件,带来的经济损失堪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疫情暴发初期,货物、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因疫情中断、停顿和迟滞,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断裂”,全球贸易受阻,投资大幅下滑,经济全球化停滞。
然而,这次全球疫情危机没有带来应有的全球合作共治。我们没有看到所希冀的曾经应对金融危机时全球协同治理的景象,因为这不符合大国战略竞争的逻辑。在霸权国家看来,联合抗疫必须服从大国战略利益的需要。因此,疫情不但没有成为合作的纽带,反而成为某些国家打击和推责于其他国家的机会。疫情反复冲击助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全球经济治理陷入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变局,国家中心主义回归,多边制度秩序遭遇困境。
2. 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
俄乌冲突是超越俄乌双方多方力量间复杂而深刻的冲突,不仅直接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甚至会动摇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战略挤压。
俄乌冲突中,西方国家将金融工具“武器化”,充分显示了全球治理平台面临被政治工具化的风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安全问题凸显,相伴相生的还有能源危机、全球通胀加剧、粮食危机等问题,世界格局“冷战回潮”难以避免,“真正的多边主义”面对前所未有之制度压力和成本。同时,俄乌冲突中,“泛武器化”现象凸显“和平赤字”,全球议题饱受影响,合作机制遭受破坏,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重构。
3. 科技革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
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开拓了世界市场,推动了规模经济,也使得国界不再成为跨境经济活动的制约。技术是制度变迁的动态原因,制度面临新技术的外部冲击,全球化市场边界被逐步拓展。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各个领域间的联系加强,社会分工愈发细化,带来了集体行动成本的降低。但是,重大外部性事件,如核技术、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转化,也凸显了一系列全球问题,使全球科技治理赤字凸显。另外,科技本身渗透于环境、能源、健康、安全等多个领域,需要协同并多主体共同治理,并根据需要,改革和建立科技领域的新制度。
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
内生动力与大国博弈
实际上,制度变革是行为体持续博弈的结果。外部冲击事件并非全球经济制度变革的必要条件,只有外部冲击引起了行为体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博弈策略,打破了原有的博弈均衡,才会推动制度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外部冲击是制度变迁的导火索,内部驱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重大非预测性事件造成了制度的生成分裂(generative cleavage),破坏了现存制度的内生性因素,形成结构性和能动性张力而推动变迁。也就是说,外部冲击之所以可能会引发制度的急剧变迁,关键是因为发生冲击的事件引发了相关制度主体的观念改变或权力结构的调整。
(一)内部驱动:观念、权力和利益的结构性力量
国家行为体观念、权力和利益的结构性变化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动力源。首先,制度是某种观念的固化,由文化传统、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构成。制度的存续是因为适应了观念、传统、规范而带来的合法性。新观念的输入使得旧制度下的利益团体重新思考,并形成新的政治力量组合,实现对原来制度的改变。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革体现了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商业道德和认知模式等新变化。新观念可以通过学习、社会科学研究、引入新知识产生,也可以在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智库等各类行为体与国家的观念互动和交换中出现。当今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全球治理已远离全球主义理想的善治目标。针对西方国家现实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思潮回归,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感召力,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革的内在精神动能。
其次,制度又是权力的结果,特别是对国际制度而言。权力变化是推动制度变革的关键性力量,新权力主要来源于和平崛起,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的提高是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结果,新权力也可能由战争和武力较量中的取胜方获取,如二战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领导权的掌握。权力运用在制度上表现为制度的投票权、设计权、解释权和执行权等制度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由国家物质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转化而来。经济实力是直接的制度性权力资源,一些正式国际组织的投票权份额正是由國家的经济总量决定的。在制度博弈中,不存在压倒性的权力时,国家行为体权力博弈的合力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存在压倒性权力时,权力垄断者会主导制度的设计、执行,推动新制度的构建。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过程中,由于美国的黄金储备地位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得以形成。
再次,基于利益的考量也是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力量。现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仅享有更多信息、资源以及更多制度赋予的优势,在全球治理变革过程中也处于更中心的位置,因此拥有捍卫当前制度的动力。意欲变革当前制度的也是参与制度的利益相关者,但往往是从制度中获取较少收益或承担更多成本的一方。如承受了美元的“溢出效应”和国内金融系统不稳定的后果后,基于对自身脆弱性和损失的考虑,新兴国家实现合作并形成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呼吁IMF推进份额改革和治理改革。
还需强调的是,制度参与者的观念、权力和利益三要素只有在整体格局中体现,才能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结构性张力或压力。就新制度塑造而言,发起者提出的观念的认同性越强,实力和权力越集中,承担制度建设初始成本的意愿越强,为参与者带来相对公平利益的预期越强烈,成功建制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既有制度而言,制度运行的分配效应会带来所谓的赢家和输家,也无可避免地带来观念、认知甚至意识形态的分野,现有制度下的受益者会强化制度的稳定并使制度合法化,利益受损者则会质疑甚至挑战现有制度体系。制度最终是否变迁取决于参与者的博弈行动。
(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直接动力:大国博弈
行为体博弈策略是针对制度变迁程度、性质和方式的具体行动方略,是直接决定制度变迁结果的重要环节。行为体通过博弈,才能最终得到具有一致预测性和稳定性的策略组合以实现制度变迁。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大国是重要的行为体,大国的策略选择是决定制度变迁最终结果的关键。
1. 身份选择
美国是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是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及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中国是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和2001年“入世”以来,在不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并非扮演体系捍卫者的角色,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不是以体系推翻者的形象出现的。
可以说,美国是有选择的“修正主义者”。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先后退出多个多边国际协定,以规则和多边主义为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而其愿意供给的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维护自身霸权的战略工具。美国做出这一身份选择的原因在于,一是要降低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尤其是在遭遇经济危机的环境冲击后,美国实力相对衰弱,无法承担高昂的治理成本。二是受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发展的影响,传统的多边贸易制度有利于制造业优势国家、崛起国家持续获利。三是美国出于转嫁国内矛盾和持续维护霸权的需要,通过“小院高墙”式的伪多边主义,损毁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在融入国际规则的过程中学习国际制度,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面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合法性不足和崛起新兴国家发展利益诉求,中国扮演了规则的改革者、完善者和补充者等角色。如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和话语权不足时,通过设立亚投行、金砖行,增强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可以说,中国始终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致力于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 场域选择
行为体对场域的选择,是指确定在双边、区域还是全球多边机制上实施制度变革,目的包括形成利益同盟追求共同利益,或结成联盟打击第三者。在全球经济领域,国家行为体通过与一个或若干个国家达成合作,通过逐步实现制度共识,建立制度同盟。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兼具双边、区域和多边的综合性合作机制,虽未形成正式机制化的多边制度结构,但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参与性。这一连接欧亚,扩展到非洲、南太岛国的合作机制不同于欧美国家主导的排他性机制,通过倡导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促进各国携手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同时,“一带一路”以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实现为导向,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创新模式。
带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拜登政府的区域选择策略,显示了美国想要拉拢其他国家联合遏制中国、主导亚太地区经济的企图。美国借助这一封闭排他机制,意欲实现和中国的“脱钩”。同时,印太大部分国家和中国存在密切的经贸往来,与“一带一路”、RCEP的成员国多数重合,这些国家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因此选择同时加入两个大国分别主导的机制,在场域选择中通过运用对冲策略降低风险,它们作为博弈参与的局中人,会影响中美大国博弈的策略,进而影响两国博弈的均衡结果。
(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图景:大国博弈均衡
制度是行为体博弈的均衡解,制度变迁是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转变的过程。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在单极结构下存在压倒性霸权时,霸权国会主导策略行动,控制规则的制定。此时,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成为霸权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霸权国家自行承担或强制、诱导其他国家分担全球治理的成本,替霸权国承担部分霸权义务。此时,均衡结果体现的是霸权国家的观念、权力和利益。但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大国博弈的环境中,制度变迁实现的过程更为复杂。中美两个大国在多个领域都存在博弈,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各类机制、机构、议题方面也存在大量共同利益,一旦二者制度完全“脱钩”,全球稳定和世界经济将面临重大风险。因此,从理性的角度看,二者在不同制度领域应选择不同的制度策略,建立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同时,在关键领域有效管控风险、防范重大冲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向前发展,扩大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框架的包容性空间。
国际制度的竞争很难脱离国内制度的影响。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化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异质性是影响大國博弈均衡的重要因素。在两国综合实力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时,美国加强对中国政策的“意识形态化”,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尽量避免意识形态冲突和民粹思潮的裹挟。国内制度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是由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在开放条件下,制度互动为规则和管理方式提供借鉴机会,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自身的制度路径和发展模式,才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在制度博弈过程中,可能形成以两国为主导、双中心化的、在功能领域高度重叠而规范领域存在一定分离的制度网络。而制度的分离化程度或是否形成平行体系取决于两方的具体博弈策略均衡:中国是否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更为重要的是美方是否能做到摒弃霸权思维、零和思维,停止“价值观外交”。不同制度的国家行为体的制度博弈,除了相互自由竞争外,还存在相互合作与借鉴,即通过制度互补或发挥各自的比较制度优势开展经贸往来,在良性竞争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与合作。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趋势
研判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趋势研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的发言中表示,当今世界处于“混乱和未知”中,也许会分裂为一个“一分为二”的世界。但是,真正的“一分为二”平行体系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存在两大相互对峙、经济互不往来的阵营。二是存在两种货币分别是各自体系的主导货币。三是体系成员在现有的IMF、WTO、WB多边体系中不共存。根据现实来看,这一结果可能性不大。究其原因,第一,尽管美国推出“新冷战”陷阱,意图谋求中美全面“脱钩”。但目前并不存在以美国为主导国的发达国家群体和以中国为主导国的发展中国家群体上演零和对抗,中美双方仍然是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2021年中美贸易额为7556.45亿美元,同比增长28.79%,全面“脱钩”势必对两国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二,人民币地位显著提高,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仍然处于霸权货币地位,本质上美元具有“强排他性”的货币权力。第三,中美两国一直是WTO、IMF和WB三大国际组织的主要成员,这些多边体系囊括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通过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维护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同时中美两国仍然在G20峰会机制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沦为两个完全对立的平行体系目前来看是小概率事件。
上述分析表明,在外部冲击导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及大国战略竞争格局加剧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能演变为一个“准平行体系”,基本的发展趋势是:一是中美尽管仍然共存一个多边制度秩序,但该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不足。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协商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日益增长的全球不信任、民粹主义和贸易紧张局势将不断加剧全球经济多边制度的脆弱性。同时,传统治理机构大多以发达国家为主导,难以满足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二是在区域协定中,中美分立于两个不同的网络。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主导亚投行、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式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美国有意避免在区域协定上与中国共存互动,从奥巴马政府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特朗普政府的频繁“退群”和签订《美墨加协定》(USMCA),再到拜登政府的 “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国正在积极打造针对中国的区域协定,未来会进一步固化、做实甚至扩张这些围堵中国的“小院高墙”。三是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中国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逐步实现区域化,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会加快,在数字人民币大范围应用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有望探索出新路径。四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主要目标,未来将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五是未来新型领域规则互动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前沿科技的不断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凸显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乏力。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及治理理念等的差异,需要各个主权国家特别是数字经济大国加强政策协调,以构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避免“新冷战”和“脱钩”的语境下陷入两个“平行的世界”,有责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观念、制度和行动三方面着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观念方面,一是要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伪多边主义,维护和完善现有的全球多边制度秩序。二是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共建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制度方面,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对标高标准国际通行规则,以制度创新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制度供给,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制度公共产品,形成更多参与者认可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合理改革。
行动方面,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金砖+”合作机制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最佳实践,“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关注项目发展、融资保障、贸易畅通等方面的机制建设。加快推进“金砖+”合作机制,以此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谋求更广泛、更高质量的跨区域合作。此外,关注科技革命冲击下新兴领域的治理问题,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的规则制定。
[参考文献]
[1] 保建云,李俊良.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与中国的政策选择[J].国际经贸探索,2022,38(7):104-116.
[2] 蔡拓.被误解的全球化与异军突起的民粹主义[J].国际政治研究,2017,38(1):15-20.
[3] 陈伟光,刘彬,聂世坤.融合还是分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J].东北亚论坛,2022,31(3):29-43+127.
[4] 陈伟光,王燕.共建“一带一路”:基于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6):93-112+159.
[5] 陈伟光,钟列炀.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要素构成、机制分析与难点突破[J].国际经济评论,2022(2):66-75.
[6] 陈伟光.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发展趋势与中国策略[J].社会科学,2022(1):14-23.
[7] 崔珊珊.权力、观念与制度[D].长春:吉林大学,2019.
[8] 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12):81-97+159.
[9]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D].上海:复旦大学,2003.
[10]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J].国外社会科学,2002(5):25-33.
[11] 黄宇韬.俄乌冲突对全球治理形成挑战[J].世界知识,2022(10):48-49.
[12] 鞠国华.“外部冲击”的国内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9(5):75-78.
[13] 李菲菲.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从逆全球化现象谈起[J].学理论,2022(2):41-43.
[14] 李向阳.“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5):51-70+157.
[15] 李晓.全球化分裂:成因、未来及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18(3):3-5.
[16] 李晓华.数字科技、制造业新形态与全球产业链格局重塑[J].东南学术,2022(2):134-144+248.
[17] 李晓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基于发展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比较分析[J].东北亚论坛,2021,30(1):92-103+128.
[1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处于困境”之中的世界面臨五大分裂 [N/OL].联合国新闻网,2019-11-11.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11/1045431.
[19] 刘彬,陈伟光.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J].国际论坛,2022,24(1):62-77+158.
[20] 龙豪.走向有效的多边主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6-10.
[21] 卢江,许凌云,梁梓璇.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创新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13(3):118-143.
[22] 马得勇.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兼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5):158-170.
[23] 任琳,张尊月.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复杂性分析——以亚太地区经济治理为例[J].国际经贸探索,2020,36(10):100-112.
[24] 史晋川,沈国兵.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标准[J].经济学家,2002(1):41-46.
[25] 宋静.美国制度霸权的变迁与中国的国际角色[J].社会科学,2020(9):24-40.
[26] 隋广军.全球经济治理新范式:中国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27] 孙伊然.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竞争格局与中国应对[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6):15-24.
[28] 王辉.特朗普“选择性修正主义”外交的特点及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19(6):28-34+67.
[29] 王森垚.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困境及中国因应之道[J].理论探讨,2021(5):61-69.
[30]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5):96-130+159.
[31] 向松祚.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不对称性和不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什么崩溃?[J].金融博览,2014(7):9-11.
[32] 徐明棋.论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效应与趋势[J].社会科学,2017(7):34-46.
[33] 张发林,杨明真,崔阳.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与全球货币治理改革[J].国际经贸探索,2022,38(2):100-112.
[34] 张宇燕,倪峰,杨伯江,等.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4):4-26+155.
[35] 赵隆,刘军,丁纯,等.俄乌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笔谈[J].国际展望,2022,14(3):56-78.
[36] Hogan J.Remoulding the critical junctures approach[J].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6,39(3):657-679.
[37] Koning E.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Understanding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Change[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2015,36(4):639-664.
A Study of Trend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Chen Weiguang, Han Xueying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Guangdong 51042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external impact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s facing the biggest adjustment and structural reshaping since the Cold Wa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we can see that the external shock is the destructive force of the system evolution, causing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l concept, power and interest structure of state actors. The great power game based on structurally changing state actors will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spread of COVID-19,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and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is intensifying, which may lead to the fiss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nto a “parallel system”. To avoid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should actively play its role, oppose unilateralism and pseudo-multilateralism, practi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omote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and enhanc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power; We will advance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and BRICS Plus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mplement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nd participate in leading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External Impact; Power Competiti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收稿日期:2022-08-20 責任编辑:罗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