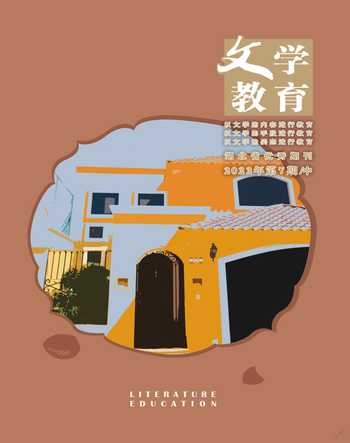小说《竹林中》与电影《罗生门》的对比
2022-05-30钟文彬
钟文彬
内容摘要:芥川龙之介的著名短篇小说《竹林中》有着独特的叙事方式,至今被众多喜爱悬疑小说的读者津津乐道。而日本导演黑泽明根据该小说,并结合芥川的另一部短篇小说《罗生门》而拍摄的电影《罗生门》也于1951年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引发了众多观众迷探寻其故事情节的真相。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电影,其核心故事情节类似,均是讲述了一桩离奇的杀人悬案。故事中的角色众多,对案件的描述也存在多个不同视角和形式,使得看似简单的案件呈现出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本文主要从叙事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比分析小说和电影的故事情节,探寻其在叙事过程中的特点以及导致故事不确定性存在的原因。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竹林中》 《罗生门》 叙事学 不确定性 日本文学
叙事,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事件和空间里的事件。叙事学则是关于叙事文本或叙事作品的理论,其重视对文本叙述结构的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出分析。
《竹林中》作为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著名短篇悬疑小说,其故事情节扑朔迷离,悬疑重生,涉及多个人物角色,包括武士、女人(武士妻子)、盗贼、樵夫、行脚僧、捕役、老妪共七人,主要围绕探寻武士之死的真相来展开叙述。在作者芥川龙之介的巧妙构思下,本该只存在一种客观事实真相的案件,却经由以上七人各不相同的描述反倒成了一桩“找不出真相”的奇案。而这一极具特色的故事后来被日本导演黑泽明搬上大银幕,又让电影观众们再次体验到了这一故事的悬疑魅力。
因此,文章将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分析小说和电影极具叙事特色的故事情节,以探求整个叙事过程中两者的特点以及导致故事最终产生不确定性的原因。
一.跨时空转换叙事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首先在时序上,小说《竹林中》没有采用顺叙,而是从事件发生后采用倒叙的形式,让七個人对同一起谋杀案进行回忆。整个故事情节正因为是由多个回忆片段组成,所以会存在小说的叙事时间、空间以及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即“现在时空”和“过去时空”。通过证人的证词,可以得出叙事时间是在“今天”,空间是审案人在公堂上逐个询问有关证人。而自然事件发生的时间是“昨天”,空间则是按照武士夫妇前往若狭、武士夫妇从山科走向关山、盗贼引武士夫妇入竹林、盗贼石桥上被抓、樵夫竹林发现尸体这一顺序不断移动。
对比小说,电影《罗生门》开篇则是一个樵夫和行脚僧坐在罗生门这一破旧的城楼下避雨,回忆之前在公堂上所听到的供词。其中那个樵夫承认自己其实曾在竹林中看到当天的真相,但因为怕受牵连,才没有在公堂上说起自己所看到的事实。电影同样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回忆事件,但是,首先是让樵夫、行脚僧在罗生门这一空间回忆公堂上的事,然后在公堂上再次回忆几个证人和当事人过去的各种言行,可以说是营造了在回忆当中再次进行回忆的“三重时空”。这种拍摄手法一方面是跟随小说情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在小说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导致电影在时空上,环环相扣,情节更加的扑朔迷离。
由此可见,小说和电影都存在不同时空,并且在叙事过程中,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叙事镜头也不断从这些不同时空之间来回切换。小说中的表现就是不同证人对事件的回忆会导致情节不断从“现在时空”(公堂审案)和“过去时空”(案件发生)来回切换。而电影情节则是从“现在时空”(罗生门避雨)、“过去时空”(公堂审案)、“过去的过去时空(公堂回忆)”来回切换。而由于回忆本身具有不完整性、模糊性,在樵夫、行脚僧、捕役、老妪的回忆中只能窥探出整个事件的些许事实,但同时这些事实又并非解决案件的决定性事实,外加上事件的当事人,即武士、女人、盗贼三人的供词存在矛盾,虽然能够自圆其说,但小说中由于没有决定性证据来进行支撑,所以结局也没有判定出谁才是真正的凶手。而与小说略有不同,电影中由于安排了证人樵夫在罗生门下向镜头前的观众揭露了事实真相,但就公堂上审问时的情节而言,樵夫并未当众指认凶手。单从这一层面来看,电影中的真相也并未大白天下。因此,可以说叙事过程中因回忆造成的跨时空转换导致了不确定性的产生。
二.“无效”第一人称视角叙事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一书中,把叙事视角分为零聚焦型、内聚焦型、外聚焦型三大类。之后又将内聚焦型细分为固定内聚焦型、不定内聚焦型、多重内聚焦型。而当中的多重内聚焦型视角是指通过对同一事件中的众多不同人物的多次叙述,以达到相互扩充或相互矛盾的效果。因而在人称视角层面,小说是让前四个证人和后三个当事人都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多重内聚焦来叙述整个故事,而电影也是如此。
第一人称视角本是以亲身阅历者的眼光去观察和叙述的,能使人物心理刻画更为细腻,情感也更为动人,更具有真实性。然而,就是在这种最真实的视角下却得出了不确定的结果。小说中,前四个证人(樵夫、行脚僧、捕役、老妪)虽提供了证词,但由于没有确凿的决定性证据,这四人的证词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樵夫发现了凶案现场并以个人的经验推测武士是他杀,且在死前有过抵抗。行脚僧叙述的是案发前武士夫妇的外貌,并表现出了对武士之死的可怜同情,大致认同是他杀。捕役提供了抓住盗贼的时间、地点等细节,并通过职业眼光推测凶手就是盗贼。而老妪是那个女人的母亲,武士的岳母,她从母亲袒护孩子的这个角度交代了武士夫妇的基本信息,一口咬定凶手就是盗贼。他们都并没有亲眼所见发生在竹林中的事件,提供的证词都是案发前后的描述,对凶手的判断也都源于自己的主观推测和猜想。另一方面,三个当事人也都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由于他们的叙述互相矛盾,但又毫无破绽,那么这些叙述和其他证人的推测和猜想对案件的解决均无帮助,而这些“无效”的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促使了不确定性的产生。
三.选择性和虚假性叙事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相对于小说中真相的不确定性,电影《罗生门》安排了一个相对来说合情合理的真相,那就是盗贼凌辱过女人后让她跟了自己。女人却为武士松绑。盗贼以为女人是让他们决斗来决定跟谁走,就拿起刀做好准备。然而武士以轻蔑的态度说自己不会为了这种女人赴死决斗。盗贼这时也突然醒悟开始鄙视起这个女人,最后谁都不想把她带走了。这时的女人怒吼眼下的武士和盗贼都没有男子汉模样,骂武士是因为他看到妻子被侮辱却没有勇气去杀掉盗贼,骂盗贼是因为不但没有把女人带出绝境,居然也不想决斗。这时的两个男人都心虚了,为了显示男子气概而开始决斗,然而实际情况是两人都非常害怕,整个打斗看不出谁是英勇无畏的强者,而是两人畏手畏脚乱打一气,最后盗贼侥幸把武士杀死了,可是盗贼杀死武士的那一刻非常恐惧,而女人也就轻易地逃走了。
结合电影创作的真相,再来看看小说当中当事人的说辞。在盗贼的叙述中,他先是强调自己希望避免杀人而实现占有女人,而后来又说是为了能娶到女人才杀了武士。而且,他杀武士也是采用公平决斗的方式。在他的描述之中,他是一个仁慈、痴情、做事光明磊落的男子汉。对比电影中的真相,看得出盗贼的叙述是有意将自己塑造成剽悍勇敢的英雄形象。女人的忏悔则强调了自己受辱后又遭到丈夫的厌恶、蔑视。这使她备感愤怒和耻辱,决定杀掉丈夫后自杀。但她杀了丈夫后,虽然也多次尝试自杀,但都没有成功。在她的叙述下,她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贞烈、知耻、悲惨、令人同情的女子。这和电影的真相明显是有差距的。而武士强调的是女人的不忠让他对妻子的憎恶和蔑视变得很合理,也突出了自己的不幸,同时表明自己作为一名武士的清高不愿受屈辱,以自杀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同样,这与电影的真相相差太大。
虽然电影创作的真相不一定就是小说中的真相,但从小说中当事人互相矛盾的说辞来看,三个当事人在回忆时的口供真假参半,每个人都在对真相进行选择性叙述,几乎都抹去了对自己不利的证言,增添了虚假性叙述来塑造正面形象。最后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盗贼杀人只是因女人的唆使,女人杀武士是害怕武士轻蔑的态度,武士自杀是无法承受妻子的软弱和背叛,明面上都是承认自己的罪行,但言外之意是将这些矛头指向他人而非自己。因此,正是这种对真相的有意选择以及对谎言的故意添加,让整个案件的真相变得不确定。
四.叙事内核的表达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一部内容完整、意义深刻的叙事作品,除开作者在行文用词以及叙事方式上具有特点之外,其叙事内核或者说作者透过故事想揭露的核心也通常是耐人寻味的。而小说《竹林中》这样一部扑朔迷离的悬疑小说,叙事独特并且故事情节又具有不确定性,那么在对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也需要对其“透过现象看本质”。申丹在《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一书中提到:“分析一个作品怎样形成、为什么形成不可靠叙述的‘场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无论它是以怎样的形式展现其不可靠叙述,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进行‘双重解码: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开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
芥川龙之介在小说《竹林中》,通过安排七人对同一事件进行回忆叙述,但最后也仍未给读者一个准确的故事真相,反而通过众人的叙述让结局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很显然,这种叙事方式是作者有意为之。芥川就是想通过真实的第一人称视角叙事来促成整个故事谜团的构成,从而从侧面揭露出人性中的贪婪与虚伪以及自私自利的阴暗面。而这一内核通过设置不确定的“真相”才能够表达地淋漓尽致。反之,如果小说依据故事情节走向,通过七人的不同叙述,以及公堂的推理审问,最终顺其自然地捉拿出真凶,那么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所表达出的作品内核,其意义深刻程度远没有原作那么精妙,很明显,还是原作不确定的结局更能烘托出芥川想要揭露的人性。因此,叙事内核的表达也是导致故事结局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之一。
相比小说完全揭露的是人性阴暗面,黑泽明在电影当中却进行了适当的改编。除了在影片前段安排樵夫诉说凶案真相,让原本“不确定性真相”拥有了“确定性结局”,在电影后半段,导演将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的故事情节也添加进来并做了适当修改。罗生门下的樵夫、行脚僧、过路人突然听到附近有婴儿哭泣,过路人迅速跑到婴儿前,把包裹在婴儿身上的棉袄等衣物剥了下来,樵夫与行脚僧都非常愤怒,大声斥责过路人,认为他和林中的那三个人一样都是自私自利骗人骗己的恶人。过路人则大笑,对樵夫说:“你不也一样吗,偷走了那把匕首还隐瞒不说”。之后便带着衣物逃走。电影通过安排樵夫看到的真相,既戳穿了盗贼自己塑造的英雄假象,也撕破了武士委屈可怜的清高伪装,更让观众看到了那个女人不忠虚伪的真实模样,同时也借用过路人的一句话揭露了樵夫不把真相报官、掩盖自己私藏匕首的贪婪。而在电影的最后,樵夫决定把弃婴抱回家抚养,当他抱着婴儿走出罗生门时,原本的倾盆大雨早已停止,身后天高云散,太阳也照耀出几缕光芒。
在一般的认知观念中,婴儿本身就代表着新生,加上樵夫最后这种发自内心的善良,伴随着云散雨停,暖阳普照,这一切都象征着对人性美好的希望与期待。虽然影片的前半段基于小说《竹林中》的故事情节,透露了人性虽有丑陋虚伪的一面,但在结尾却安排了“樵夫救婴”这一善举,也是向观众传达出人性仍有值得相信以及期待的一面。因此,可以看出黑泽明导演对于人性的理解还是和芥川龙之介的理解有些不同。比起芥川所要表达的仅仅讽刺批判人性阴暗面的叙事来说,黑泽明更强调的是一种对人性善良与诚实的希望。而从这一层面来看,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与批判这一叙事内核的表达,导致了电影前期公堂上凶手存在的不确定性,但对人性美好的期待则是导致了电影后期真相的确定以及雨过天晴充满希望的结局。
综上所述,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整个故事都是让多人对同一件事进行回忆式叙述,虽然是真实感强烈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但个人在回忆过程中由于主观意识的影响,叙述的人越多,其中对真相的偏差和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小说和电影也通过运用这种多重叙事所展现的不确定性来进一步深化其故事内核。因此,由于回忆导致的情境多次跨时空转换、“无效”第一人称叙事、对真相的选择性和虚假性叙事的存在以及叙事内核的表达需要,最终造成了故事真相不确定性的产生。
参考文献
[1]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龚一鑫.从《竹林中》看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叙事特点[J].艺术品鉴,2016(09):391.
[3]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黄海英.《竹林中》:不可靠叙述及深层认同[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30(12):74-77.
[5]仲冲.从叙事视角探讨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2(19):117-118.
[6]马蕊.浅析《竹林中》的多重叙事手法[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4(04):51.
[7]王磊光.“众声并置”下的现代小说空间形式探析——以《竹林中》为例[J].美与时代(下),2014(02):101-103.
[8]姜雨萌.多角度敘事的策略改进——浅析电影《罗生门》的叙事策略[J].青年文学家,2017(02):163.
[9]郭潇颖.《竹林中》的不可靠叙述[J].北方文学,2019(06):93.
[10]李静宜,邓斯博.《罗生门》中的他者叙事[J].戏剧之家,2021(28):138-139.
(作者单位: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