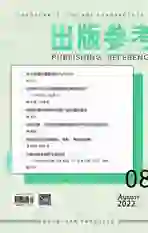文本与历史:《马君武年谱》的翻译史研究意义释评
2022-05-30孙艳
孙艳
摘 要:《马君武年谱》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现代意义上有关马君武的常谱体例年谱。除了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著名学者和诗人的身份,谱主马君武还是一位译作颇丰的杰出翻译家。年谱的编者从事翻译史研究近三十年,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该年谱的撰写在翻译历史的文本化和翻译文本的历史化方面对翻译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并为其他人文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全面详实的史料参考。
关键词:马君武 年谱 历史化 翻译史
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中国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的第一人,是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著名学者和诗人。此外,马君武还是一位译作颇丰的杰出翻译家,他“曾发愿尽译世界名著于中国”[1]。从1901年到1935年,马君武以战火中依然笔耕不辍的毅力留下译述60余篇(部),被誉为继严复、梁启超、林纾之后的第四位翻译大家。国内学界对于马君武的研究著作可谓盈千累万,但尚无正式出版的独著年谱。目前可考的马君武年谱、年表类文献,均以专谱或学谱的形式散附于其相关传记或研究书籍内。从某种意义上讲,由张旭和车树昇编著、商务印书馆印行的《马君武年谱》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现代意义上常谱体例的年谱,它准确、客观、系统、全面地反映了马君武一生的思想演变和创作历程[2]。编者张旭从事翻译史研究近三十年,出版翻译学术专著10余部,并编撰了《林纾年谱长编》(2014)、《陈宝琛年谱》(2017),在编年谱尚有《林语堂年谱》和《辜鸿铭年谱》。得缘于编者深厚的翻译学和历史学素养,编撰《马君武年谱》的史料来源除了信札、日记、诗文,同时涵盖了大量马君武的译文、译著、译论以及对马译文本的评议,这为《马君武年谱》与翻译史研究领域的融合提供了理据。
“年谱是记载一个人物或若干人物生平事迹为中心的编年史,是探讨或了解历史人物生平或其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3],其史料价值在于“为历史人物的生平提供资料”,“为论史、证史提供论据”[4]。可见一部精心编撰的年谱不仅史料价值极高,而且对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但目前的翻译史研究中则缺乏对年谱这类历史资料价值的挖掘与应用。翻译史研究即研究翻译的历史,历史性应是该学科自主与自足的必要前提。只有“历史化”(historicize)这种从文本走向历史的辩证运作过程[5],才能弥合翻译史研究中常见的“文本”与“历史”的割裂。《马君武年谱》的编撰过程做到了文本与历史的统一,体现出翻译史研究中应具备的“历史化”精神。本文试以《马君武年谱》为例,从“历史化”角度解读年谱类著述对翻译史研究的现实文献意义。
一、从《马君武年谱》的编撰看翻译历史的文本化
贾红霞认为年谱“知人论世”的特点与新史学思想相契合,其客观的史料价值更是与近代史学精神相一致,经过胡适、梁启超等学者对年谱编写的改造,扩大了年谱的容量与深度,也赋予其新的价值和生命力[6]。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编撰的《马君武年谱》,正是通过翻译历史的文本化扩充了年谱的容受度,大大增强了其学术效用。历史的文本化可以理解为历史是通过文本记录得以显示,被认为是历史化的第一阶段[7]。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历史本身并不是一个文本,但除非以文本或叙事的形式,否则我们无法接触到它,或者说我们只有通过某种事先的文本化或叙事(再)构建的方式才可以接近历史[8]。从此种意义上讲,《马君武年谱》的编撰使散碎的翻译历史文献在编年体形式下得以重构,其过程凝结了极强的历史化意识,是翻译历史文本化的示范性实践,从以下方面可以窥见一斑。
首先,翻译史料取材广泛。由于谱主马君武的翻译实践贯穿其一生,对马君武翻译史料的搜集可以说是编写《马君武年谱》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年谱编制的繁简程度受到编谱目的、编者才识、谱主史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编谱目的,《马君武年谱》的编者在“前言”中明确写道,之前存世的马君武专谱或学谱“或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或是限于编撰者的视角,或是其内容过于简略,无法完整地反映出谱主的生活全貌以及历史地位,无法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9]。所以在搜集史料时,编者的首要意旨在于尽全。《马君武年谱》记述了马君武一生所有可考的翻译作品,凡涉及译作之处,每条信息都力求完整准确。比如在撰写1902年11月4日马君武译作《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时,编者将原作、原作者、出版者、印刷者、联合发行者、丛书名称、封面题字都一一记录。此外,还附有章节细目和主要内容,并指出《斯宾塞女权篇》“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西方女权思想的译著”[10]。在整理谱主的报刊译文时,编者还非常周密地将谱主撰文时所用署名列出,如1905年12月1日发表的《汽机重说》,刊于《醒狮》第3期,署名“君武”。正如前文所言,编者的才识也是影响年谱编撰质量的重要因素。《马君武年谱》的编者接受过系统严格的文献学训练,具有深厚的翻译学养,马君武一生曾使用贵公、马贵公、馬悔等笔名,编者深知史料中的点滴细节都可能影响读者对于年谱的使用。《马君武年谱》在信息承载方面超越了前人对马君武翻译活动的梳理,最大程度地将翻译历史文本化,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通过文本无限接近翻译历史的平台。
其次,辅证史料安排精当。除了马君武本人的译作,《马君武年谱》的编者还根据多年的翻译史研究经验,选取了顾燮光著《译书经眼录》、沈兆祎著《新学书目提要》等颇具史学价值的书籍评论作为马译作品的辅证。例如1903年2月27日马君武译《弥勒约翰自由原理》出版一条后,就附有以上两书的介绍和评点,比如称“弥勒约翰为泰西十九世纪之哲学家,所著得学界荣伟位置”,“西国法家之说陈义既高,则析理至赜,其著书之文亦多渊邃之致,惟弥勒约翰推论自由之理一书……今此书在日本译成,译笔明畅有条,尤使读者易于入脑,因以养成其性质,则异日之收效必有惊人之奇”[11]。此外,编者还善于从他者视角还原谱主的翻译经历,《马君武年谱》借鉴了日本著名妇女史专家小野和子所撰《马君武的翻译与日本》等外国学者文献,从侧面印证了谱主的翻译活动与翻译思想。其中,有关《弥勒约翰自由原理》一书的翻译,《马君武年谱》中就附有小野和子的见解,她讲到马君武“一到日本,就将原文与日文译本对照着开始着手介绍翻译弥勒和斯宾塞的学说”,“需要注意的是,他所选择的翻译对象是在日本明治三十年代已经过时的弥勒和斯宾塞。他们超越时空,成为本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们关注的对象,其中包含着民权主义理论者们深切的期待”[12]。这种编谱意识其实已经摆脱了年谱体裁固有编年体体例的束缚,在力求将翻译历史文本化的过程中又暗含了“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的自我要求。
二、从《马君武年谱》的示范看翻译文本的历史化
历史化要求我们既“做具体切实而又烦琐细致的知识考古、谱系分类等基础工作,同时还要对之作立足高远的整体观照和会通融合”[13],这里点出了历史化两个不同阶段的要求与联系,文本的历史化应以历史的文本化为基石。结合编者强烈而敏锐的历史意识,《马君武年谱》在历史文本化阶段做到了全备精当的翻译史料铺陈,其包含的马君武翻译活动内容本身就是翻译文本历史化的经典示范。从现代翻译学的角度看,所有的译文都与其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相关,不可割裂。翻译文本的创作背景、底本选择、翻译技巧、传播流转,无不关乎历史语境,只有将这些文本外的因素一一厘清,才有可能重构对于翻译文本的立体认知。
根据现有文献可考的马君武翻译的第一部书籍为《法兰西近世史》(1902),原本为日本史论家福本诚所著《现欧洲》。如果将《马君武年谱》中此书成书前后年份的记述关联起来,就是一个颇具借鉴价值的翻译史研究案例。据《马君武年谱》的记述,1901年9月中旬清廷命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同月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经引荐与孙中山相识,受到国父革命理论和实践精神的感召。是年冬天,马君武受资助赴日本留学。此处附小野和子的评论,认为马君武赴日留学是由于路途较近与需要经费较少的原因,并介绍大同学校是一所华侨学校,是在日本的中国改革派人士的集中地。马君武于此结识梁启超,并协助他编纂《译书汇编》和《新民丛报》,埋头从事翻译。《马君武年谱》也录有马君武的自述,讲其初到日本时经济拮据,只能以写作投稿为生。至此,《法兰西近世史》问世前译者马君武的语言学习、思想转变、个人境遇都在《马君武年谱》史料中得以呈现。《马君武年谱》所记《法兰西近世史》原作名为《现欧洲》,为福本诚于1898年至1899年游历欧洲时所著,并考证了莫世祥编《马君武集》中将原作者误为“福本源诚”的错注,以及《现欧洲》并不是福本诚之代表作品的史实。《马君武年谱》的以上收录,从历史化的角度溯源了原著在源语文化中的地位,进而隐喻马君武翻译这样一部不知名作品的目的究竟为何。而《马君武年谱》全文记述了1902年4月7日马君武所作《法兰西近世史·序》,其抒发了“法兰西……困于暴君之专制,法国人民之困苦,正与吾中国今日之地位无异也”的感慨,就是对于他翻译报国目的的最好回应。以上部分可视为对翻译起始规范和预备规范的考察。而后《马君武年谱》又引用《译书经眼录》和《新学书目提要》对《法兰西近世史》的介绍和评价,采用多渠道史料来确定马君武译本在目标文化社区中的地位,并呈现出他人对于马译文本的评价。仅仅两页的记述,《马君武年谱》就将《法兰西近世史》的翻译背景、翻译版本、翻译目的、翻译接受、翻译影响等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因素囊括在马君武一生的历史脉络中。如果研究者据此进行翻译文本的细节考察,一则可以节省收集史料的时间,二则会增强对文本语言规范的有力解释,从而弥合翻译史研究中常见的“文本”与“历史”的割裂,进一步深化翻译史的研究。
此外,编者对马君武译作版本的传播考证也颇为关注,虽然马君武在1935年已经封笔,但1936年的谱记里还收录了马译《足本卢骚民约论》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第8版的信息,这对于译作的影响研究都是颇具史料意义的。而对谱主马君武这样身处历史动荡时期的风云人物,在研究其翻译活动时,其思想脉络很难把握,所以更需要借助年谱类的文献来辅助了解他的思想流变。
三、结语
当下的翻译史研究常常陷于“有史料堆砌、无史论提炼”的窠臼,缺乏史学思想和史学意识的指导。而作为常常交织于历史研究的多进路学科分支,翻译史自学科概念提出伊始,就有着原始的、自发的历史化要求,也只有通过历史化的路径,才能完成翻译史的学科建构。翻译史不仅仅是在宏大敘事中存在,通过对个体译者、译作的研究更能体现社会大背景下历史化的步伐。詹姆逊曾经指出,历史化操作可以遵循两条不同的路径,它们最终只会在同一个地方相遇:对象的路径和主体的路径,事物本身的历史起源和我们试图理解这些事物的概念和类别时更无形的历史性[14]。颜水生认为:“在研究实践中,研究主题只有实现了‘自我历史化和‘对象历史化的统一才能真正做到历史化。”[15]显然《马君武年谱》的编者在编谱之初就显现出了詹姆逊认为研究主体应具有的历史性。张旭在《马君武年谱》后记中这样写道:“如果将广西视作一个大的文本,我们对它的阅读和鉴赏又可从‘眼入手,而重要的历史名人和文化大家无疑构成了这个大的文本中的‘眼。”[16]编者寄希望于通过梳理这些重要人物活动的场域和时空,以便让读者对该区域有更广视域和更深层次的了解。研究主体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历史意识,使得《马君武年谱》中的文本和历史做到了实践意义中的辩证统一。于微观角度看,《马君武年谱》的出版为马君武翻译及翻译史研究者提供了历史化的研究导向;在宏观层面上,该书的问世也可视为区域文化史研究的一次互文性考察,为我国人文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史料和路径借鉴。
(作者单位系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