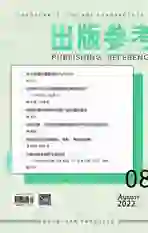汉唐地志文献整理出版的回顾与展望
2022-05-30韩轲轲
韩轲轲
摘 要:汉唐地志是我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但因保存不佳和流传受限,已基本亡佚。现有的整理出版成果偏重于文献辑录方面,这为日后深入的辑佚、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就各家所复原的辑本而言,仍有诸多谬误纰漏之处,使研究者无法直接加以利用。汉唐地志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需要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得到重视。应充分吸收自明清以来的已有辑佚、研究成果;规范整理方式、统一整理体例;提升汉唐地志文献整理出版的质量;适当引入“佚文+图注”的成果出版形式;重视佚文和文献的可视化、数据库建设,倡行融合出版。
关键词:地志文献 辑佚 古籍整理
汉唐地志是我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不仅是对传世正史文献的补充,而且为进一步开展区域史、地域社会史等中古史较为薄弱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地方资料。然而,因保存不佳和流传受限,汉唐地志已基本亡佚。值此之故,首要的工作就是对汉唐地方史志资料进行辑录、考释与整理,在其基础上展开文献的编纂、流变与王朝制度、地方社会间关系的综合研究。由于对后世地方志在内容和编纂体例方面的深远影响以及对历史地理学、汉唐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汉唐地方史志资料的整理,得到了传统学人和现代学者的关注,形成了整理散佚地志资料的良好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和新的学术视角的推动,有关汉唐地志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推出了一大批整理成果,为学界提供了更为全面、可靠的地方资料。本文拟对汉唐地志文献整理出版现状进行梳理,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期为更好地做好汉唐地志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提供参考。
一、地志文献整理出版现状
汉唐地志包括汉魏南北朝地记、隋唐图经和异物志,记载了山川地理、行政区划、地方物产、风俗和人物等具体内容,是有关汉唐时期的重要的地方性史料。地志,或谓地记、地理书。《隋书·经籍二》“地理记”篇叙曰:“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1][2]姚振宗说道:“陆、任二家所集,但依其先后远近,编而为部,有如今之丛书,重复互见,时所恒有。后人钞节其书,省并复重,故有上三家书钞,而失注钞撰者姓名耳。”[3]早在齐梁时期,地记(地理书)就经历过一个文献整理的过程。后世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等引用的汉魏六朝地记,应以陆澄、任昉收录在《地理书》《地记》中为主。然而也正是在重新整理和诸种类书节引条文的过程中,汉魏六朝地记的原貌很有可能被打乱了。加上地记的基本亡佚、名目繁多和存世佚文分散零乱,使得我们对其体例和内容,仍旧无以详知。正因为此,首要的工作便是从文献学、目录学等方面对地记进行辑佚、考辨与整理。
就目录学与考据学方面而言,自《隋书·经籍志》以来,佚书文献逐渐为目录学家所重视。他们以考订文献的作者、内容与编纂体例为宗旨,通过爬梳史料来阐述文献产生的来龙去脉。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姚振宗《后汉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及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与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等。特别是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综合清人在辑佚与目录学方面的成果,加以自己的按语,汇编成书,颇有搜罗史料之功。
就辑佚方面而言,早在元末明初,陶宗仪编纂的《说郛》丛书,就已经对部分的汉唐地志进行初步的辑佚工作,为地志辑佚之嚆矢。其中“地理类”部分,所辑书包括周处《风土记》、潘岳《关中记》、任豫《益州记》、盛弘之《荆州记》、王韶之《始兴记》、张僧鉴《浔阳记》、山谦之《丹阳记》、雷次宗《豫章记》、顾微《广州记》、邓德明《南康记》、罗含《湘中记》、袁山松《宜都记》、沈怀远《南越志》、沈莹《临海异物志》等。而后,张澍《二酉堂丛书》、王谟《汉唐地理书钞》、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曾钊“岭南辑佚书”、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与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则是真正意义上对古籍悉心钩沉、整理汉唐地方史志资料的重要成果。《二酉堂丛书》辑佚了《三秦记》《三辅旧事》《十三州志》《凉州记》《沙州记》和《凉州异物志》等十种相关地志;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据其重订目录,计划辑佚二百四十九种。然而最后完成的辑本大概仅有五分之一。其中,“秦汉至隋唐地理书”“各省古地理书”部分,辑录《张氏土地记》、应劭《地理风俗记》、袁山松《郡国志》、阚骃《十三州志》、王隐《晋地道记》、刘澄之《永初山川记》《周地图记》、顾野王《舆地志》、虞茂《隋区宇图志》、郎蔚之《隋州郡图经》、梁载言《十道志》《贞元十道录》、贾耽《郡国县道记》、辛氏《三秦记》、山谦之《丹阳记》、纪义《宣城记》、盛弘之《荆州记》、郭仲产《荆州记》、鲍至《南雍州记》《宜都山川记》、裴渊《广州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并州记》《冀州图经》、陆广微《吴地记》等,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對汉唐地志进行辑佚,已初具规模。曾氏“岭南辑佚书”收录于伍崇曜《岭南遗书》第五集(伍氏粤雅堂刻本),所辑相关汉唐地志文献有《异物志》《交州记》和《始兴记》三种。《麓山精舍丛书》第一集《辑佚类》则主要辑录了荆湘地区的六朝地记和隋唐图经,包括盛弘之、范汪、郭仲产、刘澄之等编纂的《荆州记》《荆州图记》《荆州图副》《荆南地志》《荆州土地记》《荆州图经》,及罗含《湘中记》,甄烈、庾仲雍和郭仲产等编纂的《湘州记》,黄陵、伍安贫的《武陵记》《衡州图经》《道州图经》《朗州图经》和《澧州图经》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以辑佚经书佚文为主,不过“史部”却也辑录了《钱塘记》和《会稽典录》两种;在马国翰的基础上,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增辑了顾野王《舆地志》《括地志》《十三州志》《太康地志》《永初山川记》《郡国县道记》《襄阳记》《湘州记》《湘中记》《荆州记》《豫章记》《广州记》《南越志》《荆州图经》《朗州图经》《衡州图经》《沅州记》等汉唐地志四十八种。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取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其中有关地记者,为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和夏侯曾先《会稽地志》。
以上是明清以及民国时期有关汉唐地志文献的整理出版情况。这些成果虽初具规模,但是辑佚成果还未达到科学、规范的程度,如所辑佚文不全、未对佚文进行校勘和考证。总而言之,辑佚工作尚处于初步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汉唐地志文献得到进一步的整理。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996年增订本),辑佚历史上云南地区的佚书,其中与汉唐地志有关者,有《哀牢传》《南中巴郡志》《永昌郡传》《云南行记》《云南别录》和《云南事状》等,作者对每一佚书进行解题和佚文的初步校勘。和《云南古佚书钞》相似,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也是对山西一地的各种方志的辑录。存留的有关汉唐时期地志,主要有《赵记》《三晋记》《河东记》《上党记》《冀州图经》《并州图经》《代州图经》和《上党图经》等。作者于每一佚书前,编排解题,同时对一些佚文进行校勘。此外,还有骆伟、骆廷《岭南古代方志辑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与《三秦记辑注 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及孙琪华《益州记辑注及校勘》(巴蜀书社2015年版),都是对一地区地志文献的辑佚。值得一提的是《益州记辑注及校勘》,整理者对每一则佚文有较详细的考证,并与其他有相似内容的佚文进行比较。
除了专门针对一地区的地志文献进行辑佚外,还有学者专对一朝代之佚书进行整理。朱祖延《北魏佚书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辑录考释魏人撰述之佚书,其中“史部地理类”部分,辑录《十三州志》《大魏诸州记》《后魏舆地图风土记》、李义徽《舆地图》、崔鸿《西京记》、王尊业《三晋记》、刘芳《徐州人地录》、李公绪《赵记》、卢元明《嵩高山记》、杨衒之《庙记》。每一种书目下,简要交代佚书作者的家世爵里,并附有朱氏的按语。此外,亦有张崇根《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收入齐鲁书社《清儒地理考据研究·隋唐五代卷》2015年版)与顾恒一、顾德明等《舆地志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等辑佚成果。他们的工作以爬梳佚书条文为重点,并对佚文和文献进行初步的考释、断代。
与上述专于一方隅的辑佚书不同,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应该说是全面整理汉唐地志文献的重要著作。此书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专门对汉唐地志文献进行辑佚。据作者所言,他“从四十余种、六千余卷类书、地志、史书、子书中,共辑出汉唐方志四百四十种,约四十万字”。每一书均写明书名(异名)、朝代、撰人、著录情况。佚文注明出处,并有简单的校勘。不过,此书出版后,引起学界的极大反响,其中不乏批评之声,[4][5]亦有不少学者撰文对其错谬进行补正。[6][7][8][9]这也反映了佚书整理是一项长期伏案的精细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后来,刘纬毅、郑梅玲等《汉唐地理总志沟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辑录了汉唐亡佚和存世残卷的地理总志六十九种,也算是对《汉唐方志辑佚》一书阙少地理总志内容的补充。不过,小至文字,大至佚文内容及其归属,仍存在不少错谬。如,此书所辑《大魏诸州记》“益州汶山郡”佚文,“岁更互枯、互生,不俱盛”,整理者却录成“岁更牙枯、牙生,不俱盛”。其他如佚书体例、佚文归属等等,都存在不少问题。关键的是,整理者不仅没有做细致的版本、文字校勘,而且没有对佚文和佚书进行深入考证。
此外,王仲荦、池田温、郑炳林、李并成、李正宇与屈直敏诸位学者着力于敦煌文书所出地志残卷的考释校注,下功尤深,尤其是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值得借鉴。
二、地志文献整理的基本理路
这些整理成果之间的差异,也反映出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与学科理路。概括而言,它们受到如下三个方面的学术传统和路径的影响。
第一,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汉唐地志文献进行辑录、整理。这一研究理路承袭了辑佚学、目录学与考据学的优良传统。
第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将汉唐地方史志资料纳入到地理典籍、方志与古代地理知识等层面上加以探究,关注的主要选题有:地理志书的产生与编纂的历史过程;地理典籍与地理学史的关系以及地名考证、地名学的源流。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青山定雄有關“六朝之地记”系列文章、史念海《河山集》(版本较多)、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辛德勇《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与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
第三,在史学史方面,主要的研究思路是考察汉唐间史学发展及演变、史学典籍产生的政治、社会基础。其重要成果有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2000年版)、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永田拓治《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4期)、仇鹿鸣《略谈魏晋的杂传》(《文史知识》2006年第1期)与王琳《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文史哲》2012年第1期)等。
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偏重于文献辑录、整理方面,这为日后深入的辑佚、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就各家所复原的辑本而言,仍有诸多谬误纰漏之处。不少条文更是张冠李戴,使研究者无法直接加以利用。此外,佚书断代、作者和内容亦须做更翔实的考订与辨析工作。因此,我们需要对汉唐地志文献重新进行更为全面、细致的辑录、整理和出版。此外,与汉唐地志文献相关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这和地志文献的整理尚未到位有一定的关系。
三、地志文献整理出版的展望
汉唐地志文献的整理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就学术意义而言,汉唐地志文献的整理出版不仅对汉唐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颇有裨益,而且能够突破旧有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促使学者重视地域社会史的研究理路,进而拓展区域历史地理、汉唐地方史研究。简言之,汉唐地志文献是今后深化汉唐史研究的重要文献材料之一。故学术界、出版界必须通力合作,在前人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辑录、整理汉唐地方史志资料,供将来的研究参考和使用。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地志资料是地方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深入整理和出版,一方面有助于传承地方历史与文化,加强人们对地方文献的保护意识,弘扬多元的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地志文献中的山川环境、物产的记载,为地方环境变迁、物产演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值此之故,汉唐地志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就需要在以往整理出版的基础上,继续得到重视。
1.充分吸收自明清以来的已有辑佚、研究成果
在没有数据库检索的时代,辑佚者们靠的是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一纸一页的翻检。通过几代人的不断积累,才形成今日已亡佚的汉唐地志文献的规模。因此,在对佚书进行辑佚时,我们要充分吸收既有成果,这样既避免了重复劳动,又能在原来辑佚的基础上,深入校勘和考释。
2.规范整理方式、统一整理体例
从已出版的汉唐地志文献中,我们发现辑佚成果有着较多元的整理方式,各有局限性。一些整理出版成果,尤其是传统时期的辑佚文献,仅有佚文,没有出处,更没有校勘和考释。还有一些整理出版成果重在校勘,但对佚书和佚文的解题和考释就很不到位。因此我们今后的整理出版工作应该包含:佚文的辑录考释,文字的校勘比对,实地调查与文献断代,并附解题,同时出注按语。具体来说,按文献类型(地记、图经、异物志与行征记等)依次辑录至今已经失传的地志文献。“地记”“图经”的编排原则应是全国性的总志在前,各郡、县“地记”、“图经”在后。各种文献总体上以时间、州郡为纲,同时每一佚书按照解题、内容(条文)与考释的顺序进行整理。“解题”应包含佚书的断代、作者与体例,“内容”依据“解题”中的“体例”进行排列,在每一条文后出注来源,同一条文出自不同的典籍时,择善而从;“考释”部分应针对条文中的人名、地名与条文内容本身加以考证、辨析。另外,根据佚文内容,适当参考各地出土的考古资料。不仅如此,辑佚的范围,不应仅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典籍,还应将目光投射于域外的汉籍,比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大量汉籍。
3.提升汉唐地志文献整理出版的质量
汉唐地志文献的辑佚工作,繁琐且极费精力。一些整理者将之看作毫无用处的工作,常常将其委派、分发给学术训练和基础都还欠缺的学生。这样的辑佚成果,其质量可想而知。汉唐地志的整理出版,需要综合运用辑佚、目录学与史料互证的研究方法考订文献的断代、作者与编纂体例;对因文献流传、传抄引发的讹误遗漏等问题,进行辨伪考释。这对整理者具有极大的考验。在日后深化、提升该种文献整理出版时,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整理者的学术水平和相关的业务能力。同时,在相关的选题和整理工作中,学界和出版界应加强沟通联系,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另外,在地志文献的编校中,编辑也需及时提升业务水平,避免诸如文字舛误、佚文重复的成果出现。
4.适当引入“佚文+图注”的成果出版形式
汉唐地志文献涉及广大的区域,佚文中涵盖大量的地名。专业学者往往不知其所在,更不用说普通的读者。为提高汉唐地志文献的使用率和成果转化率,在今后的整理出版中,学者可吸收借鉴优秀的文献图注的整理方式,如《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水经注校笺图释》等已有的学术成果,将适当的佚文加以图注,使得佚文和相关的地名更为直观。
5.重视佚文和文献的可视化、数据库建设,倡行融合出版
在上述基础上,加强纸质出版和数据库建设的融合。根据汉唐地志文献与考证结果,绘制出不同区域、不同主题的地图,进而将地方文献数据化,制作“汉唐地志文献”数据库,直观形象地呈现汉唐时期各地域的地理风貌,进而推动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互动。既实现了古籍数字化的目标,又可与时代接轨,深化数字人文研究。
四、结语
汉唐地志是研究汉唐地方史的重要文献。不过,在汉唐史研究的诸种文献中,地志文献是使用相对较少的一种。因此目前的汉唐地方史研究仍旧局限于傳统的眼光与视角,很难有所突破。在全面认识汉唐地志资料的基础上,再结合石刻、简牍与敦煌文书等史料,对汉唐时期的区域差异、核心与边缘、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有整体的把握,由此获得对地方史的全新认识,拓展地方社会、文化史领域的研究。因此,全面辑录、考释与整理汉唐地志文献,进而探究文献与制度、社会的关系,同时运用文献资料探析地方社会的运作实态、地方史的建构与地方知识的确立等问题,将成为学界在汉唐史领域的重点。
近年来,汉唐地志文献的整理出版成果,表现出整理范围扩大、涉及地区宽广和整理更加深入的特征,然而整理的质量总体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整理成果出现不少问题,如辑佚不全面,没有解题和文字校勘,对佚文的差异未做辨析、考释等。文献辑佚并非是简单的复原工作,而是一项极其繁琐的互证、校勘与比对印证的过程。整理者应认识到,后世典籍在引用条文时,或不加出处,或删减篡改,或二书同名而不加作者。诸如此类问题,极大影响了辑佚工作的进展。因此,在具体的条目辑佚过程中,须慎重考释,择善而从,而不是一成不变地沿袭、重复传统时期的简单辑佚工作。我们应吸收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重视对汉唐地志资料的辑佚、解读、辨伪与实证研究,采用传世文献与汉唐地志文献互证的方法、文本和文类的研究视角、历史地理学的考证、定位方法,对其内容进行长时段、深入细致的考察,推动汉唐地志文献整理出版工作的进展,以期取得更多优质的出版成果。
(作者单位系厦门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