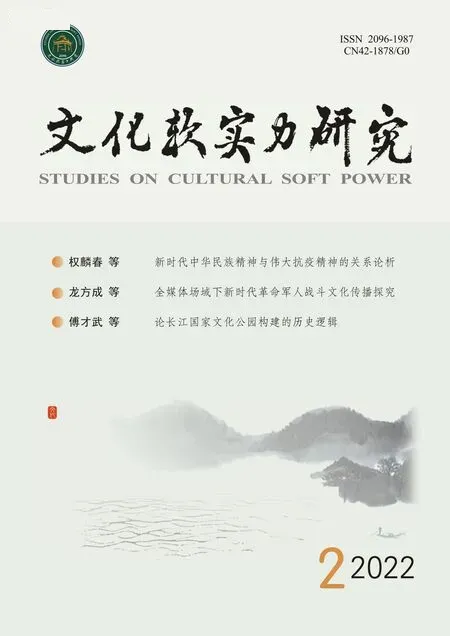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构建的历史逻辑
2022-05-19傅才武程玉梅
傅才武 程玉梅
(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2)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的战略目标。2015年全国旅游规划发展工作会议中,国家旅游局(现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明确将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发展规划纳入工作要点,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发展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有学者认为,长江流域特有的生态环境提供了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具备较大的文明发展潜力,长江流域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化形态,引领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文明进程中有重要地位。[1]开展长江文化的研究是时代的需要,长江文化作为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机与创造的活力,时至今日,长江文化的研究依然十分必要。[2]由此可见,关于长江文化的研究不仅关乎长江流域的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然而当我们在中国知网上以“长江经济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到以经济体制改革、环境与资源、宏观经济等学科为主的期刊文献6912篇;而以“长江文化”或“文化长江”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到期刊文章134篇,其中文化研究占主导(48.34%),旅游和中国通史分别排第二(占比5.3%)和第三位(占比4.64%)。从文章数量看,相较于长江经济的研究,长江的文化研究相对薄弱,需要学界投入更多的关注。
2022年1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正式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中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包含了长江流域的13个省(市、自治区),通知要求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能够激活长江历史文化资源,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李飞等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政府依托深厚的历史积淀、磅礴的文化载体和不屈的民族精神构建的新的中国国家象征,对内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对外成为中国印象的重要代表。[3]张祝平认为,国家文化公园要能够代表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文明,并且能够获得全体国民广泛认同。[4]
对照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要求,目前学界关于长江文化的研究则显得整体性和融合性不足。首先,对于长江文化资源的活化方面,有学者认为长江流域是高品位的人类自然和文化遗产集中地,也是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5]。国家在战略层面上也提出了长江文化旅游带,但是学界跟进研究受限于行政区域的限制,呈现区域性强而区域间的关联研究弱的特征。其次,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导向下,学界重点关注长江文化旅游的“绿色”功能,少有研究长江文化在促进民族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上的独特作用。也有学者前瞻地看到了长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认为长江文化带建设要创新长江文化的发展形式,建立长江文化共同体,以推动长江文化的新繁荣,实现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6];或有学者以“点”到“面”,借助长江流域稻作文化遗产为切入点,讨论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文化旅游资源价值。[7]
刘庆柱认为,“黄河文化”正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故而理所当然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对象,且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该定位于“根”与“魂”的“物化载体”展示之上。[8]而这个“根”和“魂”正是流淌着的中华文明史。在长江文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无论是“彰显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能载体”[9]的效用,还是“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彰显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展示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4]的时代价值,都是构建于长江所承载着的历史的“根”与凝聚着精神的“魂”之上。李飞和邹统钎认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受到国家——政治、文化——价值认同和公园——组织管理三种逻辑力量的支配,认为“政治、文化、组织管理”三种逻辑力量促使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最终确立。[3]我们认为,这三种逻辑的底盘均是历史逻辑,离开了历史逻辑,政治、文化和组织管理就失去了基点。本文拟就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和建设的历史逻辑展开讨论。
一、中华农耕文化的摇篮,世界稻作文明的源地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后世称其为大河文明。大河流域地处北纬30°人类文明生发线附近,光照充足,再加上河流的冲刷,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合作物生长,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农耕文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此大河流域也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是麦作文明发源地。而在中国,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与黄河流域的粟作文化共同养育了中华民族。也正是因为如此,“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避免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发展中断的命运,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很幸运地拥有一条同样自西向东与黄河平行的长江,以其富有增产潜力的水稻作为后续接班,而且后来居上,继续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10]。
(一)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并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在世界稻作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被誉为“世界稻作之源”[11]。在经历了“印度起源”“东南亚起源”“阿萨姆—云南起源”等不同的主张之后,随着近年来考古证据的增加,初步奠定了长江流域作为世界稻作文明起源的地位。1972—1974年,在长江下游的浙江河姆渡(距今7100年)发现4000多平方米堆积的稻谷、稻壳1米以上。同时发现耕地的骨制耒耜,家畜猪、狗、水牛,还有干栏式榫卯结构的建筑物,表明河姆渡文化已经进入到了较发达的农耕文明阶段。在中国,早于8000年的水稻农业遗址共有16处,除了广东的牛栏洞遗址(113.45°E,24.33°N)和河南的贾湖遗址(113.70°E,33.62°N)外,其余14处遗址全部位于长江流域,其中包括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三个水稻遗址,即江西省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117.179°E,28.721°N)和吊桶环遗址(117.178°E,28.721°N)、湖南省道县的玉蟾岩遗址(115.00°E,25.50°N)、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110.40°E,29.42°N)。尤其是澧县城头山将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历史推到1万年前,不仅出土了水稻,还发现了古老的稻田,考古学家评价城头山为“城池之母,稻作之源”。城头山遗址不仅表明了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是水稻驯化起源地,也推翻了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的说法,表明长江流域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一样历史悠久、灿烂辉煌。
2012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联合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水稻基因图谱揭示的栽培稻起源》[12],研究表明栽培稻的两个亚种——籼稻和粳稻起源于中国。粳稻是中国的先祖们最先在华南珠江中部地区由普通野生稻中的某个特殊品类驯化所得,而籼稻是由粳稻与当地的野生稻杂交形成,并作为最初的栽培稻种传至东南亚。从目前的稻作遗址分布和年代久远程度来说,都表明长江流域是稻作文明起源的中心(至少是中心之一)。并且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流域,早期的发展中心在长江流域,至今最发达的地区仍然在长江流域。[13]稻作文化遗产之所以成为人类文化记忆,就在于其拥有丰富的人类共有的精神内涵。水稻驯化及稻作农业为长江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也是长江流域为人类做出的巨大的开创性贡献。[14]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成熟,逐渐影响了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南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恒河流域等。如今,水稻依然是这些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而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虽然最初传入这些地区的是黄河流域的粟、黍等北方农作物,但随着中国水稻种植技术和青铜器、铁器的逐渐传入,大规模地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生产力,逐步形成了东亚稻作文化圈,对后来的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世界,水稻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广(全世界水稻种植面积约15500万公顷)、产量最高、养育人口最多(全世界大约50%人的主粮)的粮食之一。有日本学者认为,4000年前“气候恶化使北方旱作畜牧民大举南下,代表长江文明的‘三苗’受其驱赶,逃进云贵山地,海岸附近的吴越人则成为海上难民,逃往日本列岛和台湾岛。日本列岛的稻作渔猎神话源自长江流域,八岐大蛇、玉珠、鳄鱼、鸬鹚等都是铁证”[15]。另外,东南亚地区传统建筑也与中国(尤其是百越族地区)的干栏式建筑有“源”与“流”的关系。而居住在干栏式建筑的人民在语言、祭祀等方面保持着共同的习俗。[16]如“那”在壮族语言中有“田”“稻田”的意思,并且“那”在中国—东南亚的壮侗语、泰语、老挝语、掸语中通用。[17]
(二)水稻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稻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组成部分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于宗教观念”,都是“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方式决定了文化形态。稻作农业不仅是经济行为,同时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18]稻作生产方式作为物质基础和经济方式,对中华文化形态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漫天星斗式的聚居地,多样的文化形态。由于长江流域自古以水稻作为主要农作物,而水稻的种植受地形、降水、光热等自然环境约束,需要丰富的水资源以及可以聚集水源的地形,同时还需要集体作业来修筑不漏水的田埂、便利的注水和排水系统等,这迫使长江流域早期社会人口既相对分散,但又小规模聚集。这样的居住和生产模式导致了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像漫天星斗,分散但各放异彩,形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也造就了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例如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云南元阳梯田等,构成了古老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记忆”。长江流域的礼仪风俗、时令节气也大多与水稻有关,如春节的年糕、正月十五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等。
第二,农业经济的发达支撑了农耕区稳定的社会系统。由于水稻特殊的耕种体系,让农人可以以年为周期在同一块水田中重复耕作,不必像旱地作业一样需要轮荒,因此水稻作业的社会相比旱地来说也更加稳定;且精耕细作的水稻相较早期“靠天吃饭”的旱地作物更加高产,这也催生了水稻种植地区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有较好的改进和发展,养成了水稻种植区人们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水准,例如长江流域的玉雕文化、漆器、丝织等。由于水稻种植对水的需求,导致水稻种植区的人更早也更方便食用水中鱼虾、贝类,鱼米之乡的生活环境造就了长江流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膳食结构,较为均衡的营养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智力发展。
第三,造成了具有组织性的社会大众心理结构。长江流域特定的自然环境及物质生产方式,影响着居住其上族群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大众心理意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曾就不同耕作方式导致的文化差异对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进行了比较研究,将其研究成果《水稻与小麦耕作对比视角下中国人群普遍心理差异解释》[19]发表于《科学》杂志。通过对中国南方水稻种植区与北方小麦种植区的人群进行研究,发现南北两种种植方式对生产方式的组织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造就了中国麦作产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和稻作产区(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南北文化差异。南方稻作区的居民表现出明显的整体思维模式,而北方麦作区的居民则表现出较强的分析思维模式。稻作区的居民更具合作精神,善于形成商业合作组织,离婚率较低,但缺乏创新精神,发明专利少。而麦作区的人更擅长在商界表现自我,富有创意,有更多的发明专利,同样离婚率也相对较高。这些社会现象的背后是不同的耕作方式产生的影响。相比于麦作农业,水稻的生产需要长期稳定的水源供给和精耕细作,因此在稻作区,需要建设灌溉设施以保证水源的持续供应,这就需要建立合作制度,使整个灌溉系统尽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灌溉系统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工程,每年都要进行修缮、清淤等工作,庞大的工作量,需要农户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据统计,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之前,中国稻作区的农民人均工作时间是麦作区的两倍。因此,在稻作区,其社会文化是高度集体化的互惠形式,其社会规则倡导合作重于分立,尽力避免冲突的出现。相比于水稻的生产,小麦的种植不需要复杂的灌溉系统,小麦产区的农民无需与他人结成合作关系,努力提升个体生产率才是小麦产区农民的最优策略。因此,小麦产区的农民在创新能力和个人主义的表现上,要强于南方稻作区的农民。
梁启超先生曾描述中国南北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在《近代学术之地理的分布》中说:“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多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20]归根结底,正是基于地理环境差异上的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了南北地区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及思想观念。
二、中华民族母亲河记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长江作为历史文化空间,在记录中华民族历史的同时,也建构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李白《送储邕之武昌》),以故园家国的情感认同进入到民族历史记忆的深处。
(一)对长江的认识过程与民族“领土认同”的形成
中华民族对长江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探索过程。首先,对长江的称谓,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长江”以及国外所称的“扬子江”。在中国古代,“江”是对长江的指称,特指长江;“河”则特指黄河。在《诗经·周南·汉广》中有关于汉水与长江的记载:“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由于古代交通闭塞,信息流通不足,所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对长江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如,长江的上游称为沱沱河和通天河,川、藏、滇地区称为金沙江,战国时期的《禹贡》将其称为黑水,《山海经》称之为绳水,宋朝因沿河盛产金沙而改名为金沙江并沿用至今。此外,金沙江还有丽水、马湖江、神川等别称。长江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段被称为川江,流入江汉平原后,枝城至城陵矶段称荆江,江西九江段称浔阳江,安徽一带称楚江……长江这一固定称谓则一般认为是在三国时期形成的。称“长江”首见于《三国志》记载,以后长江之称逐渐普及。[21]2“扬子江”之称源于扬州以南至镇江丹徒的扬子津。起初,有人把扬子津这段长江叫扬子江,现在成为西方对整个长江的称谓。
对长江源头的考察和辨析贯穿于古代和近代社会,构成了华夏族群的人文地理记忆。
《禹贡》记载岷山为长江之源:“岷江导江,东别为沱。”《山海经》记载也是“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入海。”《荀子》也指出“江出于岷山”。以至于很长时间内,人们都将岷江作为长江的源头。随着地理考察的逐渐深入,人们通过对长江源头的考察,对长江的认识和对中国地理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之《溯江纪源》(又名《江源考》)中认为:“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溪峒间,水陆俱莫能溯”[22]。因此导致古人对长江源头的辨认有误,认为“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经黎、雅,与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长于岷江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 。明代章潢也曾在《图书编·江源总论》中提出金沙江为长江正源之说,且早于徐霞客。[21]3但那一时期,主流依然认为长江源头是岷江,一直到清代,金沙江为长江源头才逐渐得到认可,并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关于长江的总体性知识谱系。
20世纪开始,国人对于长江流域的遗址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长江上游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巫山大溪文化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等;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江西新干商代遗址,湖南彭头山遗址、湖北屈家岭遗址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草鞋山遗址和马家浜遗址等。通过这些重大发现,学界普遍承认,长江文明无论在延续的长度上还是在发展的高度上,都不逊于黄河文明和世界其他大河文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所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起源,承载着所有中华儿女的族群记忆与国家认同。
国人对长江源头的探寻以及对于长江流域古代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活动,它体现的正是族群的“领土版图”意识和民族国家完整性的体验和建构,长江探源既是科学探索过程又是族群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起到了建构“民族想象共同体”和国家认同的独特作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等构成了族群和国家得以存在的前提,因而对族群和国家的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准确地,人们不能把它从这个系统、这种逻辑、这种总体性中排除出去。”[23]周光辉、李虎等学者也认为,领土首先作为一种物理空间,成为“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关系的场所”。因而“领土认同”是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命题,“领土认同是公民对国家的领土这种整体性特征的认同,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在场的情境感” 。领土是国家的整体性特征,领土版图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具有核心作用,领土具有从“自然空间向政治空间演变”的特征,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公民通过与特定领土的互动而将自身与领土密切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一种在场的情境依恋和归属感:我热爱甚至属于这片土地。公民的领土认同一旦形成,领土就不再仅仅是公民活动的物理背景,而成为公民建构自我的组成部分。”“能够为保持国家认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供一种情境化的基础。其实,个人就是在对国家的整体性特征形成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将国家的整体性特征内化为个人心中的一种认同信念,即个体化过程,建构起国家认同。”[24]
从古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建国后才得以完成的国人对长江源头的考察活动,正是中华民族自身为寻求族群认同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而进行的科考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与特定领土版图的互动而将自身与地理空间和地理标志密切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一种集体在场的情境依恋和归属感。在这一过程中,长江源头就不再仅仅是华夏族群的物理空间和生存背景,而成为族群自我建构的实现渠道和组成部分。族群成员在形成领土版图整体性特征(地理标识)认知的过程中,同时也将长江象征符号内化为个人心中的一种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
(二)“江河互济”避免了文明进程中的“内卷化陷阱”,形成了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直以来,中国学界和社会普遍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我国的考古发掘也多数集中在黄河流域,尤其是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让大家普遍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然而随着长江流域考古的展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江流域有着比肩黄河流域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母亲河记忆”包含着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两大文化系统。梁启超认为,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黄河和长江影响最为显著:“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25]78。
周秦以来,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峙中,南北文化长期处在竞争与融合的“太极推移”的运动过程中。[26]“江河互济”是中华文化传承五千年而不断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文明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所在。梁启超认为,中国的风俗南北差别明显,中国文化在其风格和流派上,截然而分为南北两大流派,如“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 。这种差别,体现在各个方面,如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慨” 。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观” 。[25]81这种南北差异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差别相关联:“千余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响,尤有彰明较著者” 。“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 。梁启超举例说:“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李将军之金碧山水,笔格遒劲,北宗之代表也;王摩诘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音乐亦然。……直至今日,西梆子腔与南昆曲,一则悲壮,一则靡曼,犹截然分南北两流。”[25]86-87
中华文化历来是由北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张正明、冯天瑜等学者称中华文化是“江河互济、二元耦合”的文明系统,且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回望古史,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27]正是南北(长江、黄河)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使中华文化在长期的相对独立的发展环境中,因南北交流互鉴而拥有了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
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两大亚文化系统,尽管文明形态上具有大体相同的总体性特征,但在物质生产、行为方式、观念心态和制度层面并不完全相同。东周以降,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双轨并进,“龙—凤”齐舞,“风—骚”竞辉,“儒—道”相济,构造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宏大气象,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形成了同一文化系统的内部大循环,从而避免了世界上其他文明因趋同化而陷入板结停滞的“内卷化陷阱”。黄河文明整体上体现出传统农业社会重本轻末、厚重少文、庄严正统、安天乐命的特点,但长江文明却是中国浪漫主义的代表,富于玄思,具有浪漫、灵动、超越的特征。在五千年华夏文明进程中,正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差异性,如南炎北黄、南凤北龙、南道北儒、南稻北粟、南丝北皮、南釜北鬲、南舟北车、南《骚》北《诗》等,建构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张力。
“江河互济”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构成了华夏族群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如日本学者伊藤道治称中国早期文明为东方式的“两河文明”[28]。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也认为,“中国的文明有南北两个渊源,公元前2000年见于史册的中国文明乃是南北文化之间长期冲突、混合、交流的结果”[29]。
夏商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展现出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长江流域也出现了若干个特色文化区,且文明发展程度并不亚于中原地区,例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及四川三星堆遗址都说明了彼时长江流域古代文明的辉煌,但是就总体发展程度而言,黄河流域还是略高一筹。两周之际,黄河流域文明继续发展,长江流域虽然不及黄河流域,但长江中游地区楚国发展迅速。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游的楚国尚不为北方诸侯所重,但已有脱颖而出之势”[30]164。从秦到隋唐,黄河流域俨然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的中心;隋唐至宋,由铁器农具的广泛使用,长江流域农业生产和经济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尤其是江南一带,经济已经十分繁荣,我国经济中心开始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宋元时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和文化最为繁荣的地区。“无论是科学技术、学术、艺术等文化领域,还是文化的普及和传播,长江流域都走到了黄河流域前面。”[30]719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经济依托长江航道便利的运输条件,以及发达的城乡手工业、海外贸易,形成了经济与城市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文化方面,西学东渐和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开放的文化风气使得长江流域涌现出大批文化、政治、经济、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名人大家,于此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开始。
(三)“对角线运动”与“江河互济”相嵌套,建构了中华文化“太极推移”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特征
除了“江河互济”的特征外,中华文化的另一大特征就是瑷珲—腾冲线与西域—东南线的对角线交叉和人口经济与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化演进轨迹(如图1所示)。“对角线运动”与“江河互济”相嵌套,形成了东亚大陆内部超级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其足够大的地理生态空间保障了中华民族在近古以前一直处于文明的扩张和上升中,避免了文明因内卷而陷入停滞。瑷珲—腾冲线是中国的人口地理线,研究者颇多。西域—东南的人口和文化流动线则标明了大陆型中华民族的演进路径。相对于长江流域,黄河文明的早熟使其在先秦时期形成了较高的文化势能。以“泰伯开吴”为标志,黄河文化的因素从陕西即黄河流域的上游,流播到长江中下游的太湖流域,开启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交流和流动的“对角线”。有学者认为,这条对角线的开辟,从“由北而南、由河而江、由陆而海”这三个维度上启动了华夏文化体内部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互动,启动了江南与中原的互动,从而“牵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线” 。这条文明对角线所支撑的巨大的回旋余地使中华民族不论是在古代承受北方游牧民族冲击时,还是在近代承受西方文明的冲击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传承都不曾中断。“这条对角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本质性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良性的互动互补,在承受各种强烈的挑战和震撼中,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华民族由此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26]

图1 中国文化进程的“太极推移”示意图
综观我国古代历史,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有千秋,优势互补。一旦黄河流域经济社会陷入衰弱,长江流域就会接过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火炬。长江和黄河文化的差异性,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对角线运动”的作用下,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形成了“太极运转式的南北推移”,建构了“江河互济互摄”的文化大循环,从而避免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因囿于半封闭的东亚大陆而陷入“内卷化陷阱”。同时,长江和黄河多彩的文化家园代替宗教家园,在世俗社会之上建立起一个超越性的精神世界,“江河互济”和“对角线运动”的相互嵌套协同,建构了维系中华文化共同体传承不辍的强大内生力量。
三、引领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桥梁,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核心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既来源于华夏族群的长期历史积累,也来源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塑造。人们心中对一个地方的图像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所认识的、所希望的,以及所期待的体现。[31]近代以来,长江率先参与到中华民族近代转型的进程中,长江流域中西文化汇聚碰撞,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工业化成就等,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古代“文化认同型”国家[32]转向近代民族国家艰难曲折的历程。
长江在中华民族近代化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几乎就是沿着长江、从东向西逐次推进的。从文化考察的角度,似乎可以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比作“一扇门”——门的这一边是农耕渔樵、社会缓慢发展的中世纪;另一边是车马喧嚣、声光电烁、熙熙攘攘的近世繁华[33]。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沿长江溯江而上,逐步深入到内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两年之后,美、法相继在上海设立租界,上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最集中的城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长江流域的重要港口城市如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也逐步开放成为开埠城市。在近代中国相继开辟的80多个通商口岸中,长江沿岸就有20余个。这些通商口岸城市往往成为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1879年,发电照明技术传入中国,在上海虹口第一次出现了发电照明。1882年7月,上海电光公司创立,从此以后改变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申江今作不夜城,管弦达旦喧歌声;华堂琼筵照夜乐,不须烧烛红妆明”[34]。
其他如,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1881年11月,津沪电报线架设竣工;1884年,上海至广州“通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10余年间,电报线已“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称便”[35]。1881年,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1882年,电话传入中国,上海成立“德律风”(telephone音译)公司;20世纪初,武汉出现商办电话。长江流域兴起了一系列早期的民族工业,这一时期的贸易公司、航运公司、银行以及各种工厂开始出现,并聚集在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心城市。据1931年的统计,当时的外商在华投资约有70%集中在上海。[36]189除上海外,长江中游的汉口、沙市一带也是那一时期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溯江而上,激发了民族工商业的兴起。1861年,曾国藩在长江下游安庆设立了安庆军械所,为长江流域军事科技工业的兴起揭开了序幕。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奏设江南制造局,这是自安庆军械所设立以来全国第二个军工企业。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武汉拉开了近代工业化建设的序幕。张之洞在武汉相继成立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后改为汉阳兵工厂)以及纱、布、丝、麻四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冶铁、军工和纺织工业体系。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在湖北开设新式学堂等,让武汉成为继上海、天津之后的又一洋务基地与近代大都会。此外,长江上游地区如四川、云南等地也兴办了火柴厂、造纸厂、煤矿、铜矿等近代工矿企业,近代工商业深入长江上游和内陆。到清末民初,以上海为首的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聚集地,长江流域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促进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也搅动了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轨迹,夏振坤和张艳国将长江文化的近代经历总结为“器物层面上进行的近代化努力;在制度层面上展开的近现代求索;在社会主体层面上的近代求索”[37]。
1911年,湖北新军举旗起义,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自上海开埠以来,西学即沿长江西进,最终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结出了革命的果实。[36]193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长江见证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承载着200年来中华民族的荣辱与兴衰。1949年后,长江流域继续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本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以长江为纽带、联通长江沿岸城镇并辐射全国的现代工商业体系。截至2019年,长江流域居住着超过40%的人口,地区(11个省市)生产总值457805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42%。(1)数据源于各地区统计局数据相加。长江流域是21世纪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前进基地。
近代以来长江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推进线路息息相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放口岸已从沿海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随即,外国轮船开辟了长江航线,在方便其对内地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长江沿江城市之间的联系,加速了沿江城市带的形成。”[38]201-202长江流域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交汇地带;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两大工商业基地。进入20世纪,武昌辛亥首义的发生,上海经济金融中心的形成,中华民国建都南京,三座长江干流城市的崛起和协作,改变了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面貌。此后,“长江文明在国内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新旧文化的殊死搏斗、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实现了近代化的转换。”[38]200
四、简要结论:华夏族群历史建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底层逻辑
(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再生产装置”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超级文化空间复合体,包含了长江区域范围内历史建筑、纪念物、历史遗址、文化街区、历史城镇和文化景观等文化遗产与线路所依存的长江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融合共生,是长江历史文化剖面在不断延伸的地理空间内积累、叠加和创新的“文化再生产装置”。这一装置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涵:(1)提供了与一定历史时空相关联的华夏族群生产生活活动,族群迁移、交往交流路线的标识和“索引”,体现为长江人文空间与华夏族群历史活动事件和独特价值观念相互关系的总体性空间表达;(2)提供了中华文化在长江流域空间上流动、交流和扩散的通道。不同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在长江这一特定区域内交流和碰撞,促进了中华文化观念的跨区域传播和跨文化影响。贯穿于生态长江之上的长江历史文脉,以其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连接具有了贯通古今的可传承性,获得了内在的规定性;长江流域空间地理、生态和文化整合,为华夏族群融合进程中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资源,有利于在不同社区、不同城市、不同地区或国家间建立一种文化连接,推进以长江文化为核心价值符号的文化整合与价值传播。
同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具有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功能的超级文化空间,既承担了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流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文化“存量”的功能,又承担了在此基础上凝练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与时代品格,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提供新观念、新思想和新制度实践——提供创新“增量”的功能。
一方面,长江流域的哲学思想、科技成就与文艺作品能够引发民族共鸣,实现了民族共认与共享,从“能指”单一的地域符号升华为“所指”丰富的民族文化标识,与黄河文化一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DNA中的“双螺旋”,同塑造国家文化象征的文化逻辑相呼应。另一方面,长江文化代代相传延绵不绝,在华夏族群遭遇整体性危机时为华夏文明延续“文化正统”提供了回旋空间和维护巨力;在近代面临外国列强侵凌时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力量;在现代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为国家提供了文化创新动力,由此成为了国族历史建构过程中的砥柱基石,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政治逻辑相呼应。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宏大叙事框架,其基本理念包含了从保护长江文化遗产遗址、项目和技艺(点)到保护长江文化线路本身(线),再到保护线路所依存的长江自然生态环境和华夏族群人类价值活动(面)的演进过程,突出强调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价值大于各构成要素价值之和的原则要求。正是要通过建立这一叙事转换机制,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资源向“国家文化象征”转化,以此重建的新的中国国家象征,既作为对内强化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媒介,又作为对外传播中国印象的标识,以此塑造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
(二)新时代下国家文化公园具有文化认同、形象建构和国际传播的独特价值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在文化强国战略和文旅融合背景下提出来的战略性概念,集中反映了中华文化底蕴与特色,“国家文化公园的多重意蕴包括体现‘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体现‘正义—平等—秩序’的伦理意蕴和体现‘天下观’的空间意蕴,它们‘三位一体’地诠释了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和内涵” 。 “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遗产话语在国际化交往和本土化实践过程中的创新性成果,也是中国在遗产保护领域对国际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3]
同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文化工程性概念,为新时代中华民族象征性标识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实施方案。不论是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还是文化旅游政策,长江文化的整体性价值所涵盖的内容及其高度,远远超出了任何单一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和特色文化活动的简单相加。如果单纯地评价长江文化遗产和文化活动中的任何一项,其价值均难以达到中华民族典型标识的标准,但通过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整合,即成为《文化线路宪章》所说的:“拥有动态的特定历史功能,其形成源于人类的迁徙和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地区或洲际间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等多维度的持续交流,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促进了相关文化的相互滋养并通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体现,文化线路把相关的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整合为统一的动态系统” 。这种具有大尺度、跨时空、综合性、动态性的超级文化空间,提供了新时代实现民族国家文化标识建设的新工具。
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价值,在于它承载了其他大遗址、旅游景区和线路遗产等无可比拟的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艺术、民族和国家等方面的相关信息,在民族、国家、地区和洲际间的动态文化对话和动态性变迁中,充分展示人类文明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欧洲委员会提议设立的“文化线路”——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之路(Routes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即是为欧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寻求和建立欧洲文化认同之路,它与中国的长江、黄河、长城、长征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一样,能够把民族和国家放到一个准确的空间和历史范畴来表述,对族群寻求共同历史记忆、延续地方和民族历史文脉、彰显族群身份具有独特的作用,它对不同区域的文化整合、民族情感的追忆与唤醒、国民身份认同与国际文化交往等都具有正向影响和积极的功能作用。“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和建设,为不同的地域性文化认同圈提供了一个统一而宏大的文化符号,它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包容性,将沿线众多文化子系统中的文化符号(即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地联结起来,使地域性文化符号在不改变其文化特色(文化基因)的前提下被纳入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文化遗产体系之中。”[3]这就是国家文化公园独特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