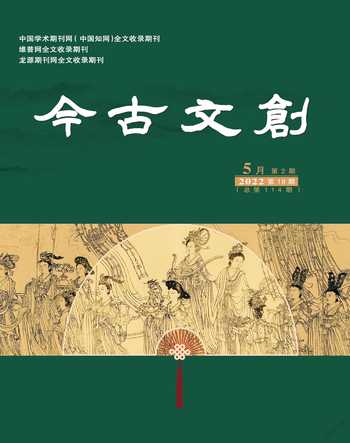民间舞蹈的创作思辨
2022-05-19陈笑嫣
【摘要】蒙古族舞蹈的创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七十余载的发展,回顾蒙古族舞蹈在这七十余年间的历程,其创作风格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那便是深扎创作的传统本真阶段,整齐划一的昂扬挺拔阶段以及解放肢体关注个体阶段。将视角放在当下,其整体还是传统的蒙古族舞蹈创作类型以及从内容到形式层面都不断寻求创新的创造性类型。了解过去与当下的蒙古族舞蹈的创作特征是为了更好地寻找未来的创作发展道路。这其中不乏去寻找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寻找化繁为简的身体文化回溯,以及全球在地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回归传统后寻找民族舞编创的现代性意义,在中国语境中塑造中国文化形象。
【关键词】蒙古族舞蹈;文化记忆;传统;创造性;历时性;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8-009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8.030
蒙古族舞蹈创作在民族舞蹈的创作中是如何在“围墙”之困下“走出去”,在语汇层面如何实现中国新表达,在情感层面如何实现超时空共情,在文化符号下如何实现跨领域认可都需要蒙古族舞蹈去不断创新与发现。这需要从蒙古族舞蹈的创作发展历程以及当下创作特征当中去寻找、研究与探索。
一、文化与记忆:蒙古族舞蹈的创作历程
学史以明鉴。从历时性的角度了解蒙古族舞台舞蹈的创作发展历程,更有利于在共时性下反思今天的蒙古族舞台舞蹈的创作发展问题。纵向看新中国蒙古族舞蹈的创作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阶段。
(一)深扎创作、传统本真
蒙古族舞台舞蹈创作的发展可以追溯至1947年,贾作光老师的创作理念深受吴晓邦先生的影响,他强调要创作首先要到牧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体验,沉浸到蒙古族原生舞蹈的风格特征与文化传统中去。他在日常生活中提取动作素材运用到蒙古族舞台舞蹈的创作之中。这一时期产生的大量蒙古族舞台舞蹈作品如《牧马舞》《雁舞》《鄂尔多斯舞》《盅碗舞》都有共同的特征,那便是以生活为本、传统本真,生动再现蒙古族人民的朴素生活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以《鄂尔多斯舞》为例,作品表现了鄂尔多斯人民在解放后以乐观主义精神去热爱劳动、热爱家乡、努力创造新生活。作品在第一段的慢板昂首挺胸,以“迈步前点甩手”出场,之后出现的“下腰甩手”“叉腰揉肩”“单腿板腰”等动作展现出蒙古族男性刚健雄浑的体魄以及粗犷豪放的性格魅力。第二段的小快板女演员以日常生活中的“挤奶”“梳辫”等动作配合硬肩、柔臂、翻腕突出蒙古族女子活泼聪颖、端庄秀丽的形象。之后男女对舞,在节奏和空间上夸张放大动作舞姿与队形,刚柔相济,形成了最终的视觉形象文本。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蒙古族舞台舞蹈创作虽取材于生活但却高于生活,面向生活的同时也不忘传统,立足于人民的同时更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和观赏性。
(二)整齐划一、昂扬挺拔
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蒙古族舞蹈创作在1966至1977年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强调动作的整齐划一,风格的昂扬挺拔。这一时期的蒙古族舞台舞蹈创作体现了这一时代烙印下的审美观念。代表性作品如《草原女民兵》《红雁高飞》《牧民见到了毛主席》《接过套马杆》等等。从《草原女民兵》中可以看出,這一时期的舞台蒙古族舞蹈创作在动作语言风格上,实现了当地民间舞蹈风格与芭蕾审美的融合。以芭蕾中开、绷、直、立的审美体现主人公形象;以芭蕾的高空旋转、大跳等技术体现人物的精神面貌与必胜决心;以独特鲜明,富有风格性的蒙古族舞蹈中的勒马硬腕、硬肩、碎抖肩等富有力量的动作表现战时国家运动员。作品中有勒马手立掌马步结合立脚掌九十度勾绷脚抬腿、以及弓步扬手的动作塑造了昂扬挺拔、英姿飒爽的女民兵形象。由作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蒙古族舞台创作作品结合“洋为中用”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精致化、生活美的审美倾向中,在整齐划一、昂扬挺拔的动作风格中体现这一时代下的蒙古族人民精神风貌。
(三)解放肢体、关注个体
蒙古族舞台舞蹈创作从1978年至今进入多元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的春风为舞蹈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进入新世纪后,受到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舞蹈创作注重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生活与传统,表达个性的同时也强调动作的本体意识与身体语言的觉醒。首先在动作层面上,这一时期的舞蹈创作向着蒙古族舞蹈动作语言的内部动律特征去挖掘创造,例如《奔腾》在舞蹈语汇上不局限于传统的动作风格要求,而是放松手腕、肩肘,不以特定经典动作来对人物进行定位,而是以人的运动状态与内在气质反身定义舞蹈人物形象的民族属性。其次在身体姿态上,《奔腾》放松了臂膀,强调自然顺畅的线条,突破了以往的蒙古族舞蹈的定势和形态,为作品注入了时代的气息,体现了马背上的人民对待生活的热情与积极向上的精神。这一时期同样涌现了其他经典蒙古族舞蹈作品,例如《出走》《鄂尔多斯》《盛装舞》等等。它们呈现出的共同特点便是从动作本体出发,不局限于既有蒙古族舞蹈语汇而是大胆创新,根据个体的理解去创新创造,体现出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审美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二、原真与创造:蒙古族舞蹈的创作方向
从蒙古族舞蹈创作发展历程来看蒙古族舞台舞蹈创作有两大创作方向,一是保留典型性,另一是启发创造性。前者在寻找“传统”的道路上不断深入,后者在情感归属上表达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和思想认知。
(一)保留典型性——寻找“传统”
蒙古族舞台舞蹈的创作方向之一是保留既有的蒙古族舞蹈教材语汇的典型性,寻找“传统”。这里的“传统”是编导们基于内蒙古人民的生活经验与传统文化,提炼转化出的具有代表性与程式性的,反映民族精神风貌的舞蹈语汇与舞蹈风格。保留“传统”风格的蒙古族舞蹈不胜枚举,《鄂尔多斯舞》《盅碗舞》《筷子舞》《牧马舞》《心中的歌》《蒙古人》《顶碗舞》《盛装舞》等等。以《盛装舞》为例,编导运用了萨吾尔登的元素,强化了代表性动律,放慢了节奏,与脚步的质感相契合,重构了具有鲜明个人语言风格的动作语言美感,表现了蒙古族人民的肆意洒脱以及不失热烈的自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创造的集体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寄托,渗透在中国传统艺术继承者和创作者的血液中,影响艺术创作者的精神旨归与文化胸襟。所以编导也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对待传统文化,需要明白传统与现实是一条不可割裂的河流,真正的传统就在现实的人生中。在传统风格中,在典型动作中体现着这一民族的民族审美旨趣和民族文化内涵。需知“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二)启发创造性——情感归属
除去典型化的蒙古族舞蹈创作,另一创作方向便是启发创造性,这类型的蒙古族舞蹈不囿于既有的蒙古族舞蹈语汇,而是在动作中融入多种元素,思想上启发创造,突破传统的歌颂式表达,展现个人思想情感。新时代下社会快速发展,在时代发展的气息下“人文关怀”的潮流也更加凸显。传统的民族民间舞在继承与发展中,在动作语言的风格性、艺术形象的独特性等方面,逐渐建构起自身的审美特色与风格,并追求深刻的人为内涵,展现了更富有时代感与人民性的审美现代特征。它们无论是立意思想、动作语汇、编创技巧等方面,都在不断地发展中寻求着突破。这类型的舞蹈作品在新世纪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老雁》《独树》《长调》《额尔古纳河》《独树》《我们看见了鸿雁》《国家的孩子》等作品,都在内容与形式层面都不断寻求着创新创造,熔铸着编导个人的情感归属与时代思考。《老雁》是编导在感受深厚草原文化后,创作出的新维度民族舞作品,它在有限的空间中寻求发展。一人一凳突破了以往首先想到辽阔草原、万马奔腾的固有印象,这里“老雁”背后的翅膀,或是青春时的梦想,或是对另一个“雁”的思念,又或是已不能起飞的“老翅”,无限的遐想熔铸在这一小方凳之中。由此可见,蒙古族舞蹈创作不仅仅是停留在一招一式的动作风格和服饰道具之中,更要活用素材,以少言多,在表达中传递着人生、生命、成长的经验。
三、继承与创新:蒙古族舞蹈的发展蠡测
纵观国内传统舞蹈的发展史,民族舞蹈创新是必然趋势,蒙古族舞蹈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新时代下蒙古族舞蹈创作受诸多外在与内在因素的影响,无论如何创新,未来蒙古族舞蹈的创作发展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一)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
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是北京舞蹈学院王玫老师提出的一种舞蹈艺术编创方法,它不失为民族民间舞蹈当代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一观念的提出是基于民族民间舞的创作困境,尽管有一些民族民间舞蹈有意识地借鉴或贴近现代风格,但仍在传统的桎梏内。基于这样的现状,王玫老师提出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相对于“传统”它更加关注“现代性”,在不同的语境下对“传统”也有不同的解读。这一观念同样适用于蒙古族舞台舞蹈的创作。如何赋予传统的蒙古族舞蹈以“现代性”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蒙古族舞蹈的特点是表现风格热情奔放,舞蹈节奏轻快明亮,动作多有抖肩、翻腕,蕴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现代性编创需要在动作语汇上“去形留律”,在保有原有动律风格的基础上去寻找动作的多种形态。在内容方面需要去寻找这一民族的精神品质,将其与当下社会、时代、人民的思想相契合,把握时代的脉搏,既有民族的精神内核,又有时代的现代性思考,从而引起观者情感的共鸣。但在具体实践创作中,如何去实现是需要不断思考与尝试的。
(二)化繁为简的文化身体回溯
蒙古族舞蹈有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动作元素,在惯性的创作观念上,多是去思考如何丰富作品形式,增强视觉观感,表达编导的思想情感。除此之外,也有化繁为简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在简单的元素或是动律中去不断变化时间、空间、力量,在有限中超越无限,实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的艺术效果。《希格希日——独树》仅用“溜达”构成一部作品,在2/4拍的节奏中实现身体的变化,双脚不同方位与节奏地走以及双人接触三只脚的行走包括一人拖拽地走,不同的走的方式并不会引起视觉疲劳,并且为作品整体基调和风格服务,结合音乐体现了有意味的形式。编导纯熟于动作规律却又打破以往风格,精准揣摩每一次变化与小细节背后的文化隐喻,化繁为简,放弃了高难度技术动态,将真正的视觉技术埋伏于动觉空间之中。
王玫老师在其创作手记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不是豪华,而是朴素;不是繁复,而是单一;不是用力,而是松弛;不是艳丽,而是自然。”或许只有那些深明此道,以退为进,以回溯的方式而同步于时代,化繁为简,在极简的身体语言中传递出有意味的思想內涵与文化基因,留白却又不白,正如宗白华老师所说:“中国画留白而不白,正是它的妙处。” ①
(三)全球在地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在全球在地化的今天,现代艺术潮流是国际性的,为不同民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开阔的国际视野,但也带来一个危险倾向,那便是民族性的淡化乃至消失。因此对于蒙古族舞蹈未来发展方向,也可将其民族文化传统与国际视野有机融合。民族性作为一个民族的根本特性,也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同时,彰显着独特的个性。蒙古族舞蹈的艺术语言背后有其民族文化内涵,它的站姿、坐姿强调重心后倾、动作风格沉稳有力,似是悠闲地坐在马背上,这一动作语汇很好地体现了蒙古族舞蹈的风格特征,也与其奔放豪迈的性格息息相关。从作品来说蒙古族舞蹈创作可以在思想内涵的表达上实现世界性共鸣,在对生命的诉说、对家乡的怀念、对故土的思念表达中是没有地域限制的。在这一维度下,突破蒙古族舞蹈创作的民族性界限实现世界性共鸣。
《长调》作为表达对家人、故乡、美好山河怀念的作品,游牧民族的生活居无定所、长年漂泊,这一背景使得他们对家有着天然的渴望与向往。编导设计了圆场“之”字形的运动路线,步伐碎而小,保持平稳的基础上步伐迅速,展现出草原儿女的稳重气质与开阔胸襟。舞者手指、手腕、手臂、肩部等关节独特细碎灵动节奏的处理方式,让观众好似看到了孤雁飞过蓝天,塑造了“雁孤飞,人独坐,看却一秋空过”的画面。
《长调》在保留民族特性的基础上表达了共通的情感,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并且真正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结合的艺术作品,是能实现跨领域认可、跨地域共识与跨时代共鸣的。对不同民族艺术的交流融合,仍需要明白既吸收外来艺术的精华,又与世界艺术同步发展,同时突出民族的艺术传统和特质。
四、结语
蒙古族舞蹈的未来创作可以在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上、在化繁为简的文化身体回溯中、在全球在地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中,把握自身的尺度,在本土境遇中寻找他者眼光与普遍尺度,实现中国民族精神的无声绽放,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国族认同。但这其中“度”的把握是需要不断地去探索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艺术审美的奥秘要经历时间的洗礼。但不论如何创新,一言以蔽之,都要让艺术和艺术技术理论得以回归它原本的学术品格。这就需要文艺工作者要牢记自己的责任与担当,不因追赶时代热潮而放弃对艺术品质的追求,要有“小火慢炖”的工匠精神。捧一把中国美学精神的沃土,不畏浮云遮望眼,去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②的蒙古族舞蹈作品。
注释:
①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②赵琳:《民族歌剧〈沂蒙山〉形成很强的震撼力,引来知名艺术家赞许共鸣》,《大众日报》2019年5月25日。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吕艺生.中国古典舞美学原理求索[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3]毛毳.民间舞蹈创作与原真性——新中国蒙古族舞蹈创作七十年的形象、观念与美学[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1,(5).
[4]陈琳琳.贾作光蒙古族舞蹈创作及其审美特征[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8,(2).
[5]仝妍.新中国民族民间舞审美范式的构建——兼论贾作光蒙古族舞蹈的“规范化”[J].内蒙古艺术,2018,(4).
[6]易雅雯.浅析蒙古族舞蹈的艺术风格特征——以剧目《长调》为例[J].明日风尚,2021,(1).
作者简介:
陈笑嫣,女,汉族,四川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舞蹈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