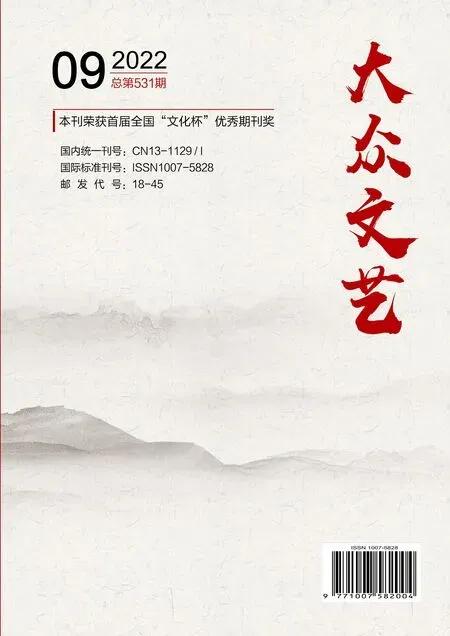我国近代女导演纪录片创作中的“她力量”
2022-05-17于汶灵
于汶灵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江苏苏州 215124)
一、中国新纪录片运动
1.独特的背景优势
纪录片作为一种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深入现实生活,记录着时代的变化。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法国女性主义是世界女性运动的第一声,它在法国大革命中发展起来,参加运动的妇女数量非常可观。紧接着,英国以及北欧部分国家的女性参政热潮又被重新燃起,继而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又蓬勃发展,最后遍及西方社会。在妇女解放运动清晰的发展脉络和理论支撑下,西方女性导演创作的纪录片大多与女性解放有关,而中国女导演的创作情况却与之完全不同。我国对近代妇女的解放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戊戌变法后“不缠足”“办女学”,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男女同校”“自由恋爱”“社交公开”“婚姻自主”等等,是中国女性走出封建社会“大门”的第一步。真正迎来发展的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新社会开始重新定义女性角色,通过动员农村女性参与农业生产,城市女性进入工厂做工的方式保障女性工作权利,改善妇女的地位。后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相结合,大力倡导全党全社会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前进方向,对于大力传播先进思想文化,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全面促进妇女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因此我国妇女的解放身份主要是被国家、政权自上而下赋予的,这和西方等发达国家妇女通过自下而上地对社会男性统治者进行抗议,由里而外地对社会性别文明进行批评,最终身份地位逐渐上升的模式有所不同。这也是中国女性的独特环境优势——一夜之间性别平等从观念意识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郑重保证,将实现男女平等当作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前进的一个基本国策,而90年代正好也是中国女性纪录片编导们开始制作纪录片的时期。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纪录片是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与社会历史背景中,不断实践的重要成果。
2.新纪录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第一个开始进行独立纪录片制作的女编导是刘晓津,受吴文光的《流量北京》等影片的影响,在云南电视台工作的刘晓津找到了自己创作的出口——真实。一九九〇年她与好友李晓明自费摄制了《我国西南当代画家五人集》纪录片,但中途李晓明放弃,最后由刘晓津一人完成。影片中大量运用了纪实手段,充分体现了她当时的创作理念。虽然这个片子仍然保持了电视台制作的特色,但这是刘晓津对电视台专题片“反叛”精神的第一次实践。一九九四年她来到了北京,并试图用一部家用摄像机来制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这便是后来的《寻找眼镜蛇》,它不仅记录了在北京工作的女艺人的日常生活,更是体现了几乎所有中国女人面对“婚姻”和“家庭”选择两难的困境。刘晓津自己也认为,《寻找眼镜蛇》里每一位女性的身上都有自己在当时存在的心理矛盾,而拍摄这部影片也给予了她生活上莫大的启示。
1997年,由李红执导的《回到凤凰桥》上映。该片被看作是我国女性纪录片的成熟作品,讲述了四个来自安徽凤凰桥的女孩去北京务工的故事,成为最早将视线聚焦于社会底层女性的作品。与1993年由男性导演陈晓卿执导的《远在北京的家》中积极参与的模式不同,李红在《回到凤凰桥》中更偏向“隐匿”。自始至终没有记者和编导露脸,只有声音入画,全程没有人为的干预被摄人物生活。据说在该片的拍摄过程中,近距离的细节和生动的谈话都是李红和姑娘们同睡一床的时候,用小型摄像机搁在被窝垛上拍摄的。
同年,由冯艳导演的《长江之梦》入围了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的亚洲新浪潮单元。该片讲述了长江三峡的两个村落由于水库的动工而失去家园,当地人民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作为环境经济学博士,冯艳对三峡水库的动工十分敏感,便一头扎了进去。她的纪录片中不仅有当地美丽的自然环境,也有个人命运的波折纠葛,有历史的纵深感,也有人物的万般无奈感,都令人感慨唏嘘。
1999年,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季丹结束了她的西藏纪录片《老人们》《贡布的快乐生命》。季丹的作品大部分聚焦群众的真实生活,她擅长从不同的角度、微小的细节去构造生活的氛围。因此她的纪录片也指向了一类纪录片的美学,那就是尽可能地展现出生活的味道。
1999年,杨荔钠执导个人首部纪录片《老头》,把镜头对向北京城内和她住在一个小区的没事儿就坐在大树底下聊天的老头们。有趣的是在最开始杨荔钠请来了电视台的专业摄像、录音团队,但后来发现他们的存在会让老头们特别不自然,于是杨荔钠解散了专业团队,自己拿起家里人资助她的DV,跟老头们建立了和谐融洽的亲密关系。2000年,杨荔钠执导了纪录片《家庭录像带》,从名字我们就可以得知这次她把镜头转向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希望能够找出她小时候的问题的答案:父母为什么离婚?然而这错杂的家庭矛盾和情感纠葛,让母亲和弟弟不愿说出背后家庭暴力的真相。一开始杨荔钠在镜头后还是很乐观的,可是到最后她也忍不住声泪俱下。其实不止《家庭录像带》,唐丹鸿的《夜莺没有真正的歌喉》、章梦奇的《自画像及和母亲对话》与它们都是同类型影片。DV摄像机就像女导演们手中的一把手术刀,一步步剖开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自我治愈、或自我堕落、或自我麻痹。或许到影片的结束,她们都不能看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或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与自我和解,解放了心中那块无人踏足的禁区。
吕新雨曾在她的论文《在乌托邦的废墟上——新纪录运动在我国》中,追述记录运动在80年代的“文化精神血缘”,“针对这批人来讲,80时代是一个青春时期的躁动,表现形式其中一点也都是‘理想主义者的远游’——这是吴文光的说法,他去的是新疆。而更多的人去的是藏区。”季丹正是带着这个理念奔赴藏区拍纪实,刘晓津、季丹、李红、冯艳等均为八〇年高校毕业生,每个年轻女性纪实编导所关心的主题以及摄制的创作都有一个“不约而同”,正是对民间社会的转变,把眼光放低,把拍摄者的姿势放低,把态度放低
二、女导演被“本质主义”绑架的创作特点
在我国80年代末的新纪录片运动中,国内女性导演的纪录片作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吴文光曾说道:“我始终能感觉到,一个极其私密的女性视角闯入了纪录影像世界。”在此处,吴文光将现代女性导演的创作特点叫作“女性视角”。这对曾经的纪录片创作领域来说,是陌生的、新奇的,也是具有颠覆性力量的。国内现有的诸多理论会把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性导演的创作特点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女导演情感细腻,更擅长拍摄一些私密的话题;二是女导演性情温柔善良,更容易走进被拍摄者的心灵;三是DV摄像机的出现是女性进入纪录片创作领域的关键推动因素。但是这些总结,基本上都是带着本质主义的偏见。女导演温柔、细腻、可亲这些特点,既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与自身的经历和成长环境有关,抑或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这些不是女性的专属,许多男性导演身上也有这样的特点,同理很多女性身上并没有这样的表现。DV摄像机小巧轻快的确给女性导演带来了便利,为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但这种便利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人类的便利。因此“女性视角”不单单是专属于女人的视角,男性编导拍摄男性被摄者、男性编导拍摄女性被摄者,以及女性编导拍摄男性被摄者和女性编导拍摄女性被摄者,都有可能采用“女性视角”。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生物学理论能够证明这种视角和生理特征相关,因此将这两者捆绑在一起,根本上是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
西方妇女纪录片编导从事创造的主要途径,和中国国内女性纪录片编导方式判然不同。西方妇女编导选择从事纪录片写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践行女性主义的影视学说,以抗议父权制话语方式中通过虚构影片对女性主义所实行的“他者”意识建构。面对着当时西方影视剧中普遍存在地对妇女外貌特征的刻板化再现、把妇女当成“凝视”的客体并对其实施了色情化描写、对二性出现比例失调现象、脱离了妇女的现实生存经验等问题,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作品《第二性》中写道:“我们将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女人,给我们的全部处境以应有的重视。”而纪录片的存在刚好满足了西方女性的需求。真实性作为纪录片的基础属性,其中会展现女性群体尤其是社会边缘女性的真实生活,所以西方许多女性导演认为这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创作表达方式。国内女导演进入纪录片创作的背景和西方完全不同,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社会女性的“美”开始重新被定义,新社会赋予了女性更多的权力。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下,中共动员女子参与生产生活,展现出了妇女在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国内外学界对于女性纪录片没有确切的概念和定义,但我相信它所涵盖的不仅仅是以女性导演或者以女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它更是表现妇女个人或群体的生存状况,关心妇女生活与发展命运,表现妇女群众的愿望与需求,使人反思的影视作品。而所谓女性意识,指的是女性可以通过独立自觉、有意识的承担和实现自己的生命义务、社会责任而且清醒的认识自身特征和内涵,并以自己独特意识来参加和影响整个社会,最终实现自我的价值。当然我国也有许多优秀的男性导演拍摄女性纪录片,例如郭柯执导的纪录片《二十二》曾获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釜山国际电影节提名为最佳纪录片奖等等。《二十二》讲述了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22名“慰安妇”,用口述的方式串联起她们的生活状况,这部影片也成为中国大陆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
三、新媒体时代"美丽神话"的塑造者
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女性赋权和女性发声,同时也带来了社会中性别文化传播的复杂化。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我们很容易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内容:“妆前无人问津,妆后人人搭讪”;减肥成功就可以完美逆袭,让男神倒追自己;美妆博主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变美不仅能够得到甜蜜爱情,还能获得诸多便利,最终促进事业的成功。“漂亮”这个词越来越被提升到重要的地位上。《媒介与女性蓝皮书: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报告(2020)》中这么写道:现代传媒中对女人形象的描述往往存在着狭隘的观念,女人被部分媒体灌输着极为可怕和粗鄙的价值观念:一个女人的价值取决于她的美貌、性感,但却不在于其才华和领导力。现代媒体制造出“美丽神话”,通过作为“意见领袖”的各个网络博主来制造和传播“美丽神话”的论据和故事,让女性相信美丽是女人的必备品质。“我们看到都是年轻、漂亮、苗条的女性……好像一个肥胖、普通的女性没有权利爱和被爱”由媒体制造、生产出的“美的标准”,对大部分样貌普通的女性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压迫和“变形”的追求。
随着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多,女性地位逐步提高,女性意识逐渐苏醒。越来越多的有经济实力的女性不仅为了自身的“保值升值”消费,还担起了全家的采购大权,成为市场发展中强劲的主力军。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女性消费者有4.8亿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50岁年龄段的女性,占总人口数的21%。据全国妇联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半边天”力量进一步彰显。78%的已婚女性会为家庭平日开销和购买衣服做出决定;23%的已婚女性表示能在购买房屋、车辆、奢侈品等大件商品时独立做出决定,剩余77%的女性表示会与配偶商量后再决定,但是她们的喜恶态度会对最终结果起重要影响。阿里数据也显示,每年电商平台消费额的70%都是由女性贡献的,马云自己也在首届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上调侃:“他们都说马云是被妇女们包装起来的。”然而这一点也被资本所洞察和利用,他们对女性所追求的独立自主价值的实现路径,由个体奋斗和群体联合统统简化为消费,用消费主义对女性主义进行了再一次的消解。“美丽神话”把女性严严实实的包围起来,鼓动她们盲目投身"美丽消费"的热潮,在情绪的狂欢下缺乏理性的判断,成为人云亦云的附庸。同时部分媒体还以“检验真爱”的名义说服女性让男性为其消费,但这本质上依然是有经济实力的男性掌握着主导权,而收礼物的女性则为被动的客体地位。
这样的“美丽神话”其实是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重新把女性推到了被凝视者的位置上。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凝视是一种作为权力的观看,凌驾在被凝视者之上。“她们将身体看作是一种资源,过度突出其功能性,通过对外表的过度追求来满足相应的社会规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追求时尚成为社会女性进步的外驱力之一。美丽作为一种资源,有其市场,“美女经济”油然而生。但资本下场,媒体由最初旁观者、描述者的身份转变为如今的参与者,甚至是“美”的规则制定者和缔造者。“美女经济”逐渐脱离最初的解放女性的目的,反而成为束缚女性的新规则。现代资本塑造各种具体的“美女”形象,并通过不同的传播媒介广泛地向现实社会营造逐美思潮,而部分女性由于其自身与传媒所塑造的“美女”形象有差距,出于对美貌的强烈渴望,开始过度注重浅表的外在美,反而忽视和削减了内在审美标准,将价值判断与时尚追求与资本所营造的审美规范同步,然而这一切并非女性理想的追求,反而可能会对女性造成伤害。
我们现在生活在“她世纪”的现代传媒时代,传媒塑造着时代标准,但更肩负着培养媒介消费观和消费意识的重要社会责任。媒介是工具,这就要求传媒人应更加珍视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思想,通过新传媒重塑时代女性自身的完整意识形象,全面且真实地记录当今女性的生存状况。我们提倡女性朋友们忠于自我,认识自身的优势特长,并抱有自信心。
总的来说,女性纪录片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趋势。女导演的作品数量也日渐增多,与女性有关的主题也更加全面和深入,独特的、敢于突破社会规范的女性形象也应运而生。展望未来,媒体深刻的影响女性群体生活。我们要积极提高广大妇女群众的媒介素质,积极引导媒体宣传先进性别文明,逐步完善女性主义理论,切实唤起和坚守妇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