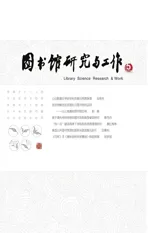《四库》本《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校勘探微
2022-05-10徐梦瑶
徐梦瑶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曲阜 273100)
1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概述
胡安国《春秋传》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据《元史·选举制》,元延佑二年(1315年)定科举新制,胡《传》被立为学官,成为开科取士的标准,尊崇胡《传》成为元儒研治《春秋》学时的一种风尚。元末学者汪克宽①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②》(以下简称《纂疏》)以阐发胡氏之说为主,兼采诸家传注,疏于其下,是研究胡《传》的重要资料。汪氏自称:“《春秋》传注无虑数十百家。至子程子始求天理于遗经,作传以明圣人之志,俾大义炳如日星,微辞奥旨,了然若视诸掌。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之说,著书十余万言,然后圣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于后世……元统甲戌(1334),教导郡斋,讲劘之暇,因阅诸家传注,采摭精语疏于其下,日积月羡,会萃成编。”[1]8此书始撰于元统二年(1334年),前附至元四年(1338年)汪泽民③序、至正元年(1341年)虞集④序,故汪克宽历经七年定著此书。汪克宽在自序中明确了编纂此书的目的:“详注诸国纪年谥号,而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而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传》之阙遗,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庶几初学者得之,不待遍考全书,而辞义粲然,亦不为无助也。”[1]9由此可知,汪氏详注纪年、谥号等客观事实,列经文同异,于胡《传》基础上,取诸家学说之所长,以使后学明其历代见解,考究经文。
关于其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谓其“然能于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于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明永乐中,胡广等修《五经大全》……乃全剿克宽此书,原本俱在,可以一一互勘也”[2]。此书援引丰富,内容详尽,是研究胡说必不可少的资料,亦为后修《五经大全》提供依据。汪泽民序曰:“遍取诸说之可以发明胡氏者,疏以成编。观其取舍之严,根究之极,明永乐亦精于治经者欤?尝病世之学者,剿尘腐,矜新奇,窃附作者之列奚可哉?德辅学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思欲羽翼乎?经传可尚也。”[1]2虞集又序曰:“能取胡氏之说,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类例之始,发而尽究其终,谓之《春秋纂疏》。”[1]3其门人吴国英称:“先生手编《胡氏传纂疏》,虽一以胡氏为主,而凡三传注疏之要语暨诸儒传注之精义悉附著之,且《胡传》博极群经子史,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据之所自与音读之所当。先生详究精考,一一附注。于是读是经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传之意,而且趋流寻源,亦可识圣人作经之大旨矣。”又称:“不惟诸生获春秋经学之阶梯而凡学者开卷之余,不待旁通远证,事义咸在。是则先生纂疏之述,有功于遗经,而有助于后学,岂曰小补之哉?”[3]由此观之,此书详究精考,参酌众说,可窥胡《传》一家之旨,学界对其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故此书在《春秋》学史上尤其在对胡《传》的研究中有独特地位。
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学术界却至今没有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本文探讨《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的版本与文字校勘问题,是对该书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
2 《四库全书》本及底本来源
《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小注双行,字数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鱼尾上题“钦定四库全书”,鱼尾下题书名、卷次、叶次。卷首将汪泽民序和虞集序合并,首行顶格题“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原序”,序文顶格。序后次有先儒格言、凡例及汪克宽识语、引用姓氏、卷首(《春秋胡氏传》序、进表、述纲领)。首卷首行顶格题“钦定四库全书”,次行低一格题“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一”,尾题同,第三行低十三格题“元汪克宽撰”,春秋白文顶格起,传文低一格以示区别。
《春秋胡氏传纂疏》⑤的最早刻本为元至正八年(1348年)建安刘叔简日新堂⑥刻本(以下简称“元建安本”)。今著录为元建安本者有七,经比对,版式行款皆同,实为同版。其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本(A01146),残存14卷,存卷1—6,卷9—14,卷19—20。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同。“疏”字以墨盖子白文别出,版心小黑口,双鱼尾(鱼尾相随),中间记书名及卷次,下方书叶次。首卷首行顶格题“春秋胡氏传纂疏第一”,卷末尾题“春秋卷第一”,次行低十格题“新安汪克宽学”。卷首汪泽民序有缺损,凡例后镌有“建安刘叔简刊于日新堂”牌记,先儒格言后有吴国英《跋》,吴《跋》落款为“至正八年(1348年)岁在戊子正月人日,紫阳吴国英再拜书”。其余卷首内容与《四库》本同。其二为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本。其三为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其四为京都府立综合资料馆藏本。其五为尊经阁文库藏本。其六为2007年北京德宝拍卖有限公司藏本。其七为2018年夏季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藏本。关于是本原委,汪克宽《环谷集·答刘叔简启》中书曰:“愿安承教,用底成功,守约信于末域,有如皦日;寄抄誊之善本,期以明年。”[4]表明汪氏与刘叔简定有刻书契约,并望双方信守其约,吴《跋》及“建安刘叔简刊于日新堂”牌记可证双方遵守约定,完成了此书的刻梓,即至正八年(1348年)戊子,此书才得以付梓版行,故此本当为是书初刻。
关于《四库》本底本来源,据《四库全书总目》,《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为“浙江吴玉墀⑦家藏本”。考之《四库采进书目》,仅有浙江吴玉墀家进呈过此书,著录:“《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元汪克宽著,二十九本。”[5]85又检《四库采进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载曰:“《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天一阁藏刊本),元新安汪克宽撰。”[5]242更检《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春秋类》著录曰:“《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元汪克宽撰。版本失载。薛编天一阁进呈书目据浙江书录补。”[6]由此可知,浙江吴玉墀所呈《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可能是天一阁藏刊本。今未见天一阁藏刊本,但此书版本可知者有二,一是初刻元建安本,二是《四库》本,故吴玉墀藏本与天一阁藏刊本皆渊源于元建安本,底本当是。
3 比勘
今将《四库》本与元建安本(今国家图书馆藏本)⑧文本内容比勘,《四库》本《纂疏》与元建安本异文有370多处,情况复杂,现通过校勘实例说明之。
首先是更改“华夷之辨”内容。“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儒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历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极力推崇,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严格执行,根深蒂固。清朝时,满族统治中原,汉族“攘夷”思想依旧存在,局部的反清活动时有发生,对政局的稳定并不友好。对此,清代统治者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多采取民族政策,文化上,《四库全书》的编纂亦是其中一项重大文化政策,不仅贯彻了清代民族和睦的理念,也对钳制汉族反抗意识有一定作用。胡《传》充满了浓厚的攘夷思想⑨,清代皇帝致力于消除“华夷”的心理隔阂,促进民族团结与统一,巩固统治。四库馆臣编修《四库》时不惜大量篡改原文,该书因其改动高达一百六十余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词语的改动。如“夷狄”改作“外冠”“远人”“外域”“蛮荆”等,具体改动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四库》本《纂疏》将带有“夷”字的词语进行大量改动,以此打压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宣扬满洲取得政权名正言顺,以稳固政局。

表1 “华夷之辨”词语改动详表
二是句子的改写。如《四库》本《纂疏·春秋胡氏传序》第六叶上半叶:“使祸乱相仍莫之”,元建安本作“使夷狄乱华莫之”。《四库》本《纂疏·春秋胡氏传序》第十四叶上半叶:“纵至四边纷扰”,元建安本作“纵至夷狄乱华”。《四库》本卷一第三十二叶下半叶:“中国而自外则外之”,元建安本作“中国而夷狄则狄之”。《四库》本卷一第三十三叶下半叶:“轻信外蕃”,元建安本作“夷狄豺狼”。《四库》本卷一第三十四叶上半叶:“盟逮戎世变之”,元建安本作“戎狄变夷之”。《四库》本卷一第三十四叶上半叶:“不罪乎戎也,其不罪戎者。”元建安本作“不罪夷狄也,不罪夷狄者”。《四库》本卷十一第二十八叶上半叶:“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桓公救中国。桓公救中国,而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元建安本与《公羊传》文本同曰:“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元本保留《春秋》中带有贬斥“夷狄”的句子,《四库》本对其径改,或有删漏,句意稍有不同,或感情色彩有异,与《春秋》之法谨严的一面相悖。类例颇多,不尽举。
三是大段的删减。如《四库》本卷二第四十五叶上半叶删掉了原本中:“啖氏曰:‘公羊曰:“其曰伐大之也,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书戎狄侵罚城入,岂皆是之乎?榖梁曰:“戎者,卫也。”若实卫伐改曰戎是为卫掩恶,何以惩劝乎?’”啖氏认为少数民族侵占中国一事有违“春秋大义”,应当批判,元本保留此说,不仅是遵从《春秋》之本意,亦是个人感情色彩与态度的体现。《四库》本此处大段删减,丝毫不见底本原貌,虽在版本学上犯了大忌,却正是清代统治者宣扬政权合法性,消弥汉人反清情绪的体现。
以上改动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四库》本在编纂时刻意消除旧有典籍中任何对少数民族特别是满族不利的因素,此书之删改颇为明显。
其次是异体字或通假字,如伯通霸、觉与斍、举与㪯、辞与辝、虫与䖝、鄱阳与番昜⑩等。由于时代相差,同字异体也是正常的。
最后是刊刻疏忽之误。《四库》本《纂疏》错误百出,讹误、倒文、衍文、脱文上百处,今通过校勘实例分析《四库》本的误脱衍倒等问题:
(1)《四库》本讹误。《四库》本讹误有八十余处,今举数例以明之。
①《四库》本卷一第二十一叶下半叶“五命以申天子之禁”之“申”字,元建安本作“备”。据《春秋谷梁传》:“为见天子之禁,故备之也。”[7]当以“备”为是。
②《四库》本卷一第二十四叶上半叶:“武帝令助谕南越,王还,又谕淮南王与之相结而还。”“王还”,元建安本作“助还”。按:此句源自《汉书·严助传》中严助谕意淮南王一事,先闽王伏辜,后南越被泽。大意为:汉武帝命令严助到南越传达天子旨意,严助回来后,又命令严助向南越王传达与其共同返回的旨意。“王还”文义不通,当依元建安本作“助还”。
③《四库》本卷五第十九叶上半叶:“委裘,若容衣,太子幼,未坐朝。”“太子”,元建安本作“天子”。按: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委裘,出自《吕氏春秋·察贤》:“天下之贤主,岂必苦形愁虑哉?执其要而已矣……故曰尧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8]指君主任贤举能。除此之外,“委裘”还有以下两种解释:一是旧谓帝位虚设,唯置故君遗衣于座而受朝。二指幼君在位。因幼君不胜礼服,坐朝则委裘于地。此句显为幼君在位之意。以等级论,古代天子和太子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天子是皇帝的称谓,太子是皇帝继承人的正式封号,二者不可混淆。“坐朝”意为君主临朝听政,太子虽为储君,却非正式君主,不能“坐朝”,当依元建安本作“天子”为是。
④《四库》本卷六第三十二叶下半叶“如商鞅立二丈之木于国都南门”之“二”字,元建安本作“三”,今检《史记·商君列传》原文为:“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之南门。”[9]当以元建安本作“三”,《四库》本作“二”乃形误。
(2)《四库》本倒文。《四库》本卷二第一叶上半叶:“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罪大矣,而夺取其土。”元建安本书曰:“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夺取其土。”按:成书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的《春秋大全》与元建安本同,又据其文义,“受之伐”中的“之”字作代词为宜,《四库》本作“伐之”,属于倒文,当据元建安本乙正为“之伐”。且《四库》本倒文的同时,误把“其罪”衍作“其罪大矣”。
(3)《四库》本衍文。《四库》本衍文三处(含上文提“其罪大矣”一例)。现举其余二例于其下。
①《四库》本卷一第三十二叶上半叶:“先君征戎而已,乃与之歃血约盟,可谓宜乎?”元建安本无“血约”。
②《四库》本卷六第四十四叶下半叶:“讨贼之责不在于鲁也。”元建安本无此句。
某些衍文不影响义,归入下文“妄加润色”部分。
(4)《四库》本脱文。《四库》本脱文近十处,今举三例以明之。
①《四库》本卷二第二十四叶下半叶:“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祭享之所”下,元建安本有“孔氏疏”三字。
②《四库》本卷二第三十七叶下半叶:“其不名公羊,谓微国也。”“微国也”下,元建安本有:“榖梁谓狄道也,按附庸及真夷狄皆有名况”十七字。
③《四库》本卷十二第四十一叶上半叶“《公羊传》”下,元建安本有“孰执之?楚子执。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二十一字。
(5)《四库》本妄加润色。《四库》本妄加润色三处,今列于其下。
①《四库》本卷一第六叶下半叶:“定之比宣,则又有间焉矣。”元建安本无“焉”。
②《四库》本卷一第十二叶上半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者也。”元建安本无“也”。
③《四库》本卷十三第二叶上半叶“或陆氏曰”,元建安本无“或”。
以上诸例,另有类似情况近十处,不尽举。此部分对原本文句稍加润色,虽不改文义,确是古籍整理所不允许的,当遵原本。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本虽讹误颇多,但亦有厘正之处,这是四库馆臣的校勘贡献,当加以珍惜。据统计,《四库》本校改元建安本二十余处,今举例说明之:
①《四库》本卷二第三十五叶上半叶:“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一”,元建安本作“二”。据《春秋公羊传》原文,当作“一”;且此句反映的是春秋战国的“媵妾制”,诸侯一聘九女,据史亦从“一”,当依《四库》本作“一”。
②《四库》本卷四第三十八叶下半叶:“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驰骋弋猎之娱。”元建安本无“百”。据《汉书》:“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10]当依《四库》本作“千八百国”为是。
③《四库》本卷十三第二叶上半叶:“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礼”,元建安本作“服”。检《左传》原文,当作“礼”。此处为馆臣改正底本之误。
当然,亦有元建安本与《四库》本各异且讹者,如《四库》本卷五第二十三叶上半叶:“杜氏曰:‘榖国在南乡宜阳县北。’”“宜阳”,元建安本作“统阳”。检之杜预注,作“筑阳”,又考之地理,亦从,故“宜阳”“统阳”皆误。这一情况显示了版本校勘的复杂性。
4 结语
综上,今存《纂疏》版本有二,元建安本刊刻时间最早,其后有出自元建安本的《四库》本,二本异文较多。《四库》本受政治因素影响,有目的地对建安本“华夷之辨”内容进行大量改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词语的改动,二是句子的改写,三是大段的删减。《四库》本讹误颇多,包括讹误、倒文、衍文、脱文、妄加润色,多被后世诟病,但对元建安本有所校正。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对《春秋》学研究和胡《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却没有一部校注本,无不是一缺憾。对于古籍整理工作者来说,如整理、研究《纂疏》一书,《四库》本是不能不校的。
注释:
① 汪克宽(1301—1369年),字德辅,号环谷,祁门县城南乡桃墅(今属塔坊)人。元末明初理学家、教育家。著有《环谷集》《诗集传音义会通》《程朱易传义音考》《春秋经传附录纂疏》等。
②“纂疏”是以某一经为主,荟萃诸家之言,并附以己意。“附录纂疏”就是“先把朱熹文集、语录中涉及经学的文字附录在相关经文之下,然后把诸儒之说之合于朱子的纂疏于附录之后,使后学能轻松得窥朱子与历代学者的见解与心得……元代新安经学家最擅长此种体例。详见刘成群:《“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经学为叙述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 年第 3 期。
③ 汪泽民(1285—1355年),字叔志,江西婺源人。宋端明殿学士汪藻七世孙。延佑五年(1318年)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累官至礼部尚书。汪泽民为汪克宽祖叔。
④ 虞集(1272-1348年),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祖籍成都仁寿(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临川崇仁(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人。元朝官员、学者、诗人,南宋左丞相虞允文五世孙。
⑤《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元本书名与汪泽民序称其《春秋胡氏传纂疏》,卷次部分皆称为“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二者皆可。且《四库全书》改书名情况较为常见,不足为疑。
⑥ 刘锦文,字叔简,元代建阳人。日新堂是刘锦文的书坊名,为建阳刻书名坊。自元迄明代中叶,刻书甚多,有宋王宗传《童溪先生易传》30卷,元赵汸《春秋金钥匙》1卷等数种。
⑦ 吴玉墀(1737—1817年),字兰陵,号山谷,清浙江钱塘人。清藏书家。乾隆庚寅(1770年)顺天举人,历官贵阳府长寨同知,家富藏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诏征遗书,他捡“绣谷亭”“瓶花斋”所藏图书进呈,计经部图书90余种,史部20余部,子部30余部,集部305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其家藏152种。
⑧ 元建安本《春秋胡氏传纂疏》卷9—10、卷19—20多有漫漶,暂不计入。
⑨ 胡安国处于两宋之交,目睹北方国土沦丧,徽、钦二宗被掳,有切肤之痛,故而对“攘夷”一义反复申述,这就招致了后来清朝统治者的厌恶。乾隆怒批道:“胡安国华夷之见,芥蒂于心……诚所谓胡说也。”并谕令纂修《御纂春秋直解》以驳斥胡传。相应地,馆臣对元明两代“《春秋》学”著作的褒贬,基本是根据对《春秋传》的依违来展开,不主胡传的学人著述得到馆臣认可,以胡传为皈依的书籍则多被贬入“存目”,态度鲜明而决绝。详见唐海韵:《论〈四库全书〉对清代民族和睦理念的贯彻与裨益》,《民族学刊》2021年第4期。
⑩ 鄱阳自夏至周均称“番邑”,秦称作“番县”,西汉改“番昜”,新莽时一度改称“乡亭”,东汉时期,将番昜左右加“阝”旁,遂有“鄱阳”之谓。尽管“番昜”这一名称只有在西汉时使用过,但它在后来还偶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