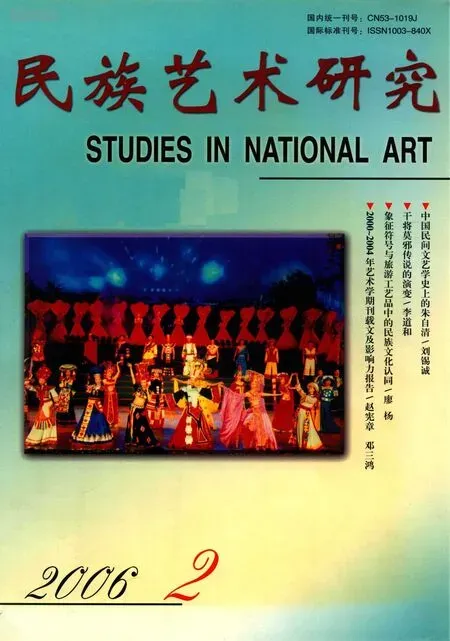跨界族群音乐
2022-05-06董宸
董 宸
一、概念的一条发展进路
(一)概念创建与学科溯源
跨界族群(或民族)①本关键词中对族群(或民族)的使用,仅为民族音乐学界目前在“跨界族群音乐”这一关键词中的一般性用法,不涉及各学科在各自研究语境中对民族和族群不同用法和内涵的辨析,后文同。音乐文化研究概念主要由中国民族音乐学界提出和发展,其中“跨界族群(或民族)”(也称“跨境民族”“跨国民族”)源于人类学/民族学界。通常英文翻译对应Cross-border/Trans-border ethnic group更为恰当,相对强调研究的区域性和民族的分布状况,而具体指向跨国民族时“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或“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②Gehan Wijeyewardene.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0.也有比较高的认可度,“因为这种说法兼顾了跨界民族的地域性、政治性和社会文化属性”③雷勇:《跨界民族问题研究:理论与现实》,《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美国学者伍德维尔对跨界族群④Doglas woodwell,Unwelcome Neighbors:Shared Ethni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During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terly,2004(48),pp.197-223.文中共使用了Trans-border ethnic Groups/ethnicity/groups三个英文主题词来表述其研究的跨界族群。的不同构成方式进行了阐释和界定,即同一个族群跨国存在的二元现象共有三个变量:两个国家都作为主体民族而存在的跨界民族;在一个国家是多数,在另一个国家则是少数;在两个国家都是少数。其阐释基本与国内主流学界对“跨界族群/民族”概念的界定类似,国内学界普遍认可也一直使用的是陈永龄提出的观点,即指“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但是就这一“基本保持按照历史源流和客观特征而非主观认同界定‘跨界民族’的传统”①梁茂春:《跨界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越边境的壮族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学者们莫衷一是。在研究过程中,对民族/族群的界定是文化性②Fredrik Barth,“Pathan Identity and its Maintenance”,in Fredrik Barth edit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1969.Little Brown and Company.作者认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国界两边的帕坦人,在生活方式上有较大差异,但他们认为自己有共同的祖先、相同的宗教习俗等、是一个共同的族群。的还是政治性③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作者认为同一族群在划归不同国家后,遵循不同的社会制度、族群政策和文化导向,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逐步演变成为不同的族群了。的,是由主观心理认同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认为民族可以具有共通客观文化特征,但缺乏共同体想象的人群不会是同一个民族。还是客观特征所决定等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因此,综观对跨界民族/族群研究界定的讨论,这一概念在既定的一般性界定的基础上,其观点内涵还需综合研究对象的社会语境和学者的专业语境。
中国学界对跨界民族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受到国际国内多方面条件限制,此后成果一直较少。直至21世纪以来,伴随国际交往环境的日益好转及我国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跨界族群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增长、提高。
而对跨界族群研究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形成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两种观点主要是在研究范畴界定“狭”与“广”的差异上。一种较为严格或者相对狭义的界定,认为“跨界民族限定于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割而居于毗邻国家的民族”⑤葛公尚:《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强调同一原生民族、传统聚居地即陆路边界的毗邻。另外一种则认为跨界民族除了狭义的限定,还应该通过更广义的界定拓宽研究范畴,例如“实界”和“虚界”的方式⑥严庆、周涵:《浅谈跨界民族的认同构成及调控》,《民族论坛》2012年第6期。,由此超越传统的陆路边界内涵,囊括更多的研究对象。
(二)概念的引入、发展
民族音乐学界对周边国家音乐文化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之后发展缓慢,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是世纪之交开始提出和拓展出来的新问题,在西方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领域至今尚无法找出较多的先例”⑦杨民康:《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民族音乐学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的研究范畴主要借鉴民族学界严格和相对狭义的概念,指的是“聚焦于内陆边界——国境线两侧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的跨地域比较研究,其外延分别涉及中国汉族传统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两个外部因素或学术范畴”⑧杨民康:《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第9页。,对应研究内容交叉比较多的是西方区域音乐研究中涉及跨国/跨民族界的范畴。随着研究的稳步发展,该研究议题热度不减,研究视野逐渐转向“广义”,例如有学者提出“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对应西方“移民音乐”及“离散人群音乐”的研究对象⑨郝苗苗:《后现代主义理论作用下的西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由此也逐渐将海陆边界、路带研究、移民音乐研究等纳入对象范畴当中。
基于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相关概念的溯源和梳理,发现该研究领域不是在核心概念上达成绝对共识,而是进入到对概念内涵和外延在有限的共识中进行相对性界定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在变量积累中,逐渐明晰提取一定的共性,然后以共思共存的关系继续发展、持续接纳的过程。
二、中西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两种实践动力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在“西方研究中,族群成员的越洋(国)流动是常态;而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定居则是常态。再者,在西方讨论音乐文化的混生及融合问题者较多;而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有关音乐文化的变异与交流的比较研究更为重要。”①杨民康:《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第9页。因此,中西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表现出两种实践动力。
(一)由外向内:西方学界由他文化回看自身
西方跨界族群研究从相对宏观的角度看起始于比较音乐学阶段,而后至民族音乐学的专业研究,多基于区域音乐研究逐渐拓展产生跨界、跨族群研究。例如,西方学者对东南亚国家和族群的音乐研究属于开展较早、成果较集中的部分,其中中南半岛跨界族群音乐的“区域化格局”②徐欣:《西文视野中的中南半岛音乐区域化格局》,《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研究具有代表性,涉及对其中不同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或中南半岛音乐整体观的探讨③如Amy Catlin.ed.,Text,Context,and Performance in Cambodia,Laos,and Vietnam.LA:Department of Ethnomusic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2.加文·道格拉斯:《东南亚陆地音乐》,王先艳译,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等。。
而后,西方学者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在后现代思潮和全球化进程影响下,关注现当代世界音乐文化交流、移民音乐文化现象,这一研究视角启发学者们由他文化回看自身,就世界音乐文化在西方的发展传承、对西方音乐教育的影响④Elizabeth May.Mantle Hood.Javanese Music for American Children.Music Educators.1962(48),pp.38-41.李海伦:《文化之旅中的音乐之旅——西方国家中东南亚及南亚印度民族表演艺术传承研究》,《中国音乐》2021年第5期,等。以及本国的各族裔音乐文化进行研究⑤Sydney Hutchinson.“erengue Típico in Santiago and New York:Transnational Regionalism in a Neo-Traditional Dominican Music”.Ethnomusicology,2006(50),pp.37-72.[美]饶韵华:《跨洋的粤剧: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国戏院》,程瑜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
(二)由内而外:中国学界由自身向周边延伸
与国际学界的发展向性不同,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则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并分别在研究的狭义(区域音乐研究)和广义(移民音乐)对象范畴与国际学界形成对话平台。
20世纪初期和中期中国音乐学者独立收集整理、研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虽然逐渐意识到对跨界民族开展境外音乐调查十分必要,但条件受限难以成行。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在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区域音乐调查,难以涉入中国境内。由此,形成了中西方学者分别在国界线内外对跨界族群音乐进行研究的局面。
而后至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对周边国家音乐文化进行研究,直至21世纪随着多方面条件具备,才真正开始进行目前普遍意义上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起初以跨界民族的音乐个案研究为主,通过积累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可以按照区域、路带等多元视角连接成片。至后现代,全球化的跨界音乐研究思路也影响到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不仅由陆路边疆向海上丝绸之路等更广泛的边界范畴转移⑥2021第三届中国(南方)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国际论坛,设立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发言小组。,而且在全球化、城市化影响下以洛秦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开始关注广州、上海等地的移民音乐文化研究⑦2014年《文化艺术研究》发表关于移民音乐文化研究系列论文;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上海城市文化中心移民‘飞地’音乐研究”及课题相关成果。。
三、“跨界族群音乐”的三大研究视域
(一)对象视角:音乐民族志书写
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方面,最主要的研究范式,是从对象视角出发的音乐民族志书写。西方学者在区域音乐研究中,以该类型的研究为主。
首先,针对音乐事项的专题研究,逐步拓展范围涉入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如米勒针对泰国各种音乐类型进行了详尽系统的研究①Terry E.Miller,“Traditional music of the Lao:Kaen Playing and Mawlum Singing in Northeast Thailand.”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5.以及此后针对泰国佛教音乐等发表的系列论文。.,后涉入其中某种音乐类型的跨界比较研究②Terry E.Miller,“The Classical Musics of Cambodia and Thailand:A Study of Distinctions”.Ethnomusicology,1995(39),pp.229-243.etc.。
其次,跨界族群音乐结构和分类的专题研究。如卡特琳对中南半岛上跨国而居、移民美国的苗族音乐进行研究的系列论文③Amy Catlin“Homo Cantens:why Hmong sing duing interactive courtship rituals.”Selected Reports in Ethnomusicology.1993(9):43-60.etc.,此外其进一步对金三角地区分布的更广泛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和音乐结构进行了梳理、比较④Amy Catlin.“Music of upland minorities in Burma,Laos,and Thailand”,The Garland encyclopedia of world music.IV:Southeast Asia.1999.pp.537-559。。
第三,从区域音乐研究涉入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以东南亚区域音乐研究从整体到局部的研究为例,层层收缩来看其中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发展轨迹,从较早对东南亚音乐进行的普遍、整体研究⑤JoséMaceda.A Search for an Old and a New Music in Southeast Asia,Acta Musicological,1979(51).pp.160-168.etc.,此后持续对东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音乐进行探索⑥Elizabeth May.Mantle Hood.Javanese Music for American Children.Music Educators.1962(48),pp.38-41.李海伦:《文化之旅中的音乐之旅——西方国家中东南亚及南亚印度民族表演艺术传承研究》,《中国音乐》2021年第5期,等。,进而对更为集中地对中南半岛上最典型的跨界族群聚居区金三角地区⑦Victoria Vorreiter:Song’s of Memory:Traditional Music of the Golden Triangle,Thailand:Resonance Press,2009.、高地民族⑧Hans Peter Larsen.“The Music of the Lisu of Northern Thailand.”Asian Folklore Studies.1984(43).pp.41-62.等多元音乐类型进行讨论。
(二)学科视角:理论方法范式
跨界族群音乐涉及不同国家同一族群内(民族文化感召)、外(国家政治分割)作用的交互影响,其多元音乐文化事项中凝聚力和分隔力杂糅的复杂表现使得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在理论方法范式上表现出的几种研究类型如下。
1.音乐与跨界民族和国家关系间的探讨
西方学者多关注音乐与权力之间关系⑨Craig.Lockard.Dance of Life:Popular Music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Publisher: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1998.etc.,中国学者则注重在解读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意涵时涉及的国家、民族身份关系等方面的问题⑩杨民康:《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音乐与认同”——兼论当下在国内开展“音乐政治学”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纪念《音乐研究》创刊六十周年座谈会”,2018年9月;董宸:《中—泰泼水节仪式音声中的国家、城市与族群》,《中国音乐》2021年第5期,等。。而中、西方学者普遍都比较关注的是音乐与文化认同的研究,欧美学者21世纪以来有较多将跨界族群音乐置于历史发展、文化语境之中探讨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成果⑪杨烁:《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的中西方研究比较与分析》,第三届中国(南方)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国际论坛,2021年。举例如Andrew McGraw对古兰纳弹拨乐器传承与兰纳身份认同的关系,Andrew C.Shahriari探讨泰国北部族群的音乐舞蹈宣传与族群认同建构的关系。,中国学者自2010年起发表的“音乐与认同”专题系列成果中从个案分析⑫赵书峰:《跨界族群与音乐认同——老挝优缅瑶婚俗仪式音乐的身份问题研究》,《中国音乐》2021年第3期。到理论建构⑬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多角度涉及有关跨界族群音乐研究。
2.交叉学科理论方法视域的多层次建构
民族学界认为跨界民族研究的层次,从细节来看,有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本国诸民族认同(或地域认同)三个层次和国家认同、跨国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间的认同、跨国民族内部的认同、跨国民族内部亚族群的认同四个认同层次的不同划分⑭朴婷姬:《试论跨国民族的多重认同》,《东疆学刊》2008年第3期;王丽娜、朱金春:《西南跨界民族的边界意识与身份认同》,《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从整体来看,则可以分为政治与文化认同两个层次①白志红:《湄公河流域跨境民族的认同》,《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民族音乐学与之呼应,杨民康分别针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对象的狭义性到广义性②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以及纵向社会分层③杨民康:《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提出原生文化层、次生文化层、再生文化层的多层次分析解读视角。
这种学理层面的交互,说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实现了自身的对象性整合,并处于向思维学科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分支”④杨民康:《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
(三)发展视角:深入、拓展与反思
第一,区域研究的持续拓展深入。欧美学界21世纪以来对中国及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持续拓展和深入,如布莱恩对越南苗族音乐,沙利亚里对泰北掸傣、孟等民族的音乐,阿林顿对云南傈僳族基督教音乐⑤Lonan O.Briain.Musical minorities:The sounds of Hmong Ethnicity in Northern Vietn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Andrew C.Shahriari.Khon Muang Mudic and dance tradition of Northern Thailand.Bankok:White Lotus Co.,Ltd.2006.Aminta Arrington.Songs of the Lisu hills.Practicing Christianity in southwest China.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20.的专题研究等。
第二,移民音乐研究。欧美民族音乐学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开始对现当代社会语境下产生的移民音乐文化进行研究,研究范畴日趋多元⑥Catherine Falk.“Upon Meeting the Ancestors:The Hmong Funeral Ritual in Asia and Australia”Hmong Studies Journal.1996(1),pp.1-15.etc.,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系统也有了相对成熟的体系⑦Amanda Rogers,Performing Asian transnationalisms:theatre,identity and the geographies of performance,Taylor&Francis Group,2014.etc.。21世纪以来,该研究类型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关注。
第三,音乐文化变迁研究。民族音乐学界在现代化发展语境下,关注跨界族群传统音乐在现代化、城市化⑧LonánóBriain.对Hmong传统音乐运用网络等现代技术资源、应对旅游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于Asian Music(2014)、Journal Of World Popular Music(2015)发表系列文章,由于篇幅限制,此处暂不列举。等诸多现象影响下是如何应对并产生变迁的,此类研究目前主要聚焦在以传统区域/族群音乐为对象的研究中,但为开展更深入的跨界族群研究和更广泛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方向。
第四,音乐文本研究的多样化视野。针对跨界音乐文本自身的分析,有结合语言学⑨D.Bradley,“Speech Through Music:The Sino-Tibetan Gourd Reed-orga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79(43),pp.535-540.Amy Catlin“Puzzling the Text:Throught Songs,Secret Languages,and Archaic Tones in Hmong Music.The World of Music.1997(39),pp.69-81.etc.、局内-局外观反思与音乐表达⑩Hakan Lundstrom and Damrong Tayanin.Kammu Songs.The Songs of Kam Raw.Copenhagen:NIASPress.2010.etc.等多样化的探索方式。此外还有将音乐纳入文化语境当中,对音乐表达与音景⑪Gavin Douglas.Performing Ethnicity in Southern Shan State,Burma/Myanmar:The Ozi and Gong Traditions of the Myelat.Ethnomusicology,2013(57),pp.185-206.etc.、图像⑫杨民康2016-2020年对柬埔寨吴哥窟和印尼佛塔乐舞壁画石雕图像研究的系列论文。等社会文化事项之间的关联表达方式进行探讨。
第五,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新视野。一方面,从研究对象上依托中国跨界民族分布情况和条件优势将其向外扩大,从学科上探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范式,表现出研究的中国经验。如杨民康的系列论文讨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如何从研究对象到学科理论方法,提升整体研究观念⑬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作为当代史及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释义性解读——以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为实例》,《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4期。。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语境,思考/反思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实践和发展方向。如张伯瑜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如何走向“国际化”进行反思①张伯瑜:《“跨界”能否成为国际化概念——“跨界”高层论坛之后的思考》,《音乐研究》2014年第1期。,并借助跨界研究项目,加强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合作②张伯瑜、格桑曲杰、[芬兰]皮尔克·莫伊莎拉、[美国]珍妮特·赫尔曼、[不丹]肯·索南姆·多吉等:《环喜马拉雅山音乐文化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对可行性进行探索。
四、“跨界族群音乐”中国实践的四方范畴
中国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主要以中国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分布的东北、西南、西北和东南四个方向范畴为主,研究通常从境内单个的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逐步涉入共同的文化圈、文化区域、路带等视角的跨界研究。
(一)西南区域
在中国各区域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成果是最为丰富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云南与中南半岛跨界族群音乐研究。论著成果如杨民康针对傣族与孟高棉语族从微观到宏观、从对象到学科的系列跨界音乐文化研究③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董宸《云南傣族与孟高棉语族音乐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1期。;黄凌飞、董宸、李纬霖④董宸:《云南傣族与孟高棉语族音乐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1期。、范瑞⑤范瑞:《中泰跨界民族哈尼-阿卡阿茨咕、滇航嚓音乐文化研究》(上、下),《中国音乐》2015年第2期、第3期。等针对不同跨界族群的诸多音乐类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跨界比较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有赵塔里木、杨民康、黄凌飞、董宸等的课题项目针对这里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展开⑥赵塔里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2011年重点项目“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杨民康:2020年一般项目“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的理论建设和选点、比较研究”;黄凌飞:2019年一般项目“中国西南地区哈尼族音乐民族志研究”;董宸:2018年青年项目“仪式表演语境下中-缅-泰南传佛教诵经音声比较研究”。。此外,云南艺术学院成立了“南方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心”。
第二,广西与越南壮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有范西姆、杨秀昭对中、越、缅、泰、老的壮侗语族音乐文化关系(圈)进行了探讨⑦范西姆:《论壮侗语族诸民族音乐文化的渊源关系与互渗》,《民族艺术》1991年第4期;杨秀昭:《壮侗语各民族音乐文化论纲》,《艺术探索》1996年第3期。;孙莉、白雪、陈坤鹏、张灿、高嬿、李亚楠等分别就不同民族的不同音乐类型进行了中越跨界比较研究⑧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李延红、白雪《百越走廊上的多民族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研究》2021年第2期。。而广西艺术学院则成立了“中国-东盟音乐文化跨界传播研究中心”。
第三,环喜马拉雅藏族文化圈跨界族群研究。21世纪以来田联韬先生以藏文化圈为切入点,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进行了探讨⑨田联韬:《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人民音乐》2011年第12期。。此后格桑曲杰和银卓玛各自就不同藏族音乐类型进行跨界溯源、比较研究⑩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银卓玛《田联韬先生的藏族音乐研究及其学术传承》,《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2期。。随着藏族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推进,“环喜马拉雅”藏族音乐研究渐成热点,产生各类高端成果和课题项目⑪觉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喜马拉雅艺术图谱绘制”等。。
(二)东北区域
中国面向东北亚地区的跨界族群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蒙古族、朝鲜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东北、北方跨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
我国蒙古族跨界音乐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如杨红、萧梅、楚高娃等就蒙古族不同音乐类型进行了宏观、微观视野兼具的多国跨界音乐研究⑫杨红: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亚洲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的跨境研究”及其相关成果;萧梅:《从“弦功能”再看亚欧草原的“双声结构”》,《音乐艺术》2018年第2期;楚高娃:《多元化进程中探索学科前沿——学术谱系视域下的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实践回顾》,《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2期。。对朝鲜族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宁颖对中、韩“盘索里”进行比较研究⑬宁颖:《中韩跨界语境中延边朝鲜族“盘索里”溯源与变迁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毕业论文,2014年,等。的系列成果为代表。其他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有刘桂腾对萨满音乐的跨界研究①刘桂腾:《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的通古斯萨满鼓——以“流域”为视角的跨界族群萨满音乐研究》,《音乐探索》2012年第2期。,韩冰对中、俄赫哲族音乐文化变迁的研究②韩冰:《赫哲-那乃跨界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变迁研究》,《中国音乐》2015年第2期。等。此外,该区域有“东北亚音乐舞蹈文化研究中心”在沈阳音乐学院成立。
(三)西北区域
西北地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西北新疆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或围绕丝绸之路上跨界族群音乐的探索。
其中,赵塔里木对中国西北与中亚跨界而居的东干人(回族)民歌的一系列跨界溯源、比较研究③赵塔里木1999—2003间年发表的东干人(回族)民歌跨界研究的系列论文。。王慧、迪娜·叶勒木拉提、哈斯巴特尔分别开展了针对该区域不同民族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且有的主持相关课题项目④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王慧《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多民族音乐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另有,中国音乐学院与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中亚音乐文化研究中心”成为西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基地。
(四)东南区域
对我国东南和南方海岸线和“海上丝路”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海南黎族以及华南地区的华人离散族群的音乐研究,该视角在我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尚属比较新的研究类别。
代表性成果如杨民康对海南黎族道公祭仪音乐元素跨族群、地域关系的研究⑤杨民康:《海南黎族道公祭仪吹打乐的跨时空关系比较研究》,《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蔡宗德对印尼华人音乐与认同的探讨⑥蔡宗德:《印度尼西亚华人布袋戏的历史、演出形态与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仲立斌对新加坡的华人流行音乐的调研⑦仲立斌:《建构空间、凝聚族群——新加坡巴刹的华语流行歌曲表演》,《中国音乐》2021年第2期。等。而占据地缘优势的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成立了“岭南传统音乐舞蹈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五、“跨界族群音乐”中国经验的五个特征
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无论是将其狭义研究范畴与西方以区域音乐研究为核心涉及跨界族群的渊源相比;还是借鉴后现代西方研究经验,将移民音乐文化研究纳入广泛的跨界/国族群音乐研究范畴,但“更多隶属于城市民族音乐学范畴”⑧杨民康:《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第9页。,都具有典型的中国化学术语境特征。
第一,发挥自身优势进行研究布局,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分布着诸多跨界族群的客观条件便利。
第二,受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境外调查的需求驱动和21世纪以来跨界多方面综合条件好转的内、外双向带动。
第三,在近三代学者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积累下,研究话题和规模不断拓展和创新,从个案和比较研究,有体系地向音乐与认同、路带通道⑨杨红:《民族音乐学的理念转型与中国经验——以“路学”视域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为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张伯瑜:《论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的意义》,《音乐研究》2016年第3期,等。、流域⑩黄凌飞:《澜沧江流域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文本的当代实践》,《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等。等角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探索。
第四,在研究成果上,形成涵盖论文论著、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课题结项报告等各研究阶段和规模的深浅错落的成果类型;在研究规划上,形成短期以课题项目为导向、长期以组织跨界研究中心为导向、通过组织专题会议搭建国内外学者学术交流平台⑪2011年第一届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论坛;2019年第二届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论坛;2021年第三届中国(南方)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国际论坛。的分层交织研究布局。
第五,从对象到方法,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于前期成果的积累,探索规律,发展自身理论方法的系统建构,逐渐建构起自身多样化音乐文本分析与主位-客位研究视角结合①杨民康在《论音乐民族志研究中的主位客位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兼论民族音乐学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方法的来龙去脉》(《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中提出“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此后如王慧、腾祯、张鹤、宁颖、董宸、李纬霖等青年学者针对各自研究对象,提出并运用新的音乐记录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协调音乐记录、分析与主位-客位的观念转化。;历时-共时②和云峰:《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边界——以历时性与共时性二则调研案例为中心》,《中国音乐》2016年第4期。、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研究规模兼具;原生-次生-再生各研究层次并存;交叉学科理论方法共建的跨界族群音乐理论方法系统。
综上,随着学科观念的不断完善、学界沟通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因“努力探讨符合中国学术语境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一个个具有独特视角和独特价值的研究理念逐渐成形,其中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便是其中之一”③张伯瑜:《人群关系: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中国音乐》2016年第4期。。以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发展为代表的中国经验的突出表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贡献于国际跨界音乐研究的交流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