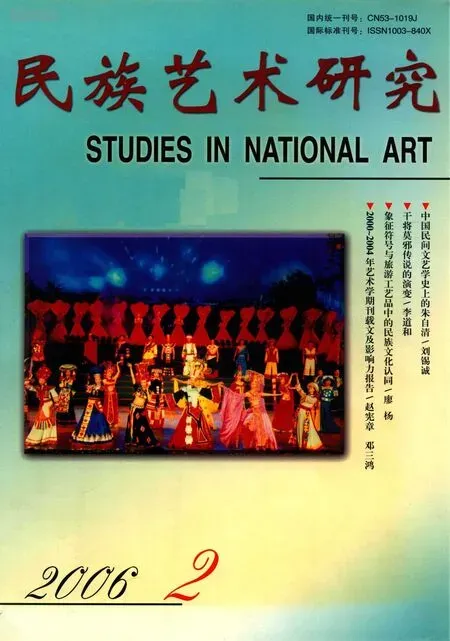梅兰芳的戏曲美学观
2022-05-06李志远
李志远
在当前的学界或戏曲界,梅兰芳作为一个语汇应该说有着两种所指:一是指作为乾旦演员的梅兰芳本尊;一是作为京剧甚或说戏曲的艺术符号,这无论是曹禺先生所言的“梅兰芳三个字已经成了美的化身”①转引自宁殿弼:《梅兰芳改革京剧的艺术理论概观》,《戏曲艺术》1996年第2期,第22页。,还是戏曲学界在谈论世界三大戏剧观时把梅兰芳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代表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相并列,都可于中察知。本文所言梅兰芳是就第一种所指而言,即是立足学习作为乾旦演员的梅兰芳所留存下来的相关资料,于中探讨作为优秀戏曲表演艺术家的梅兰芳,秉持着什么样的美学观进行戏曲创作及其对今天的戏曲美学建构的启示。
梅兰芳对戏曲艺术具有美的本质有着清醒认知,如他在《国剧学会宣言》中直称“愈信国剧本体,固有美善之质”②梅兰芳:《国剧学会宣言》,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而在国剧传习所授课时也讲到“中国戏曲,处处离不掉美,同是一种动作,但有些就引不起观者快感,就是因为不够美的成分”③梅兰芳:《在国剧传习所之一课》,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正是因为他在进行具体的戏曲作品创作时,无时无刻不按照内心所总结出的戏曲美学原则进行美的创造,如他称,“中国的古典歌舞剧,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有其美学基础的。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失去艺术上的光彩”④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他在讲解戏曲化妆时提出了明确的美学理论主张,即“根据‘为美’的原则,找出学理的一种技巧”⑤梅兰芳:《国剧化装术之一部》,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在谈到如何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表演素材时称“要什么,不要什么,这里牵涉到一个美学的问题”⑥梅兰芳:《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400页。。这一“美学基础”“为美原则”“一个美学的问题”,显然就是梅兰芳戏曲创作的核心美学观,并且将其运用于戏曲创作的每一部分。
依据今日留存下来的、较为易见的梅兰芳有关戏曲美学的文字表述,对其戏曲美学观进行归纳,笔者认为约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戏曲艺术之饱蕴内神的外形美
戏曲作为舞台表演艺术显然要注重唱念做打等手法的视听美感,即从外在创作手法上就要形成吸引观众的强有力元素,对此,梅兰芳应该说有着清醒认知,如他曾说,“在舞台上的一切动作,都要顾及姿态上的美”,正是基于这种美学创作见解,他在每部作品的舞台创作上都极力追求作品的外在形式美。如他阐释《宇宙锋》赵艳蓉的表演身段称,“赵女在‘三笑’以后,有一个身段,是双手把赵高胡子捧住,用兰花式的指法,假做抽出几根胡须,一面向外还有表情。这个身段和表情,虽说是带一点滑稽意味,可是一定要做得轻松,过于强调了,就会损害到美的条件。”①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关于《贵妃醉酒》的舞台身段,他说,“高力士跪在下面,也应该向后坐下,使一矮坐的身段,跟上面杨妃做的,一高一矮地对照着,才显得格外美观”,而剧中的打嘴巴“以前是用手打的,总觉得不美观,近来改为用水袖打,两次的打法不一样,打裴是用袖正打,打高是用袖反打”,总之是要舞台上“显出舞蹈上美的姿态”②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57、265、266页。。在人物化装上,他强调说,“除去由化装上可看出剧中人的个性外,同时尽量往‘美’上追求,并且这种美是立体式的美,图案式的美”③梅兰芳:《国剧化装术之一部》,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因而在对待时装戏《童女斩蛇》中寄娥的装扮,力求“要使观众觉得和日常生活里接触到的人差不多,但比她们更鲜明,更美”④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再加上他对戏曲表演中手势的重视,特别是古装新戏装扮的精益求精,都可以看出梅兰芳对戏曲艺术外形美的重视。正是由此,有学者称“梅兰芳戏曲美学体系明显的特点是很强调外部形式美”⑤宁殿弼:《梅兰芳改革京剧的艺术理论概观》,《戏曲艺术》1996年第2期,第22页。。
当然,梅兰芳注重戏曲艺术的外形美,并不像其在访问苏联时一些人所评价的戏曲仅注重了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内容,如他创作的时装新戏就多是取材于现实生活,而《抗金兵》《生死恨》的创作也与时事相关。事实上梅兰芳所注重的外形美是以饱蕴内神主导的,如他称《童女斩蛇》的创作“是从内到外来表演的,用心里的劲头指挥动作”⑥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告诫青年演员“内心与形体动作的统一,这是非常重要的,更需要耐心体会”⑦梅兰芳:《对小朋友们提出几点要求》,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30页。;并称戏曲传授一定要“亲传”,否则“终必至于袭貌遗神”⑧梅兰芳:《国剧学会宣言》,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这些言论无不表明他注重的是有着内在精神的外形,而不是单纯追求舞台上的外在造型,且他对舍神取形的戏曲创作有着清醒认识,如他明确表示“身段假使没有内心表演,就会流为形式主义”⑨梅兰芳:《看日本歌舞伎剧团的演出》,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47页。。
二、注重戏曲创作手法与人物形象的契合
无论戏曲作品要表达什么样的主旨,显然是要通过在舞台上塑造出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得以实现的,这就需要采用恰切的创作手法使得人物形象圆满和立体,对于此,梅兰芳所言“演员的任务是把剧本所规定的人物在舞台上表演出来”①梅兰芳:《对小朋友们提出几点要求》,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页。,应该说是阐释得非常清楚的。但具体如何在舞台上把人物表演出来呢,显然是需要采用最为恰切的创作手法,就演员而言就是用最为适合人物形象塑造的唱念做打等表演技巧,以把人物形神兼备地呈现于舞台上。如他所说,“剧中人的性格和身份是靠演员的唱、念、做、表四种工具表达出来的”,所以人物“一出场的念白、动作、神态,先由尺寸上”来展现“她们的性格”②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84页。。梅兰芳多次谈及杜丽娘形象塑造与身段改换,可视作此观点的最好注脚,如他称在唱“和春光暗流转”时的三个下蹲动作,“是一个刻画得比较尖锐的老身段”,后来一则因自己年龄大的原因,认为“再做这一类的身段有点过火”,二则认为“在入梦之前,过于露骨的身段,对一个像杜丽娘那样身份的女子还是不大适宜”,于是就“改成转到桌子的大边,微微地斜倚着桌子,有些情思睡昏昏的娇慵姿态,最后轻轻地一抖袖,就结束了这一句的动作”③梅兰芳:《谈杜丽娘》,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70页。这种立足于人物身份、内心、性格以选用舞台创作手法的见解,几乎成为梅兰芳人物创作的核心遵循。他曾多次有着相近的表述,如:“假戏真唱要设身处地地琢磨每一个剧中人的身份性格。”④梅兰芳:《对京剧表演艺术的一点体会》,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页。“演员在表演时都知道,要通过歌唱舞蹈来传达角色的感情,至于如何做得恰到好处,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⑤梅兰芳:《谈表演艺术》,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我从小就喜欢跟人家讨论剧情、研究人物性格,总想把我演的戏里每一个角色的内心情感通过艺术提炼,用表情和动作表达出来。”⑥梅兰芳:《不抄近路是我学戏的窍门》,《中国戏剧》1995年第7期,第11页。“演正德这个角色,偏重佻达,固然会令人生厌,过于堂皇华贵,也不合适,应该从华贵中带点故意模仿旧社会里少年军官的习气,才符合这个好色贪玩的风流天子的性格。”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页。对于演员表演的好坏,他也多是从是否能够采用恰切的表演手法成功塑造出剧本规定的人物为依据。如他评价贾洪林,称其“尽管嗓子不好,对于体会剧中人的身份、性格,是有他独到之处的”,“他扮演任何角色,都情态逼真,处处合理”⑧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223页。。
当然,在达到创作手法与人物形象塑造契合的目的后,一定要追求创作手法给观众的最大美感,这既是与梅兰芳注重外形美的美学观紧密相连,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物形象的审美效能。他作为乾旦演员,曾多次强调旦行要注意行当美,称“唱旦角更应处处合乎‘美’的条件”⑨梅兰芳:《旦角的化装术》,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现在最通行的一种毛病,就是旦角站立时,都把重心移于后边脚上,这种姿势最不美而且最费力”①梅兰芳:《剧舞笔记》,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他还用他的表演实例予以述明,如他说《贵妃醉酒》中杨贵妃醉酒后的三个卧鱼身段本来是没有目的的,他进行了多次深思与修改,就是要“给观众一种真实的感觉”②梅兰芳:《谈表演艺术》,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即要达到做出来的“身段得相真,得好看”③梅兰芳:《在国剧传习所之一课》,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5页。;对于《黛玉葬花》之所以没有采用旗装、京白,就是因为会使舞台上的贾宝玉“未免显得俗气,更不能表现林黛玉的绝世聪明”,而采用古装装扮“一则可以尽量发挥林黛玉的才华,二则可以在葬花时表演种种姿势”,且扮演出来的舞台上的林黛玉,“大家都很满意,认为理想中的林黛玉,应该是这个样子”④梅兰芳:《四十年戏剧生活》,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而对《思凡》中色空的扮相,则并不是据“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这句唱词而扮作光头尼姑,就是因为舞台创作手法的选用“处处要照顾到美的条件。像这种一个人演的独幕歌舞剧,要拿真实的尼姑姿态出现在台上,那末脸上当然不可能擦粉抹胭脂、画眉点嘴唇。这就跟种种美的身段、唱腔、表情都不能够调和融洽了”⑤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70页。。正是因为梅兰芳注意创作手法与人物形象的契合,他不仅强调要“根据传统技巧的表现原则来创造适合于现代人物的新唱腔、新格式、新手段”,认为“光从唱词字面上去表演,就会流于肤浅以至歪曲,必须从剧情里去分析人物思想感情的来龙去脉,处处想着角色的身份,进行创造”⑥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不要“为了搬用传统技巧,而不顾人物性格、环境,就会走上为运用而运用、生搬硬凑的形式主义道路”⑦梅兰芳:《运用传统技巧刻划现代人物——从〈梁秋燕〉谈到现代戏的表演》,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186页。。
如果我们再稍加注意的话,甚至可以看出梅兰芳对创作手法与人物形象契合的关注,甚至不仅仅局限于唱念做打等舞台表演元素,而是扩展到演员自身是否适合剧中人物形象的创作,如他在《虹霓关》中头本扮东方氏,而在二本中改扮丫鬟,这是他的首创。为何如此呢?他称,“这是因为我的个性,对二本里的东方氏这类的角色,太不相近,演了也准不会像样的原故。”⑧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当然,如再进一步追寻梅兰芳为何会有如此的美学见解,可能与他所认为的,“戏曲演员,当扎扮好了,走到舞台上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普通的人,而变成一件‘艺术品’了”⑨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三、注重舞台表演的剧情规定性
戏曲剧本是戏曲舞台创作的最终遵循,所有的人物形象、场景展现以及主旨表达等,无不是依据戏曲剧本的设定展开,这就需要舞台表演要紧扣剧本所设定的剧情进行。正是基于此,梅兰芳特别注重剧情对表演的内在要求,力求舞台创作能够较好地完成剧情的立体呈现,以较美的形态实现潘之恒所言“显陈迹于乍见,幻灭影于重光”⑩。
梅兰芳对舞台表演要达到剧情规定性的要求,他在不同的文章中分别从不同方面予以阐释。如:就舞蹈而言,他说,“中国戏曲的表演方法,是把舞蹈动作融化在生活里,人物登场,一举一动都是舞蹈化的,其中个别场子如‘剑舞’‘羽舞’‘拂尘舞’虽然着重在舞蹈,但仍然是为剧情服务的”①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七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页。。就表演身段而言,在有人问他演《汾河湾》唱完“等你回来我好做一做夫人”后的极美妙身段是怎么做出来的时,他说“那时的动作只是随意而为而已,只是符合剧情,是不会重复的”,并称身段要符合人物内心、恰到佳处,就要“不断分析剧情”②梅兰芳:《说戏》,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42页。。就念白而言,他说,“不论是韵白或京白”,都应该“根据剧情,运用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技巧”,否则就“如同小孩背书,索然无味”③梅兰芳:《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91页。。就表演道具而言,他以《断桥》中青蛇是否要背剑上场为例说,剑“拔出来是容易的,插回去就难了。要不插回去,老让青蛇背上插着一把剑,这多么难看。其实《断桥》出场,就换了打扮,武装已经解除,何必再带武器,所以不插剑的方式,对于剧情比较合理”④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于是就不让青蛇背剑上场。就舞台表演所采用的耍戏法而言,他称赞《封神榜》表现狐狸精吃掉妲己采用的耍戏法,因为它“没有离开剧情”,而批评《欧阳德》的耍戏法则正是因其与剧情没有关系⑤梅兰芳:《赣湘鄂旅行演出手记》,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55页。。就突破戏曲表演常规而言,他认为只要是符合剧情都是可以的,如他说,“演老派青衣的不常露手,而我们演柳迎春可以常常露手,因为有许多动作是必须要用手的。当年有位时小福老先生,演柳迎春就时常露手,当时有人叫他为‘露手青衣’。柳迎春有许多做派是需要露手的,时老先生这样做是合乎剧情的。保守派称他为‘露手青衣’,是一种讽刺性的外号,这是不对的”⑥梅兰芳:《旦角表演及〈穆桂英挂帅〉的形象塑造——一九六○年五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09—410页。。就剧作表演成规的修改而言,也是依据剧情进行的,如认为《奇双会》中赵宠与桂枝斗趣若如一贯的以开玩笑终场,就“失去了桂枝救父的悲痛心情”,于是在桂枝掩口一笑转身朝下场门走时,又增加了桂枝“又回转身来,看了看手中状子,做出啼哭的样子,然后才走了进去”这一身段,这样就更符合剧情规定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60页。。他对《龙凤呈祥》中赵云、孙尚香上下场的重新安排,是因为这样“对剧情是比较合理的”⑧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一如他要求创作手法契合人物形象之后还要注意外形美,在强调舞台表演要符合剧情规定性的基础上,他提出,“要在吻合剧情的主要原则下,紧紧地掌握到艺术上‘美’的条件”“除了很切合剧情地扮演那个剧中人之外,还有把优美的舞蹈加以体现”⑨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303页。。显然,就此所表述的美学观而论,依据剧情规定进行舞台表演是基本的美学要求,而能够以更为优美的外形呈现剧情则是相对较高的美学要求。
四、注重戏曲舞台创作的适度与整一
戏曲作为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形式,内在地要求戏曲作品各方面的恰适与整一,而不能单独凸显某一个方面,即使对于演员个体而言在舞台表演时也须如此,否则就会出现卖弄某一技巧的嫌疑。对戏曲创作的此种特点,梅兰芳显然有着独到的认识,并从此内在特点出发,总结出在戏曲创作时要遵循表演的适度与整一的美学原则。
适度美表现在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一是就戏曲作品创作而言,即要演员表演不能出现“洒狗血”的过火现象。如他说,“京剧有一定的绳墨,工夫要深,一举一动都得按规矩,不然就要脱格,哪怕是一个写实的动作,写实也有程度的限制,超出限度,就觉得刺眼,不调和”①子冈:《梅兰芳抵平记》,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三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页。,“我对于舞台上的艺术,一向是采取平衡发展的方式,不主张强调出某一部分的特点来的”②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页。,身段“只要做得好看,合乎曲文,恰到好处,不犯‘过与不及’的两种毛病,又不违背剧中人的身份,够得上这几种条件的,就全是好演员”③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82页。。批评一些演员“只顾为了吐字清楚龇牙咧嘴,矫揉造作,就会有损舞台形象,给观众以过火的感觉”④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56页。。批评有演员把《玉堂春》中王金龙与刘秉义的对手戏“演成对立的地位,好像当场要开火的样子”,就“犯了过火的毛病”⑤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同时也要求舞美不能过度,他说,“我见过有些剧团,遇有八员将的场面,为了增加威严火炽,让八员将都戴翎子狐狸尾,其实八员将中至多有二员翎子尾就够了,‘整齐美’超过了饱和点就不美了。”⑥梅兰芳:《谈戏曲舞台美术》,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三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页。二是观众的审美感受,即戏曲创作要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红,着粉则太白”的美。关于此,他在评价日本歌舞伎时有着明确表述,他说浮世又平扮演《倾城返魂香》中的弁庆,在表演上有着“内在的节奏”“极精确的格局”,“所以才使观众有一种‘适度感’”,并说“表演艺术能使观众有‘适度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⑦梅兰芳:《看日本歌舞伎剧团的演出》,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348页。。可能正是为了实现戏曲创作给观众以“适度美”,梅兰芳先生才更为注重戏曲舞台表演的“适度”和内在的“分寸”,甚至告诫青年演员,“假使火候不到,宁可板一点,切不可扭捏过火,过火的毛病,比呆板要严重得多”⑧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页。。之所以“严重得多”,显然是此类表演严重违背了梅兰芳的戏曲美学观。
戏曲创作讲求“一棵菜”。如余叔岩就说:“戏要演得‘整’,一场,一节,乃至一个身段,都要像‘一棵菜’那么整齐才有精神。”⑨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页。就戏曲演员表演而言,既强调多位演员在舞台表演上的紧密配合,也强调单个演员表演的完整,以及乐队与演员之间的配合。如梅兰芳在谈及《穆桂英挂帅》“坐帐”一场中四员大将的盔头时称,“比武的几个人,身份职位并没有规定相同,应该有理由一个人一种打扮。‘坐帐’一场四员将都扎靠已经表示了身份大致相同,盔头还是差开来戴比较好些。这一类型戏的服饰安排,应该是在整齐一律当中,要求每人有特点。‘整齐美’表现在几员将一律都扎靠,‘特点美’表现不同的靠色、不同的盔头。”①梅兰芳:《谈戏曲舞台美术》,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三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页。这里虽然意在说明四员大将要从靠色、盔头上有所区别,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前提是四员大将都扎靠,即首先是有“整齐美”的存在,然后再注意“特点美”,“整齐美”与“特点美”在作品内的共同呈现,正是“一棵菜”创作原则的遵循,亦是整一美学观的实践,更是为了配合适度美学观的实现。再如梅兰芳谈群戏的舞台创作称:“群戏就是集体制作,每个角色都要演得有分量……戏扣子要扣紧,不能有丝毫松懈……要严丝合缝,否则戏就瘟了,就索然无味,集体创造的群戏就无法达到很高的境界。”②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由此可以看出,这就是说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配合要整一,只有这样,作品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给观众以美的享受;就每位演员的表演而言,亦要达到各种创作手法的相互谐和、完整如一。如他称演员“必须吐字准确,气口熨贴,面部还要保持形象的‘美’,然后配合动作表情,唱出曲情、味儿,使观众看了听了之后,回味无穷,经久难忘”③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56页。;称赞谭鑫培、杨小楼的演出“从来是演某一出戏就给人以完整的精彩的一出戏,一个完整的感染力极强的人物形象”④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63页。;批评以前的“观众只注意一腔一调一举一动,每到一个所谓‘俏头’的过节,观众经常报以彩声”;称扬现在的观众“从整体上欣赏”⑤梅兰芳:《劳动人民使我的艺术创造有了新的生命——庆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76、277页。表演艺术。对演员与乐队之间的配合,梅兰芳也有明确的表述,他说:“有了好演员,还要有好乐队的伴奏……主要的是打的、拉的和唱的都应该了解剧中人在特定环境中是有些什么情感,把它充分而恰当地表达出来,这样,才是一出完整无暇(瑕)的真正好戏。”⑥梅兰芳:《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程式》,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页。可以看出,一出真正的好戏,梅兰芳认为不仅是有好演员的好表演,还要有好乐队的好伴奏,双方紧密配合,完好地完成剧情设定的情感与人物形象。对梅兰芳的整一戏曲美学观,学界已有关注并予以总结,如刘祯就称:“梅兰芳的‘完整’理论,追求的是艺术完整,不是表演的一招一式,不是唱念,不是身段,但又是包涵了唱念和身段的艺术整体。”⑦刘祯:《论梅兰芳表演理论及体系——〈舞台生活四十年〉个案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15年第1期,第79页。
五、追求戏曲表演的平淡、自然
人的审美无疑会受到阅历、年龄等变化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梅兰芳亦是如此,他晚年对戏曲美学的追求与他早年相较,已经由追求新颖、炫奇转变为追求平淡、自然。关于此,梅兰芳在多篇谈戏的文章中都有述及,如他在《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中说:
我早期的唱腔是当时流行的青衣的传统唱法,比较简单朴素。自开始排演古装新戏,自己就琢磨比较新颖的唱腔来配合新颖的装束。当然这是和先后伴奏的几位琴师如茹莱卿、徐兰沅、王少卿等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从初期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一直到四本《太真外传》为止,我觉得在唱腔方面已经繁复多样,似乎不能再向这方面发展了,所以后来排演的《抗金兵》《生死恨》,在唱腔设计上就走向了平正通达的一路,不以追求新奇为目的了。我在去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排演《穆桂英挂帅》一剧,唱腔设计更以沉着简练为主,听上去好像比以前所排新戏的腔调简单些,但实质上并不简单,也就是说这出戏的唱腔和唱法,更多地注重表达剧中人复杂的思想感情方面。①梅兰芳:《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93页。
可见,梅兰芳早期在唱腔的美学追求上,因为那时的青衣唱腔整体上“比较简单朴素”,他为了实现青衣唱腔美学的突破,于是就以“新颖”“新奇”“繁复多样”为唱腔设计的美学标准,同时还配合以“新颖”的装扮。这时他的戏曲美学追求鲜明地表现在一个“新”字上。但到他演艺日益成熟之后,他却不再以求“新”“花巧”②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页。为美学旨归,而是追求以“平正通达”的形式进行基于剧情的人物形象立体塑造。另如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在民国初年,新腔之风虽未盛行,但我排演新戏时,总想琢磨些新颖动听的腔调”,只是后来他渐渐觉得,“有些炫奇取胜的唱腔,虽然收效于一时,但终归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本身是不协调的,同时,风格也是不高的”③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256页。。可见,梅兰芳之所以认为唱腔不能再向“繁复多样”的新颖、炫奇一路发展,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戏曲美学的风格不高,只能收效于一时。于是,他开始在戏曲创作中以平淡、自然为戏曲美学的遵循,对此他有着明确表述:“我觉得演剧的要诀,由绚丽归于平淡,方是学到功深。譬如运一腔,做一身段,教台下观众注意,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一定要耐人寻味,好像吃橄榄,有回味,越到后来越甜,才能够抓得住观众”④梅兰芳:《缀玉轩回忆录》,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我认为:一些生活细节的描写,要准确而又自然,不能被程式束缚,同时要理解到细致不等于繁琐,紧凑不等于赶落”⑤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306页。;“我的中心主张,在唱念做工表情方面,属于舞台上的基本工作,全部吸收了进去。我觉得最需要的是‘自然’,最忌的是‘矜持’。在我演出的技术上,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境界”⑥梅兰芳:《拍了〈生死恨〉以后的感想》,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从这些表述中不难看出,他不但把表演的“归于平淡”“自然”视为表演功力深化的表征和“新的境界”,而且最终是要通过以看似平淡无奇的创作手法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作品。
如果再进一步追寻梅兰芳所追求的平淡、自然之戏曲美学观是一种什么的艺术境界,也许从他评价“谭老的艺术,晚年已入化境,程式和生活融为一体,难于捉摸”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71页。中可以窥知一二,亦可从称赞梅雨田胡琴艺术是“浑脱绵密,天衣无缝”⑧梅兰芳:《缀玉轩回忆录》,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的评语中略知其概。
结 语
以上仅是从梅兰芳有关戏曲美学的表述中进行的梳理、勾勒与归纳,同时为了叙述的方便把其戏曲美学观划分为五个方面。就其戏曲美学观的形成来看,除在其演艺生涯中有着从追求外在表演手法的新奇到平淡通达的变化外,其他几个方面皆是紧密相连于一体的,无论是讲求创作手法的新奇,还是追求创作手法的自然,皆不是脱离剧情、人物内心情感体验的单纯炫技,如他称所编古装新戏中,“‘剑舞’‘羽舞’‘拂尘舞’虽然着重在舞蹈,但仍然是为剧情服务的”①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七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页。,在民国初年琢磨的新腔调也是为了“加强表现剧中的人物”②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页。,且他从小“就喜欢追究剧中人的性格和身份,尽量想法把它表演出来”③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载梅兰芳著、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可以说,正是因为梅兰芳立足于自己多层位、多侧面的戏曲美学观,依据剧本及剧本所设定的剧情、人物,使得他在走上戏曲舞台成为“艺术品”的同时,也创作出了一系列令观众视听适度而内心又回味无穷的戏曲作品。既然事实已经证实他的戏曲美学观对戏曲表演创作是行之有效的,显然其对当今青年戏曲演员的美学观形成与建立有着重要的效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