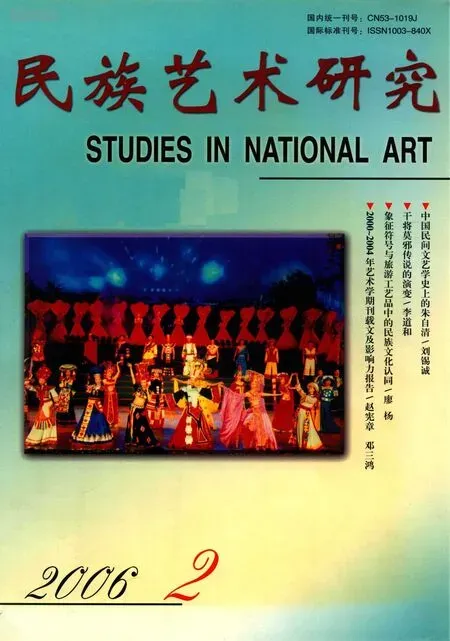近十年中国院线纪录片的发展趋向(2011—2021年)
2022-05-06牛光夏
牛光夏
作为以非虚构为根本特性而区别于故事影片的电影形态,纪录片取材于现实或历史世界中的真人真事,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加工与展现,用以表达创作者的主观认知与审美观照。被称为“电影长子”的纪录电影相较于故事影片来说确属“穷兄弟”,不论中外,能够进入商业院线公映的纪录影片比故事片都要少得可怜。但由于纪录片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纵观纪录电影史,可以说绝大部分纪录电影创作从来都有着无须掩饰的现实的、在地性的诉求,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更与国家所实施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一种主要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生产、被置于故事片前作为“加映片”播放的带有一定新闻时事性的纪录短片,在电视机还没有进入普通百姓家庭的岁月里,这种微型的纪录影片有助于对民众进行直观形象的信息传递和宣传教育。1966年,带有浓厚的阶级斗争意味的纪录片《收租院》曾创下了在电影院连映八年之久的纪录。而篇幅不论长短,以“政治挂帅”为前提决定了纪录电影在这一时期均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宣教色彩。电视普及之后,院线电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曾经热闹的电影院变得门前冷落,纪录电影更是鲜见。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的黄金时代,《话说长江》《望长城》《最后的山神》等经典电视纪录片承担了记录现实、回顾历史的重任,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等知名纪录片栏目的打造则进一步增强了电视纪录片在国内的影响力。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而摄制的纪录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在影院上映后,当年曾位列包括故事片在内的电影票房之冠,但这只是一个与领袖人格魅力和组织收看直接相关的特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整个电影市场延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迷之气惨淡经营,纪录电影更是因缺乏市场空间而徘徊于电影院线之外,只有《布达拉宫》(2004年)、《圆明园》(2005年)、《筑梦2008》(2008年)等屈指可数的纪录电影试水大银幕。同时以作为后现代大众文化范本的“超女现象”为标志性起点,电视媒体掀起娱乐化狂潮,相对小众的纪录片栏目遭遇无情的收视率考核制度与末位淘汰制度,更名为《见证》的原央视《纪录片》栏目的播出时间被安排到午夜。而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进入这种几近停滞的瓶颈状态大为不同,同一时期的西方纪录电影则较之过往以较高的票房收入大规模进军院线,如《迁徙的鸟》(2001年)、《华氏911》(2004年)、《帝企鹅日记》(2005年)、《牛铃之声》(2008年)、《海豚湾》(2009年)等。在第二个十年中,中国电影在影像生产、传播影响力和市场回报诸多方面都回暖向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这为纪录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外部条件与产业基础。同时,以2010年为转折点,中国纪录片发展进入快车道,这一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纪录片创作与传播被纳入整个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层面,在政策倾斜、资金扶持、平台建设等方面都出台了若干激励措施,明确提出“扩大国产电影纪录片放映规模,采取措施将优秀国产电影纪录片推向主流院线和主要影院,在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建立数字电影纪录片专门放映场所,在高校建立数字放映院线播放优秀国产电影纪录片”①参见201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尽管上述目标目前有些还未实现,尚处于努力探索中,但这无疑是中国纪录片由此走向生机勃勃春天的重要契机。同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设立“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发展专项资金”,此后对纪录片产业进行政策扶持和资金奖励的措施不断出台,纪录片的相关节展增多,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成为其发展的关键词。这使得中国纪录电影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迎来了它重返院线的曙光,整体上呈增长性势头,作品数量和质量较之从前都有了提升,创作主体和客体及接受主体较以往有了新的变化。从其流变的生成和因果机制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电影的生产、传播和发展与技术、经济和社会诸范畴息息相关并相互作用,同时它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形式又隶属于美学范畴,如电影学者所说“它们是同一织物的所有经纬”②[美]罗伯特·C.艾伦、[美]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6页。,其审美趋向总体呈现出主流美学、工业美学和新平民美学的共生并进,而其接受主体之于内容创作、拍摄资金、放映场次的众筹和互动的积极参与也成为其一大发展趋向。
一、创作主体:主流美学和工业美学主潮下的产业化制作者与作者式创作者的互补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电影市场的扩大以及电影观众和市场评价的成熟给纪录电影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纪录片在媒介融合的传媒生态环境下,以多模态、多渠道的形式存在着,传统电视媒体依然是纪录片生产与传播的主阵地,依托于互联网络的各种时长和类型的纪录片在各视频网站和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而电影院线对纪录影片的内容倾向、技术指标、艺术审美都有着更高的要求。首先纪录片要获得“龙标”,即电影公映许可证,方有资格进入院线,只有那些经电影机构专家小组按照《电影管理条例》的严格审查,符合主流审美要求和价值观的影片才会在影院公映,得以抵达观众。也即能够进入院线的纪录电影必须是符合主流美学的,即在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加持下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审美志趣与情感需求的。不论是记人还是记事,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与主流美学相契合是所有院线纪录电影的基本生存法则。但邵牧君先生在纪念电影诞生百年的一篇文章中还曾指出:“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与其他传统艺术有一个本质性的不同点,那就是它首先是一门工业”①邵牧君:《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是一门艺术》,《电影艺术》1996年第2期,第4页。。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产业化、技术化、媒介化或网络化生存的语境下,其工业特性比中国电影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凸显,在第二个十年之后,工业美学更是成为电影产业发展主导性的美学范式之一。陈旭光在《电影工业美学原则与创作实现》一文中首次对“电影工业美学”的概念进行阐释,并在此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对其予以进一步深化阐述。他认为中国电影的“新力量”导演从观念到实践的共同表征为“遵循或正在建构一种‘电影工业美学’原则”②陈旭光、张立娜:《电影工业美学原则与创作实现》,《电影艺术》2018年第1期,第99页。,指出电影工业美学就是“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水准和运作上的工业性要求,彰显理性至上原则,在电影生产过程中弱化感性的、私人的、自我的体验,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标准化的、协同的、规范化的工作方式,力图达成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统筹协调、张力平衡而追求美学的统一”③陈旭光:《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8页。。一般而言,除非像《话说长江》《望长城》《复兴之路》等大型系列纪录片,中国纪录片创作大多是低成本和由小团队、家庭作坊式甚至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完成的,导演身兼摄像、剪辑、特效、宣传等若干职务于一身,不需考虑生产环节的标准化、规范化。作为电影众多品类中的一种,直接反映现实生活、面向大众的纪录电影同样是电影文化工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进入院线与故事片分庭抗礼,追求最大数量的观影人群、票房收入和影响力亦是它的终极诉求。那么纪录电影同样“要尊重电影的工业特性和技术美学,在技术指标、工业水准上给观众以符合审美要求和技术、工业要求的视听觉享受,这也是对观众的基本尊重”④参见陈旭光《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思辨与体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17日。。全球化时代影视领域面临日趋白热化的竞争,工业化、市场化是国产纪录片生存发展的必然道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电影开始遵循工业美学的创作原则,服膺于制片人中心制,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展所长的团队中以更为严谨细致的产业化流程完成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与宣传发行,使纪录片生产的各环节能够高效运转、衔接流畅,使拍摄时间和成本可控。影片在叙事上则注重节奏和戏剧性的把控,努力贴近观众的审美需求,视听美学相较以往则更为华美、精致和电影化。
作为特殊的大众文化和工业产品,与其他门类艺术品要充分展现艺术家个体的审美意识不同,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则是要体现出更为社会化的、集体的审美意识。与故事片导演亦有区别,纪录片人大多是情怀驱动下的创作者,不完全纯粹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美国纪录电影史学家埃里克·巴尔诺曾如此总结:“在世界范围内,纪录电影工作者历来回避大制片厂,他们组成小规模的制作单位,到制片厂以外的世界拍片。他们在电影和电视工业中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他们已在其中站稳脚跟……影视工业倾向于重复制造社会神话,纪录电影工作者似乎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然而,这些影片又被看作是必不可少的”⑤[美]埃里克·巴尔诺:《当代纪录电影概观》,载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720页。,这又使得很多纪录电影带有一定的“作者电影”色彩。整体来看,中国纪录电影创作的主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纪录片创作主导力量而存在的政府各级部门。二是作为纪录片创作生产的组织和制作发行机构,这些机构既有国有机构,也有民营影视公司。民营公司试水纪录电影拍摄成为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如2018年获得发行放映许可权的57部纪录电影中,超过70%由民营公司出品⑥数据来自樊启鹏、李瑞化、任伯杰《2018年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电影艺术》2019年第5期,第120页。。三是大量的直接从事纪录片生产的编导人员,这些编导人员有些隶属于主流媒体机构,有些则属于民营公司或有艺术热情和追求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运动中涌现,但彼时他们的作品往往与“边缘”“底层”和“地下放映”等关键词相连,往往只能依靠到国外参赛参展与数量极为有限的观众谋面,再通过媒体报道为人所知。而要逃脱被“地下”的命运,拿到公映许可证,让自己的纪录片进入院线公映,从面向少数人群进阶到大众消费,就要在影片内容、题材和审美上谋求与主流价值观的一致,不能任由无所顾忌的个性主义张扬和铺陈。但与此同时,与故事片的商业逻辑不同,后影院开发使得纪录电影可不完全依赖和受制于票房收入,而是在整合营销战略之下成为产品链条中的一个节点,如纪录电影《生门》虽然在院线公映只获得100多万元的票房收入,但其在电视和网络媒体播放的《生门》系列纪录片却有不错的收视率和收入。有些得到政府机构或企业支持的纪录片也不以商业回报为主要诉求,而是追求形象的传播和品牌的构建。这种现实情形为纪录电影一定的作者性创作的存在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
但即使是由独立纪录片导演创作、作者性质非常鲜明的纪录片要进入院线,也必须并入工业化轨道,迈上产业化的征途。如进入院线公映的《四个春天》(2017年)源自导演陆庆屹多年独自拍摄的家庭影像,但要成为进入院线的纪录电影,仅凭一己之力则难以实现。这种以独立纪录片导演身份安身立命、采用小火慢炖式工作模式的创作者必需告别单打独斗,寻求商业化的团队合作,组建包括制片人、剪辑师、音乐等后期制作团队,以在技术指标上达到院线标准。影片经过一系列更具“电影性”的包装处理后,还要有负责海报创意和先导片制作、路演等事项的营销宣传推广和发行团队。当然这类片子相较于从头至尾在工业流水线上制作出来的纪录电影而言,仍然承载了导演更多的生命体验和细腻的人文关怀,也显示出导演一定的个人化风格。
而不进入院线只参加纪录片展映和比赛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往往囿于经费或资源不足,从前期选题、调研、拍摄到后期的剪辑甚至推广和发行都是一人唱独角戏,由于缺乏他者的深度介入和帮助,导演有时容易陷入自己的思维定式,或无力、无暇把片子做得更精致。
对于近十年的纪录电影来说,创作主体的多元并存已成常态,在工业美学不可阻挡的潮流之下,产业化是主流、是趋势,是对作者式创作的互补。而十年来进入院线公映的纪录电影,不论是阐述国家话语的主旋律纪录片,如《旋风九日》(2015年)、《蓝色防线》(2020年)、《武汉日夜》(2021年)等,或阐述个人话语的独立纪录片如《四个春天》(2017年)、《二十四号大街》(2017年),或产业化语境下的工业化纪录片IP开发如《爸爸去哪儿》(2014年)、《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年)、《舌尖上的新年》(2016年)等,不同创作主体的作品虽异质而可通,均符合主流美学的规约。有学者称中国电影自“90年代起,官方和非官方的界限已经模糊,两方常常互相越界”①张英进:《审视中国:从学科史角度观察中国电影与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纪录电影在这个十年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也使得纪录片得以走进更多观众的视线,同时亦使纪录片的口碑和社会关注度得到以提升。
二、创作客体:小人物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平民叙事中的主要拍摄对象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是消费社会的崛起和大众文化的兴盛,我国的社会价值观总体上出现了从整体价值观到整体价值观和个体价值观融合、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②参见廖小平、成海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此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浓厚的“泛政治化”色彩大为弱化,大众传播的“去政治化”趋势则有所呈现,文艺作品的叙事更多以个人遭际、个人视角来展开,而非仅限于表面上亢奋昂扬的国家话语叙事。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重新进入院线的纪录电影创作客体从过去的英雄、伟人、模范先进、名胜古迹,如《铁人王进喜》(1966年)、《周恩来外交风云》(1997年)、《圆明园》(2006年)等,转变为更关注小人物、为他们代言、让他们被看见。而这种转变自2011年获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映许可证的《归途列车》为先声,这部2009年出品之后在国际上获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伊文思奖和艾美奖等重要奖项的纪录片用三年的时间跟踪拍摄农民工张昌华一家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辗转的辛酸与纠结,虽然此片在“一城一映”中票房表现并不佳,但却仿佛由它而始打开了院线纪录电影关注普通小人物琐碎生活和内心世界的闸门。2011年,同样是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的纪录片《浮生一日》(Life in a Day)在美国上映。在东亚影视圈,韩国的《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2015年)和日本的《人生果实》(2017年)都以平实的记录反映一对年迈夫妻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却以直抵观众内心深处的温情叙事,获得口碑和票房的双赢。地球东西两端这种有趣的呼应也似乎昭示了纪录电影的镜头不仅眷顾风云变幻的政治、经济事件和叱咤风云的领袖与英模,也正聚焦到那些寻常巷陌的平头百姓身上。随之《乡村里的中国》(2013年)、《自行车与旧电钢》(2013年)①此片2013年11月2日首映,后于2018年1月27日开始由大象点映组织其放映活动。、《金色时光》(2014年)、《千锤百炼》(2014年)、《喜马拉雅天梯》(2015年)、《生门》(2016年)、《我的诗篇》(2017年)、《二十二》(2017年)、《四个春天》、《我只认识你》(2017年)、《一百年很长吗》(2018年)、《大三儿》(2018年)、《生活万岁》(2018年)、《最后的棒棒》(2018年)、《大河唱》(2019年)、《城市梦》(2020年)、《棒!少年》(2020年)等纪录电影承载着社会转型期出身草根寂寂无闻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陆续在院线亮相。
虽然有《旋风九日》这样以惊险、悬疑风格来揭秘邓小平访问美国遇刺的重大历史题材纪录影片,有《我就是我》(2014年)这样有娱乐明星加持、由热门电视真人秀节目《快乐男声》作为IP衍生的选秀纪录片,有《舌尖上的新年》(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年)等由人气电视纪录片升级而成、同样有IP效应的纪录电影,有《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2019年)、《五月天追梦》(2011年)、《五月天诺亚方舟》(2013年)、《火力全开》(2016年)等一系列定位明确、主要由粉丝买单的“演唱会电影”,有《我们诞生在中国》这样的与迪士尼跨国合作、虽是中国“面孔”但有多国“基因”②参见冯欣《中国“面孔”与多国“基因”——评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中国“面孔”与多国“基因”系指《我们诞生在中国》由美国、中国、英国联合拍摄,导演为陆川,所拍摄的为中国大地上的动物。、带有一定虚构性的自然类纪录电影,有《共同命运》(2019年)、《港珠澳大桥》(2019年)等国家主导、展示成就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纪录电影,有《九零后》(2021)、《大学》(2021年)这两部分别以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的精英人物为拍摄对象的教育题材纪录电影,但每年不断有小人物纪录片进入商业化生存的院线是这个十年中国纪录电影非常突出的一大表现。这些纪录电影选择那些能够引发普通观众产生共鸣与共情的世俗生活中平凡人的生活境遇和精神诉求,记录他们在各自生活中虽有种种挣扎和不易却依然满怀希望和憧憬的努力。它们从纪录片原来惯有的宏大叙事转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展现,满足观众对近在身边的现实生活进行审美观照的心理需求,对大众关切的、来自真实生活中的亲情爱情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通过纪实影像进行选择和放大,它们也与其他所谓“高大上”的纪录片和充满奇特情节的造梦故事影片形成差异性存在。这些影片的规模化出现契合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党的十八大后又着力重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原则,这是纪录电影作为一种重要视觉艺术形式的时代呼应。
虽然创作客体同是以小人物为主,但与20世纪90年代新纪录运动及之后独立纪录片中以苦难、悲惨为基调的底层叙事不同,这一时期的小人物纪录电影所秉持的是以乐观、向上、豁达、温暖等与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新平民美学,在对小人物生存困境有所克制的纪录中注重诗意的抒发,在普通民众丰富多样的个性化生命体验中发现世俗生活之美、粗粝现实之美,包括他们在困境中如何勉力应对各种不期而至的磨难和无奈但却又满怀希望——如:《四个春天》里父母老年丧女后饭桌上每餐为女儿摆上碗筷和女儿坟前的种植美化与歌唱;《一百年很长吗》中都面临金钱匮乏与亲人病痛折磨的佛山青年黄忠坚和新疆老人阿合特,选择的是“这条路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要走下去”;《生活万岁》被称为“中国版《浮生一日》”,它以15个普通人一年里真实的生活状态为内容,不论是只身一人带孩子开出租的单亲妈妈,还是相互搀扶卖唱的盲人夫妇、将要做心脏移植手术的病人、孤独的护林员等,他们尽管身份卑微、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和坎坷,但都努力而坚强地活着,影片“将他们奋力生活的饱满生命底色,呈现给更大社会范围中无名彷徨的人们”①《电影〈生活万岁〉曝“时代印记版”海报》,手机人民网,http://m.people.cn/n4/2018/1012/c160-11728072.html,发表时间2018年10月12日。。《武汉日夜》告别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宏大叙事,选取医、患、家属及志愿者等几组小人物,记录他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武汉这一非常时期的命运遭际,生离死别的悲怆与新生婴儿带来的希望交织,以小切口呈现历史剖面的细致肌理,以诗意和温情、爱来表现灾难,对疫情中死亡和恐惧的呈现较为克制却动人心弦。这些采撷自生活之流中小人物的故事没有精心设计的戏剧冲突和过度加工的起承转合,没有炫目特效与视觉奇观,只是依照生活自身的逻辑进行温情表达,但却在对发生于你我身边真实生活的铺陈中抵达人心。这种接地气的平民视角和平视精神也让观众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创作者们在这种主流美学和平民美学的合奏中,以影像谱写关于小人物的心灵史和民族志,反映具有时代特质的社会大众民生,亦借此寻找纪录电影更新的动力和活力。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虽然阶级话语已经不再适用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但这些小人物纪录电影在替作为社会结构性存在的普通劳动者立传和谱写赞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现阶段所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社会现象,故有学者认为“中国纪录片底层叙事的观照实际上重构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视野”②罗峰:《“底层”的言说及命名:“去政治化”与重返阶级想象之可能——以中国纪录片为中心的考察与反思》,《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第77页。。而这些小人物身上所充溢的阳光向上的、正能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使纪录电影更好地承担起促进各阶层沟通和理解、鼓励社会发展更加多元和包容的媒介使命。
三、接受主体:内容创作、拍摄资金、放映场次的众筹者和积极参与的互动者
纪录片在政治与国家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观众一般是作为受教育者而存在的,是被动的接受主体。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传媒生态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技术重组了社会的诸多方面,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给民众的互动和参与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平台和渠道,这使得接受主体变被动为相对主动,在影片的内容集合、资金筹措和传播发行层面都可以众筹的方式参与其中。美国学者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在《未来的影像》(Image Future)一文中曾提出“信息美学”(Information Aesthetics)这一概念,把资源共享和信息共建作为数字技术时代的文化所体现出的美学特征。这种信息美学即是当代互联网美学一个十分突出的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也是平民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世界范围来看,2011年由纪录片创作者与YouTube合作推出的纪录电影《浮生一日》就是一部以互联网思维整合全球各地网民所拍摄影像(192个国家和地区、近4500小时视频)的结晶,它标志着世界纪录电影史上内容众筹式纪录片这一新类型的出现。至此,“纪录片的制作过程变成一种高度协作的实践活动”③孙红云:《数字时代纪录片形态及美学嬗变分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50页。,这样一部纪录影片其创作团队由所有参与素材拍摄的众多平民、网络工程设计师、网站管理员和最终对视频进行剪辑制作的执行导演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等共同组成,是一个群体劳动的成果。当然这些视频拍摄者最终也是影片的核心观众,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互联网时代的观众所具有的积极参与和分享互动的特性,而这一群体与以往的纪录片受众相较更为年轻化,在互联网络上活跃的网生代用户占据绝大多数。
时代大潮席卷全球,国内这十年的纪录电影观众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种特性。内容众筹上,虽然还没有此种类型的国产纪录电影进入院线,但无疑这种理念已经触动了一些创作者。2020年春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一部18分钟的纪录短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由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和快手联合,利用77位快手用户的112条短视频剪辑而成,来自民众的看似碎片化的影像拼接成了非常时期鲜活生动且丰富多元的疫区生活影像志。曾执导过《我的诗篇》的导演秦晓宇也在疫情初发后通过互联网络发布了一个类似《浮生一日》的视频征集项目——“余生一日”全民纪录计划,他认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记录者,通过众多普通人记录的方式最大程度地规避了摄制组模式的主观和局限,以其最宽广入微的拍摄,来实现进行真正扫描中国的全景式纪录”①郭靖雯:《〈余生一日〉:一部普通人的战“疫”影像日记》,《四川日报》数字版,https://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200306/232390,发表时间2020年3月6日。。该项目邀请生活受疫情影响的普通人拍摄自己在2月9日任何一时刻的生活片段,很快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人积极报名参与这项活动,最终以全民参与和个人视角完成了一部反映疫情期间中国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纪录电影《一日冬春》上线优酷。2020年10月,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开幕式影片《烟火人间》就是集纳800多个来自快手的短视频而成的纪录电影。这些来自大众拍摄的日常生活印痕经过专业人员的剪辑重组,虽难免有碎片化和弱叙事的不足,但却因其充溢的生活质感和包容众生而成为时代档案中特殊的一页。
除内容众筹外,还有基于互联网络的影片创作资金众筹和观影众筹。借由京东众筹等众多网络众筹平台,金额不论多寡,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可以参与到纪录片项目的资金筹措中去,这突破了过去纪录片仅能依靠有意愿的投资机构和个体进行融资的框限。自《我的诗篇》获得1304个人参与众筹、募集216819元以来,陆续有《喜马拉雅天梯》《二十二》等纪录电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资金支持,这种新的运作模式,使得小投入、资金不足的纪录电影项目得以顺利摄制。这些影片的片尾除了通常出现的各工种名单外,每个参与众筹者的名字也被一一呈现致以谢意。
从影院排片来看,不论中外,作为小众类型的纪录电影在整个电影市场中普遍居于“弱势群体”的边缘地位。虽然2016年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支持下,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联合国内主要电影院线、网上售票平台及电影创作领军人物等多方力量,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作为长期放映缺乏雄厚资金投入宣发的艺术电影的社团组织,以期促进中国电影创作多样化发展。但常被纳入艺术电影范畴的纪录电影尚未形成成熟规范的放映机制,在天然地奉行票房为王原则的电影市场中,纪录电影在院线中依然排片较少。于是,借助于数字技术时代基于互联网络的社交媒体的力量,众筹观影这种由普通观众发起产生的观影方式应运而生,具有相同观影喜好和需求的群体达到影院规定的最低上座率便可包场观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内首家众筹观影平台——大象点映建立,而大象点映的诞生则缘起于纪录片《我的诗篇》导演之一吴飞跃为了给这部纪录电影创造登陆院线的可能。1000场众筹观影行动在中国近百个城市陆续展开,合力把这部描绘打工诗人群像的纪录片送进了院线。之后,众筹点映观影遂成为《大河唱》《二十二》等其他进入院线的纪录电影一种非常重要的寻找目标观众、扩大市场的有效手段,《二十二》甚至以1.7亿元成为纪录电影的票房黑马。“借助互联网的社群效应,这一模式成功地将利益链上的片方、影院和观众高效地连接在一起,这既减少了影片制作方的宣发成本,降低了影片发行的门槛和投资风险,又提高了影院上座率,而且观众分众化、个性化的观影需求同时得以满足”②罗锋、王诗颖:《从隐匿到再生:纪录片“跨屏之旅”的学理审视与反思》,《电影新作》2019年第1期,第85页。。可以说,是来自观众的力量将原来大多以书店、咖啡厅、节展等为阵地的纪录片送进了院线,《我在故宫修文物》更是因为其电视版在B站走红点击量达70万人次,尔后同名纪录电影进军院线。这一时期的观众不再是单纯的、被动的看客,参与众筹之外他们还通过豆瓣评分、撰写影评及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发声等,在接受过程中主动参与影片的意义建构,从而最终对影片票房收入和口碑产生一定影响,他们是对纪录电影有“迷影情结”的一群人。纪录片能够开疆拓土,其播映从电视媒体到新媒体再到电影院,网络时代这样一批参与众筹和积极互动的观众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而这同时也是一部纪录电影观众不断得以培养和增多的过程。
结 语
纪录电影是电影,也是社会生活本身一种艺术化的表现形态。作为与社会思潮律动直接相关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追求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文化动势等时代背景紧密相连。虽然自2011年之后因国家对纪录片的扶持政策,其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其生态还是相对脆弱的;纪录电影的产量总体上虽呈增长趋势,也有像《二十二》这样的现象级影片出现,但最终能走进院线的纪录电影数量仍屈指可数。十年来,进入院线与观众见面的纪录电影对现实、历史和自然类等题材均有涉及,“为行进中国留影、为崛起中国存像”,以其真诚而浓厚的人文关怀向观众呈现中国社会的时代镜像乃至人类与自然界的多样性,获得了日渐提升的社会关注度。在真善美这三种审美价值取向中,由求善求真到真善美并举,在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中愈加注重形式美和艺术性的提升,整体品质相较提高。但对变动不居的转型期中国来说,还需要更多不惧观照现实,甚至是介入现实、勇于批判的院线纪录电影来进行社会历史记忆,人们希望在纪录电影里能够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