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气球飞向天空
2022-05-05邹江睿
热气球就是在我刚睁开眼时猛地出现的。
模样很大,和天空一样,蓝颜色,中间位置点火燃烧,冒出灰褐色的烟。它是从南边飞来的,顺着海风在连绵的桉树林上飞过,像一只飘飘忽忽的风筝,晃悠悠地,打着转落在坡前的空地上。
很难说明白热气球突然降临这里的缘由。或者说,为什么偏偏是这里,而不是其他更加肥沃的土地。
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小芸,不止一回。热气球是她的。当然那时候她还不叫小芸,准确来说,她没有名字。当我询问她时,她靠在篮子沿边,低下头去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很费劲地摇起脑袋。
“没有名字,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她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那你从哪儿来?”我问她。我平生没听过什么不用姓名的去处。
“很远很远。”她说着伸手指过去,“那儿是我完全瞧不清楚的云端之上,有老鹰盘旋的地方。”她告诉我,热气球和她就是从那儿来的。后来我就开始叫她小芸。当然,我晓得,应该叫小云才对,但是她非得改成这个“芸”字。“喜欢草木这类东西,不成吗?”她这样说给我听。
我很好奇她来这做些什么。既无美景,也缺人烟,哪有人没事往这种地方来?
她不回答我,眼睛四下乱瞟,似乎在找些什么,嘴里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飘了好幾天哩!”她边用手拍着热气球篮边抱怨,“带的面包全都吃干净了,现在肚子饿得快瘪下去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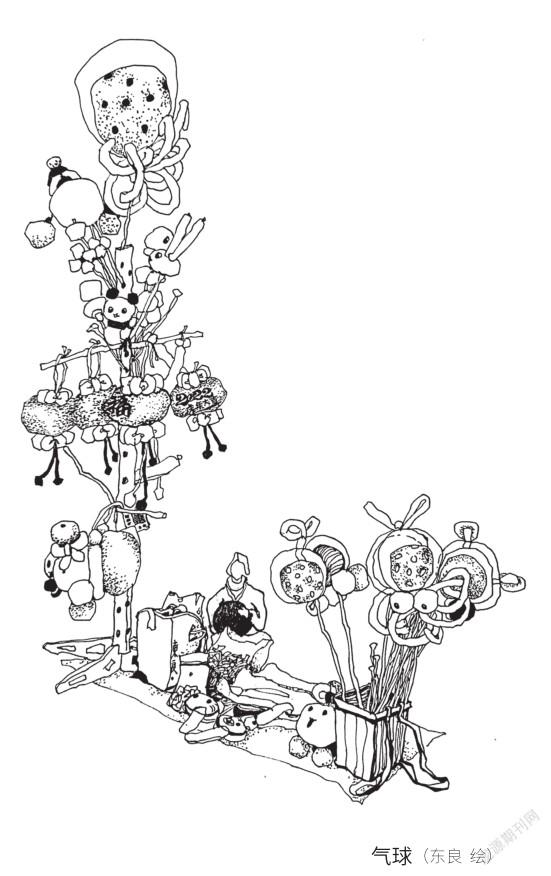
出于好意,我邀请她去家里吃点东西。她欣然接受,推开篮子一侧的门,我趁机仔细瞧了瞧她的模样。说实话,我看不出她的年纪,也许只有十一二岁,也许比我还大,我分辨不出。她说话的语气也令人捉摸不透,自言自语的时候我时常什么也听不懂。我扶她从篮子里下来的时候,摸到她胳膊上冷冰冰的肌肤。它们几乎贴在骨头上生长,我仿佛能嗅到血液流淌时的颤动。这让我又回忆起晴朗的午后,那些抛向空中的细碎的泥土,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幕幕梦境。
我一向喜欢做这种无意义的梦,有关远方、飞翔和天空。我记不清自己是在几岁那年第一次梦见这些的。我只记得那片了无边际的蓝色,一朵望不见瑕疵的云在头顶绽开。那背后深不可测的地方,新鲜的阳光透过雾珠,折射出绚丽,落在我张开的双臂上。那儿的皮肤被晒成褐铜模样,像是姥姥晾在屋子外头的红碎茶,太阳一照,就反射出幽幽黄色。
印象里我不是这样的皮肤,也没见着身边有这样皮肤的孩子。年轻的肌肤向来是水嫩的。我又想起红碎茶旁弓起腰走路的姥姥,每一步都深深踩到泥土凹陷处的姥姥。她才是那样的肤色,和碾成末儿、晒得卷边的茶叶一模一样。
我问过姥姥,我们全家是否都是这种肤色,包括爸妈。她没说话,只拿两只睁圆的眼睛瞪着我,像看怪物。
“他们不在这儿。”她说,“你没必要知道这些。”
姥姥是从不肯和我提及他们的下落的。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没必要知道。我曾经发疯似的在家里寻找有关父母的一切,从书柜的每一个角落里渴望找到哪怕是一根毛发、一丝气息,甚至在静悄悄的夜里,我会趴在水泥墙上,敲击墙壁,听听里头是否传来回声。然而一无所获。没有照片,没有物件,回忆也一概全无。他们存在过的痕迹无证于世,仿佛我生来就是孤儿。
后来有人告诉我,人末了只有两个去处,要么衰老,要么腐烂。在那样的年纪,我不懂这两个词的意义。它们就像我站在土坡顶上遥望大海时那样遥远。然而我却在那时开始做梦。梦里我毫无预兆地变成了干茶叶一般的肤色,皱巴巴,树皮似的随着呼吸起伏。脚趾间,有个什么东西在延展伸长,往泥土深处蔓延。我感觉自己正在变成一棵树,树皮已经长成,根部正在膨胀。它永永远远离不开大地。一棵囚徒似的树。
身旁不远的地方,有人在很小声地喊我。是姥姥。她已经干枯、痩瘪,一片叶子也瞧不见,脚下是冻结的土壤,身前一片了无边际的林木一直延伸到看不着的地方。空气里弥漫一股死灰的味道,我只喊了一句,姥姥便失去动静。她活到头了。而我的牢笼才刚刚落下。
反反复复,我将这个奇怪的梦来回做了七遍。生长、挣扎、渴望离地,然后精疲力竭。我近乎无助地望向幽远的天,看着那儿绽放的云和太阳,想象云端新鲜自由的空气在我的身体里流淌。然而我始终没能逃离那片阴沉的林木。那儿的空气格外浑浊,我在呼吸中逐渐失去了记忆。
每天六点钟一到,夜幕刚刚褪去的时候,我就从那可怖的梦里惊醒。惊醒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自己的身体有没有长出枝丫藤蔓。实际上从那时起的每个早晨,我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分辨梦境与现实的分界。
那一周时间,身体变得格外沉重。午后爬上土坡的过程简直要了我的命。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我每天一定要坐在那大叶桉树下休憩一阵。只有在那儿,身体的疲惫才得以消减,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之处,视野开阔或是空气清新,我只知道自己逐渐灰蒙的瞳孔,唯独在那坡上放出光来。我站在树下,把口腔鼓成球,唱着没有含义的旋律。树顶有鸟儿被惊走,我竭力向它们飞去的方向张望,然而我什么也瞧不见。
一无所获。
那段时间我过得浑浑噩噩,集中不了精神,也不主动跟任何人交谈,整日瞪着一双血丝密布的眼珠神游。午饭一过,就从学校里溜出去,跑到没有人瞧见的山坡上。首先发现不对劲的当然是姥姥。我已经整整一周没有认真吃饭了,浑身泄了气似的没劲。
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她显得很不安,紧张而焦躁,甚至摔碎了手里的瓷碗,双脚在凹凸的地上来回踩,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一周前。我回答。连续七天,一天也没有断过。
嘎吱嘎吱。
摔碎的瓷碗片正在断裂,姥姥的脸上出现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像是在数九天里把人丢进冰窖一样,没错,就是那样的感觉。她一句也没有说,就直直地盯住我。梦里的天空、阴沉的树林与浑浊的空气,还有姥姥变成的那棵死树,她统统窥探,一样也不放过。我感觉她粗糙的手在我的树皮上摩挲,两只脚踩在我凸出地面的树根上,一根、一根,折断我伸向空中的枝干,将它们整摞丢在泥里。嘎吱嘎吱,死去的树枝在脚下呻吟,我瞧见姥姥泄出嘴角的笑。
那以后我明白,这些梦是不能随便说给别人听的。尤其是姥姥。即便之后她再也没有露出过那样可怖的表情,但是我仍时常想起那毛骨悚然的笑容,以及她踩碎树枝时嘎吱作响的声音。
改变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梦境在第八个夜晚发生了变化。我发觉自己的枝干变得格外长,被姥姥狠狠折断的地方纷纷长出新的枝丫,比先前的更粗更大。这是否是某种巧合,我不得而知,但事实的确如此。我感觉梦里的我正一日比一日高大,空气愈发清新,灰暗的阴霾正逐渐散开。有时抬眼望去,似乎有种即将腾空而起的错觉。甚至那些鸟呀雀呀的,也会飞来我的四周,落在树梢上叽叽喳喳。它们此前从未接近过我。
每一夜,我都变成那棵不断长高的树,枝干生长不止,苏醒的我也愈发精神。我的身体再没有像先前那样疲倦过。我感到那里面有东西在燃烧,烧得滚烫,简直要冒出火来。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谁也说不上来。
我更加频繁地跑去那棵大叶桉树旁,有时候想象自己从这扑腾翅膀飞起,逃离这片黑黝黝的大地。也有时候什么都不想,脑袋里的一切全都消失,就那么坐在树下,一整个午后动也不动。
那天是不寻常的乌云天气,大风十分猛烈地从海上刮来,太阳夹在那些疾速掠过的云里,间隔着露出光。两只鹰正逾越光与暗的分界,朝云层彼侧展翅飞去。就在那画面出现的一霎,有种感觉猛地钻进我的脑海,针扎一般,越发强烈而清晰,但我说不上来这种感觉。
嘎吱嘎吱,声音源源不断地从我身体里流出。树后面有动静传来,我瞧过去,谁也没有看见,但我知道是姥姥。一定是姥姥。她正站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死死地盯住我,目不转睛。
天空中,两只老鹰发出尖锐刺耳的啼叫。
从我带着小芸走进家门以来,她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窗外那处半人高的土堆。
我以为她是不会注意到的。那地方到处堆着干枯腐烂的红碎茶渣,阴雨天时,总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夜晚还时常有老鼠爬行弄出的吱吱声响传来,如果不仔细点瞧,恐怕谁也发现不了那儿的土地徒然多出一块。然而它最终还是被瞧见了。
她是从屋子里面,透过正对着院子的木窗户看见那鼓包的。说起来是木头窗户,实际上已经朽得不成样子,风一吹就摇摇欲坠。昏暗的屋子里头到处是这样的家具。缺一根腿的红木椅子,遍布污渍的茶几,整个屋子静悄悄的,几乎没有声音能听见。
“你也没有亲人,对吗?”她望着门外的鼓包,仿佛自言自语。
我想了想,什么也没有说。
既然是自言自语,当然也不存在什么答案,哪儿都不存在。
姥姥去世的那天晚上,也问了很多含糊不清的问题,大部分我根本听不明白。她瘫在木板床的一角,弱小的身体在硬床板上缩成一团,像只被人戳破的气球,皮肤干瘪粗糙,黑成了泥巴的颜色。我一眼就断定,姥姥很快就要咽气了。因为我见过这副模样。在梦境里,那棵姥姥变成的树也是如此的奄奄一息,就这样耷拉着躯干,没多久就死去。
“你恨我吗?孙儿,你告诉姥姥。”她已经几乎张不开嘴。说话的时候,僵硬的手指微微抬起数秒,指尖颤动,仿佛想要抓住我的衣角,但她已没那个力气。
“姥姥给你熬药吃,你别怪姥姥。”她说这话时,我正盯住她的眼睛。那里面有什么震了一下,就一下,但我看得见。
直到最后,我都没有张嘴回答姥姥的问题。惊奇的是,离世之前,已经彻底无力移动的姥姥竟猛地伸出手来,一把掐住我的胳膊,将我死死地往下拽。我惊叫一声,拼命想要挣脱,手腕处一阵剧痛令我皱起眉头。那力度,简直可以拖住一只正要起飞的老鹰。她终究是没了力气。拔出手时,我看见贴近腕骨的位置一道鲜红的血印。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姥姥是从何时开始断定我生了病的。
或许从最初发现我每天做着奇怪的梦时,她就已经觉得我病了。现在想来,她那时急促不安的神情、审视似的目光,似乎都可以印证。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我每天午后穿过一整片桉树林,往土坡顶上前行时,我都感到有人在背后跟着我。是姥姥,毫无疑问。在密林深处,最不起眼的草丛里,一双苍老的眼睛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她的目光企图扒光我的衣服,将我的每一寸皮肤裸露,从我的身体里取走什么无比重要的东西。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那是什么。我的姥姥,从小独自抚养我长大的唯一的亲人,像幽灵一般窺探我的行踪,这简直像倒着写字一样荒唐无比。然而它的的确确正在发生,并且正以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持续下去。
我已经记不清楚姥姥是在哪天傍晚突然开始熬药的。我只想起那天暖和温润的太阳,云层沿着阳光照射的方向整齐排列,我一整个下午都没有离开土坡,坐在那儿畅想自己变成一只海鸥。海面上乌云密布,暗无天日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我展开翅膀穿行其中,简直乐此不疲。
咕噜咕噜噜。回到家里时,一推开门就听见这样的声音。姥姥在厨房里烹煮东西,那是我平生从未见过的容器。泡菜坛子那么大,像是用红土糊上糯米制成,表面因为加热,有水珠从瓶身的裂缝里渗个不停。我在滚滚而起的水雾里瞧见姥姥窃窃地笑,转瞬即逝,很不起眼,但是我看得一清二楚。屋里弥漫一股焦土的气味,我跑进厨房去开窗户,直到这时我才瞧见姥姥正把一整盅的稀泥倒进容器里,用一根铁棍粗的树枝来回搅拌。我瞟见壶里满是热得滚烫的泥水,表面鼓起一个个灰褐色的气泡,然后又在高温的紧逼下一个个爆掉。
“你病了,我在给你治病。”她没有瞧我,甚至头都没抬,就那么一边搅拌泥水一边警告我,用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我受了惊吓,捂住鼻子跑出了屋子,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姥姥熬药。
“你真的生病了吗?”当我跟小芸说起这段经历时,她这样问我。
“我不知道。也许病了,也许没有,我一点也弄不明白。我只是经常做梦,比别人多那么一些。这就是姥姥所说的病。”
“做梦?”
“对,做很奇怪、很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一棵树,所有人都变成一棵树。我不停地长呀长,枝干朝着穹顶之上,躯体尝试着拔起树根,飞向云层深处看不见摸不着的某处。”
“关于飞翔的梦,是这样吧?”她想了想说道。
“没错,关于飞翔的梦。”我重复一遍,“飞上天空,离开这片湿答答的土地,这就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去到那土坡顶上,幻想自己变成飞鸟苍鹰。实际上我根本飞不起来,我的根深深埋进土壤,永永远远也飞不起来。”
听我说这话时,小芸没有反驳。她瞧向窗外面,望着远处的热气球一言不发。我也扭头看过去,看向它投射下的巨大阴影攀附在地面。它真的很高大,比我平生见过的一切都要高大。我想一定是这样雄伟的东西才能够飞上天空,毋庸置疑。
姥姥喂我吃药的那天晚上,我把混杂着沙土和泥浆的药水艰难地吞下去。味道太难闻,以至于中途我无法控制地呕吐了两次。姥姥一直在旁边安慰我,拿着瓷汤勺,一边舀一边和我说话。
“有病一定要治。”她吹了吹滚烫的药,一股死蛤蟆气味随之飘来,“这病是要命的,会死人的,可不是唬你。不吃这药的话,几十天就没了命。”
汤勺伸进我的嘴里,药一口接一口地被灌进喉咙,她当着我的面,头一回说起我的父母。她告诉我,父母亲也得了病,和我一样的病。每天都需要从靠近树根的地方取最为新鲜的一瓢土,丢进冰冷的井水里,煮上整整三个钟头,熬成一锅治病的药。
“生活在荒野上的人们时常会这样不幸。”姥姥说,“从古至今就是这样。它们像瘟神一样在草原和田野间游荡,钻进人们的身体,吞噬灵魂、篡改思想,迫使人们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人们受到蛊惑,尝试离开大地,呵,最后呢,连肉体也消耗殆尽,就这么白白死去,谁也救不了。”姥姥说着就大口喘着粗气,我看见她的脖子上藤蔓似的血管一张一合,像在吞噬什么。
吃完药的那夜,我的身体烧得滚烫。姥姥拿来冰毛巾帮我擦拭,我瞧见自己的皮肤变成难看的红褐色。姥姥说这是在排毒,把瘟神从身体里赶出去,说着就用毛巾在我身上来回摩挲、按压。我疼得快要叫出声来,然而一双手紧紧捂住了我张开的嘴。
我没有做梦。我骤然在那晚失去了做梦的能力。身体里那种燃烧的感觉正渐渐消失,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饥饿。翻箱倒柜之后,我吃光了屋子里所有的麦粒和面饼,把一切能塞进肚子的东西全都吞下,然而我还是饥肠辘辘到站不起身。身体里有样东西被剥夺了,虽然我也说不上来那到底是什么。我干脆窝在床上,把自己用被单裹住,一言不发。好几次我都尝试着让自己重新回到那片梦境,我知道自己回到那儿就一定可以摆脱这种局面。然而它再也没有出现。我像得了肌溶症似的失去了力气,整日里瘫在床上,等着姥姥准点送来食物和新熬好的药水。她像照顾瘫痪病人一样扒开我的嘴,咕噜咕噜噜,难闻的汁水贴着我的食管流进胃里,我感到一阵呕吐的欲望,却怎么也吐不出来。我连最后的这点力气都已丧失。
“乖。良药苦口嘛。”姥姥对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姥姥突然间病倒,已经失去做梦能力的我永远也不会再有机会做梦。
那是她开始熬药以后几个礼拜的事。要不是因为一整天的饥饿而迫使我不得不爬下床去寻找食物,姥姥恐怕当时就没了命。那时我已连着两天没有吃药,身体明显变得更有力气。我把奄奄一息的姥姥拖到床上,她半眯着眼,颤巍巍地指着药罐。
“快去煮药,快。”她喘着粗气说道。
当我毫不理会地把药罐砸碎在角落时,她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和我说话,脸上爬满痛苦的神情。碎片在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姥姥望向地面发出绝望的呻吟。我从来没有从她的嘴里听见过这样的声音。
收拾遗物时,我从姥姥房间一处桉木柜子的夹层里翻出许多东西,几件破衣衫、四处可见的缝补工具、一张红色的胶制大布和几张老照片。衣物看上去都不像是这个年代的产物,上面缝缝补补添了许多处补丁,其中一条灰色的涤卡裤上沾了像血一样暗红色的东西,还有针线残留在修补处没有取走。老照片有好几张,我全都没有见过。其中一张上一个穿着涤卡裤的男人抱着怀里的婴儿和女人合影,他穿的似乎就是柜子夹层里的那件染上血迹的旧裤。他们站在大树底下露出笑容,正是那棵山坡上高高大大的大叶桉树,我一眼就瞧出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击穿我的大脑。我一言不发地瞧着那张照片和照片上的婴儿,就这样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整整一个下午。
那天晚上我终于又一次做梦。距离我上一次做梦已经过去了太久时间,以至于我几乎忘记梦境与现实的不同,想不起那特殊的触感。果然一进入梦里,我就感到身子轻飘飘,仿佛被托在空中。再朝四周仔细一瞧,这竟不是先前梦境里的画面,周遭成片的树林不见踪迹,只看见雾蒙蒙的云在穹顶之下悬浮。我站在麻绳绑成的篮子里,头顶上燃起熊熊火焰,庞大的气球被滚烫的烟撑成椭球状,几乎大半个天空都被遮蔽。这是我头一回梦见热气球的模样。嘎吱嘎吱,木柴燃烧发出干燥裂开的声音。不远处的云层之上两只老鹰正盘旋不止,尖锐的啼叫刺穿一整个梦。
那之后的每个夜晚,我都梦见自己坐上热气球,飞跃云层到达最接近太阳的地方。我和小芸说起这段经历。实际上那时候我从未见过热气球,甚至连照片都没看过一张,直到你飞来这儿,我说,我才算是人生里第一次看见热气球。它在梦里就这么凭空出现了,和你那只几乎没有分别。
姥姥的那堆遗物被我放在屋子一角。小芸翻来找去把那张红色布料拎了出来。
用来做气球皮的,这是。她把它对准阳光瞧了瞧。很古老的材料,已经淘汰很久了。而且上面残缺了几处洞,应该很早就报废了。
它为什么在姥姥的柜子里?我十分不解。姥姥一辈子活在大地上,双脚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土壤。她憎恨飞行,憎恨一切尝试脱离大地的举动,我看得出。她比任何人都更不可能飞翔。
關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从傍晚到午夜,一言不发地想,却找不到任何可能来解释。这种无法解释的事使我头痛欲裂,仿佛有细小的尖针扎进我的头皮。
在那种沉默、痛苦的触感里,我听见黑暗中传来隐约的说话声,像是做梦,却又的确在我耳旁。
“乖。吃药。”她摸着我颤抖的脸说道。
小芸是在冬天即将降临的某个深秋夜晚不辞而别的。
我根本没有来得及和她举行任何道别的仪式。一起身,透过刚刚天明时雾蒙蒙的天气朝外看,那时已见不到热气球庞大的身躯。我发了疯似的跑出去,冲上土坡,对着云端大喊她的名字。没有回应。我知道,她也许再不会回来。
走之前,我曾经送给她一份礼物,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正准备离开。是那棵大叶桉树的一粒种子。我费尽周折才把这颗最大最圆的挑出来,对着阳光瞧过去,竟还熠熠地发出亮光。我翻箱倒柜,从家里找出一个玻璃罐子,把反反复复洗了七遍的种子放进去,然后亲手拿去给小芸。
送给你,最大最圆的一颗。我说。是从桉树上摘来的,树的孩子。
在那之前的几周时间,她一直窝在她那只蓝色热气球的粗绳吊篮里,用树林里捡来的桉树枝排列成竹排模样,把它们垫在吊篮底下来加固。她把自己的手弄得到处伤痕累累,我拿来屋里的白酒给她消毒。浇在她手心的时候,发出嗞啦的灼烧声,小芸轻轻握紧拳头。但她一声也没吭。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开始跟着小芸学习热气球的制作工艺。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会的东西比我想象的多得多。比如迎着海风的树上常常挂有许多摇曳的藤蔓。小芸懂得如何将这些几乎作废的植物编织成坚硬的绳子。又比如哪些果子好吃又能存,哪些树叶可以碾碎了抹在伤口上消炎,她全都知道。
从那些千篇一律的桉树林中她甚至能识别出几种隐匿的木材,并把它们一一斩断,扛在肩上。她扛着木头穿行在丛林当中就像扛着一把宝剑。我在她的指导下也开始认识什么样的木头适合垫在吊篮下充当砝称,什么又可以当作柴火燃烧。在我第一次拿起镰刀亲手砍下一排矮灌木的时候,我不知怎的忽然就记起梦里那些弯曲、延展的枝干。我愣在那儿半天没动,直到小芸拿树枝戳了我一下,我才恍然回过神来,继续拿着镰刀挥向树丛。
小芸将所有材料都备齐是在某个午后。深秋的天气,温度不高,我和她拎着整堆的木材、藤蔓编成的绳和四处寻来的干粮水果,累得浑身流汗。她把拽住热气球的巨大粗绳固定在树干上,不知是幻觉与否,整棵树看上去似乎被提起来,仿佛下一秒就要拔根而起。梦里那些竭力向天空伸展的树的模样在我脑海里浮现。在我回忆那些扭曲枝干和茂密树叶时,小芸已经悄无声息地爬到绳子末端,接近气球顶的地方。她朝我挥舞手臂,我清楚地看见阳光洒在她的脸上。
“那你准备去哪儿,接下来?”我抬起头大声问,云层上传来阵阵回声。
“我不知道。”她摇头:“这事谁也说不清楚,或者说,它压根就没有定论。我也许会一直在路上,直到死去,就是这样。”
“一直在路上,直到死去。”我在心里重复默念这句话,翻来覆去很多遍。我那时还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我认为人注定是要叶落归根的,无论你飞翔在多遥远的天空。
直到很多年之后,在我快要将这一切遗忘的时候,我遇见另一位乘坐热气球遨游天空的旅行者。我和她说起小芸,那个生来就没有亲人的姑娘。
“哦,那个孩子。她叫小芸,是吗?”他望向远处冉冉升起的太阳,“我见过她的,在一个暴风雨将至的前夜。发现的时候,她闭起眼躺在吊篮里,手里紧攥着一颗叫不上名的种子,已经失去了呼吸。”
小芸离开的那天晚上,我做了梦,一个匪夷所思的梦。
奇怪之处不在于无厘头的梦境,相反,这次的梦格外真实。它没有半点浮想联翩的成分,真实到几乎让我分不清这是不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天气格外晴朗,差不多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天上一朵云都见不着。远处成片的桉树静静伫立,最高最大的那棵生在土坡顶上,枝干直直地向上生长,从坡底瞧过去,几乎把半边太阳都遮住。
穿涤卡裤的男人牵着女人往这边走,步伐很轻、很慢,好一会儿才走到坡前。因为他们怀里还抱着孩子,男人伸出手去,把刺眼的阳光挡住,以免小小的美梦被惊扰。孩子睡得很乖,没发出一点动静,细小而愉悦的呼吸声在胸脯间跳跃。
“你说,这小子是不是也在做梦?”男人说。
女人咧开了嘴:“当然,他一定在做梦。我们的儿子嘛,八成也在梦着飞上天空呢。”说完两人的笑声就荡漾开去。
一家三口的身后,老人缓缓地跟着,每一步都在结实的土地上踩下印记。是姥姥。那时候她年轻得多,但她扎实的行走模样却一直没变。
她着实走得太慢了。那对年轻夫妇已经走上土坡,正站在树荫下朝她兴奋地挥手。阳光底下,四处明亮的地方,姥姥朝那儿望过去,笑得很开心,比印象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开心。她也朝他们招手,周遭里升起拥抱般温暖的气息。
男人女人挽着手站在树下,怀里的孩子还在安详地沉睡,姥姥终于慢悠悠地爬上坡来,端起一架看上去很旧的相机给他们照相。快门按下,机身发出抖动的声响,画面被永远定格在一方胶卷里,只有时间还在流逝。孩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哭闹,谁也不知道原因,年轻夫妇一番折腾,竟吵得更凶了。姥姥见状赶紧接过手去,把孩子温柔地揽在怀里,夫妇俩束手无策地站在旁边,这时姥姥哼起古老的歌谣。
潮湿的大地上
幽靈在游荡
树根盘踞石头
杂草肆意生长
蔓延啊蔓延
黑色的泥土里黑色的血液
铺满天空后遮蔽光明
孩子在角落里哭泣
人们把古老的歌谣传唱哟传唱
在土坡的背面,红色的热气球伴随姥姥的歌谣逐渐升起,男人和女人站在吊篮边,朝着地面高声呼喊。它庞大的身躯在地面投下巨大的影子,然后逐渐缩小、缩小,小到谁也看不见的时候,就代表它已飞向天边。
接下去发生的事我几乎一样也记不起来了。梦境变得混乱、颠倒,记忆像倒转的沙漏再也分不清左右上下。发生过的历史正一点点侵入未来,当下这一时刻在那种境地下变得不复存在。我只能想起哭号与尖叫、气球爆炸时清脆的声响、涤卡裤上沾染的血迹和一小片破损的热气球布。
除此之外,还有两只老鹰在高空盘旋,我看得见。它们努力嘶吼,尖锐的鸣叫却还是被扭曲的痛苦掩盖。
整个世界,连同天空和大地一块儿,只剩下无穷无尽的哭泣声回荡,永永远远。
小芸离开以后,不到一周时间我就造出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热气球。
她留下的很多材料我都用上,包括树枝、藤蔓和多余的热气球皮。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在没有图纸只剩记忆的情况下,一点点拼凑出一整只热气球的。记忆里只剩下一些细节,比如首先编好的是竹篮,外头敲上一圈细桉树枝加固,接着是一根根粗过手臂的藤蔓绳子绑在四角上。姥姥柜子里那块残缺的皮也被我缝了上去。我将它缝在整座热气球的最高点,用大浆果的黏液和两颗铆钉牢牢地固定住。那上面破旧的痕迹相当突兀。但我毫不在意。
热气球造好的那天,我看着它仿佛做了一场梦一般。它几乎就是小芸那只热气球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这一只的外皮被染成鲜艳的红色,从远处看过去更加显眼。我轻轻踏上吊篮,晃晃悠悠,仿佛踩在航行的甲板上。
绳子就是在那时突然断裂的。
谁也说不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是我自己解开绳子的。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热气球已经载着我升到比山峦更高的地方。云层就在我的四周,触手即可碰到,空气里散发着一股雨水的气息,我深吸一口气,感受它们在我的身体里流动、吸收,然后消失不见。
我想起很长时间以来一切关于飞翔的梦。那些云端的呐喊、身体的飘浮,阳光顺着缝隙缓缓洒落,我都一一想起。它们和眼前的情景没有分别,一点也没有。
没错,简直像梦一样。
恍惚间,我听见姥姥的声音。她在呼喚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四下里我没有看见她的身影,但我知道她一定在那儿,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瞧着我,目不转睛。父母亲和她在一起,我感受得到。他们互相搀扶,跪倒在地,用最虔诚的方式祈祷,似乎整个世界即将不复存在。
极远的天边,太阳升起的地方,三只老鹰在那儿飞翔、遨游,自由自在。我直直地望过去,冲着光的方向什么也瞧不清楚,只看得见他们的影子翻飞不止,仿佛映在水里。
远处传来悠长的一声鹰啼,刺穿一整个梦。
作者简介
邹江睿,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统计学本科生,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第三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青蓝人才。高中期间开始写作,小说散见于《青春》《延河》。
责任编辑 孙海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