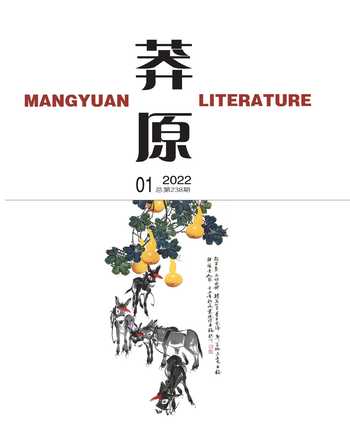白日梦
2022-04-29王小白
王小白
只不过区区一个感冒,就打败了她。
她蹲下身,望着一地彩色胶囊,摸着那些软黏黏的长颗粒,犹豫着。制药厂把它们造得像糖果,它们也像糖果一样诱人。小时候,她妈禁止她吃糖,说她的牙全蛀了,说她不好好刷牙,吃零食对她没好处。她妈是精神科护士,像管理病房一样管理这个家。她一直奇怪,她爸怎么没变成真正的病人——可能他老是出差不在家?谁知道他是不是找借口逃离像精神病房一样的家。
而药不同,它们跟自然博物馆展出的毒蛇、蜘蛛一样,同属干巴巴的动物标本纲、毒物目、药品科、死亡属。她捡起一粒,闻了闻,没有味道。因为感冒,她失去了嗅觉。否则,应该能闻到一点淡淡的苦味,还有胶囊的味道。
她把它们装回药瓶。刚才同男友的争吵让她怒火中烧,筋疲力尽。男友摔门离开时,她把桌上的药瓶扫到地上,瓶盖脱落,彩色膠囊洒了一地。
分手吧。他不看她,看着窗外。
窗外是小区去年才种植的水杉,它们长得很快,树顶已经到达六楼了。他们曾手挽手在树下散步,和那些裂开的树皮交换呼吸。她说,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说。男友嗤的一声冷笑,取下眼镜,眼球往外努,你是不是老师当久了?把谁都当学生?
她想完了,真的完了。这时候,男友在她心里激起的不是怨恨或憎恶,而是一种奇怪的令人战栗的激动,像一杯高浓度黑咖啡流进胃部,结成黑褐色固态,像原油一样缓慢挥发,污染着全身。她应该愤怒,同意分手,找个更好更帅的,天天在朋友圈里晒恩爱,让他后悔,让他求复合;或者穿他最喜欢的红绸吊带睡裙拍照,告诉他,要扔了这裙子了,因为现任不喜欢。
他哪点好?她妈问。
男友高她半个头,是三甲精神病院放射科医生,工作轻闲,每天午休溜圈儿喂院里几只流浪狗,十几只流浪猫。那些猫又生了幼猫,两只住在病房对面,三只住在“当心触电”的绿色粗铁丝网内。周末有轮休。但这些都不是他们在一起的理由。
在他俩感情最浓烈时,她靠着他粗壮结实的手臂在街边等信号灯。看着对面一动不动的红色小人,她想,那就是她,关在小黑屋里不能动弹;而同处一室的小绿人却迈开腿,不讲规矩,没有限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总能成功。她把食指和中指伸进他的衣袖,优衣库的黑色防晒衣里,像昆虫潜入,用长钳掐他手臂上的肉。他哎哟一声,莫名其妙,可是忍气吞声,当成是丰盛的爱意宣泄。
她妈不同意,嫌他不是本地人。
她说他买了车了。什么车?一辆十多万的领克。没听说过,而且他没房子。母亲把他的情况摸透了,跟同科室的同事在医院附近一个小区合租一小套房子,养了一条金毛。那只尚处于幼犬期的金毛晚上会叫,常常引起邻居投诉。他认真跟同事讨论要不要去给金毛做个声带切除手术。叫了几天,金毛发现铁石心肠的主人还是不让它进卧室,就认命了,低沉地哀哀呜咽,用爪子刨门。
她倒了两粒胶囊在白里透红的手心,胶囊立刻黏紧了皮肤。她想把药放回药瓶,胶囊在手心抖了几抖,不甘心地被剐了回去。
脏了,不能吃了。可是,不吃挨不过今晚。母亲值夜班,拿药要等她明早回来。
两人吵架是因为她要查他的手机,他不给,结果,手机掉在地上,iPhone12的屏从中间裂开。他说,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考虑要不要继续。语气像窗外的水杉那样冷静。从那时起,她又开始服药,各种安眠药镇静剂。
等了两周,他还是没联系她。
她出门淋雨,做最后挽留。夏天,南方雨多,时大时小。她出门时雨小了,淋在头上觉得脏,就用衣服帽子兜住头。经过一座桥,桥下有条青灰色的脏水河,可能属于护城河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支流,上面架着粗大的可以走人的水管,去年漆成了黄色,在一片葱绿中格外刺眼。
河边有人垂钓。只要有一个小水塘,不管水多臭,都会有男人在上面架起钓竿。一位看不出年龄的男人穿着灰蒙蒙的雨衣,目光忧郁深远,若有所思地盯着沸腾的水面,似乎溶化在了雨中。他用钓竿划出了地盘,她没有理由驻足河边,只好缓步向前。
叶心深绿叶廓暗红的红李树掉了一地残果,还挂在树上的果实也长不大了,很快会落到地面,成为盛夏一景。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孤零零地倒在雨中。回到家,手臂凉了,手心还是热的,这样不行,她打开淋浴冲冷水澡,又打开空调,调到16度,一个喷嚏接一个喷嚏地打了起来。量了几次体温,分别是37、37.2、38.2。体温升到38.2度后不再上升,她在无印良品的蓝色条纹床单上躺下,给他发微信。
我生病了。重感冒,发烧了,好难受。她拍了一张水银体温计的照片给他。额头好烫。鼻子堵了。她继续刷屏。长短不一的绿色长方形小条像诗一样一行一行地排列下来。少了回复,DNA双螺旋不再进行有序的绿白缠绕,显得异常孤独。
她发了一张红李树烂果子的照片,像在给文字配图;又发了一张雨中的天蓝鼠尾草,这些草被雨水泡软了,关闭了铃铛。原先给他发过阳光下的鼠尾草,那些蓝紫色花冠在风中发出幸福的风铃声,像家养动物特有的娇憨的笑。她想了想又问,囡囡怎么样了?
囡囡就是那条金毛,一岁大的母狗,刚做了绝育手术,她有两周没见到它了。它喜欢把半圆形脚踩在她的鞋面上,伏下半个身子等待她的爱抚,再伸出牛奶布丁般的舌头舔她。她一直以为自己宠物过敏,母亲说的。她小时想养狗,或是猫,兔子也行,羞怯的雪白柔软的小绒团,沉默地缩在笼子的最底端,多可爱啊。母亲以她动物过敏为由拒绝了。
他没有回。等到吃晚饭,在内心的反复煎熬中她已经绝望了,想着要不要提前吃药,以度过这难熬的一晚。她把药瓶拿出来放到床边,凝视着。这时,听到了敲门声,她戴上口罩去开门。
绿色小人微微弓着背,两只外八字松松地套着耐克拖鞋。他还是来了。
取下来我看看。
她取下口罩,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椰子油味。
你刚刚和谁在一起?她想问。这个问题一诞生,就在胸中踉踉跄跄,冒到喉咙,像引发不良反应的呕吐物。她扼住喉咙制止它出来,深呼吸,用舌尖抵住下颚,怕它不小心泄露,毒死他俩。
不用问,就算不问,她也知道是谁。这些椰子油分子常年与灰尘产生化合反应后附着于客厅、卧室、卫生间、沙发垫子,所有的遥控器罩子,还有母亲挂着的粉色发帽上。一个德国大众品牌,Balea护发精油,深层滋养修复受损发质。母亲自五十岁后一直烫发以保持头发的厚度,用4号染发剂,淡褐色或是亚麻色,根据光线起轻微变化。
开始,母亲只是买粉色蕾丝纸巾盒,后来在淘宝抢到一双打折的粉色拖鞋,尴尬地解释说只有这个颜色了。母亲身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粉色,睡衣,运动鞋,运动裤,防晒衣,背包,粉框太阳镜,发帽。
她穿莫兰迪色系,性冷淡风,灰度很高的粉,不是母亲那种少女粉;她不用香水,过生日他想送香水作礼物,她说自己香水过敏。她有一个漂亮实用的鼻子,能分辨多种不同的植物,曾令大学老师啧啧称奇,想收她做硕士研究生。她妈不同意,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不好找男朋友,让她赶紧毕业,找个稳定工作,最好是公务员,当老师也不错,有寒暑假。父亲在她高考那年出了车祸,母亲瞒着她独自去了父亲出事的城市办理后事,等她高考完才告诉她。工作后,她去医院找母亲,母亲在忙,她和一个老护士闲聊,才得知当年和父亲一起出事的还有一个女人。两人是去参加一个会议,为什么在开会时间出现在离会场很远的旅游景点,没人知道。父亲酷好钓鱼,说不定是去钓鱼。可是有女人喜欢钓鱼的吗?蚊虫,臭水沟,阳光下的暴晒。她跟父亲去过一次,蚊子叮了她一腿包,皮肤晒伤了,最后只能待在车里等,车子散发出闷死人的车载香水味,一波一波地打头,她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回的家。母亲怪父亲怪了一个星期。
没和谁一起。
你撒谎,我闻到了。
你不是感冒了吗?
他抓住了她的逻辑漏洞,把粉色旗子插上了她的发顶,像给她戴了一顶粉色发帽,从色彩上污染了她,把她的莫兰迪色系彻底抹杀了。
没错,每次感冒,她都会丧失她引以为豪的嗅觉,什么都闻不到。她喜爱的食物,撒着细长椰丝的费列罗,日式咖喱,浓稠的罗宋汤,血红的番茄酱,香水柠檬,百香果,他衣服上洗衣液混合着阳光的味道。她枕在上面睡觉,睡得特别好;还有他的手臂,她埋在他热乎乎的粗糙掌心,好像他第一次捧着她的脸,惊叹好软好嫩。她深深地吸气。有研究说人们靠气味寻找伴侣,不知道别人如何,但她绝对是这一挂。她常看着囡囡想,要是它失去嗅觉还认识她吗?她感冒了,成了失去嗅觉的囡囡,不再爱他,不管他怎么对她,她只冲他疯狂吠叫,安抚不了。
她想利用感冒,结果感冒成了他的同盟。
我们分手吧。他挺直后背,像窗外的水杉一样直,又取下眼镜,擦拭镜片。屋外下雨,屋里气温高,眼镜起雾。闻不到他的味道,她心里充满疑虑。
你吃晚饭了吗?她一天没吃,开始胃以疼痛的方式提醒她,后来就放弃了。感冒了更没胃口,胃丧失了感觉。
她想给他煮点吃的。她进厨房拿陶瓷锅,放到灶上。
不用了,我马上走。
她像没听见一样,继续放水。水从龙头冲出来,打在米上,形成螺旋星云。她淘米,开火,煮粥。她想问他去哪?是不是去找我妈?你跟她约了吗?但她没问。更多的话积在喉咙和下颚处,也许感冒导致了扁桃体发炎。幼年时她几乎一感冒就扁桃体发炎,像一个习惯。母亲反复询问医生要不要切除扁桃体,得到的都是否定答复。她想其实是堵住了,如果能随心所欲地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可能就好了。十二岁时,她写过一段时期的日记,大概有两个月。日记本封面蹲着一只放电的皮卡丘,里面堆砌着那些她当面说不清也不敢说的话,一层一层精心地码,用涂改胶带修改写错的字。结果引来母亲更多暴跳和电击似的怒吼,之后是委屈的哭泣,我一个人带你容易吗?要是现在,她会说丧偶式育儿,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
她在厨房守着粥,听到他轻轻带上大门,打湿的拖鞋在地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她才想起他没回微信,一句也没回。她刚才又忘了问,囡囡还好吗?它一向活泼好动,手术后就不能动弹了,应该乖乖地躺在她买的狗窝里,那款狗窝和她的床单一个色,蓝白条纹。他跟她分手,会不会把狗窝也扔了?然后按新品味给囡囡换成粉色的狗窝?想想也没什么不好,粉色更适合俗气的金毛。也不光金毛,狗都是俗气的,总是跟在人身后摇尾乞怜。
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她揭开白陶瓷盖,让粥透气。粥没有像往常那样散发香气,是的,她感冒了,什么也闻不到。为了再次验证这一点,她进入卫生间,对着母亲的毛巾吸气。他说得没错,她不可能闻到椰子油味。她去医院等母亲时,听他们聊到过一个专业名词,幻嗅,说有的精神病人能闻到一些不存在的气味,通常是毒药,煤气,或其他怪味。
两周前,椰子油味进入她的大脑,占据了里面的每一个细胞,像黑色原油入侵了蔚蓝色的大海。
她往粥里加了兩勺白糖。母亲嗜甜,她去南方上学后爱上了咸粥,回来后就嫌母亲炖的银耳羹腻,红烧肉甜,烤麸咸。要说原汁原味,还是粤菜。她的大学老师会煲汤,猪脚,鸡爪,配一些她不认得的中药材,食物的香气和药的苦味从厨房向饭厅弥漫,包围了年轻的她。再炒个菜心,加一点生抽,够两人份。他给她盛饭,用木勺在电饭锅里转一个圈,盛到碗里就是一个白色星球,再洒几粒黑芝麻。你们广东不是重男轻女吗?她很惊讶。
母亲每周给她打电话,不停问她有没有交男朋友,说不要在外地找男朋友,外地人不好,催她回家;又问她睡得好不好,一个宿舍七八个女生,要是有一个人打呼那可怎么睡。她坐在老师的阳台上,心不在焉地嗯嗯,从十四层楼看着远处的暮色,远方流动的灯河。老师新买的小区房,周围还没有太多人住,小区内一片死寂。老师开了很久的车才到达,又花了很长时间煲汤,等吃好饭天已经黑了,坐在阳台的木椅上,有种荒凉的快感。
父亲刚走,母亲或许很寂寞。虽然父亲常出差,可是家里有男人跟没男人还是不一样的。父亲不在时,每逢睡觉前,母亲总要检查床下,仿佛下面藏着人。去上夜班了,就把门反锁,反复叮嘱她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开门,不管她是八岁还是十八岁。她想问着火了也不开吗?但看着母亲担惊受怕的脸,又咽了回去。
母亲喜欢说梦见她死了。从小说,一直说,觉得会有可怕的事发生在她身上。直到父亲死去。
阳台的玻璃门开了,老师端着两杯咖啡,一模一样的白瓷杯,杯身轻盈,握柄光滑,光闻味道就知道哪杯是她的,奶更多更甜的那杯。老师喝黑咖啡。他把握柄朝向她,意示她小心烫。她用两个指头捏住细白的长柄,碰到了他的大手。他抖了一下,白咖啡跟着荡漾,热蒸气扑到老师眼镜上。老师眼中的她,一定雾蒙蒙看不清抓不住,所以不再费力去抓。毕业后,她听同学说他叫过很多学生去他家吃饭,叫他们报考他的专业。
她按母亲的愿望当了教师,教初中生物。因为不是中考必考科目,一到复习阶段,课时就被主科占用,甚至期中考也不例外。由于沉默寡言,她在学校里存在感不强,同事说起她,常说就是那个她妈妈做的食物很好吃的女老师。工作一年多,大学老师结婚了,很快有了一个女婴。满月时,在朋友圈里晒全家福,晒他给老婆煲的烫,是她没见过的新品种,黑白配,椰子炖乌鸡。师母圆眼长脸,刚生产过就恢复了身材,看着像师妹,也有细长的白瓷似的鼻子。那时,她才产生了强烈的想交男朋友的愿望。
她去医院找母亲,经过那棵合抱粗的银杏树,看缤纷的落叶在秋风里旋转,玩一种炫目的特技,她停下来拍照。这时,看到他捧着一大袋猫粮在喂流浪猫。棕色的爱心形小饼干撒了一地,四五只流浪猫围着他喵喵直叫。她想给学生做教学素材,换了几个角度拍落叶,怎么也拍不好。这实在太难了,她抱怨。我拍的有视频。他说,并给她看手机,问她要不要,他可以传给她。她把脸凑过去,闻到他的衣袖气味。植物在阳光下晒干了,野菊花混合着鼠尾草,密密实实一整个草坪。她觉得要是能躺在上面睡觉就能睡个通宵。那时,她失眠已有两年多,大学毕业也有三年。开头她以为是洗衣液的关系,换了洗衣液,但是不行,还是失眠。奇怪的是,上大学时七八个人住一个宿舍反而不失眠,一倒下就睡着了,梦都不做,听同宿舍的说有人打呼有人说梦话还感到诧异。上班一年后,她经常要到晚上一两点才能进入浅睡眠,而且容易惊醒,迷迷糊糊去看床底下,好像床下真的有人。早上五点就醒了,打开窗,植物的气味争先恐后地攀爬进来,撞进她的鼻子,像匕首,一直刺入心脏,她忍不住默默流泪。
她想就他吧,气味相投。
没想到母亲不同意。
他哪点不好?你宁愿我吃药吗?
母亲没回答,还是照常给她带药回来。
她想把药扔了,从六楼往下扔,完成高考那年未完成的壮举。当时,她就想把所有的书本从教学楼上扔下去,随着那些成片的欢呼,所有衰败的干墨枯纸纷纷扬扬地坠落,象征着一个残酷季节的结束,成人生活即将开始,这是她的成人礼。可是,还没有扔下去,她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问她考完了吗?考完马上回家。她有些不快地追问,怎么了?母亲说,你爸出车祸了……
粥又开始吐泡。小区池塘里养着数条锦鲤,大约有几十只,太挤了,那些锦鲤不得不定期游上来换气,特别是在下雨前,一大片鱼唇探出水面,蔚为壮观,那些嘴唇一张一合,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像默片。
此时下钩最好。父亲喝下小酒,偶尔会传授一些钓鱼秘籍给她。她以为自己早忘了,可这些话却时不时冒出头来,提醒她曾有过一个父亲。
要是父亲在,会喜欢男友吗?只要是有人愿意陪他去钓鱼就行吧。出差,钓鱼,父亲在这两件事之间来回切换。他死后,母亲把家里十几根钓竿全扔了,父亲的形象也越来越淡。交了男友,她不再时常想起父亲,好像算是给了他一个交代,他也不来打扰她了。老鱼沉到湖底,不再上潜。
睡眠好转,人生圆满。她开始买化妆品和裙子,把眉修细,按男友的品位打扮自己。同事说她变漂亮了。有双眼睛关注你,不是看你脸干不干净,头发整不整洁,衣服穿得够不够。她觉得自己像受宠的猫,开始学习撒娇,体内的小红人试着动一动,试着把脚趾探出去,搞一些违禁的事。
两周前,他说加班。囡囡刚动了手术,她给它带了狗罐头。他住的是新建的小区,近来种了绣球,一种叫雪球的品种,大朵的粉色与淡蓝遍布整个花坛,欣欣向荣。还有一些零散地栽在路边,看着就不像同类,而像另一个品种。电梯安静地上行,没有广告。他同事开的门,两人租的两室一厅,他住次卧,同事住主卧,多付一千元钱。囡囡带着伊丽莎白圈,没精打采地侧躺在客厅的狗窝里。她用小勺喂它罐头,它也不是很感兴趣,给面子似的吃了两口。
他同事个子很高,大概1米88,长相憨厚,留着一圈漂亮的胡子,说单位发了电影票,有多余,要不要一起去看。
电影院就在附近,十分钟路程,两人并排下楼,出了小区,站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黑色高跟鞋使她高了五厘米,看上去只比同事矮一个头。银色纱裙上的亮片在红色灯光下微微反光,像山谷间闪烁的瀑布。春天的夜风有点凉,她上半身只穿了件黑色长袖T恤,高个男生问她冷不冷,要不要他的牛仔外套。她笑着侧身,看向马路对面——突然,她那惬意的微笑凝固,慢慢僵化,像注射了肉毒杆菌。
同事急速回头,也看到了,很尴尬,替她尴尬。他说了一堆话,她一句也没听见,只看到他胡子下的厚嘴唇在她眼前动啊动,像下雨天浮上来换气的鱼,像卓别林的哑剧。后来她才想到,同事应该不知道那是她妈,只是看到他搂着一个中年妇女,而他的女朋友站在他的身边。同事可能说了什么替他打掩护,她没听见,也不好意思再问。你刚刚说什么了?两人继续往电影院走。
到了电影院,同事让她选片,她站在几幅电影海报前发呆。他说要是没有想看的,就回去吧,他送她。她家远,坐公交要半个小时,还要走一小段路。
这次她听见了,固执地说,看!然后也没看名字和内容介绍,指着一幅视觉冲击强烈的红蓝海报,上面有一对男女相拥的黑色剪影,說,就这部。
放映厅熄了灯,她没注意放的什么,内容乱七八糟的,无非就是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心里的红色小人在蠢动,她伸出脚趾去够他,刚碰到那双45码的白色运动鞋,他立刻把脚往回收。她的心凉了半截,红色小人安静下来,不再妄动。
出了影院,他说送她;她说已经叫了美团打车,两人微笑着挥手作别。上了车,司机向她确认手机尾号的后四位数,她竟然想不起来。司机踩下油门,说是不是4137?她说对的。把头向后转,看到他也正向后转身。她刚才为什么不再试一次,让他退无可退?就像那次在老师家,如果她胆子再大一点,老师可能就是她的了;那些三口之家的相片,那个肥胖的婴儿,椰子炖乌鸡,黑白配,就属于她了;那个荒凉的小区,堆满专业书的书房,流动的灯河,就是她的一生。
有可能是误会了。他只是陪她散步,不小心搂住了她粉色的单薄的肩,感受那绵软小巧的温暖;也许她在哭诉,劝他另找佳偶良配,不要耽误自己女儿,眼影和眼线弄黑了眼眶,泪水冲掉了粉底,拉扯着细小的皱纹。那些粉色和泪水让她看起来不像慈母,而像迷人的寡妇。谁知道呢。她不知道,她要证据,给他定罪或宣告无罪。他不给,她摔了他的手机。他说她触犯了他的底线。真的吗?到底是谁触犯了底线?不是你和那个粉色女人吗?
今晚怎么过呢?夜色像个贼,偷偷溜进房间,偷走了光明。她把房间的灯打开,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脸色发青,是不是她体内也有个绿色小人在向她呼救?想脱下红色外套,逃出黑色禁锢?
胶囊脏了,但里面的药粉是干净的。绿色小人拆了一双一次性手套。这种手套外卖送了很多,母亲精心收好,放在厨房最上面的抽屉里。绿色小人把胶囊用小剪子剪开,把药粉倒在餐巾纸上,白色粉末堆积成白色尖顶,像小小的富士山。粥咕嘟咕嘟,像巫婆呼唤宠物,小亲亲蟾蜍,自己跳进来吧。绿色小人把白色魔粉倒进锅内,用白调羹慢慢搅动,白糖晶体溶化在粥里,那些药粉也不见了。
绿色小人坐下来,安静地等待母亲回家。小时候,她半夜醒来,靠在黑暗中等待妈妈短促的脚步声敲打心脏。钥匙叮当响着,急切地撞击铜锁,插入,亲吻,绞成一团的内脏松开了。有时,红色小人会鼓起勇气冲下床,按开日光灯,白色的光充盈整个房间,恐惧像潮水慢慢退却。在光亮中,红色小人又能睡着了。
看了看时间,母亲还有几分钟就该到家了。
门开了,母亲放下玫瑰色的铂金包,换上少女粉拖鞋,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按下洗手液瓶子,挤出粉色液体,按标准程序洗手,再从粉色纸巾盒里抽纸擦手。
她起身拿碗,打了一碗粥,端到饭桌上。母亲还在卫生间。她靠在卫生间门上,说:“我煮了粥,给你打了一碗,放在桌上了。”
母亲对着浴室镜子看自己疲惫麻木的脸,没有表情地嗯了一声。
她知道她知道了吗?她有一股冲动想问。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喜欢什么,你就要破坏掉?你们接吻了吗?他摸你的脸,会不会摸下一手粉底液?会吃掉你的口红,皱眉说味道怪怪的吗?他会不会伸手进入你垫着厚海绵的垫子,发现你根本没胸,说,哇,就结了两颗樱桃?他会看着你的粉色高跟鞋,说,红色好看,然后家里就多出一个什么都是红色的女人,红睡衣,红裙子,红色高跟鞋,红色铂金包,红框太阳镜,红色发帽。
母亲坐到餐桌前,拿起调羹搅了搅,舀起一勺粥往嘴里送。
“脏了,别喝了。”她体内的红色小人冲出来,抢走了粥碗,把粥倒回锅里,然后全部傾入马桶。她按着按钮不松手。在水流旋转向下的瀑布声中,她听见母亲气愤地说,你又发什么神经?吃药了吗?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