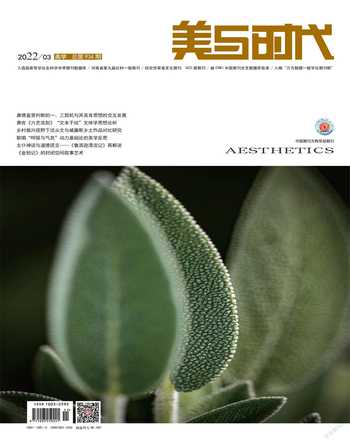主仆神话与道德谎言
2022-04-27吴雨婷
摘 要: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塑造了鲁滨逊与星期五这对完美主仆形象,他们代表了英国清教伦理中的主仆范式。主人鲁滨逊以上帝之名统治着他的仆人,仆人星期五则以基督之徒的虔诚臣服于他的主人。然而,完美主人潜意识中的自我是孤岛国王,理想仆人的外壳下难掩其工具属性及他者本质。笛福虚构的这一主仆神话背后是主人的伪装与仆人的牺牲,借由鲁滨逊的诡辩笛福编织了一个关于主仆神话的道德谎言。
关键词:鲁滨逊;星期五;主仆范式;道德谎言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笛福与仆人问题研究”(2020XKT652)阶段性研究成果。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以下简称《鲁》)开启了英国小说的大门,历经三百年的历史涤荡,俨然成为文学史上的神话。20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对《鲁》进行了后殖民重构,对其解读及批评也大多从后殖民视域展开,鲁滨逊与星期五逐渐成为英国文学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白人与黑人、驯化与顺从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主奴原型。但跳出后殖民的文化语境,回到鲁滨逊与星期五的故事本身,这是一个主仆的关于创造、爱、教诲和征服的故事。保罗·亨特认为,鲁滨逊的荒岛历险“利用简化的背景来提醒读者注意不同层次,即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之间矛盾关系”[1]。受后殖民理论影响,我们逐渐忽略了鲁滨逊与星期五最为单纯直接的那层关系——主仆关系,这一关系是18世纪英国日常生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关系之一。笔者试图从仆人星期五形象入手破解笛福的“密码”,即他如何将本应是用道德和资本奴化他人的故事,塑造成这一主仆关系的神话,以及笛福的道德谎言又暴露了“主人”们何种阶级意识,遮蔽了仆人们怎样的隐形生命史。
一、理想仆人与家仆之德
笛福在《鲁》中虚构的仆人们大都符合其理想仆人的设定,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清楚顺从及忠诚是身为仆人的基本准则。星期五出现之前还有一位仆人值得一提,他就是鲁滨逊逃离摩尔海盗的控制时遇见的少年苏里(Xury),他本可选择将苏里杀死,但是其顺从和忠诚使鲁滨逊放下了象征暴力的枪支,“这少年微笑的脸庞和无辜的话语让我不得不相信他;他发誓对我忠心耿耿,愿跟我去世上任何地方”[2]73。面对潜在的野人袭击,苏里对主人说:“假使有野人来,他们吃掉我,你走掉。”[2]74同样,星期五更是不止一次用夸张的姿态以示忠诚。鲁滨逊的自述中常有类似表述:“他(星期五)终于走到我的面前,这时他匍匐在地上,吻了吻地面,把头贴在地上,他把我的一只脚捧到他的头上,似乎要发誓终身做我的奴隶。”[2]207“他(星期五)一看到我,就朝我奔来,再一次匍匐在地并做出种种让我觉得好笑的姿势,表明他对我的感谢心情和唯命是从的态度。”[2]209在后来一系列英国小说中,好的家仆一定带有顺从及忠诚的“主旋律”,苏里与星期五为这一众仆人形象确定了基调。
结合笛福撰写的“仆人行为指南手册”(Conduct Book for Servants)便可窥知这种顺从及忠诚的来源,某种程度上,这些手册直接“引导”了小说中仆人的具体行为。《鲁》中,笛福有意地放大并强调了仆人对主人的顺从,匍匐在鲁滨逊面前的星期五无疑是宣扬这种仆人美德的典范。除此之外,星期五还是勤劳朴实、信仰虔诚、自我牺牲等家仆之德完美践行者。鲁滨逊教星期五种庄稼、开垦荒地、打猎、做船,“星期五在干活的时候不仅非常认真,而且总是心甘情愿(willingly)”[2]214。不仅如此,星期五还欣然接受鲁滨逊向其传递的宗教观念,成为一名基督徒,鲁滨逊甚至坦言,“这原先的野蛮人,现已是虔诚的基督徒了,而且比我虔诚得多。”[2]220在危险面前,星期五更是显示了仆人的“崇高”,当鲁滨逊问星期五是否愿意同他一起战斗时,他总是给予同样的回答:“主人,你叫我死,我就死。”[2]227如此,原先暴烈的野蛮人逐渐修炼为忠诚的理想仆人。鲁滨逊将星期五视为仆人的最高标准,笛福意图利用这个虚构的仆人形象给18世纪英国仆人们树立道德楷模。
然而,理想仆人外壳下的星期五真实的自我究竟如何呢?鲁滨逊甚至从未问起过理想仆人的真实姓名,与其说是仆人中的道德楷模,不如说星期五代表了英国仆人们的工具属性及他者本质。星期五的出现似乎是上帝的旨意,他在那孤岛上等待着鲁滨逊的拯救,最终这个可怜的野蛮人成为主人逃离荒岛的工具。鲁滨逊确实教会了星期五许多事情,目的是使他成为有用的、使用方便很有帮助(useful,handy and helpful),以便包揽以前他在荒岛上所有的活儿。[2]212-214星期五的到来让鲁滨逊在劳动上得到了全然解放,他和当时英国主人们广泛雇佣的一种全职女仆(maid of all work)类似,在主人眼中她们不过是减轻劳动的工具。星期五的到来极大地缓解了鲁滨逊身处荒岛的孤独,他不再苦于无人说话而只能以猫狗为伴,但身处“主仆伊甸园”中的星期五却仅仅成了主人逃离荒岛的工具、减轻劳动的工具、消解孤独的工具。同样,回到现实世界中,18世纪的英格兰,仆人作为当时数量最大的职业群体,不过是主人们的廉价工具而已。雇主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将仆人視为“机器”而不是人,他们通过房屋设计、安排工作时间和住所等举措,将用廉价工资购买的各种“机器”变成服务于家庭的“隐形工具”。由此,仆人被物化,成为雇主家庭中永恒的他者。
二、完美主人与主仆范式
与理想仆人星期五相对应,鲁滨逊则成了完美主人的代表。笛福在《下层人的伟大法则》中论述了18世纪英国仆人问题(The Servant Problems) 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是愚蠢的主人造就了游手好闲的仆人。的确,像是孩子的行为反映了家长的行为一样,仆人的德行往往被视为雇主德行的象征,18世纪的英国,家仆之德等于主人之德。表面上看,鲁滨逊对待仆人确实表现出了主人之德,尽到了主人应尽的义务。他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关心和教导着仆人星期五,给他衣服穿,使他改掉吃人肉的恶习,学喝羊奶、吃面包及盐,考虑他的住处,教他打猎,说英语,乃至信仰上帝等各方面的文明习俗。鲁滨逊称,“他(星期五)对我的那种感情,犹如孩子对父亲”[2]211。鲁滨逊确实为不知如何做主人的18世纪的英国人提供了示范,这也是笛福赋予鲁滨逊在道德说教上的另一重隐含期待。
然而,在鲁滨逊主人身份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更大的野心,这位完美主人潜意识中的自我,始终是一位国王。尽管鲁滨逊在其自述中竭力将自己美化为一位完美主人,但与仆人星期五相处的过程中,显示更多的却是君主对奴隶的权力。在最初流落孤岛之时,鲁滨逊内心甚至有一丝喜悦,因为他想到:“这里全归我所有,我是这里至高无上的君王(King and Lord),对这岛国拥有绝对主权;如果我有后代,我可以毫无问题地把这主权传下去,就像任何一个英国的领主把他的采邑原封不动地传下去一样。”[2]131鲁滨逊不断暗示自己的国王身份,当星期五真正加入他的孤岛王国时,所谓的王国和君主才有了实质的意涵。正如黄梅所言:“标志贵族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词句反复地在鲁滨逊的思想和叙述中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他本人、他的创造者和那个时代的奋斗者们刻骨铭心的念想。”[3]因此,某种程度上鲁滨逊潜意识中的国王身份是18世纪英国主人阶级内心权力欲望的折射。
确定星期五的仆人身份后,鲁滨逊便把自己幻想中君主的绝对权力施加于星期五。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以自我为中心,他是主仆王国的绝对掌权者、主仆契约的规则制定者、仆人生死命运的决裁者、仆人行为的发号施令者、仆人思想的精神控制者。相识之初,鲁滨逊甚至都未曾问起这位仆人的真实姓名,而是直接给了他一个看似十分有意义的名字——“星期五”,“因为我正是在星期五这天救了他的性命,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天”[2]209。在卡罗· 凯看来,“星期五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鲁滨逊专制权威的象征。”[4]鲁滨逊教星期五说的第一个英文單词是“主人”(Master),然后告诉他要用“是”和“否”回答,如果星期五违背了他的命令,鲁滨逊便可杀了他。现实世界中的主仆契约,在星期五那里成了“生死契约”,仆人被解雇的代价之于星期五则是生命。匍匐在主人面前的星期五、愿意为主人献出生命的星期五、竭力取悦主人的星期五,利用自我的牺牲成就了小说中的主仆范式。
一直以来,鲁滨逊被视为“资本家的原型”或“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5]68,他荒岛历险的神话也成为资产阶级成长过程的写照,成为一个解析英国资产阶级价值理念建构及权力建构过程的阐释性神话。在鲁滨逊与星期五的主仆神话中,鲁滨逊是多数资产阶级主人阶层的代表,这个主仆神话是他从主人阶层的角度出发,以荒岛为场景、以征服为动机、以拯救为借口、以情感为掩饰,借由重重诡辩,编织的一个“主仆伊甸园”的故事。主人鲁滨逊带着他的仆人星期五走上“神坛”,而这一切都是笛福尽心策划的结果。
三、主仆神话与道德谎言
在笛福的主仆神话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关于仆人星期五的自我表达,关于仆人的一切似乎都是主人的自圆其说。主仆神话中,一方是来自欧洲的文明人鲁滨逊,另一方是来自荒岛食人部落的野蛮人星期五,凭借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笛福为其诡辩找到了第一重依托。已有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鲁滨逊与星期五的这种身份对立,或认为,鲁滨逊与野蛮人的相遇使得他得以与他者对话,进而完成了文明人身份的自我确立;从欧洲或西方文明角度,鲁滨逊将食人看作文明的对立面,将食人部落看成人类堕落的表现,但又夸赞食人部落的原始天真,是为达成基督教化和文明教化的理想。笔者认为,作者从主仆关系的角度,一方面,利用鲁滨逊文明人的身份显示主人的崇高,为主人权威的实施埋下伏笔;另一方面,利用星期五的野蛮人形象为仆人群体创设一种粗野、愚昧的刻板印象,借以反衬主人的魅力,利用文明人的优越性达成对仆人的绝对控制,借以文明对野蛮的驯化促成主仆神话的谎言。
除了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上帝是笛福实现其诡辩的另一重依托。在星期五身上鲁滨逊贯彻了那种“神的旨意”,在拯救星期五的过程中他瞬间成了“此岸上帝”,仆人则成为“尘世耶稣”,星期五对主人的服从等同于对上帝的服从。用麦克尔·麦基恩的话来说:“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这种必然的隐喻关系很快被直译为社会政治从属关系,带着这种信物,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统治不再具有比喻意义。”[6]笛福同时代的批评家卡尔斯·吉尔顿也在其讽刺著作《D先生的生平与奇异历险》中提及鲁滨逊的种种“捏造天意”之举,显然,吉尔顿早已意识到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借上帝之名进行的一系列诡辩。在与星期五的相处中,他将上帝的权威内在化,借“神的旨意”达成了主人的权威,进而达成了家庭神权统治的理想。
主人鲁滨逊的国王野心和仆人星期五的工具属性及他者本质,暴露的是主人的伪装与仆人的牺牲。18世纪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仆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严格的、基于契约的工资关系。然而,契约关系是用制度的和工具的而不是情感的词汇来表达,主仆契约的本身就预设了主仆伦理对于家庭的经济价值而非情感价值。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更多是以“誓言”而非真正的“契约”为纽带,“誓言”凸显了主仆之间强烈而深刻的情感联结,但也掩盖了物化仆人的具体行为。鲁滨逊与星期五在荒岛上共同度过了三年时光,鲁滨逊称,星期五是他“知恩图报的朋友”,认为星期五对他的那种感情“犹如孩子对父亲”,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星期五都会舍命救他。与星期五相处的三年是他最为快乐的时光,“达到了人所能享有的十足美满的幸福(complete happiness)”[2]220。在主人的情感伪装下,仆人星期五的牺牲似乎是理所应当也不值一提。来自野蛮人世界的他在那荒岛上等待着鲁滨逊的拯救,他无处可逃,除了当一个忠仆之外也别无选择,星期五早已将家仆之德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和行动指南。用瓦特的话来说,在主人鲁滨逊眼中,似乎星期五的“社会本性、对友谊和理解的需要,完全可以被正常的赠与、感激的收条、仁慈而又不需要花费什么的恩赐态度所满足”[5]70。大部分时间里仆人们被要求保持沉默,沉默是身为仆人的重要美德。因此,仆人的奉献和牺牲便理所应当地被遗忘,在主仆情感的掩饰下沦为主仆神话的献祭。
在星期五的自我牺牲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仆人群体的牺牲。18世纪的英国,对于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来说,仆人是职业上的唯一选择,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方式。那些真正的完美的仆人们一生都藏匿于主人家庭的一隅,没有爱情、婚姻、孩子,朋友很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人生价值可言,她们的全部人生意义都在于献身于主人。在上帝安排的等级中,仆人们大多因出身卑微而理所当然地被置于社会最底层,和星期五一样生而为仆,别无选择。对于当时英国社会的仆人来说,宗教顺从和社会顺从这两者并无区别,而所谓的社会顺从旨在告诫仆人们安守自己的仆人身份。至此,当主人成为“上帝的使者”时,当仆人愿意承认自己“生而为仆”时,当社会在这种严格秩序的约束下不再有流动的可能时,笛福理想中稳固的社会秩序终于成为现实。
四、结语
约翰·理查蒂《笛福评传》的引语是:(笛福)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谎言家,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家。在鲁滨逊与星期五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主仆关系的神话,然而主仆神话或许又是笛福的一个道德谎言。更重要的是,神话与谎言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段关于18世纪英国仆人们的隐形生命史,他们的故事从一位叫星期五的仆人开始。
参考文献:
[1]J. Paul Hunter. The Reluctant Pilgrim:Defoe’s Emblematic Method and Quest for Form in “Robinson Crusoe”[M].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6:127.
[2]Daniel Defoe.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M].W.R.Owens ed.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
[3]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7.
[4]Carol Kay. Political Construction: Defoe, Richardson, and Sterne in Relation to Hobbes, Hume, and Burke[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87.
[5]Ian Watt. The Rise of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and Fielding[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6]麦基恩.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M].胡振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86.
作者简介:吴雨婷,江苏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