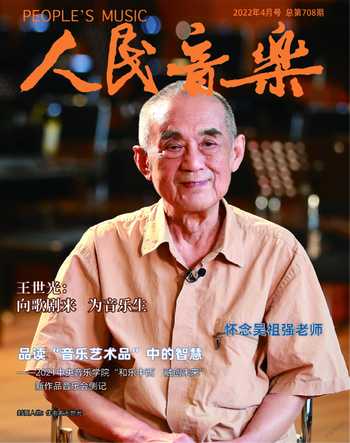共性-个性-可能性:权衡中的探寻
2022-04-27杨其睿
维冬初,以“和乐中西 融创未来”为主题的管弦乐和民族室内乐新作品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歌剧音乐厅中接连两个周末分别上演。两场音乐会终了,坐在台下,任凭脑海中充盈着适才涌入的音响,我若有所忆。
2021年深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承办的“中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上,众多音乐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的讨论中,尤记得作曲家郝维亚的一番言论令人印象深刻。郝维亚的发言以“创作中的妥协”为主题,抛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基于自己的创作历程提出“妥协”的概念——这种妥协并非贬义,而意味着融合、折衷,意味着一种宽容的心境和中庸的智慧。作为一名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专业作曲家,他“不得不”在一系列的矛盾:古与今、中与西、个体与社会之间不断妥协,在妥协中实现进步。
我想,不若用“权衡”来称谓作曲家口中的妥协,或许更为适宜。在我们的社会中,凡是被称之为智慧的事物里总包含着某种权衡。对于政治家来说,智慧在于权衡各利益群体的利弊,在社会的矛盾中寻找发展之道;对于军事家来说,智慧在于权衡战场上的关键要素,战胜对手取得胜利;对于厨师来说,智慧在于调和五味,在酸甜咸淡中权衡,取之适宜以餍口腹。那么,对于一名作曲家来说,智慧也正在于权衡之中。这种对权衡的感知绝非郝维亚一人的偶然之思,它反映出中国当代专业作曲家这一群体对于其职业身份和时代境遇的自觉与选择。郝维亚的发言在与会作曲家中引起的热烈反响,无疑更加确证了这一想法的普遍性。
中国当代专业作曲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群体。作为艺术家,他们追求个性以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他们渴望纯粹主体性的宣扬,通过创造音乐作品,在超越客观现实的感性世界中表达与实现自我。而作为其从事的领域,作曲又为他们赋予了一种独有的价值追求:可能性追求。作曲(composition)作为一种诞生于西方的艺术活动,生来就伴随有某种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起源自18、19世纪的西方,并随着西方音乐范畴的扩张在全球的专业音乐创作中被普世性地树立。它以不断拓宽音响形式的可能性作为自身的发展逻辑,驱动着作曲家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已树立的范式与边界,在追求音乐可能性的过程中延展自我的可能性。此外,更重要地,作为时代和民族的儿子,这个群体又肩负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和使命,并在当代中国的一切基础上展开创作,回应时代的需求,由此获得了文化语境下的“共性”。由此,共性、个性和可能性构成了一组相互制衡的三角命题。处于中国当代专业创作的语境下,任何一名作曲家都自觉或不自知地在创作中“权衡”着这组命题,并试图以音乐作品给出自己的答案。
如今,那场精彩的研讨会已经过去了一年有余。一年之后,中国当代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作曲家们究竟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怀揣着这样的好奇,我走进了歌剧音乐厅。两场音乐会中,作曲家们向听众呈现了十二种各辟蹊径的“回答”。这十二首作品的作曲家群体横跨数代,从“50后”到“80后”,成长背景也各有所异。他们的创作既颇具代表性地展示了中國当代专业作曲家这一群体的观念和共识,又彰显出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人基于自身经历与处境所作出的选择与权衡。并不夸张地讲,这两场音乐会堪称中国当代专业作曲家群体一张生动的群像,它集中地展现了这个群体在共性、个性和可能性命题下权衡中的探寻。
于梦石的管弦乐作品《长青马》以宏阔的意境拉开了第一场音乐会的帷幕,其中浓烈的民族色彩和恢弘的声势给我以最初的震撼。作为“80后”的蒙古族青年作曲家,于梦石在这首作品中选择拥抱本民族的文化,将蒙古族的传统音乐语汇交响化,并用西方管弦乐的编制加以演绎。作曲家格外强调大提琴和打击乐的使用,以营造出草原的音乐色彩。首席大提琴使用了两把不同定弦的琴,其中一把将D弦调成E弦,造成纯八度的音响效果,以接近马头琴的音色,悠长延绵,如同原野上穿透苍茫岁月而来的长调。打击乐则为整个音乐赋予了生命的脉息,在弦乐和铜管的悠扬流淌间骤然激起,形成音乐性格的强烈反差,并伴随着大提琴的独奏片段穿插进行,铸就了该部作品的强大张力。与音乐会中其他作品相比,《长青马》的音响呈现并不给人以意外之感,于梦石给出了一个更接近于传统范式的回答。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即使这是一场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音乐会,我也希望作品不仅寻求复杂的技术,也应该与不同的观众群体都产生共鸣。”相比个人话语和音响可能性领域中的探索,身为青年作曲家的于梦石显然更希望通过对于共性的表达,在相对传统和原生的音乐语境中实现与听众的沟通。为此他在宏大的交响乐编制中融入本民族的语言和气质,并藉以诉说那片辽阔草原上的故事。
同样是出身于草原文化的作曲家,秦文琛以舞蹈组曲《伶伦作乐图》向人们展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探寻途径,他将寻求灵感的目光投向了中华民族的远古神话。《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黄帝命乐官伶伦创制音律和乐器。伶伦寻求心中的声音,离开中原来到大夏之西的圣山昆仑,在那里,他被凤凰的啼鸣所吸引,为大自然中的天籁而沉醉,遂分别十二律、调和五音,以为音乐之始源。在这部作品中,秦文琛彻底抛弃了传统民族音乐语汇的使用,转而以极富个性化和幻想力的音乐语言表现了这段古老的传说。《伶伦作乐图》的题材内部即隐含着对“前音乐”时期古老、遥远的声响的追求。为体现这一音响追求,作曲家选择摆脱既成的音乐素材和结构原则,以非范式的语言,更本真地展示了他在纯粹音响世界的审美追求。仿佛追溯数千年时光,秦文琛回到了和伶伦相同的起点上,只是凭借人类内心所固有的对声音之美的追求而创作,将一个作曲家内心对音乐的敏感而深刻的感知借由远古神话故事的画卷,徐徐呈现在听众面前。
在这种几近纯粹的音响追求下,一切被使用的声音都超越了其原有语境的局限,成为表现作曲家意图的手段。整首组曲中,有两点设计令人大为惊艳。其一,秦文琛颇具独创性地用木管乐器摹拟泰国鸟笛的声响,以象征神话中凤凰的啼鸣。这种极具穿透力而“非常规”的音响效果以结构性的地位贯穿始终,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它赋予整个作品一种自然与野性的舒张,使其超脱于交响乐所固有的工业化色彩。其二,在组曲的中间段落,秦文琛使用了长达四分钟有余的持续性单一音。以A为核心的单一音块持续流淌,仿佛混沌中初生的音响秩序,在不变中变化,在沉闷中生机涌动,于管弦乐江河般的绵延中取得深邃而雄阔的气势,令人心神震慑。单一音的设计体现了秦文琛在音响可能性中的追求。单一音技法和十二音技法相对应,标志着音响组织结构原则上的两极。后者意味人为控制的极端秩序,每个音都置于理性的设计之中而获得呈现,处处体现着计算的精密和逻辑的严谨;单一音技法则在音响呈现上更贴近于东方的哲学思维和音乐语言,它是顺乎自然的、非理性设计的,更倾向于展现音乐的时间意向。
在《伶伦作乐图》的创作中,秦文琛以宏大孤旷的单一音作为背景,铺陈复杂细腻的节奏和音高装饰,赋予音乐以脉搏和变化,在单一音的阈限中实现变与不变的统一,可谓颇得“审一以定和”的传统美学意蕴。他抽离了表达中国题材的传统要素,代之极富个性化的音乐语言。为这种语言所使用的语汇被抽离其原生的文化语境,在作曲家的设计下重获新的意义。然而,这种新的意义又不得不根植于作曲家所生长和承载的共性文化背景。一方面,伶伦作乐的故事本身就深有中国神话的色彩,给音响的设计与构思提供了独特灵感,并作为共性文化的具体体现为作曲家和中国听众架构起理解的桥梁。另一方面,秦文琛笔下极富个性的单一音技法,亦深受中国哲学和民族音乐的启发,从而内含独特的文化气质,区别于西方简约派作曲家笔下的单一音技法,并以此突破音乐的可能性边界,获得了作曲家所獨具的风格标识。可以说,秦文琛的创作展现出这样的一条探寻路径:向传统文化乞灵,以共性融铸个性,再用个性为矛打破固有的范式,最终实现音响可能性的突破。
另一部向“传统”乞灵的作品是贾国平的《琴况二则》,这部作品根植于中国古代的文人精神。《溪山琴况》是晚明时期的琴学巨著,堪称古琴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仿照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架构,徐上瀛总结出了古琴艺术的二十四个审美范畴,作曲家选取了其中的两个范畴加以描摹。管弦乐组曲《琴况二则》由贾国平在2021年新创作的《太和》与他1998年在德国学习期间创作的《清调》组成。早在上世纪末的《清调》中,贾国平独特的探索途径就已经初露端倪。在这部作品中,贾国平一方面汲取了琴曲《广陵散》的音高素材,设计了颇具民族色彩的十二音音列,使作品整体具有五声性的旋律特点;另一方面,又有意规避了显著、重复的节奏,如同琴曲中常见的散拍子,让音乐在严谨的设计下呈现出玄秘的意境。同时,作曲家用竖琴、钢琴和低音提琴拨弦分别摹拟古琴的不同音色,以制造古琴音乐所独具的气韵。以上种种设计,在源自西方的十二音技法和管弦乐编制的基础上,赋予了音乐以独特的个人色彩和中国音乐的鲜明标识。而在《太和》中,贾国平则更进一步,与秦文琛的做法类似,他在这部作品中也对传统的音乐素材进行了更为彻底的解构,得其意而忘其形,将具体的感性标识化为抽象的气质弥散在音响构筑的意境之中。“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而和至矣。”贾国平以技法与意蕴高度融铸为一体的音响,使听者怠其细微而得其气势,直指作曲家心中所向往的审美境地。
相较于秦文琛的《伶伦作乐图》,《琴况二则》无疑更富有中国传统文人音乐的审美气质。与其说向传统乞灵,毋宁说作曲家将个性视为通向中国古老文化共性的途径。在创作中,贾国平似乎在检验这条途径——以个人创作为纽带,用现代音乐的形式来表述、来接续中国音乐所独具的审美旨趣和文化意蕴。他抛却了民族化的音乐语言,又凭借民族的美学和文化意蕴在自由而自我的音响领域中描绘中国音乐的可能性。从这一点来看,贾国平和秦文琛的探寻是异径而同工的。
与贾国平向传统文人精神寻访的道路不同,郭文景以民乐六重奏《寒山》展示了另一条十二音技法的可能性道路。作为一名极富突破意识的作曲家,郭文景曾称自己创作的每一首作品都试图解决某个问题,《寒山》当然也不例外。在上演前,他就自己的作品做了简短的说明。在这部作品中,郭文景意在实现两个目的:致敬和追缅对他影响深远的两位作曲家——勋伯格与罗忠镕;探索十二音技法的可能性。勋伯格所开辟的十二音技法为调性瓦解之后的西方音乐提供了重建秩序和逻辑的方式,罗忠镕则将十二音技法加以中国化,赋予其中国音乐的审美气质。这两位先辈作曲家的创作成果给郭文景以颇深的影响,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罗忠镕的中国化十二音技法毕竟是在设计序列的时候,就把中国音乐的音级特征或素材设置其中,而郭文景的野心却在于“用勋伯格的音列写出中国山水画的意韵”。一方面突破罗忠镕所建立的传统,寻找十二音中国化表达的新途径;另一方面则解构勋伯格《一个华沙幸存者》序列的本身含义,用同一个序列写出远非同一个情绪和色彩的音乐,以此展示十二音技术风格上的包容性,并将其提升到“元规则”的更高层面。
在《寒山》中,既已排除了音列中的民族语言因素,郭文景通过中国化的音乐结构思维和器乐音色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就前一方面而言,郭文景更多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描绘性思维,重在意境和场景的渲染,同时打破了十二音技法中音与音之间的孤立处境,将基本的单一音连缀成为音腔,赋予其逶迤曲折的韵致。就后一方面而言,民族乐器的音色本身就构成一种共性的文化符号。《寒山》引子中,几声孤疏的管钟,如夜风呼啸的笙,宛如山中鸟啼的梆笛与曲笛,点描出独特的文化意境,让人不由被牵入张继《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情中去。郭文景充分运用了民乐表现自然声响的长处,用音色编织出自然山水的审美意境。现代作曲技法和中国民乐犹如一对天作之合,民乐中自由而多变的音色表现力,较之西方管弦乐在工业化下造就的统一性,反而更契合现代作曲技法在音响表现上的要求。而大量民乐特有音色和演奏技法的使用,也使得《寒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色彩,区别于任何一部外国作曲家用十二音技法创作的作品。如此,郭文景在可能性的探索中实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用极富个人色彩的语言触及了中国传统音乐更为深层的审美气质和文化意蕴。
同前面的作品相比,陈欣若的《倾杯乐》虽是最后出场,却显得格外轻松、豁达。《倾杯乐》取自唐朝教坊曲名,在创作中,作曲家也依据自己的想象,展现出了唐朝兼收并蓄、从容自达的文化风貌。陈欣若在这部作品中对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音乐进行解构-融合-重组,皮黄腔的曲调、古琴的吟猱、奔放的鼓点等多元风格的材料被并置在统一的织体中,各不妨碍,彼此衔接,相互贯通,构成崭新而流畅的整体。东取西引,全然股掌之中,令人深感酣畅淋漓。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作曲,《倾杯乐》中带有一定“自由即兴”式的发挥,作曲家为音乐构造了一个由散漫到热烈的半开放结构,让不同风格的音乐自由地在其中轮番舞蹈,呼应出一面生动的“声音景观”,其背后反映出作曲家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声音“调色板”。陈欣若对多元音乐风格的接纳和探索在中国当代专业作曲家群体中堪称独树一帜。从早期《探个够》《颐和园华尔兹》等作品中对不同音乐风格模仿与融合的尝试,到《尽觞》《色俱腾》中依托传统而蓬勃挥发的个性与想象力,在横跨中西、并立雅俗的写作探索中,陈欣若逐渐找到了一条“大象无形”的音乐可能性之路。在这条路上,他以从容的姿态和赤子般的好奇拥抱音乐风格的广阔世界,超越隔膜和标签尽情地挥洒笔墨。如此看来,陈欣若选择以唐朝教坊乐为题材并非偶然,在《倾杯乐》中,他向人们展示了一种超越风格阈限的音乐互动的可能,这种可能性的背后是一种自信而开放的时代心态,一如他笔下所描绘的盛唐气象。
限于篇幅,本文只选择了十二部作品中的五部稍加以展开评述。在我看来,这五部作品颇具代表性地展现了中国当代专业作曲家在权衡之路上的探寻,体现了这一群体在共性-个性-可能性命题中的思索与选择。他们以清醒的身份认知和执着的创新意识探寻着独属于自己的艺术理想,而在这些各领风骚的艺术理想背后,我想,还有一个更为宏观的时代风貌已然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中国专业音乐创作迄上世纪初兴起,便背负着“道路”的使命。音乐创作不仅仅被看作是艺术活动本身,它被视作一种文化象征的高度,而与国家的出路,民族的前途休戚相关。百年之前,王光祈振臂高呼:“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从那时起,这份使命就如同一面神圣的旗帜,吸引无数音乐家前赴后继,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而奋斗,从而铸就了我国百年以来历程艰辛而辉煌的近现代音乐史。这份历史与国家的使命一直赓续至今,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文化认同的大国,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势必要接过这一极具历史感的旗帜,在名为“中国音乐”的文化认同中接受世界和本国人民的评判,在古老的文化传统和先辈的成就中探寻自己的可能,并由此思考中华文化的进路,书写属于当代的中国音乐史。
这种共性的文化传承,是中国专业音乐创作所特有的羁绊,这种羁绊既无形地规定着作曲家的创作,又为他们提供了一片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田野。两场新作品音乐会中的几乎每部作品都从这片广袤的田野中取己所需,它们从多元的角度展现出,在作曲这项属于全人类的文化事业上,中国当代专业作曲家这一群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可能性意义。而这种可能性意义的具体体现,便是每个作曲家在自己创作的音响中所展示的个性。于是,郝维亚“创作中的妥协”言内之意逐渐明了,不是别的,正是共性、个性和可能性这三点中的权衡,在权衡中,中国当代专业作曲家们深入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以寻求自己的可能,并通过个体的探寻以启示中国音乐的道路,这正是“和乐中西,融创未来”的题中之义!
(本文获中央音乐学院首届音乐评论比赛一等奖)
杨其睿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20级本科生
(责任编辑 李诗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