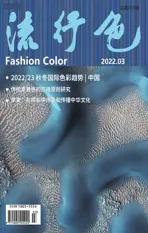绘画中的幽暗与澄明
——以透纳为例
2022-04-25方赞茹
方赞茹
中国美术学院专业造型基础部 浙江 杭州 510000
一、与光之交汇
自从古希腊学者将艺术的本质解读为“自然的模仿”,后续者包括诗人,画家,雕塑家们便忙于对此定义进行验证,修正甚至升华。作为“行者旅人”的透纳在经验山呼海啸,日月星辰的行程中,他找到了与雪莱不差累黍的来自于神的灵感,他们常驻燃火的海面,凝望波涌筑起的云山和绽出一丝眼珠的太阳。绘画模仿诗歌,诗歌模仿音乐,音乐模仿诗词,“模仿的模仿”这在艺术家的创作经验中很常见,而观察者的共鸣来源仍然指向同一个境域世界。为了观察风暴,更好的模仿自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1775-1851)请求水手们将他捆在船的桅杆上,在被风浪击打了四个小时之后,仍然没有想下来的意思,为的是把眼前所见和感受记录下来,透纳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面对自然的力量中表达光与色,自然界的光影在他的作品中变幻为绚烂的色彩与抽象的形态。
长期以来,在列奥纳多•达•芬奇明确规定了光照的性质并验证其对绘画起决定性作用后,照明光总是起着艺术模仿和显像的揭示暗的能动性,能够以“适合意图的显像”产生出雕刻,建筑,绘画艺术“自为地实际构成的东西”,其对象实际聚集于主体的眼目之中,视觉为一切事物的万能裁判,作为主体的人具有类似太阳般赋形的能力。而西方的“风景”观念直到18,19世纪之后画家才有投入到现实之景去感受人与自然交融的经验,此时,从柏拉图以来的非感觉的、理式的世界进入到可感觉的世界,画家们开始走出画室,直观自然。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将自己捆绑在了船桅上驶入狂暴中的海洋,与船只共同接受袭来的风暴与骇浪,在经验所得的《暴风雪-汽船驶离港口》再现中(图1),巨大的漩涡正吞噬着随浪欲坠的船只 ,让人难以辨认眼前所描绘的具体物像,然而却又如此真实的再现了浑浊晦暗与熠熠生辉之激烈的自然动态转变的过程。他对色彩的使用往往控制在两到三种冷暖色,暴风雪中席卷着呈蓝绿色的浑浊的气流,远处一道暖橘色在四周暗淡的氛围映衬下放射出格外耀眼的曙光,似一团灼热的烈火将金色化作团团云朵出现在广垠的天空中,死亡般静谧的海面时而升腾起迷雾般的蒸汽,抑或呼啸着狂风席卷暴雪,万象笼罩于大有吞没宇宙之势的悲怆悒郁的黑暗意象之中,他似乎一味的执着于创世的过程,如同万物皆不可分的原始浑沌处于上帝的灵光运行的一刻间,在“大自然明暗的映衬”下发生着这样的情形:黑色的暗影与似火般的光亮在撞击中交汇,迸发,暗影里搅混着血液般的红色,其中缠绕着被丢弃的奴隶尸体,以及分食中的鱼和鸟,难以分辨的形骸在幽暗里若隐若现,等待揭示。

图1 透纳,暴风雪-汽船驶离港口,布面油画,91.4cm×121.9cm,1842年,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
像这样对于不具备鲜明轮廓含糊不切确的描绘在透纳的画面上极为常见,“抽象的模糊性”为透纳展开的自然帷幕呈现出空无的虚幻感,黒兹利特曾为透纳的作品留下这样的评论:“空无一物的画作,像极了。”关于“空无”的力量同样出现在同为浪漫主义者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774-1840)的作品中,相对于透纳在光色使用上充斥着动感,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在色彩与造型的渲染上显得寂静且阴沉,色彩的使用尤为节制、内敛,如《海边的僧侣》(图2),铺陈在远处的蓝灰色光线,黑色凝固的海水如一块磁铁般具有吸附力,靠近海岸线的天空越发沉郁幽暗,面对这黑色景象的是伫立于岸边的僧侣,在画面中显得渺小而含糊,除此之外空无一物。

图2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布面油画,110cm×171.5cm,1810年,德国柏林阿尔特国家画廊
正如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rl K1eist,1777~1811年)对此作的观后感:“由于画中的单调与无止境,只有一个框架作为前景,别无他物,这让人觉得,似乎他的眼皮被割掉了,空旷无物。”画面中无限延展的天际弥漫着奇异的寂静与冥想,黑暗处呈现宇宙的表征,那是来自原始的幽冥深处,生长于天与地混沌未开的原初域,无边的虚空奏出的悲怆曲调大概是弗里德里希在自然中获得的超验的冥思默想。
透纳在表达光辉时具有炉火纯青的色彩技巧,他常用一种氧化铁橙色,比一般的天然土质颜料饱和度高,在混合其他颜料时使得覆盖区域整体发暖,通过将浓厚的颜料涂抹在画布上,经笔刷的洇开,使得画面形成四处弥漫着光辉的印象,这样的景象可以在作品《小帆船靠近海洋》中见到,如图3,金色炫目的光芒几乎占据了画面绝大部分,左下角的小帆船在焦褐色海岸前隐没了形体,只有从在暖橙色背景下显得格外亮白的三道笔触那可以辨认出迎风撑开的船帆,在强势炫目的一片光晕中更显得摇摇坠坠,整体充斥着透纳典型的旋转与闪耀的光色表现,而色彩产生于光之交汇之处。正是从英国画家透纳开始,色彩的地位在欧洲的绘画中开始变得越发显赫,也因此透纳成为了19世纪印象派描绘外光色彩的先驱。

图3 透纳,《小帆船靠近海岸》,102x142cm,藏于伦敦泰特美术馆
二、遮蔽与澄明
浪漫主义者柯勒律治认为“自然是有生命的”,一旦将自然理解为充满神圣者的领地时,这种自然观已经取代了静态的物自体观,正如诺瓦利斯认为的:“如果上帝会成为人,那么他也会成为岩石、植物、动物和自然环境,或许持续的救赎以这种方式存在于大自然之中。”这种超验自然观强调体验者游于天地之间,融入宇宙,迷失其中,与自然合一。那么,与其说透纳借自然光照再现了平静的晨光,炽烈的午光,幽暗的夜光,暴风雨中的光,海葬上的死亡之光,不妨说在捆于船桅上穿越光与暗的经验中,透纳避开了物理性的“照明光”与暗影给定过程的联系,任其自然之光在无限与自由的精神意象世界中绽开,自行照亮。
在自然界中,万物的形状原本实际就已圆满,显现着形状的光和影附着于原本就已存在的事物上,而后者的圆满并不依存于自然光的介入与否,哪怕藏匿于深深的幽暗之中。光的出现更像是一种揭示,它使除光自身之外的对象事物得以显现,包括暗影。暗影自黑暗而来,因光照而出现,本身以一种遮蔽的状态自持却使事物以各种形态,距离,界限,圆整等差异而为人的视觉所接收,正是这样的一种显现方式使得在绘画里,“光与影以及它们所有的不同程度的细微分别和最微妙的转化却属于艺术材料的要素,它们把雕刻和建筑把原来实际情况表现出来的东西只表现为适合意图的外貌。
光与影,对象在照明中显现为饱满圆整的东西的过程,都是通过艺术而不是通过自然光来产生的。自此,光分解为明与暗,黑与白,甚至色彩在画面中形成统一体进行交互作用,光亮与暗影无法割裂各自独立存在,光亮受到黑暗的侵蚀而变暗,同时微光却也穿透和稀释了暗影。而色彩在透纳营造的光影世界里,已然脱离传统的理式世界里为明暗服务的程式,同时也没有依循牛顿发现的三棱镜原理的科学光谱规律,色彩的表达更接近画家进入可感知的世界里,冥契自然后的自行显现,画面中荫影处同样保存着光明的颜色,而光明的颜色中却也隐匿着幽暗,色彩在自行遮蔽中澄明。
如透纳临终前对光的告白一般,在透纳的作品中看不出正统的基督教义,那么把“太阳就是上帝” 这一遗言引向上帝代替人作为本体的解读并不可信,上帝之光在中世纪的神学中光源于上帝,而非指光即是上帝,于是,在透纳这里,光不以任何作为本体,而是像上帝般,它照耀,它创造,如其所是的以光的方式存在。那么循着“光即神祗”的指示,我们是否能尝试着理解为透纳不再将光聚集于个体上,他试图摆脱一切源于最高存在者即以人为主体存有的先验之光与“对象”的关系?然而,这对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家来说十分艰难,毕竟脱离“主体性”与“绝对精神主体性”的浪漫型艺术相悖。
黑格尔提出“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他将艺术的发展进程理解为从无主体的抽象概念,到“理想符合本质”,再达到无限自由的主体性,即人的理性朝向最高境界—绝对精神发展的过程。形而上学的理念之光启示了现代艺术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在朝着绝对主体性艺术发展的观念里,在绘画中具有构成作用的明暗问题也随之隐匿了,而主体性观念的极端便在于主体性表现的艺术在直面自然时带有征服,侵占,奴役,为所欲为的潜在暴力,因此使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被切断甚至对立起来,海德格尔正是基于此反对把艺术家作为艺术创造的本源,他认为艺术家是艺术品的一个通道,而非本源,艺术品的本源来自于世界,所有的创作便是一种汲取,他否认艺术家的创造力:“毫无疑问,现代主义直接曲解了创造,把创造看作是骄横跋扈的主体的天才活动。”自此艺术创作中的明暗问题便被指引到不同于美学的思想道路上。
其中,恩斯特•施特劳斯以现象学为定向研究的《论明暗的开端》中写道:然而,至少在其17和18世纪的完美发展时期,绘画所形成的明暗恰恰表现为这样一种状态的反面:在这种状态中,被聚集的,大多情况下直接延展的明亮和沉入自身中的暗,在其所有介于阴暗和幽暗的阶段上,都被带向直观。它的光和它的暗处于相互的两极张力的关系中,或是相互渗透的……只有这样,现代绘画的构成想象才能创造那种出离其图像世界的关键的艺术手段,它具有充分的效力,足以去规定一种艺术所具有的最深刻的超自然特性,这种艺术表面上恰恰是通过它有意识地诉诸于可见的材料而与中世纪的绘画以及当代的绘画区分开来。从上文所描述的,我们在透纳与自然之光的交往结果当中似乎找到了相似的“状态的反面”,而作为旅者画家的他在汲取自然的过程中总被带向直观,不得不承认透纳已然克服了浪漫主义型的光之形而上学。
在《暴风雪中驶离港口的汽船》中,蒸汽船吐着浓烈的深褐色烟尾和翻起冲向空中的白色浪花在暴风雪里盘旋挥舞,浑沌之象难以辨别其中个体,他绘的并不是为了让人们理解,而是在光的介入下发生的一场光亮与黑暗相互争夺,相互揭露的自发性的能量释放。与其说其绘画的对象在“自然的明暗映衬中”显现,毋宁说是绘画的明暗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成其所是,两者交互运作,比邻而立,真理在光与暗的争执间无所促迫的涌现。
三.幽冥之趣
如若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自然”概念是在以主客体截然对立的世界观下演化发展的,“自然”的涌现是一种视觉表象的客体存在,那么中国传统山水画则是呈现出身体浸渐于自然中的交融显现,与其说古人是在观看山水,实际是顺应山水的召唤,那是古人在自然中体验到天人合一的至高精神体验却又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状态。而自西方的“风景”观念从“理念的世界”进入“可感觉的世界”后,这个转向使得东西方的艺术有了会通的内在联系。无论是透纳还是弗里德里希,在他们以及同时代的画家甚至诗人那里,超自然的体验从传统宗教转而进入天赋自然领地,濒临空无的同时,沉寂的黑暗里有着混沌中生发出动感的力量。
此时,与其说艺术模仿自然,不妨说是模仿自然之道,与东方古人遵循的山水以形媚道的观念殊途同归。所谓山水媚道即是彰显着自身浸渐于自然的光韵与幽暗,氤氤氲氲中泛着远古自然神论的余绪与踪迹。当然,这里并不是将中国传统文人的寄情山水情怀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息”完全对等起来,对于两种文化背后的内在本质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同时面对的是精神贫瘠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众神遁去,只留下踪迹,如果我们把艺术创作者比喻为诗人,在荷尔德林眼里,诗人的任务便是寻找这些踪迹,这些踪迹往往是不可知的,而诗的实质,诗的创作或者延伸为艺术的创造性活动正处于这种即是在遮蔽与揭示的关系基础上对于真理的追寻中,将无形之道化为有形之象,在这形象里隐藏着神的尺度,而对于中国诗人而言,在天地之间承接神的尺度是至高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是一种具有文化通性的冥契。这种冥契使得东西方绘画潜藏着贯通的内在联系。就如黄宾虹断言那般:“将来的世界,一定无所谓中西画之别的。各人作品尽有不同,精神都是一致的。”那么光影在绘画中无论是呈以阴阳交融之美,知其白,守其黑之道,还是真理在暗影的遮蔽与澄明之间涌现,其中暗影隐匿不可见的内在是一种超乎东西方界限的幽冥之趣。
在柏拉图这里,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致力追求的一直是终极本原的问题,在形而上学的真理观下,真理意味着纯粹的“向阳性”,“光”与“看”以及“可见之物”直接相关,“光”之形而上学是建立在光亮与黑暗对立的关系上的,且“光”等同于真理的存在,形而上学的世界是清晰的,光明的,没有夹杂黑暗和遮蔽,并且延续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对“光之至上”的拥簇达到高峰,总之,传统形而上学之光是绝对真理存在的理性之光,是所谓的真理之祛蔽,而非澄明。然而,海德格尔对整个历史性的讨论的诉求显然是克服“光之形而上学”的,他指出,光亮与黑暗的真理是在遮蔽与澄明之间显现的,光亮与黑暗的游戏运作同其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道出的“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的真理观一致,光与暗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争执且又共属为一个统一整体。这种真理观在绘画中呈现的是一种遮蔽与澄明,是一种阴阳交融之美,即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合乎自然之道。因为存有包含着有所澄明的庇护,所以存有原初地显现于遮蔽着的隐匿之光亮中。
结语
本文传达的中心所在,是通过对透纳作品中的光影现象的探讨,追问光与影的真理性问题,面对诸神隐遁,精神贫瘠,感知被技术所替代的艺术环境,在可感觉的世界中寻回光影即隐且显的原初意义,同时也是对当代绘画何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