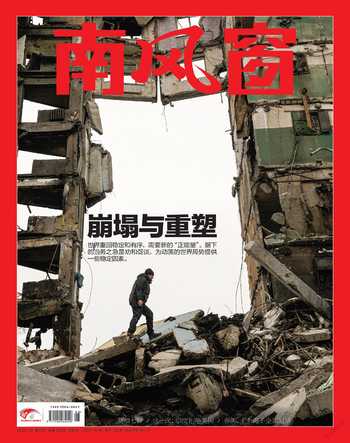当代单身青年图鉴
2022-04-25黄茗婷
黄茗婷

恋综早已满天飞的当下,新节目《没谈过恋爱的我》在海选阶段就收到超过4万份报名表的事,还是惊讶了总导演刘娴。
她们在这4万多人中,最后选出7人。有报名者从国外飞回上海,在经历了14天隔离之后,面试遗憾落选。也有人从大厂离开后报名参加这档综艺,那个报名者最后被选中,在节目里展开了一段沉默但十二分勇敢的恋爱。她是一个短发的初恋脸女孩,名叫蔡睿。
导演刘娴说起节目嘉宾来,有一种“慈祥”的姨母感。
4万多份报名表,都是些想谈恋爱的“孩子们”。他们跃跃欲试,又十分羞涩。甚至有嘉宾在参加节目之前,再三和导演组确认:“这个节目不会火的吧?最好别火啊。”让导演组哭笑不得。
庞大的单身群体,正在渴望恋爱,又害怕被关注。生于网络时代的他们,愿意将实现恋爱的希望寄托在一档综艺节目上,宛如一次孤注。
4万单身人士的报名经历,7个嘉宾的实际初恋体验,构成了一份“单身社会”的不完全田野样本,也让节目组在无意间展开了一次近乎人类学的问询。
是什么样的人在单身?他们为什么单身?
在单身岁月里,这些年轻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偏见?
如何找到对的人?如何脱单?
我们试图走近《没谈过恋爱的我》这档恋综节目,与总导演刘娴对谈,从中寻求一些回答。
根据民政部数据,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为2.4亿。《2021中国单身群体调查》显示,2021年,中国7.1%的成年人“从无恋爱经验”。伊利亚金·奇斯列夫笔下的“单身社会”,正在形成。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恋爱关系中,你最看重什么?”
“认为自己没谈过恋爱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被排列在《没谈过恋爱的我》报名表上的问题,每一个回答,都对应着一名单身青年对爱情的想象。
一层层筛选后被留下的7名嘉宾,他们都是被节目组认为“有代表性”的单身人士。
比如素人男嘉宾罗郅阳,他24岁,是一名绘画老师。
节目初期,他自我介绍,先将缺点“摊牌”:社恐、慢热、被动、记性差、容易“没电”(累),最长可以宅家两个月;其他人相谈甚欢,只有他一言不发;集体活动中,他总是落在最后面。
罗郅阳在节目中初期的表现,充满着抗拒和不自然,拒绝的原因,无他,“不相信爱情”。
他在节目中说,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从没看到过美好爱情的存在。
但这正是罗郅阳被节目组相中的原因所在。
罗郅阳身上,有着某种类型的当代单身青年的影子,原生家庭背景影响着他们看待、对待爱情的态度。
刘娴向南风窗表示,在海选阶段,节目组有意地寻找每一位能够代表着一种单身类型的素人嘉宾,以达到令“不同的观众在嘉宾身上产生自我投射以及共鸣”的可能性。
和罗郅阳相比,24岁的法学硕士研究生许文婷,是相反类型的单身青年。
许文婷出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所以她希望爱情所提供的情绪价值,要高于现在单身所体验到的一切。简单来说,她因为要求高而单身。
24岁的东北姑娘曹烨,对爱情抱有偶像剧版的“浮夸”幻想。
27岁的互联网“大厂社畜”蔡睿,她代表着太多疲于学习和工作,社交圈狭小、没有感情生活的年轻人。
还有大龄硕博单身群体、钢铁直男/女单身群体、理论满分行动零分单身群体……刘娴告诉记者,节目组从4万多个样本中,梳理出一系列的单身类型,构成了一个都市单身青年画像。
在设计《没谈过恋爱的我》环节的过程中,导演组询问素人嘉宾们:是希望(节目组)以更自然的状态介入大家的初恋,还是有一些环节推动?
大多数单身嘉宾选择了后者。
“如果不需要推动的话,我们就不来参加节目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因为缺少推动,完全靠自己真不行。”一名素人嘉宾说。
由此,观众看到的,“牡丹村”(节目拍摄地)要求嘉宾们日常出入要双人成行,每晚要在纸上写下自己心动对象的名字;通过一轮又一轮的“盲选”,开展约会,制造“缘分”……
在恋爱综艺的特定空间中,一切设置都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快速拉近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催生着初恋情愫。
“初恋,有时候会逃避,会退缩,也有时候你会非常勇敢。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呈现的会有点像一场恋爱‘笨蛋’的兵荒马乱。”刘娴对南风窗说。
当那个内敛、寡言,连续两天都没有心动对象的男嘉宾罗郅阳,在和沉默女孩蔡睿互相了解过往经历后的那个夜晚,他小心翼翼地在纸上写下:蔡蔡,你好。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高墙逐渐瓦解,初恋的可能性逐渐显现。
熟悉的句式,甚至让人不禁浮想联翩。是王小波“你好哇,李银河”的情书开头,小心翼翼的姿态;也是塞林格说过的话,“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
而初恋的美好,也伴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节目里,另一对嘉宾便遭遇了小挫折。两位嘉宾似乎明显互有好感,却因为男嘉宾的一句话,引起了对方的敏感。女孩许文婷认为,“似乎自己不是对方的首选”,为此介意,并迅速向后退,来保护自己。
初恋岌岌可危。
但这种不确定性,在节目中似乎随处可见。坐在演播室里的明星嘉宾们,看着监视器来“猜心”,错多对少,总是搞不懂初恋人的心。
对比初恋综艺和过往的大部分“熟男熟女”恋综,我们能看出一些差别。
在熟龄恋综中,一个人被至少两名嘉宾坚定地喜欢,是时常出现的情节。如《心动的信号》第二季中,坚定地喜欢杨凯雯的有赵琦君和吴翔威,在《半熟恋人》中,坚定地向罗颖表达爱意的是黄瑞恩和周锦舜。但这些嘉宾并不会如同母胎单身的嘉宾一般,一碰到竞争,便下意识地后退。熟男熟女们,仿佛能够更笃定地付出爱、接受爱,接受因爱受伤的可能性。
对比之中,“爱是一种能力”,这一学习命题接踵而至。
刘娴把《没谈过恋爱的我》看作是一个“成长的地方”。
“爱是对他人的主动洞察力。”所以,素人嘉宾们才需要在节目组设置的一对一见面聊天、给初恋的情书、在心动电台留下心声等环节中,获得主动了解、主动表达的机会。在外界的催化下,等待爱的主动产生。
但光只“产生爱”并不足够,堕入情网的人,还需要“维系爱”的能力。
对于《没谈过恋爱的我》这个初恋恋综来说,“维持爱”或许是一个超纲的命题,但如果将视域放宽至其他恋综,无论30岁以上男女的恋综《半熟恋人》,还是离婚群体的恋综《再见爱人》,都可以令观众意识到“维持爱”之必要性。
离婚恋综《再见爱人》中,每一对嘉宾在镜头的注视下,都表现出了维持爱的艰难。
已在离婚边缘的佟晨洁和KK,两人因在生育和戒酒问题上的分歧,婚姻关系几乎分崩瓦解;在离婚、复婚、再提出离婚的朱雅琼和王秋雨的关系中,两人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指责,这段关系里再也看不到给予爱、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而后面一系列词汇,正是被弗洛姆看作是爱的基本要素。当这些元素无法再结合在一起形成爱的时候,就是爱的消逝。
让爱来临,让爱别走,都是能力,我们都需要学习。
“爱需要学习”,是几乎每一档恋综面世后产生的副产品。
每一档恋综节目制作方,不一定将“爱的教育”作为出发点,但如果观众能以审视与学习的姿态来观看恋综,或多或少能获得一点零碎的建立、维系亲密关系的方法论。
倘若跳出恋综的框架,回归更宽广的现实,在单身率和离婚率渐高、结婚年龄推迟、单身社会不断成型的当下,“恋综热”的现象似乎有点反常,但又在情理之中。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纵欲、顺从与异化劳动,将削弱人对于爱情的需求。而这三者,在现代社会中早已成为了人的一种日常。
当然,纵欲不只是性行为上的放纵,还体现在对单一事物的短暂的狂热与空虚的满足,如对电子游戏、二次元、浪漫影视综的痴迷。尤其是在流水线上不断产生的工业化“糖精”影视作品,喂养了无数人,那些过分浪漫、脱离实际的情节,使一个人只需要手机、网络,便能够无休止地、单独完成“颅内恋爱”。
顺从,是一种缺乏自我审视与自我了解的低姿态,这本与爱情以自我需求为出发点相违背。
异化劳动,无疑是倦怠社会的成因之一。异化,倦怠,然后走向“佛系”“躺平”“注孤生”。
弗洛姆一语成谶地预见了60年后的未来—如今当代人“缺爱”的病症成因。三者合力,消解了爱情存在的日常性与必要性,造成了恋爱的低欲望。
但爱又是必须的,对于生存唯一圆满的回答,便是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是爱。每一个恋爱综艺,可能都想成为当下的某种弥合药剂,它以真人秀的方式来向观众展现爱、爱的过程、爱的能力。
但单身人群面临的困境与偏见,并没有消退。尽管这个群体日渐壮大。
在《没谈过恋爱的我》中,艺人嘉宾何广智坦言,自己25岁还没谈过恋爱的经历,曾经给他带来了一些外界的负面评价。
而素人嘉宾何雨欣直言,她参加节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消除外界对单身人士的偏见。
紀录片《剩女》中,34岁的单身律师华梅,哪怕在大城市拥有体面的职业,只要一回到农村老家,仍会因“大龄未婚”而被家人埋怨,被外甥称为“光棍姨”、被姐姐讽刺“单身的人没资格谈幸福”。
催相亲、催结婚的声音,甚至有日渐年轻化的趋势。据《厦门日报》,38%的单身男女首次相亲年龄不足23岁,四成“95后”已有了相亲经历。
近期,一则“妈妈让大三女儿请假相亲,不去别回家”的消息登上热搜。事件中的妈妈对尚在学校上课的女儿称:“你(女儿)21岁,虚岁22岁,正常人家23岁都结婚了。”“一天过得浑浑噩噩。”“你不去就不要进家。”该母亲的言语背后,隐藏着一种刻板成见:单身的人,生活可能过得不好。
无论是“结婚狂热”,还是单身耻辱,这两种观念都将爱的实用性凌驾于个体体验之上,结婚,是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脱单”,是为了摆脱耻辱和偏见。
但在单身和结婚中间,明明有一条长长的道路,这条路名字叫作:恋爱。
虽然我们的社会并不强调恋爱,也似乎,群体性地淡忘了“学习爱”的重要性,但发生在过去与当下的一切,都指向爱、学会爱的重要性。
爱能让人发现自己,发现我们两个人,发现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