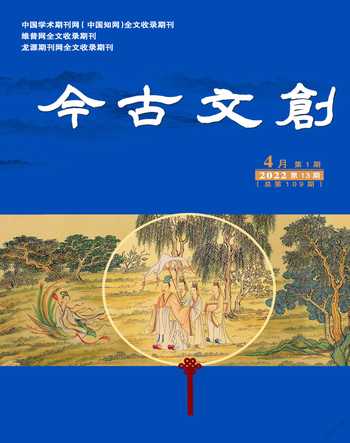斯坦纳阐释学视域下理雅各英译《诗经 · 大雅 · 大明》翻译分析
2022-04-23周怡良
周怡良
【摘要】 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重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认为译者的理解在翻译中起着关乎全局的作用,提出了信赖、侵入、吸收、补偿四步走的翻译步骤,在译文评价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诗经》内容丰富,情感真挚,在英语世界有多个版本,其中理雅各的版本流传甚广,广受好评。研究发现,阐释学所倡导的四步走的翻译步骤不论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文化传播效果上有重大参考意义。
【关键词】 斯坦纳阐释学;理雅各英译《诗经》;《诗经·大雅·大明》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3-0105-03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中,其所蕴含的各种价值也是独领风骚,古往今来,无数国内海外名家对《诗经》也是从来不吝溢美之词,各类注疏也不一而足,无数名家引经据典,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对《诗经》进行注疏。理雅各秉持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博采众长,对《诗经》进行过三次修正,力求完美,其1871年出版的全译本,至今仍被视作标准译本,理氏译本的价值可见一斑。但受制于历史局限性、译者视域、古汉语和英语间巨大差异等主客观原因,理雅各译本与源文本间的差异历来为学者们所津津乐道,许多名是大家依托不同理论对理氏译本进行了诸多分析。但检索过往文献,鲜有从斯坦纳阐释学角度出发分析研究理氏英译《诗经》,基于此本文旨在阐释学视域下以《诗经·大雅·大明》一篇为例展开分析,希望能从翻译步骤上探求我国典籍外译新途径。
一、斯坦纳阐释学理论概述
阐释学是指基于文本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最早用于分析和研究文本意义,并在其后的历史中不断发展壮大。至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 ·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将阐释学发展成为一种以理解为核心的哲学,即哲学阐释学,认为理解总是以一种历史性的方式存在,无论是作为阐释主题的译者或读者,还是被阐释的对象(往往是文本)都根植于历史当中。既然主客双方都处于历史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见”,或表述为“前理解”“理解的历史性”等核心概念,这些概念揭示了翻译过程的本质,即译者作为读者和阐释者在着手某一文本翻译之前,肯定是带着自身某种先见的、固有的“偏见”去理解和阐释文本的,这些“偏见”可能源于译者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宗教信仰、文化理念等。正是这些“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前提和基础,也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二者融合在一起也就注定了译者理解的历史性,或者说注定了译者的主体性。
自20世纪60年代后,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Steiner)率先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他以哲学阐释学作为理论依据,将阐释学融入翻译中,把翻译视作译者视阈和文本视阈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贯穿始终,因此,译文的最终呈现必然是译者理解下和源文本意义统一的产物。进而指导翻译实践。并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详细进行了阐述,即在阐释学基础上分析翻译过程,把翻译过程等同于阐释运作,指出翻译过程要经历的四个步骤,即信赖、侵入、吸收、补偿。
二、斯坦纳阐释学视域下理雅各《诗经·大雅·大明》的翻译
(一)信赖
斯坦纳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始于“信赖”,翻译活动从信赖开始,而这首先便是在文本选择上,译者选择相信和认同所选文本的价值、可译性,然后以一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所选文本。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可能会遇到“对他十分不利充满敌意的文本”,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从而进入下一阶段。
对于《诗经》这么一本兼具美感和史诗性质的儒家经典,理雅各对《诗经》的评价很高,他认为“包括《诗经》在内的古代儒家经典视为真正的圣书”,通过《诗经》能深刻理解和洞悉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本源才。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后世儒学也一直把《诗经》奉为儒家经典之一。而在早期时,理雅各对于孔子的评价也是毫不客气,他认为正是孔子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人对宗教的排斥,还曾指责孔子“更深层次的道德问题”,那么,如果能从一部流传甚广且有源远流长的儒家经典入手,动摇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无疑是一条捷径。《诗经》,这部成书时间极早,且得到过中国人心中圣人孔子亲口称赞的书无疑是最佳突破口。
此外,就《诗经》本身来说,理雅各还认为:“在历史的久远和重要性方面,《诗经》仅次于《尚书》,书中的内容也同样包含了不同材料,在时间跨度上也从远古一直持续到周代末期,就历史价值来说也是无可比拟的”。可见不论如何,理雅各对《诗经》在中国的地位以及塑造中国人精神世界;乃至于《诗经》本身历史价值的赞赏与认同。
(二) 侵入
斯坦纳阐释学视域下“侵入”是指当译者遭到源文本中对自己十分不利甚至充满敌意的情况时,译者要想完成译文就必须选择“侵入”原文,在侵略的过程中去理解原文,试图达到在理解历史性局限下自身视阈对文本视域的最佳理解,那么势必要根据自己的“前理解”或“偏见”来理解译文,而最终译文必然被打上译者个人理解和目的的烙印。
早在明朝期间,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就意识到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巨大到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西方传教士群体在传教时便采用“以中证西”的翻译策略,即在儒家故紙堆里寻找和他们信仰相吻合的部分,进而附会于儒家思想上。理雅各也延续了这一思路,并选择翻译中国经典系列丛书。因此,在《诗经》的翻译过程中理雅各一方面力求保留原著中的伦理、道德、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寻求用当时西方主流思想价值观念来译释中国传统经典,从而实现了儒家思想和西方主流思想的有效融合。所以在翻译时难免会更倾向于解构原文,那么这种结构就会带来“侵入”。
如《诗经》中多次出现的“天”,理雅各主张儒教经文中的“帝”“上帝”“天”都应该被视作“神”或“上帝”,以此契合基督教作为“一神论”的特点。故而将其译作“Heaven”,冯友兰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字中,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泛指天空或宇宙。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是具有人格和意志的天,也有至上神的含义。曰运命之天,指人生之起落皆操之所在之天,曰自然之天,也就是自然万物的运行,所谓“天行有常”,最后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
同时,冯友兰先生认为《诗经》中所说的天,抛去指物质之天外,其他都应该契合第二种“主宰之天”。结合馮友兰先生的归纳,《大雅·大明》中的“天”显然是第二类具有人格和意志的天,“天”不仅天意难测“天难忱斯”让“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让商朝的统治陷入了动荡;还时刻关注着人间;降大任于文王“天监在下,有命既集”;并明察秋毫的选中文王来统治周族“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可见,作为周人的最高信仰,“天”主宰着一切,所有的一切乃至于下文中的武王灭商都是“天”的安排。
由此可知,“天”确实在周人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理雅各在翻译时注意到了“天”的至高无上与神圣,但也注意到了“上帝”——另一个几乎和“天”平起平坐的存在,这显然是坚持“一神论”的理雅各所不能接受的。当然,“天”和“上帝”涉及商周之际的思想转化问题,“天”作为周人的信仰更像是对殷商“上帝”的继承和创新。
在《大明》中的“天”被理雅各翻译为“Heaven”,对于“天”的翻译,理雅各如是写道:“上帝 (God)居住在天堂(the great heaven)里,上帝是天(Heaven)的人格化名称,上帝主宰世间万物,滋养万物。同时,他还监察国王(也就是天子,Son of Heaven)的行为,保佑他的子民,若国王(天子)失职,就会给其带来惩罚”。可见理雅各为了维护“一神论”,试图将 “天”“Heaven”与“上帝”“God”相糅合,也就是在世界上只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不存在一个能与“上帝”比肩的“天”,使译文思想更符合基督教的特点。理雅各对“天”的阐释很好地证明了在历史性局限和自身视阈下对文本“侵入”的选择性。
(三)吸收
在经历了上两个阶段后,原文中和译者头脑中的理解达成了和解,从而形成了译者自己对原文意义独特的理解,在这一阶段,译者开始通过各种翻译技巧和手段来表达自己的理解,通常来说,这一表达结果的呈现往往有两种结果:一是原文完全被解构,彻底融入目的语,也即消化;二是原文仍然保持在目的语中相当的独立性和陌生感,即感染。可以说前者更接近归化;后者更贴近异化。这两种结果也往往和译者自身翻译水平、自身学识、翻译目的挂钩。
结合理雅各的生平及受教育经历可知,理雅各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和理解始终受到自身经历和价值观影响,因此在翻译时,倾向于用符合西方人观念的用词来阐释原文,借此彰显中西方文化的共同之处。
例如理雅各将“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译作“This king Wan, Watchfully and reverently,With entire intelligence served God”,和“上帝临女,无贰尔心”译作“God is with you”都将文中的“上帝”与西方基督教中的“God”直接等同起来,文王如同弥撒时虔诚的主教;武王则如战前鼓舞骑士的国王,直接将基督教语境下“God”的形象和原文中的“上帝”画等号。将“上帝”彻底吸收进了西方话语体系中,让西方读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原文。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在“吸收”阶段,有足够的自主性去选择到底是消化抑或是感染,从而影响译本在目标读者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
(四)补偿
最后的“补偿”阶段,是指译者对在翻译过程中丢失或孤立的结构、语言、文化等其他仍保持一定独立性、异质性的部分进行补偿,以补偿源文本的损失,进而达到意义上尽可能地再平衡,甚至优于原文的程度目的,尽管译文和原文不可能完全对等,但也正如斯坦纳所说“译者必须竭尽全力弥补以恢复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平衡”。
《大明》一诗中有许多修饰性词语,如第一章“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这句作为全诗的开头,大气磅礴,但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依《诗经注析》所言:“明明、赫赫皆是形容文王之德。在上与在下对文,下为天之下,则上为天矣”,也就是说文王的德行广惠于民;其德丕显于天,但没有明显的主谓宾语,让理雅各一头雾水,难以准确翻译,理雅各自己在注释部分也这样写道:“St.1.L1.1,2 are certainly enigmatical”(The She King, Odes of the Temple, Ta ming),在友人的帮助下,理雅各最终将译文定为“The illustration of illustrious virtue is required below, And the dread majesty is on high”。译文通过“The illustration of illustrious...”来对原文中的“明明”进行补偿,试图再现原文恢宏的气势和对文王德行的赞美,对于原文中的上下也直接给出,像原文一样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为了表达“赫赫在上”的威严,又在“majesty”前加上“dread”,结合后面的“天难忱斯。不易维王”,进一步强化和凸显了上天的威严与神圣。
此外,对于原诗中的省略,为了避免读者误会,理雅各也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补偿,如第三章中“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是说周文王德行昭昭;四方倾心,理雅各为了保持语义的完整性在译文中对“以受方国”进行补充,译作“And in consequence he received [the allegiance of] the States from all quarters”表明文王只是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忠诚,而非其他手段得到了其他国家,消弭了可能存在的误读。
三、结论
任何人和文学作品都是一定时期历史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和译者自身的“前理解”或者说“文化偏见”。也即阐释论视域下译者依靠自身所固有的“前理解”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依照信赖、侵入、吸收、补偿四个步骤对原文本进行种种阐释,在《诗经·大雅·大明》这一过程中,理雅各充分认识到了《诗经》的价值,但出于自己传教的目的和不得不对原文本进行“侵入”,在用词上既要斟酌选词,达到传教的效果,还要确保与原文含义不出现过大的偏差,导致偏离原文语义,实在是不易,对于原文本中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理雅各也充分吸收了其精华,最大限度地平衡原文本和目的语间的含义,确保译文高质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对实在无法理解的部分给予充分全面的说明。
综上所述,理氏英译《诗经·大雅·大明》充分且完整地体现了斯坦纳阐释学四步骤:从遴选翻译作品的伊始,到对原作意义的理解,再到译者在译文中阐发自己独到的理解,使得原作中所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播到目的语读者群体,这对于我国译者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经典,把优秀传统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创造性融合,从而实现中国文化从“走出去”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GeorgeSteiner,Steiner.通天塔之后[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姜燕.理雅各《诗经》翻译与儒教阐释[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4]张萍,王宏.从《诗经》三译本看理雅各宗教观的转变[J].2021,(2018-2):52-57.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理雅各.中国经典[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白欲晓.旧邦新命:周人的“上帝”与“天”之信仰[J].宗教学研究,2011,(4):7.
[8]理雅各译释.诗经·大雅颂[M].上海:三联书店,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