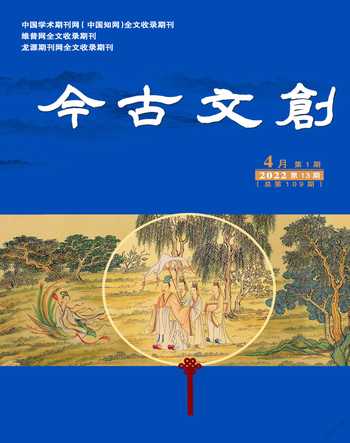浅析里运河民俗中的重商之风
2022-04-23管怡佳
【摘要】 里运河民俗是里运河流经地域民众在长久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结晶,其形成过程与里运河有着重要的关系。同时,里运河民俗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构成,重商之风作为其中受里运河影响较为明显的区域民风民俗之一,其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其表现也有着多层次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探究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里运河;民俗;重商之风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3-0053-03
基金项目:2020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重点(国家级)项目“里运河民俗文化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202011117038Z)。
一、里运河流域重商之风的具体表现
(一)经商行为的增加
里运河流域重商之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地有关经商的行为在不断增加。一方面,本地居民从事商业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商店林立,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清人吴锡麒曾在自己的《还京日记》中记载称其为“万商之涧,尤为繁盛”。此外,运河重镇逐渐兴起,这些城镇往往经济繁荣,商业兴盛,例如淮安河下古镇。
另一方面,外地的商旅云集,商户不断入迁。对于商人往来聚集,商船罗列运河河面的场景,光绪《淮安府志》有生动精彩的描绘:“自府城至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资巨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此外,在里运河运输优势和地理位置条件的吸引下,众多外地的商人纷纷来此定居经商,地域跨度十分之大。
与此同时,里运河沿岸还衍生出了一些因运河的流通而形成的马行、客栈等特色产业。因“南船北马”的政策之故,从南方来的商人大多需要在淮安王家营乘马或马车北上,因此当地车行与客栈众多。秦选之在《淮乘》中记载道:“房屋动以千计,且皆画栋雕梁,高墙峻宇,门阶石级有多至十数层。”为了满足过往商旅以及官员的饮食消费需求,各色酒楼饭庄以及小吃摊位填街塞巷,酒舫、渔船航行河面,“昼夜喧嚣,市不夜息”。[1]
(二)经商观念的转变
1.商业地位的提高
运河的开通给沿岸居民带来了更多创业的机会,同时,更多富有的商贾也涌现了出来,他们抓住了运河带来的经商机遇,以自身的经历、奢侈的生活享受等向里运河沿岸的其他居民证明经商的利处,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封建思想束缚,很多人开始把经商作为科举应试后的第二件要事。
民间歌谣“月爹爹月奶奶,把几个银钱,小孩子做买买。空船去,重船来,买鱼买肉买螃蟹”也可以从侧面展现当时里运河沿岸居民对于经商这一行为的推崇。
2.对商人评价的转变
中国古代主张将社会成员按其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其中,商人排在最末,社会地位较低。更兼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之下,统治者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轻视商人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在里运河流域,随着商业的不断繁荣,经商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会对于商人的评价也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转变。
据史书记载,盐商在淮扬两地多有结交文人、资助寒士的善举,例如扬州的盐商巨子马曰琯、马曰璐两兄弟不仅让扬州著名词人厉鹗在其所有的“小玲珑山馆”授徒为业,还曾资助纹银200两给当时生活贫困潦倒的郑板桥。
此外,这些商人还助力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位于扬州市广储门外,扬州古老书院之一的梅花书院就是由大盐商马日绾之子参与恢复的。除了兴办书院,这些商人还刊印典籍、鉴宝收藏、赞助戏剧演出,促进了里运河沿岸城市文化繁荣昌盛。
修建、扩充园林是里运河流域商贾的另一贡献,其修建的园林包括但不限于淮安河下古镇曲江楼、菰蒲曲、荻庄,扬州休园、筱园。学者韦明铧《两淮盐商》一书中认为“盐商掏钱建造了园林,园林却又提高了盐商的社会地位与公众形象”,这些园林沉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给这些建造者带来的“不仅是一片宴游的场所,而且是一种品位、修养和道行”。
因此,里运河流域的百姓逐渐认为“贾而好儒”,评价这些商人“弘扬了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的儒商精神”,还“传播了崇尚风雅、善交文人的文化风尚”。[2]最终,“通过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徽商树立了良好的商业形象,赢得了土著百姓的承认与接纳,从而为商业规模的扩大奠定了基础”。[3]
其次,从商人与士的关系来看,虽然历史上朝廷对于商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子女经商等方面设定了层层限制,但随着里运河周边区域商人财富的不断累积,捐官等方式的流行也使得商人与士的阶层能够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商人的地位及社会评价得到提高。
二、里运河流域重商之风的形成原因
(一)运河经济繁荣
经济因素是促成里运河流域重商之风形成的重要原因。运河经济的繁荣为沿岸城镇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此外,里运河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漕运。千年漕运,见证了淮扬两地的興衰,漕运的发达使得因运而兴的商品经济不断繁荣,因此,有学者认为:“运河民俗的脊梁是工商业文化,运河的漕运作为近古的一种先进运输手段和巨大的社会生产实体,顽强地表现出自己在商品流通、商品经济中独领风骚的风韵。”[4]
从运河经济的发展优势来看,运河经济具有整体性,这使得受其影响的地域能与外界不断交流和沟通,而里运河自身优越的运输条件以及关键的地理位置也便利其接受来自江南运河流域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里运河流域处于南北要冲之地,北接山东运河流域,南通江南运河地带,南北交往联结密切,受到来自江南运河流域开风气之先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众所周知,得风气之先的江南地区是明清社会风气由俭趋奢的发源地”[5],这种社会风气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商业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纸醉金迷的奢侈消费的崇尚,在运河的沟通和联结之下,来往商人旅客将这种风气逐渐传播到了江北运河各个区域。
(二)地域文化特点
运河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多元化的鲜明特点,淮扬两地在运河文化的孕育之下滋生出了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风韵。这种地域文化的特点在时代文化整体环境下显得更加突出。众所周知,农业文化一直以来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自秦汉后兴起的“重农抑商”政策更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但是里运河联结的淮扬两地,却一度成为农耕时代的异数。以扬州为例,有学者认为:“在对历史实际考察的基础上,我们说历史扬州是个商业中心城市,扬州文化就是重商崇文的市民文化,怕不为过。”[6]90
究其根本,在于地域文化中超越时代的因素。“传统文人批评扬州所依恃的就是统治经济的道德,也就是社会主流道德。而扬州市民的行为所体现的却是当时人们并不能理解的新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6]91这种现代性因素的形成与上文提到的运河经济有密切的关联。正是因为运河经济的繁荣,扬州文化才能有新的创造,这种“现代性因素”也使得扬州文化,乃至里运河流域的地域文化都彰显着与传统农业社会大相径庭的性格与风貌。
此外,“兼收并蓄”“包容南北”一直是淮扬地域文化以及运河文化的关键词,这种特性体现于当地的民风以及饮食习惯等方面,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里运河流域与时代相悖的重商之风兴起的特异性。
(三)徽商迁入
徽商是明清时期一股重要的商业力量,他们的足迹遍布京杭运河各地。大量徽商迁入淮扬地区后,不仅通过自身的努力融入了当地的区域社会,而且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有学者认为:“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7]在《扬州画舫录》中有记载的外来人数为113人,其中80人为徽州人士。位于古运河畔的淮安河下古镇也曾是大批徽州盐商迁入聚居之地,后成为繁盛的商业小镇。
除了对当地商业形式起到的实际促进作用,徽商的入迁也给当地居民的思想观念带来了革新,正如有学者所言:“举凡这一地区社会观念的改变、等级制度的被打破、社会风气的变化、商业精神的传承等等,徽商作用甚为显著。”[8]在徽商迁入的过程中,里运河沿岸的居民逐渐提高了对于商业的认识,改变了对于商人的固有认知,最终助力里运河民俗中的重商之风的形成。
徽商入迁对于当地重商之风兴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来,徽商的入迁加快了运河城镇“城市化”的进程,正因为各地盐商富豪挟带巨额资本来到淮安河下古镇,河下古镇才到达了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些商人所经手的大宗物资通过里运河往外运输,为当地商业发展创设了绝佳条件。
二来,徽商巨大的财富来源、自身极尽奢侈的消费享受等直接冲击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促成当地重商之风的重要因素。《淮安河下志》对盐商豪绅的奢侈生活有所记载:“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典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阁阂之间,肩摩觳击,袂帏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9]除了奢靡的生活享受,在婚俗以及丧葬寿宴习俗方面,徽商出于多种目的,也大兴操办,宾客往来,宴席筹办,热闹非凡,这种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风俗“让淮安正统的乡绅甚感骇异”。[10]79除此之外,“伴随着商业的繁华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商业文化对淮安民风的影响也越发明显。在生活方式上,官商与士绅们侈华雅致的追求,染及市井,潜移默化地培育了市民们诗酒雅集、听戏品茗、食药养生等风习。”[11]
三者,徽商自身对文化、儒学有着不懈的追求,这一条在上文已有陈述。除了文化层面,徽商的积极进取也体现在对社会阶级的向上追求,他们不仅与官僚结交,还极尽所能与清朝的皇室成员保持良好的关系。清朝康熙、乾隆两帝在数次南巡的过程中,徽商皆斥巨资组织策划欢迎和庆祝事项,据史书记载,徽商组织众多百姓焚香迎驾,队伍绵延数里不断绝,更兼有在里运河两岸种植名贵花草树木,点缀亭台楼阁,这些景象令人瞠目,所耗经费更是难以计数。正因如此,这些徽商也大受皇室嘉奖,地位与高级官员相近,“以布衣上交天子,成为远近歆羡的商界奇闻”。[10]74
三、里运河流域重商之风的后续影响
里运河流域重商之风的后续影响主要为当地奢侈之习的流行,《淮安府志》曾记载:“士勤学问,民务农桑,有淳厚之风,礼让之俗。”[12]113说明先前民风崇尚俭朴,《山阳县志》也称:“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豪右竞势逐利,以财力侈靡相雄长,细民争趋末利,虽文物盛于前,而淳厚之风少衰”。[12]113在里运河流经的淮安地带,逐渐出现了市场到深夜仍不关闭,百姓富庶,争相追逐奢侈生活的景象。
这种奢侈之习首先体现在当地百姓的衣食住行方面。在明代中叶以前,淮人崇尚俭朴的风尚,士大夫夏穿葛布制成的衣裳,冬着粗陋的皮衣,外出办事则多采用步行的方式,但随着运河经济的带动,外地商户的迁入,尚俭的民风发生了变化。直至明朝末年,街上乘坐轿子出行的人已逐渐变多,且十分讲究,一顶轿子的花费就可以供普通人使用许久。更有甚者,社会普遍上出现了把穿着打扮、交往对象作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和婚恋价值的趋势。
在人生礼俗方面,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一便是择偶以衣着及富有程度为标准,正如上文所述,衣着打扮朴素的妇女很少有人选择与其婚配。其二是婚丧花费的巨大,为了能够在乡邻间炫耀不惜借钱或以物贷钱的事例多有发生。从小生活在淮安清江浦附近的周恩来总理也曾深受当地奢侈之习的影响,在其生母病逝后,周家大操大办丧礼,导致本已不堪重负的家庭情况进一步恶化,最终不得不靠典当物品、借贷等方式来维持生计,正因如此,周总理一生崇尚俭朴,反对浮靡的风气。除了婚丧等人生礼俗,一些有关节庆的民俗活动也耗费巨大,《淮安风俗志》就记载了一种名叫“赛会”的庙会活动,称其“随地都有,然未有如淮安之甚者”,这种风俗源自徽商的故乡歙县,且逐渐发展成为里运河地域民众接受度较高的庙会活动,在一年中举办次数不下十余次。且铺张豪奢,举办一次所要花费的金额就达到了千金之数。当地有关礼俗的规格也在不断提升,产生了从简朴到奢侈的变化,“清河土田常罹水患,多歉少收。旧俗吉凶礼简,室服从朴,器无华饰。近滋奢侈,仍次于淮。”[13]
此外,奢侈之习的流行还体现在不同阶层的社会交往之中,《淮安府志》所载:“惟士人尚能遵俭朴、持节概,耻与豪盛相往还”,从侧面体现出当时人们倾向于与豪绅往来的景况,彰显出社会整体偏好受拜金显富风气影响之深,唯有士人还遵守俭朴的道义。
参考文献:
[1]吴鼎新,张杭.明清运河淮安段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研究[J].淮阴工学院学报,2009,18(04):10-16.
[2]王雪萍.扬州盐商文化线路[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97.
[3]郑民德.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及其社会活动研究[J].中原文化研究,2020,8(03):108-116.
[4]高建军.运河民俗的文化蕴义及其对当代的影响[J].济宁師专学报,2001,(02):7-12.
[5]张梦琪:清代运河行记研究[D].宁夏大学,2018.
[6]余大庆:扬州地域文化特性刍议[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3(06):85-91.
[7]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85.
[8]王世华.明清徽商是长三角兴起的重要力量[J].学术界,2009,(5):139.
[9]王光伯.淮安河下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21.
[10]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J].江淮论坛,1994,(5):72-82.
[11]吴士勇.试论明清时期淮安文化的繁荣[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5):485-491.
[12]宋祖舜.天启淮安府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113.
[13]卫哲治.乾隆淮安府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管怡佳,女,汉族,江苏苏州人,扬州大学本科在读,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