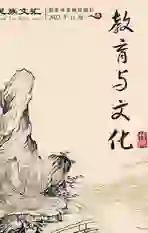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民族特色研究
2022-04-23蒋晓雨
蒋晓雨
关键词:现代传记史传传统 民族特色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陈雅芬在《传承与变革——民国时期传记文学理论转型研究》指出传记文学史传合一的形式形成了这一特殊文体,始终散发着它的艺术价值,给读者独特的审美观感。然而,与传记相关的文本相比,与传记作品相关的传记理论的发展却相当滞后。自民国起,传记文学理论开始冲破窠臼,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的传记文学理论对后继的传记理论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李健在其《论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史传合一”与西方传记的“史传分离”》的论文中,提到了中西传记在叙事方面的差异以及产生此种差异的原因。高雨从的《二十世纪中西方传记发展的异与同》中认为,中西方传记的发展之路径是一条既传承又革新的道路。在传记理论和文本创作中相互借鉴,汲取优秀的经验,取其先进理论的精华,去其落后理论的糟粕,形成独特的带有各自民族特色的传记理论及传记作品。从中西方传记发展态势,人物形象的美化和暴露以及商业价值影响下的传记写作习惯等方面来论证讲述二十世纪以来中西方传记的异同,西方的传记文学在各种文学题材当中脱颖而出,吴锡民在《论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史传合一”与西方传记的“史传分离”》西方传记文学的生存基因在于与主俱来的文学与史学的血缘关系和不约而同的人的主题;其发展轮廓在纵向上大致可分上古、中古、近代和现当代,在横向上,不外乎分传记与自传两大类;其现代个性特征为介乎于文学与史学之间.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
辜也平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土壤根基——现代传记文学的民族特色研究之一》 指出中国深厚的传记文化积淀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赖以生成的土壤根基。中国现代传记,即区别于古典传统模式的现代传记,是本世纪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在考察研究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学者中,只有陈兰村先生注意到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既受外域传记文学的明显影响,又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并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仍保持了自己历史与文学结合的独特品性。陈含英和俞樟华在其论文《现代传记文学的基本成就概论》中指出,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历史上,现代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在传记形式上,在发展旧有形式的同时,又创造出许多崭新的形式;在传主选择上,平民化成为发展趋势;在他传和自传创作上,自传创作发展迅猛,数量可观;在传记思想风格上,大胆的个性追求、自我表现与暴露、自我批判和忏悔意识成为中国现代传记的特色;在传记语言上, 新式白话传记替代了文言文传记;在翻译和评介西方传记上,大量西方传记文学作品和传记文学理论的传入,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加强了理论武装,促进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健康成长;在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上,“传记学”的提出为使现代传记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文拟在中西比较的视角下,既不讳谈西方传记文学叙事对中国现代传记的影响,而且指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仍然保留有本民族特色,同时,也不否认本民族历史传记文学叙事方式对现代传记写作的影响,应该承认的是,中国现代传记的史鉴功能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古代以史為镜、以人为镜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古代传记一样,其探究或再现的是过往的人事,目的却始终在当下,所以明显地带有现实功利性。但是在这种自觉的价值取向中,却又包括了现实社会的认识、现实人生的探讨、现代史传丰富,更加强调了从传主自身生活经历出发,既不夸大也不贬斥,强调真实性的同时,也更加强调了传记文学理论的应用,结合中西方传记理论,立足本土现实,从中国国情出发,在中国特色传记理论的指导下,创作出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传记文学文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既是历史的传承,也包含了现代的创新。
二、现代传记文学的起源及新变
中国传记萌芽于先秦时期,《尚书》《诗经》的文字记载可以说是其发轫之作。从《尚书》《诗经》《春秋》时的萌芽进入战国时代,《左传》《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开始孕育中国传记的雏形。直至两汉,传记写作才有一个大的飞跃。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开创了纪传体样式。在史传成熟和发展的同时,散传或杂传在西汉也开始出现。进入唐宋时期,史传写作逐渐走向衰落。而散传杂传,由于有许多散文家和诗人的加入,艺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文学性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传记创作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自传写作风气的形成还出现了长篇传记。元代的传记文学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自明清时期才略有起色。特别是明中叶之后,传记文学不仅完全脱离正统的史传模式,而且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唐宋散传的新特点。即传主范围的扩大,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传记写作中价值观的变法,蔑视传统礼教,追求个性自由。注重日常生活细节以及注重民间趣味的世俗化倾向。明清之际,传记文学创作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作家用文学形式传人的自觉意识增强。碑文,墓志铭等应用文体逐渐退出文学舞台,以“传”命名的单篇人物传记逐渐兴盛。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中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民强国,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思潮,这种社会状况和文化思潮,使得有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再从事任何文化工作室,都保持着直面现实的自觉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几千年的生存发展过程中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虽然古代中国并未产生独立意义的传记文学作品,但是悠久的史传传统和曾经有过的散传杂传的繁荣,以及古代学人对史传、杂传创作原理的经验总结,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现代传记文学虽然最初是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诞生的,但传统文化对于一代作家的影响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影响有时并不如外来文化影响引人注目,但却是深远的,无条件的。中国传记文学虽然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接受外来影响,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完成了现代的转型,但中国深厚的传记文化积淀无疑是中國现代传记文学赖以生成的土壤根基,传统传记写作中史传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更是无比深远。20世纪40年代就已有论者指出,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受到西洋的影响,在体裁格调方面有了改变,与过去的传记相较,换了一副神气。到90年代人们仍然认为,从戊戌维新到五四前后,是中国的传记写作在吸收借鉴西方传记经验的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逐步突破封建时代的旧传记传统,由此过渡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传记的一个重要时期,五四以来的中国传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走向,而这两种走向都是以现代性为前提的,都是在现代性的文学话语的范围之内运作的。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最初几位自觉倡导者在倡导传记文学时,无一不是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审视中国传统的传记写作,并且都带有明显的标举西方传记模式的倾向。“五四”时期,自陈独秀、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之日起,一改古典文学“文以载道”的艺术传统,开始关注“为人生”的文学。改变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为描写对象的写作窠臼和理论范式,例如,晚清以降,以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撰写消闲娱乐的狭邪小说、言情小说、宫闱小说,将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创作观,关心劳工、妇女、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将其工作、婚姻、爱情作为描写对象,亦如创造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尤其是郁达夫开创的“零余者”形象,30年代林语堂对幽默理论的倡导和发展在于文化对人的发现。他不仅发展了中国现代幽默观,推动了30年代幽默小品文的创作,而且在改变国民“合于圣道”的思维方式和枯燥的人生方式等方面也有所成就。从其幽默观出发,在题材和风格上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他的幽默观既是美学观、创作观,也是人生观,在30年代纷纭复杂的特殊社会背景下,提倡幽默并非逃避现实人生,故意遮蔽讲究繁文缛节的社会生活,不过是不想直面现实社会林林总总的冰冷刺骨,而是以超然之姿态和深远之心境,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对现实中的滑稽可笑之处加以戏谑。
林语堂的传记写作颇有不同,独具特色。在他看来,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达观的态度,一种认清现实、认识自我之后而采取的幽默闲适的心境,他非常欣赏和景仰北宋文学大家苏轼的乐观旷达的胸怀和心态,既有消闲文学的趣味又有严肃文学的趣味,《苏东坡传》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应“运”而生。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传记家在写人物传记时,会将传主“自我化”,将自己作为传主的正义化身,代他发声,因为林语堂个人对苏轼的崇拜和爱慕,加之林语堂作为传记者自身也跟传主苏轼有相同之处,在接触和搜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在梳理关于苏轼的史料记载时,选择的材料也会带有主观性,甚至会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抑他人而扬传主,在《苏东坡传》第七章“国家资本主义”和第八章“拗相公”中,通过对王安石失真地贬低的方式来赞扬苏轼的沉稳自如的性格。梁启超说自己的《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胡适和郁达夫在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的传记文学作品时也都认定这是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字。正因为中国缺少了这些,所以连一个例都寻找不出来。若从外国文学里来找材料,则千古不朽的传记作品,实在是很多很多。后来的朱东润也认为“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所以他也不讳言写作《张居正大传》的目的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由于梁启超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生期的巨大影响,人们后来在论及现代传记文学时,自然也就都格外瞩目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外来影响而忽略其民族承传。
五四过后,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作家个性充分张扬,传记作者似乎也进入无须春秋笔法,可以秉笔直书的年代。实际的情况却是,现代人的书写固然不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但受其他种种因素影响,总也还是有不便直说或不想直说之处。于是,春秋笔法作为一种叙述策略自然仍被应用到现代传记写作之中,即使像无所顾忌的鲁迅或性情豪放的郭沫若,在他们的传记作品中也仍然可以看到春秋笔法的精魂。中国传记文学在很大一些方面与本民族传统保持了承传关系,同时又体现了独特的民族品性,陈先生也未展开过充分的阐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一代作家的影响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影响有时并不如外来文化影响引人注目,但却是深远的,无条件的。中国古代传记对现代传记的影响源于任何民族文化所具有的自然承传性,源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与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思潮,与转型时期传记文学作家的文化积累和现实追求不无关系。现代传记文学最初那批提倡者与写作者从本质上说也只不过是过渡时代的先行者,在他们身上,传统的基因甚至多于现代的成分,民族文化的积淀也远远胜过外来文化的影响。
三、中西方传记文学的继承与区隔
西方传记作家大都注重对传主生平资料、乃至野史秘闻的全面搜集和运用,注重对传主心理个性的探究,他们比较一致地倾向于围绕传主私生活进行个人化的微观叙事。而“史传合一”、“知人论世”的传统则使中国传记更为重视传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忽略对传主个人生活乃至个性的探究,传记作家关注的往往只是传主作为社会的人在某些特殊职能中的行为和功能,而不是尽量提供其全面生动的人生面貌。中国传记文学虽然在19世纪后期开始接受外来影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完成了现代的转型,但中国深厚的传记文化积淀无疑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赖以生成的土壤根基,传统传记写作中的“史传’精神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其影响更是无比深远。追寻这种影响无论对于准确把握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还是对于促进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是极其有益的。因此,本文将进行的,是考察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与中国传统传记之承传关系,并进而探寻蕴含于现代传记文学创作中的民族特色。
中国传统对“实录”原则的另一具体要求是“不虚美,不隐恶”,但撰史或作传者往往因各种影响而很难真正做到,历代传记中“谀墓”之作也多如牛毛。所以胡适批评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表面上看似乎是受西学东渐影响,实际上正是对“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实录”精神的呼唤和期待。郁达夫则更为具体地谈到,传记作家在传人时,“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 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四、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民族性
陈思和在《传记文学的原则与基本精神》中说:中国现代传记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同步发展起来的,两者仍然有不同的侧重面。现代文学强调个性的解放和自我的发现,强调文学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现代传记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是传记有自身的特点和要求,首先就是要求把人物传记建立在史传的基礎之上,传主不仅必须是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而且是有据可查的。这就是“有来历”,并非是向壁虚构,凭空捏造的人物,也不是什么神仙列传里的人物。其次是“有证据”,也就是强调了史传结合,传记人物的行状不能任意编造,必须有证有据,这是传记与一般文学创作的最根本的区别,传记文学是不允许编造情节的。其三为“不忌繁琐”,这是朱先生针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所提出的一项自我限制。传记有各种写法,有繁琐的史料长编式的传记,也有简约、活泼、有见解的传记。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古典传记到当代传记之间的过渡,其对古典传记的继承与对当代传记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现代传记文学文本对文献记载和史料的推崇、对以古鉴今功能的重视和对传记文学作品中抒情性因素的注重,这几个方面是其接续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史传传统的具体表现。而当代传记作品中涌现的数量可观的英雄人物的传记文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名人自传的繁荣创作景象,以及当代传记创作方面对西方传记文本的借鉴,则是现代传记文学后继创新的直接体现。理论方面如此,反映在现代传记文学的创作方面亦是如此。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及文本创作的发展是在汲取古典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优点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承前是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功底和底蕴的文人必然的表现,也是对司马迁的《史记》开创的“纪传体”通史的良好传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讲究更加推崇全方位地利用真实的历史资料,强调传记文学文本的真实性,将史学凌驾于文学之上。五四以来,以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在充分汲取西方自由、平等和民主等现代意识的基础上,认为现代传记文学作家应该对缺乏文学性、绝对忠实于历史的人物传记的创作现象进行改革。由于受封建传统文化的窠臼和文学伦理意识的羁绊已久,过分强调传记文学文本的社会功用和训诫后人的功能价值等,将史鉴功能凌驾于审美功能之上,史传合一的传统使得中国传统文人往往将传记文本当作历史书写,强调还原真实,传记文本甚至同样承载着训导、鼓励、价值辨析等社会功用。对于现代传记作家来说,除郁达夫等少数个性张扬的作家外,大多现代传记作家均受传统道德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在传记文学文本创作中,侧重刻画传主的生平出身、家族历史、求学经历、学术创作、个人政绩等大的方面,进行歌功颂德,而忽视其个人的真实生活细节,传记文学作品以史为鉴的目的明显高于其文学审美的目的。
五、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传记文本创作对于现代传记文本的影响,不仅源于民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自然而然的承传性,也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古典文化深厚的历史结晶和持久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与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思潮、与转型时期的传记文学文本作家的文化积淀和在创作中的现实和理想追求不无关系。五四时期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与实践的最初那批提倡者与写作者,从本质上说也只不过是过渡时代的有着启蒙意识的精英,总之,中国现代传记的史鉴功能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古代以史为镜、以人为镜的民族传统,和古代传记一样,其探究或再现的是过往的人事,目的却始终在当下,所以明显地带有现实功利性。但是在这种自觉的价值取向中,却又包括了现实社会的认识、现实人生的探讨、现代人格的建构等等诸多的内涵或途径。所以,现代传记所体现出的史鉴功能远比传统的史传丰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既是历史的传承,也包含了现代的创新。笔者觉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一代作家的影响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影响有时并不如外来文化影响引人注目,但却是深远的,无条件的。中国传记文学虽然在 19世纪后期传统文化的因素甚至多于现代意识的成分,民族文化的积淀也远远超过外来文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诞生于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诞生于学习外来传记文学的创作形式的时代浪潮之中,但在精神实质上仍深刻民族文化烙印。但是,历史只能理解不可指责,这种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史传传统,这种紧密贴近现实的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诞生期的历史特征,是保留于那一时代传记文学作品中值得深入研究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1]辜也平:论中国现代战绩文学理论建构之流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2]陈含英,俞樟华:现代传记文学的基本成就概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3]韩兆琦: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
[4]辜也平: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重负”[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 (06).
[5]许菁频:承前与启后: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基金项目]项目名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民族特色研究;项目编号:2021XKT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