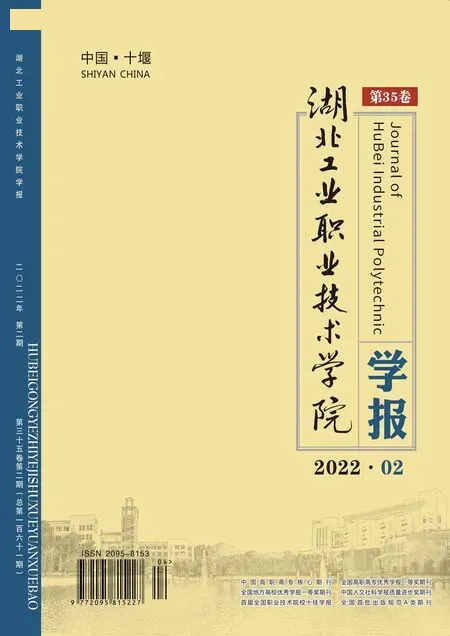孤独命运的两种书写
——《文城》与《一日三秋》男主人公形象比较
2022-04-08古小冉
古小冉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8)
“出走”是中外文学创作中不断重复的母题,代表了主人公在面对无法破解的困境时所做出的勇敢抉择——跳出困境,追寻心中所想,为自己争取新的人生可能性。《文城》中的林祥福与《一日三秋》中的陈明亮同是为摆脱孤独处境而出走的勇敢者,林祥福虽未能与妻子小美团聚,但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在精神上的收获要远远超过现实层面的结果,在溪镇人民的情谊温暖之下,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双双“安家”。陈明亮则没有这样的幸运,经历过人生的几次起伏过后,他虽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在精神上始终是无根飘零。余华用诗意的笔调将林祥福的人生书写成了一部浪漫史诗,而刘震云则延续自己一贯擅长的反讽手法、注入魔幻因素,从而在陈明亮的人生中折射出一幅荒诞现实。
一、勇敢的出走者:对孤独状态的自我剥离
(一)灰色、沉默的童年
童年是个人成长发展的黄金时期。弗洛伊德学说中提到童年经验对个体成长的决定性影响,童年创伤对于个体性格养成、心理状态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往往会从潜意识中表现出来。陈明亮与林祥福都在年少时亲身经历过丧亲之痛,林祥福五岁丧父,他全程目睹了父亲的死亡;十九岁时母亲病逝,自己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自此“他独自一人生活了五年,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1]8。陈明亮自记事起就经常目睹父母因“没劲”而吵架,母亲自杀前将他支开,成为了加在陈明亮心头的一把枷锁——他天真地将母亲的死亡与自己的贪吃联系在一起。至此,明亮开始了他的孤独人生。后来父亲再娶,继母甚至当他不存在,在爸爸的“新家”里,他不被关注、无人交流,变成了一个“多余人”。高中辍学后去“天蓬元帅”猪蹄店打工,除了身体上的疲惫、物质上的匮乏,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孤单——无人说话的痛苦,因而他只能借助吹笛子来传达自己的心声。凯·埃里克松认为,人受创伤后会躲进一种“保护性的信封”里,即一个沉默、痛苦、孤独的空间[2]。林祥福与陈明亮成长过程中的形单影只使得他们在成年后始终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孤岛”中,父母的缺席一方面使得他们较早地独立,另一方面使他们被迫从家庭结构中分离出来,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环过早断裂,使得他们本能地在潜意识中对其他人际关系产生隔膜与不信任感,因而导致了其孤独的生存状态与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
(二)生命中重要的女性
现代作家笔下时常出现“地母”式的女性形象,如张贤亮《绿化树》中的马缨花,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带有圣母光环的女性人物的出现,安抚了男性人物的生存焦虑、物质或精神的空虚,带着仁慈的理解、守护、无条件的支持,成为男性人物坚实的后备力量。纵观余华和刘震云的创作,无论他们笔下的现实有多荒诞、生活有多少苦难,在写及带有母性的女性人物时往往带有温情色彩,如《活着》中的家珍、《故乡面和花朵》中的姥娘,这与作家童年时的经历无不相关:余华父亲在海盐县人民医院工作时,余华与哥哥则跟在母亲身边生活;刘震云八岁前一直是在老庄与姥姥共同生活,作家童年时的经历投映在写作中便是塑造出了一系列带有母性的传统女性形象。
《文城》中的林母、纪小美、翠萍,与《一日三秋》中的奶奶、樱桃、马小萌等,分别给与了林祥福和陈明亮一段时间的温暖扶持,也正是因为遇到了这些生命中重要的女人,他们才暂时缓解了内心的孤独。而相较于其他女性,“妻子”这一形象无论是在《文城》还是《一日三秋》中都成为男主人公出走的坚定理由、出走的叙事动力。当明亮在延津无人说话,只能借笛声来寄托心情时,遇到了有着相似经历的马小萌。他们都生活在重组家庭中,都与继父或继母关系紧张,都是“无家可归”的孤独游魂。因为互相分享了童年的秘密,二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把彼此视作“唯一的亲人”。林祥福母亲去世后,小美接过了接力棒,每每林祥福劳作归来,家门口总有等候的身影、做好的饭菜,以及连续不断的织布机响声,为林祥福沉默的生活带来了声响,小美如水一样围绕在林祥福身边,为他缝制衣物、为他孕育孩子。林祥福醉酒时,为他熬制姜汤,雨雹来临时,二人相拥而眠。
林祥福和陈明亮对“妻子”的选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母亲影响。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俄狄浦斯情节”,即“恋母”,表明儿童在性发展的对象选择时期,首先会将目标对象定为双亲。林祥福和陈明亮依据母亲形象为标准,爱上与母亲相类似的女子,弗洛伊德将这种对象选择方式称为“依附型对象选择”,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最初的性满足来自并依附于个体体验生命的功能活动,比如哺乳、关爱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孩童会将这种依附关系持续保持在哺育或者照顾自己的个体之上,比如母亲或奶妈,直至成人之后的对象选择还会参考童年最初的对象选择而进行[3]。《文城》中,当小美像母亲一样准备饭菜、收拾屋子,甚至坐在母亲生前用过的织布机面前时,他“产生瞬间的幻觉,以为母亲正在屋中”[1]4。《一日三秋》中,陈明亮通过“上吊”这一行为在主观上将马小萌和母亲联系在一起——得知马小萌高中失恋在家上吊,明亮想起来母亲也是上吊自杀的,“别人一提上吊,明亮就想起了他妈”[4]145。对母亲的依恋是与对“家”的渴望一体同源的,母亲的离世直接导致了陈明亮与林祥福的孤独困境,在孤独无依的状态下,他们在潜意识中选择与童年时的依附对象(即母亲)相似的女性作为与自己构建家庭的妻子人选,既是对摆脱自身处境的本能性选择,也是源于他们对家庭伦理的向往。
遇到生命中的重要女性,暂时缓解了生命中的孤独,满足了他们对于“家”和“知心人”的想象,以及试图重建新的家庭格局的愿望,因而当这种圆满面临破灭时,他们只能努力挽回。马小萌被香秀揭发曾在北京做过不光彩的职业意图自尽,陈明亮为了不与马小萌离婚,只能选择离开延津,寻找新的归宿。纪小美留下孩子不告而别,为了给孩子找回母亲,找回“家”,林祥福只能离开沈店,踏上漫漫寻亲之路。
二、找寻心的归宿:被救赎与被流亡的不同命运
(一)人在异乡的不同遭遇
林祥福与陈明亮同是为摆脱自己的孤独状态而出走的勇敢者,但当他们真正离开故乡时,在异乡的遭遇却天差地别。
林祥福的出走目的明确,尽管“文城”其名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但“木屐”“蓝印花布头巾”“江南水乡”的地理特征标示着林祥福寻人的方向。林祥福带着女儿在雪地乞讨奶水时,溪镇的女人们开门便自然地接过女婴,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一个陌生的孩子;雪灾中几乎家家断粮,陈永年夫妇给了第一次见面的林祥福一晚热腾腾的粥汤,相当于“将自己的生命分给了他一部分”[1]68;灾后陈永良带林祥福开办木器行,溪镇人民不仅没有排斥这个外乡人,甚至格外照顾他们的生意,使得林祥福在异乡很快地获得了经济基础。溪镇人民用善良、真诚招待着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并热情地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社群当中,从物质到精神层面温暖、接受着林祥福。
明亮的出走是被逼无奈的,延津不仅没有给他俩归属感,甚至还把两人当笑话看,“明亮两口子,对延津伤了心”[4]166,眼看着两个孤独的人建立起的命运共同体面临崩塌,明亮才不得不寻找出路。他对出走后的目的地一无所知,就连方向也是算命的老董“胡说”的。同样都是异乡人,在西安,明亮夫妻二人并没有林祥福般的幸运,在谋生计的过程中他们被排挤、被殴打、被羞辱,就连投靠的老乡也算计他们,对马小萌动了歪心思。城市并没有给与他们温暖和包容,甚至是做人的尊严都一并剥夺。与乡土社会中以亲缘为纽带形成的“熟人关系网络”相比较,城市文明中在商品经济的运行法则规制下,人际关系的维系靠的不再是感情而是利益,传统的伦理秩序显然已成为制约商业文明中公平竞争的不利因素,因而被抛之脑后。当被故乡抛弃的孤独者陈明亮走进陌生的城市之中,便是走进了另一个支离破碎的伦理困境,这也就注定了他失语处境的宿命式延续。
(二)落地生根与无根飘零
在寻找过程中,林祥福在风雪之夜被陈永年一家收留,继而在溪镇“落地生根”。自此,“‘追寻’这一母题从现实的寻妻而拓展为精神的追寻,构成了意义的转喻”[5]。在溪镇,林祥福重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陈永年夫妇接纳了林祥福父女,将林百家视如己出,因而发现林百家与陈耀武暗生的情愫,一句“造孽呀”使得陈永年一家决心离开溪镇搬到兵匪横行的万里荡。陈家搬走、女儿外出读书后,翠萍接纳了再次“无家可归”的林祥福——在翠萍那里,他“僵硬的身体变得柔软”,“仿佛一件皱巴巴的衣服被烫平了那样”[1]163。当他只身前往万里荡营救顾益民,慷慨就义后,家中的家仆赶往溪镇将他的遗体带回家乡,故乡的土地再次接纳了他“落叶归根”的愿望。对林祥福而言,在溪镇能“落地生根”,死后“落叶归根”,故乡与溪镇都有他的牵挂,在溪镇,他的精神上是高度充盈的,尽管没有找到小美,但他在此重建了“家”的概念,他虽死得惨烈但内心满足。
明亮一生辗转于延津、武汉、西安,至亲去世后,延津和武汉对于明亮来说都只是空洞的地点符号,在这两处他都找不到归属感,甚至使得他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不复存在。明亮为了摆脱孤独的处境,踏入了“逃离——回归”的循环之中。第一次离开延津是依附于父亲的一次“逃离”——母亲因为一把韭菜自尽的事情满城皆知,父亲为躲避闲言碎语不得不带儿子离开。第二次是明亮离开武汉回延津,因为世界上唯一能和自己“喷空”的奶奶离世,因为“看到”正在受苦的母亲,也因为在父亲的新家中他作为多余人时时感到局促。第三次他离开延津,是因为延津戳破了妻子马小萌的秘密,二人在延津已无容身之处。后来回延津迁祖坟、回武汉给父亲探病,明亮事情办完即走,对“故乡”没有留恋。明亮在现实中最后一次离开延津,是因为梦到了花二娘,将自己的痛处以笑话的形式讲出来,在现实中一直逃避着的事情,被逼到梦中还要再回忆,“一个笑话,又把他逼得无耻。什么叫笑话,这才是笑话呢;什么叫故乡,这就叫故乡了;不禁感叹一声,在心里说,延津,以后是不能来了”[4]271。最后一次回延津是在梦里,梦到从前的事情和花二娘,明亮决定在潜意识中与延津决裂“梦里也不回延津了”。
五四文学以来,以“娜拉出走”为首引发了现代文学广泛开启“出走”叙事,以鲁迅的小说中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为例,主人公往往是接受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故乡”往往承担着乡土生活的困顿、愚昧,因而他们的“离去”与“再离去”是主动为之的,他们既有着对于代表着落后文化的“原乡”的批判,心中也有明确的方向指引。而对于《一日三秋》中的陈明亮,以及《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吴摩西这一类底层民众来说,他们并无多少形而上层面的追求,只有庸俗的日常生活和物欲满足,他们的出走不是主动的、自觉的,而是被迫和盲目的,无论是在“外乡”还是在“原乡”,对他们而言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故乡不是海德格尔所言的“精神之乡”,而只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肉体上的栖息之所,在精神上始终找不到皈依。
三、从文城到延津:书写人性的两种现实
(一)“中国式”的孤独和“中国式”的救赎
邓晓芒曾指出,中国人没有信仰,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没有确立,中国人自出生便处于群体关系中,受到群体法则的约束,也在群体中寻找安慰,但“这只是群体意义上的精神性而且与群体的物质性是密不可分的……拯救老百姓的肉体,而不是老百姓的灵魂”[6]。中国人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个人往往依附于集体,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人依照群体法则进行自我约束,还表现在受到伤害和失败时惯于向群体寻找安慰。西方人精神独立,故而不依赖于他人,只投靠纯粹精神上的“上帝”。正如刘震云在采访中说道的,西方人信仰上帝,当他们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便向上帝诉说,诉说的内容不会被外人得知;中国人没有宗教,社会是人际关系组成的,把秘密告诉其他人,就有被出卖的风险,因而只能将秘密埋藏在心底,或求助于伦理[7]。
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中国传统伦理强调“尚公”“重礼”“贵和”,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和利他性人格。“《文城》的深厚之处,就在于余华对诸多的传统伦理给予了深情的敬拜”[8],在溪镇,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虽然都是平凡的劳动者,但人人自食其力,在苦难中互相慰藉,归根结底是源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和遵守。雪灾来临,溪镇人民接纳了来路不明的林祥福父女二人,林百家正是吃“百家奶”才得以生存下来,林祥福正是由于一碗粥汤而在雪冻中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灾后重建时,林祥福和陈永年为乡亲们修补房屋,不主动收钱,而是放一个小篮筐,大家随意往里投钱,“不扔的说上几句好听的话也行”[1]71。匪祸来临,溪镇人民自觉加入民兵团保卫家园,即使死伤惨重也奋战到底。余华力图揭示乱世中人性的真与善,带有理想化和传奇化色彩,正是在如此重视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城”,林祥福的孤独才最终得以消弭在“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中,得到了“中国式”的救赎。
而《一日三秋》中陈明亮则走向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被伦理抛弃,且找不到通向真正宗教的入口,只能不停地穿梭于“寻找-回归”的循环中,故而是“中国式”的孤独。
自母亲、奶奶去世后,陈明亮便成了游离在伦理之外的“孤魂野鬼”。黑格尔将宗教分为自然宗教、实用宗教和自由宗教,实际上陈明亮曾试图求助于自然宗教,即我们所说的迷信,这表现在他去找老董“算命”,但由于认知经验有限,他并无可能寻求到真正的自由宗教,老董也并无可能提供给他超越性的人生答疑,陈明亮只是寻求能有人出主意,哪怕只是“把胡说当做真心话”。当他对人事、自以为的“神事”失望之后,他转向动物,“在一条狗身上,他开始感到西安亲了”[4]187。陈明亮与狗、和《故乡面和花朵》中的二姥爷与牛、《一句顶一万句》的老蒋与猴子金锁一样,人类在人际社会中屡屡碰壁后,与动物建立起一种虚构的、假想的温情,就如同西方人臆想出的“上帝”一样,在现实中找不到栖息之所,只能在精神上寻求自我安慰,这也是一种试图向宗教靠拢的尝试。但动物毕竟不是人,寿命短且没有语言功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陈明亮的孤独困境。实际上无论是求助于“天师”老董还是流浪狗,归根到底陈明亮都是在寄希望于自我幻想中伦理关系,他将狗和算命先生视作自己的“知己”,人为地建立起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但对于对象来说,“算命”只是老董的职业,他并无义务对“客户”推心置腹;对于流浪狗来说,依附于人类才能获得物质保障,而它并无能力为“主人”排忧解难,因而陈明亮的尝试注定是失败。求助于伦理被拒之门外,求助于宗教更是无路可走,对陈明亮这类的传统国人而言,由于“服务于现世”的中国经验过于强大,无论是求助于迷信还是假想性对象,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现世问题,而非超越性的纯精神层面的信仰,因而不可能找寻到西式的宗教安慰,只能永恒地处于“中国式”的孤独之中。
(二)传奇英雄和荒诞英雄
余华的《文城》从情节设置到人物塑造都带有传奇性,在超常态的天灾人祸中展现人物的行为选择,凸显出传统道义的珍贵。在叙事形式上,余华复归到中国传统的传奇当中,人物正邪对立、黑白分明,情节一波三折、曲折离奇;在价值取向上,回溯到传统道德之中,宣扬邪不压正、舍生取义,建构起名为“文城”的理想家园。如果说《文城》书写的是带有传奇性的浪漫史诗,刘震云的《一日三秋》则展现了一幅荒诞现实图景。刘震云惯于用“喷空”的形式来讲故事,《一日三秋》也是如此——突破现实生活的逻辑,使得戏中人物与现实人物、人与鬼、虚构与现实交织、梦境作用于现实,结合民间传说等资源,用魔幻的形式将现代人生的荒诞表露无遗。书中樱桃的灵魂与李延生的对话、花二娘的故事、演员自身和角色命运走向的重合等,为全书增加了魔幻和神秘色彩。全书延续了刘震云自《一句顶一万句》以来的“说话”母题,写及人与人之间的谎话、玩笑话、无关痛痒的场面话,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无话可说。“没劲”可以使人自杀,“一夜无话”可以使夫妻关系冷漠,“把胡说当成真心话”,只因无人关心。现实生活的荒诞、冷漠一览无余,“一日三秋,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意思,这在人和人之间,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呀”[4]264。
就人物结局而言,林祥福和陈明亮都是悲剧人物,但余华将林祥福的个体悲剧转向了集体主义立场中个人价值的凸显——顾益民被绑架后,溪镇人心涣散,林祥福在明知此行凶多吉少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只身前往匪窝赎回顾益民。林祥福是在集体伦理中得以解脱了自己的孤独,最终又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集体伦理。他死得壮烈,“死去的林祥福仍然站立,浑身捆绑,仿佛山崖的姿态”[1]197。余华将林祥福的结局推到了舍生取义、人间大义的集体主义层面,比起其他结束生命的方式,这一结局无疑最能符合中国人的道德价值判断,至此,刨除个人私欲,义薄云天的民间英雄形象得以树立。陈明亮则在“寻找-回归”的循环中承受着生活的荒诞,正如不断将巨石推向山顶的“西西弗斯”,加缪将西西弗斯视作“荒诞英雄”,在日复一日、无效无望的劳动中,他生活得痛苦,同时也获得了胜利。陈明亮在寻找之路上循环往复,在反抗孤独的道路上竭尽所能,明知无望,但仍充满激情。
四、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以来,“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便始终占据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重要命题,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改造国民性的同时,创造了无数历久弥新的人物形象,其中便有以魏连殳、吕纬甫为代表的“孤独者”形象系列,他们是时代的“先觉者”和“出走者”,他们的孤独源于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知,在孤独中彷徨、又在失败中走向更深的孤独。新时期以来,余华、刘震云等文坛上成绩斐然的作家,在写作中依然坚守着人道主义立场,塑造和表现着人的孤独。余华擅长将孤独置于苦难、宿命中进行表现,如《河边的错误》中的幺四婆婆、《活着》中的福贵等,刘震云则一贯将孤独的源头指向伦理秩序的破碎之中,塑造了一系列“失语”的孤独者,如《手机》中的严守一、《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等,不同于五四时期专注表达知识分子的启蒙困境、人民大众所承受的阶级压迫,余华和刘震云往往意图表现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本源性”孤独。
《文城》与《一日三秋》作为同时期出版的作品,同样包含了“出走”与“孤独”的主题,余华的《文城》对中国传统道义的深切呼唤,使得余华为林祥福孤独找到了新的出路,即回归到中国传统伦理中去,而刘震云延续了《一句顶一万句》以来的存在主义意味,使得陈明亮在荒诞的现实中寻找着无果的结局。但无论如何,表现“人”始终是文学书写的根本主题,刘震云和余华的新作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新时期作家的人道主义立场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