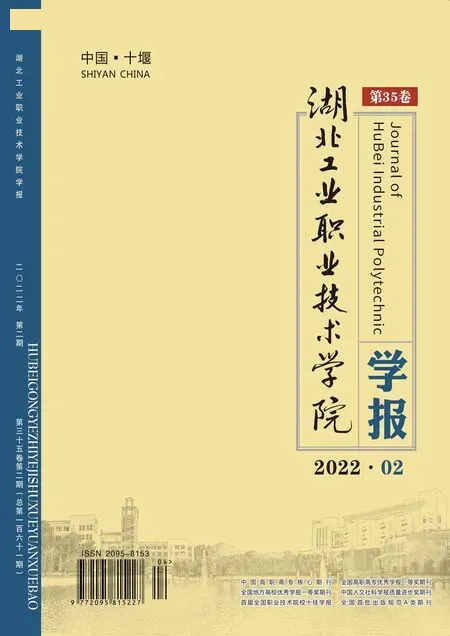自我叙事及体制运作: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逻辑建构
2022-04-08黄英豪
黄英豪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有关“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断裂关系,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初,便一直为众多新文化人阐释。由此始,白话文运动被烙上新文学史观的逻辑,在一帧帧的历史面貌中反复强调,延伸至此后的新文学研究脉络,并成为范式。李永东认为这是一种话语霸权,是新文化人通过新文学的“独家逻辑”与“一家之言”来清除异己[1]。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不仅应当对新文化人的“独家逻辑”定“是非”,而更应当运用“知识考古之法”探求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独家逻辑在历史横截面中是“如何形成”的。质言之,新文化人强调“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割裂的依据是什么,他们对这种“依据”的局限性是否有足够的自我认知?所谓“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独家逻辑”又是如何运作的?更具体地说,在《新青年》群体分裂前后,“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张在除去单一的报刊宣传渠道之后,又通过何种渠道落实其“逻辑”?
一、白话文运动的“未完成性”
新文化人对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看法,大都持“割裂”观,如周作人认为:“那时候的白话,是出于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质疑,和后来的白话文可以说是没有多大关系。[2]”因此他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态度是“二元”的,晚清的发起人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的白话,但在正经著书的时候,“依然还是作古文”。再如朱自清也是类似的看法:“他们还在用他们的‘雅言’,就是古文,最低限度也得用‘新文体’;俗语的白话只是一种慈善文体罢了。[3]”胡适强调晚清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是“绝大不同”的:“第一,这个运动(指五四白话文运动,笔者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4]。质言之,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才能取消“他们”和“我们”的界线,这同时也是新文学的“金字招牌”。
但如果正如周作人等人所说的: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主张依旧显示“贵族式”语言和平民之间的分裂,五四白话文运动比较起来更为“先进”。这也就意味着五四白话文运动弥合了所谓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之间的裂痕,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具有整一的“完成性”。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的大众语主张,延安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抗战大后方的民族形式运动?甚至在“大众语运动”中,瞿秋白认为白话文运动非但没有完成“他们”与“我们”的缝隙弥合的效果,反而已然沦为一种“新文言”:因为白话文随便乱用“口头上说不出的许多字眼,有时候还有稀奇古怪的汉字的拼凑。这样,这种文字本身就剥夺了群众了解的可能”[5]。
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历史进程中也被打入“未完成”的境地。实际上,新文化人并非缺乏“五四白话文运动未完成”的自我认知,1920年教育部发布通告:“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6]但是在胡适、叶绍钧等人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中却言及:“本科要旨在与小学国语课程衔接,由语体文渐进于文体文,并为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的基础。”[7]在《高级中学应读的名著举例》中也罗列出《诸子文粹》《四书》《古史家文粹》《王充》《史通》《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朱熹》《王守仁》《清代经学大师文选》《崔述》《姚鼐》《曾国藩》《严复的译文选录》《林纾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多种古文书籍,并且《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明确指出:“以上各种中,精读六种,略读五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白话文学篇目”:《水浒传》《儒林外史》《镜花缘》《古白话文选》《近人长篇白话文选》几种,《纲要》中指出的阅读要求仅仅是:“以上各种中,略读一种。”[8]可见,在“白话文运动”告捷之际,新文化人亲手起草的《课程纲要》中,无论是篇目数量还是阅读要求,与古文篇目相比,“白话”依旧显得势单力薄。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在现代文学发生时期,新文化人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极端”言论与其“温和”实践却有着明显差距。
陈独秀在主张“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的时候强调不能容忍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的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9]钱玄同更是直接称复古文人为“桐城谬种”以及“选学妖孽”[10]。鲁迅认为:“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1]但如果仅仅是出于对国民性的考量,就发表激烈的言论,未免过火。因为彼时的旧派文人,虽不赞成白话普遍化,但也没有对白话一味打压。具有代表性的旧派文人林纾认为:“古文者,白话之根祗,无古文安有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12]他主张文言是白话的基础,如果连文言都无法承继,不读文言原书,也无法发展白话。可见林纾在这一论述语境中,实际上已经承认了白话文的合理性。但新文化人在运作“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过程中诸多言论与骂战已经“出格”,超出了正常文化变革的讨论范畴。结合当时《新青年》与新文化人的处境,可能更易理解“五四白话文运动”对晚清的“割裂”态度。
考察《新青年》在现代文学发生进程中的地位可发现,它并非如同在之后的文学史叙事中所表述的那般“开天辟地”,它更多是作为新文学叙事的旗帜而“被树立”的。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成立之初,它还在延续着《甲寅》的办刊思路,主张思想革命。之后,《青年杂志》被迫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众说纷纭,最为主流之说是:当时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的使用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其改名。很明显,陈独秀在杂志上解释道:“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勉,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13],也属于是一种“体面”的妥协。周作人曾回忆早期的《新青年》仅仅只是“普通的刊物罢了”[14],鲁迅的观感也颇为相似:“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15]。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提及:早期《新青年》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16]。1917年底,《新青年》因发行不广,书社企图“中止”[17]。
在陈独秀被蔡元培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开始与北大的名号相关联。在蔡元培新任北大校长初期,虽然主张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北大的名声与威望并非立见成效。相比于《新青年》前期,在北大时期的《新青年》扩大了约稿作家的序列,在第二卷《新青年》中,新增作家有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吴虞、吴稚晖等人;随后章士钊、钱玄同、蔡元培等人也参与了第三卷的撰稿。但《新青年》也未能在社会上引发极大轰动。此时在文坛与出版界,风头最劲的作家当属林纾,据张静庐回忆,在民国五年到七年之间,上海文坛上出现一个“国文函授学社”的大骗局,学社社长利用林琴南的名号在各大报纸上刊载“林琴南主事的国文函授学社招生的大广告”,最终“来报名和索章的人,真是户限为穿,一天的信件,总有千封以上。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报名上学的不下两千人,以每个人十二元(六个月)学费计算起来,已经有两万多元现钞。”[18]由此事件可见“林琴南”名目在文化出版市场中的号召力。
在此时的出版市场中,林纾的文言小说炙手可热,据统计,林纾在清末至民初的十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上,一共出版了181部小说,总字数约在3600万字以上,除少数几种外,其余全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依照商务给他的稿酬标准(一般为千字6元),总收入则超过20万元。根据陈明远的研究表明,当时的20万元,按照货币购买力(1)若以1935年标准银圆购买力为基数——折合1995年人民币30元,合2010年人民币75元,作为换算的基准单元。那么——1898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100元,2010年250元;1901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70元,2010年175元;1911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50元,2010年125元;1914—1919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40—50元,2010年100—125元;1920—1925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35—40元,2010年87.5—100元;1926—1936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30元,2010年75元。(其间,1929—1930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物价波动,银圆略有贬值)转引自陈明远:《百年来中国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变迁》,名作欣赏,2011年第13期,第27-34页。,换算成现今的人民币数值,可上达数千万元[19]。张静庐曾经回忆,在晚清民国初期,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在商务印书馆里当一名练习生”[18],可见商务印书馆的体量决定了他在出版市场上的首席地位,其出版发行的趋向自然成为整个市场的风向标,决定着社会上大致的阅读风尚。
而反观提倡“白话为正宗”的《新青年》群体,在当时的报刊发行市场上缺少在“语言主张”层面的独特性。晚清1898年之后,大量白话报就开始涌现,如《无锡白话报》《常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芜湖白话报》《通俗白话报》《广州白话报》等等,据胡全章统计,在清末民初之际,出现了至少370种白话报[20]。即使在《新青年》同期的报刊中,如包笑天于1917年创办的《小说画报》同样提倡“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21]而包笑天创办《小说画报》的缘由正是因为他对鸳鸯蝴蝶派小说风格的不满,并有意扭正堆砌辞藻但内容空洞的弊病。因此,面对具有类似“白话文主张”的晚清前驱以及同时代的提倡者,《新青年》的“白话文运动”主张如何扩大影响力就成为一个问题。如布迪厄所说:“文化革命产生了这个颠倒的世界即文学场和艺术场,文化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是一心想颠覆观念和分类的一切原则的伟大异端们。”[22]而文化革命者在文学场中的“位置”就决定了他们能分配到的资本及各种特殊利益:“所有的位置从它们的存在本身及它们加在占据者身上的决定性上看,依靠它们在场的结构中,也就是在资本(或权力)的空间分配结构中当下的和潜在的状况,资本的拥有左右着在场中达成的特殊利益的获取(比如文学权威)。”[22]因此,“位置”决定了《新青年》群体必须以“非常规”方式、加以过激语词凸显与晚清白话文运动彻底“断裂”的态度。自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演出“双簧戏”之后,在文化界引起热议,《新青年》的发行量也迅猛增长,再加上北大的威望加成,《新青年》与北京几近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二、抵至基层的教育体制结构
诸多文学史的共识是:白话文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推行开来。但即使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表《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并且陈独秀受蔡元培延请,于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吸收了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人为《新青年》著稿并参与编辑工作,但在1917年年底,《新青年》依旧因发行不广,而被书社企图“中止”,直到陈独秀与之交涉,才允许继续发行[23]。可见此时《新青年》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更毋论继续推行“白话主张”。直至1918年1月初,《新青年》决定改制为同人刊物,宣布:“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共同担任……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24]在此基础上,《新青年》改整了以往舆论力量分布分散的弊病,举集体编辑之力宣扬白话文学。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发表《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复王敬轩》,即著名的“双簧信”事件,5月15日,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双响炮”打响了《新青年》的名声,并引起众多学者与读者的讨论,《新青年》以“不容他人之匡正”式的论争作为推行主张的手段,是较有效用的。《新青年》的销量急剧上升,从之前的月印一千份高涨至一万五六千本[25]。
但以“双簧信”等事件为契机,引起热烈反响只是新文化同人们的第一步,况且引发的“反响”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在“双簧信”事件发生之后,从“罗家伦、蓝志先及戴主一、易宗夔等读者的阅读观感”来看,其社会反响偏向于负面[26]。更何况,1919年3月,诸多报纸刊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已辞职”的消息,甚至流传出陈独秀嫖妓的传言。蔡元培召集诸君到汤尔和处商议,汤尔和以所传流言之事,认为陈独秀“私德太坏”,主张撤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蔡元培因是“进德会”倡导者,无奈之下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隐形中撤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胡适认为:“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汤尔和),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和思想的分野。”[27]
无论如何,《新青年》内部的分化已成必然之事,陈独秀后因分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入狱,胡适与李大钊又在舆论场中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此后又有胡适反对新文化同人轮流编辑《新青年》,试图独揽编辑权的事件。之后随着《新青年》南移并转型为推行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新文化同人试图继续在《新青年》上推行“白话文学”主张的意愿亦陷入消弭。
那么,如何将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与主张落实下来,则是新文化人需要考量的问题。有诸多研究者都将1918年4月胡适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作为“白话文运动”及“国语运动”合流的起点。但实际上,白话文运动的力量介入“教育体制”的时间节点要更早,在“国语研究会”成立的第二年(1917年),就已经自觉地与白话主张合流,并欲改革国民学校教科书为白话语体,如其征求会员书所宣:
“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原,盖由同人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又见夫京师各报章,用白话文体者,其销售之数,较用普通文言者,加至数倍,而京外各官署,凡欲使一般人民,皆能通晓之文告,亦大率用白话,乃知社会需要,在彼不在此。且益恍然于欲行强迫教育,而仍用今日之教科书,譬犹寒不能求衣者,责之使被文绣,饥不能得食者,强之使啮粱肉。夫文绣梁肉,何尝非饥与寒者之所愿?其如贫窘,力不能逮何,职是之故。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惟既以白话为文,则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而今日各地所行白话之书籍报章类,皆各杂其地之方言,既非尽人能知,且戾于统一之义,是宜详加讨论择一最易明了,而又于文义不相背谬者,定为准则,庶可冀有推行之望。此同人发起斯会之旨也。四方君子,与有同志者,幸赞助焉。此启。”[28]
根据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第一次会务报告》显示,在报刊类的“购存报章”中选取了十四册《新青年》作为参考资料,如吴稚晖、蔡孑民、陈独秀、胡适等人皆参与其中,在《抄录本会会员文》文目中包括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抄录会外与本会宗旨相同之论文二篇及诗八首》文目中包含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其白话诗八首。在第一次会务期间:
“二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借北平学界俱乐部开预备会,到者二十五人,公推蔡孑民君主席议定章程九条,并推陈颂平、陆两庵二君为临时干事,叶祝侯君为临时会计员,暂借北半截胡同内江苏学校为事务所,当收会费银五十二元。”[29]
可见,不仅当时的《新青年》群体及“推行白话”之主张与国语研究会有众多重合之处,在人事分布上,两个群体也互相纠缠,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担任国语研究会主席,在报请立案于教育部之后,可以说国语研究会带有半官方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4月21日,“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与“国语研究会”的半官方性质有所不同,前者被定性为“教育部附设之机关,以筹备国语统一事项及推行方法为宗旨。”[30]并且由完整的会议规则、会员录、职员录、议事录、议决录等组成部分形成较为规范的组织架构。其中在“推选会员”中赫然有钱玄同、胡适、周作人、刘复等《新青年》同人,委员会委员中也有钱玄同、马裕藻、吴稚晖、胡适、刘复等人。众多同人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议案:
“刘复谓增加闰母须组织审查闰母委员会并须预先规定取何种方法制造闰母。”
“刘复谓第五案须俟国语辞典国语文典等编就后始可推行现时尚非适当时期。”
“钱玄同谓国语辞典及国语文典一二年内当各有一二种脱稿国民学校改国文为国语三年后即可实行第五案第四条规定在六年后时期太迟本席以为不当。”
“刘复谓第五案第二条规定由会呈部令饬各师范学校内附设夏期国语讲习会亦不妥本席主张应由本会私人劝导。”[30]
胡适、周作人、马裕藻、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共同提请《加添闰母的提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其中提出“编辑国语辞典”“编辑国语语法”“改变小学课本”“编辑国语会话书”等几项要点,涉及到国语规范的制定、教材课本的改编、公共语言的推广等多个环节、流程[30]。可见,在《新青年》分化之际,留守北京大学的诸多教授已预备借力国家教育体制,继续推行其“白话文主张”。
如果说上述“国语统一筹备会”仅仅是在文化上层规划“国语统一”,那么此后随着1920年首届“国语讲习会”学员毕业事件的发生,就预示着“国语统一”的体制化流程进一步落实在基层。如《福建教育月刊》登载的《福建教育厅第四百三十三号训令》显示:
“令各县知事,查国语讲习会学员毕业成绩业经国语研究会考察完竣,由本厅核定,分别准予毕业修业并定期举行毕业典礼,在案计此次全体毕业人数共三百八十九人,修业人数共三十人,其中女学员共五十一人,兹发去该县籍学员……”[31]
各省级教育厅举办的国语讲习会毕业事宜都需要经过国语研究会考察。而为了进一步保障“国语讲习会”对各基层教员的培育效用,1921年10月25日,时任教育次长代理部务职位的马邻翼发布《咨:教育部咨各省区为转令所属各国民学校组织国语研究会文(附原案)》,督促各省区教育局及所属学校组织各自的“国语研究会”:
“咨:教育部咨各各省区为转令所属各国民学校组织国语研究会文(附原案)
为咨行事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称:本年八月常年大会会员张国仁提出各学校宜一律用国语教授一案,其颁发要在各学校设国语研究会作实行,用国语教授之预备。当时经大会议决成立,兹又经干事会覆议,均以为此事极为切要,现将原案抄录全份送情大部行文,交京师学务局、各省区教育厅令知所属各学校一律组织国语研究会以便将来各教员皆得研究国音、练习国语,预备各科均用国语教授等语相应抄同原案咨请贵署查照转令所属各国民学校遵办可也,此咨。
附抄原案一件。
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邻翼”[32]
随后进行的一系列体制化的落实方式,使得国语运动深化到全国各省区国语学校的课堂日常中,与此同时,在国语运动滥觞之际就与之有高度重合的“白话文运动”也随着国家基层教育体制的变动与运行,渗透在更为广泛的国民领域,而不仅仅限于《新青年》等白话报刊中。
三、教员的教材与“白话文学史”叙事
在1920年教育部发布训令,将国民学校的教科书都改为国语,胡适对此评价:“这个命令是几十年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前了十年。”[33]根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出版的《全国中学教育概况》显示,从1912年至1919年期间,全国中学数量由373所激增至715所,并且中学生人数由52100人次增加至151069人次[34],而1925年至1929年的中学数量从1142所增至2111所,中学生人数从18万余人增加至34万余人[35]。因此教育市场极具消费空间,虽然如上所述,胡适与叶绍钧等人在起草《中学国语课程纲要》时依旧是将文言作品作为占大头部分,但教育部的训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五四白话文运动”逻辑链条中的另一块“金字招牌”。在《纲要》中,周作人《点滴》《域外小说集》、鲁迅《呐喊》等书目被列入“略读书目”中,借助文学市场上的教科书出版热潮,较大拓展了白话文运动实绩在教育场的影响力。
但是,“学生教材”只是一方面措施,仅有教材的“白话意识”,而无可教授白话的教员,那么“白话文运动”的逻辑普及则更为缓慢。因此对国民学校的教员进行培训不失为一道有效途径。教育部于1920年4月22日发布训令《派送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入国语讲习所讲习令》(部令第二一二号,四月二十二日):
“本部附设国语讲习所第一班。业经开课。兹定于六月一日,续开第二班,查各省区师范学校,为造就师资机关,现任国文教员讲习国语,殊关重要。应令每校派送一名,由校酌给公费。于第二班开课前,赴所报到,以便开课。并先期将派定各员姓名履历,报部备查,至第一班派有此项教员者,毋庸再行派送。合行令仰该局、厅、校、遵照办理。此令。”[36]
将分散各个省区的国语学校教员集中起来,统一推行国语教育是较为典型的体制化运作。正是在体制化运作中,胡适受邀在国语讲习所中讲演《国语文学史》:“民国十年(1921年),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我去讲国语文学史。我在八星期之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石印的本子。”[37]《国语文学史》初稿是在1921年第三届国语讲习所上的讲稿,次年3月23日,胡适又在天津南开学校讲演,将原本讲义修改归并为三篇:
“第一讲 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
第二讲 唐代文学的白话化
第三讲 两宋的白话文学”[37]
从这三篇的目录中,始见胡适有计划将《国语文学史》中的“白话文学逻辑”进一步凸显出来。于是,1922年3月24日,胡适再次修改目次:
“一、引论
二、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
三、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是白话的吗
四、汉魏六朝的民间文学
(1)古文学的死期
(2)汉代的民间文学
(3)三国六朝的平民文学
五、唐代文学的白话化
(1)初唐到盛唐
(2)中唐的诗
(3)中唐的古文与白话散文
(4)晚唐的诗与白话散文
(5)晚唐五代的词
六、两宋的白话文学
(1)宋初的文学略论
(2)北宋诗
(3)南宋的白话诗
(4)北宋的白话词
(5)南宋的白话词
(6)白话语录
(7)白话小说
七、金元的白话文学
(1)总论
(2)曲一小令
(3)曲二弦索套数
(4)曲三戏剧
(5)小说
八、明代的白话文学
(1)文学的复古
(2)白话小说的成人时期
九、清代的白话文学
(1)古文学的末路
(2)小说上清室盛时
(3)小说下清室末年
十、国语文学的运动”[37]
在这次修改的目次中可见,胡适将“白话文学”作为《国语文学史》的论述重点,但此次修改计划却未如期实行。1922年三月中旬修改的版本在1922年暑假期间,胡适于南开大学讲演过一次;1922年12月,胡适又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上讲演一次,进一步扩大了《国语文学史》的宣传范围。但不止于此,黎锦熙曾借用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处用作讲课讲义,胡适的诸多学生也曾在别处作教员,“也有翻印这部讲义作教本的”[37]。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将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讲义排印出版,胡适在事后始知“文化学社是他(黎劭西)的学生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开办的,他们翻印此书不过是用作同学们的参考讲义,并且说明以一千部为限。”[37]可见渗透着“白话文运动”主张的《国语文学史》在教育界也广泛流传。直至1928年,胡适将《国语文学史》修改后重新由新月书店发行,改名为《白话文学史》,正式冠以“白话”之名:
“作者本意只欲修改七年前所作《国语文学史》旧稿但去年夏间开始修改时,即决定旧稿皆不可用,须全部改作。此本即作者完全改作的新本,表现作者最近的见解与工力。本书特别注重“活文学”的产生与演进,但于每ー个时代的“传统文学”也都有详明的讨论。故此书虽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今日唯一的中国文学史。全书约四十万字,先出上卷,约二十万字。”[38]
在广告中,最受强调的是“今日唯一的中国文学史”,无论是胡适自己的观点还是新月书店的营销策略,“唯一”的冠名使人不能不联想到在胡适之前,由各大书局出版发行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如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等。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发行,刚发行之后就在当年六月再版,商务印书馆将其列入“适合新学制中等教育段课程取材至现代为止的新著教科书”的广告名目[39],并将广告附录于《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尾页,这就给消费者以“此书是法定教科书”的错觉。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凌独见据称为胡适在国语讲习所中教出的学生,在此书出版之后,遭到非议颇多,其中尤其以章衣萍的批评为厉,他认为凌独见抄袭胡适在国语讲习所中所讲的《国语文学史》讲义内容:“一部分是暗暗抄袭胡适著《国语文学小史》的,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一部分是凌先生自己做的,像汉以前的文学,宋以后的文学几章内,引证的错误,诗词句读的荒谬,论断的离奇,真可令人大笑三天。”[40]此事在当时出版界中引发一定的关注,也无怪新月书店的广告中特意强调“唯一的中国文学史”一句。但也从侧面可见,无论是在教育场还是文学场中,“白话文学史”这一名目都能得到较大的关注,也是“五四白话文运动”逻辑落实的实效之一。
四、余论
即使“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逻辑通过较为严密的教育体制化运作落实到广大的社会接受场,但是在胡适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却也在不断地回望传统、归化传统。如其自序中所言:“这书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37]当时的《清华周刊》中有读者论及:在阅读《白话文学史》过程中“处处感觉到他的偏见,这或许是‘白话’两个字,害了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学史吧?可是他又说:‘这书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要是胡先生真个不客气,说它是中国文学史,那么我们对于这书的批评,便更要加多了。”[41]又有读者对书中所举例作家进行质疑:“胡先生的文学史中所举的例,都是韵文(诗和词),所举的代表作家亦是韵文作家,而对散文及散文作家却一字不提,似乎只认韵文才是白话或近于白话的文学作品的样子,其实这是胡先生的偏见。”[42]这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新文化人集体编撰的《新文学大系》的“排他性”的独家逻辑,胡适在《新文学大系·理论篇》的导言中说:“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这就是正式否认骈文古文律诗古诗是‘正宗’。这是推翻向来的传统,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43]这番论述与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偏重“韵文”的考察显出一定程度上的违和。另,《新文学大系·理论篇》中收录的篇目几近都为新文化同人所写,这或许在强调“白话文”与“新文学”的“完成”状态,但无论是在《白话文学史》的撰写还是中学国语教学纲要的编订实践中,都无不彰示出“白话文运动”的未完成性,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相悖逻辑也许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无奈之处,但同时也是建立新文学史观的必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