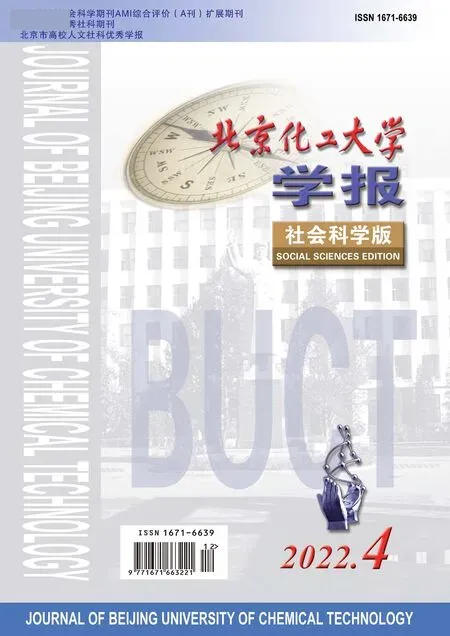晚清冒险小说译介动因探析
2022-04-07郑晓岚
郑晓岚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冒险小说(adventure fiction或adventure novel)或曰探险小说、历险小说。美国评论家堂·德阿玛莎(Don D’ Ammassa)在《冒险小说百科知识全书》(EncyclopediaofAdventureFiction)中指出:“adventure”一词在古法语中的意思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含有“危险、莽撞、勇敢”等语义要素,并将冒险小说定义为:“冒险是指发生在主人公日常生活之外的一系列事件,通常伴有危险和身体行动。冒险故事通常进展很快,节奏至少与故事中的人物塑造、背景及其他元素一样重要。”[1]本文采取“冒险小说”一说,论述范围包含“探险小说”或“历险小说”。
“冒险小说”作为文类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是在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冒险小说:如《鲁敏逊漂流记》(1)该作品为英国作家笛福的名作,在晚清有多个中译本,如沈祖芬翻译的《绝岛漂流记》(1898)、《大陆报》版的《鲁滨孙漂流记》(1902)、林纾和曾宗巩合译的《鲁滨孙漂流记》(1905)、从龛翻译的《绝岛英雄》(1906)等。目前学界通行的译法为《鲁滨逊漂流记》。之流,以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2]。这期创刊号还刊登了南野浣白子述译的《二勇少年》,这是晚清第一篇被明确称为“冒险小说”的作品。1905年,小说林社对冒险小说的题材进行了厘定:“冒险小说(伟大国民,冒险精神,鲁敏孙欤?假朴顿欤?雁行鼎足)。”[3]1908年,晚清著名小说评论人燕南尚生在评论《水浒传》时写道:“一切人于一切事,勇往直前,绝无畏首畏尾气象,则冒险小说也。”[4]综上,冒险小说旨在于以勇往直前、英勇无畏的冒险精神形塑伟大国民,以文学话语参与国民精神建构,为救亡启蒙、强国保种服务。
作为一种新文类,冒险小说在晚清的销量不如侦探、言情、社会等小说,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一文中写道:“而默观年来,更有痛心者,则小说销数之类别是也。他肆我不知,即‘小说林’之书计之,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5]然而,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冒险小说已经成为畅销文类之一,是晚清文学译介大潮中“颇受注目的一类”[6]。笔者整理晚清冒险小说篇目后发现,晚清冒险小说译介主要集中于1905—1908年间(2)根据李艳丽研究,冒险小说译介主要集中于1903—1907年,与笔者统计出来的结果基本吻合。参见:李艳丽.东西交汇下的晚清冒险小说与世界秩序[J].社会科学,2013(3):183-192.郑晓岚.晚清冒险小说(1898—1911)篇目整理、发现及刊行情况[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13-125.,来自英国的作品数量占绝对优势,而非李艳丽所说的“来自日本的作品数量占有绝对优势”(3)李艳丽的论断主要是基于转译自日本的作品而言。参见:李艳丽.东西交汇下的晚清冒险小说与世界秩序[J].社会科学,2013(3):183-192.。
一种文类的兴起或传播绝不是偶然的,必然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紧密相关。晚清冒险小说译介主要源于晚清社会这一特殊的接受语境(4)邹振环是国内第一个从接受环境论述哈葛德小说被译介到晚清的学者。具体参见:邹振环.接受环境对翻译原本选择的影响——林译哈葛德小说的一个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41-46+40.,而不仅仅是对“航海和科技”等知识的渴求(5)参见:李艳丽.东西交汇下的晚清冒险小说与世界秩序[J].社会科学,2013(3):183-192.。下文拟从民族生存危机、小说地位的整体提高及冒险小说的文类特点三个方面探析晚清冒险小说译介的动因。
一、晚清民族生存危机呼唤男子气概
冒险小说在晚清被大量译介的根本原因在于晚清的民族生存危机。晚清中国内忧外患,清政府惧内怕外,积弱不振,在与西方国家的交锋中遭遇了一系列惨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苦心打造的海军几乎溃不成军,朝野上下一片震惊,战后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加重了民众负担,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晚清开明人士掀起了救亡图存运动,然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运动却以失败告终。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民众深感亡国灭种的忧惧,“各种醒华、救华、兴华、振华的刍议、卑议、高议、新议、通议、危言、庸言竞相提出”[7]。1903年,爱国留学生发起的拒俄义勇队运动再次以失败告终。1905年,日本这个亚洲小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与日本相比,大清帝国形象却一落千丈,成为西方国家口中的“老大帝国”,犹如大清男子的辫子一般,阴柔、落后、愚昧,毫无男子气概。
面对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晚清进步人士积极探索强国保种之道,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于器物或制度层面,而在于人才,只有进行维新变革,改造懦弱、保守等国民劣根性,培养新民,方能缔造一个新国家。正如台湾学者颜健富指出的那样,“甲午战争粉碎了洋务派器物改革的理想,视角转到‘人’的改造上,强调人与国家之唇齿相依”[8]。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提出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主张,揭示了民强与国强的内在关系,为形塑新民提供了有力的行动纲领[9];1901年《光绪政要》提到,“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10]。 “少年”“学生”等年轻一代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乐于接受新思想,他们身上具有的希望、朝气、勇武、竞争、进步等新民品质,使其成为了改革的首选对象,他们“不论是作为政治或社会实体还是象征符号,都成为怀抱革新社会、振兴国家志愿之时人反复论及的对象”[11]。
晚清进步人士开始纷纷批判国民奴性,提倡冒险进取精神,弘扬尚力文化,从根源上寻找强国保种的妙方。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有感于日本的自强和中国的贫弱,将国家的落后与贫穷归结为国民性问题,于1889—1906年撰写了大量文章批评国人的奴态,强调必须去除国民奴性,弘扬冒险精神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他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将奴性视为中国人的劣根性,“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认为奴性的根源在于中庸礼让之风,呼吁冒险精神[12];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批判崇文抑武、怯懦、奴化等国民性[13];在《呵旁观者文》中深度剖析病态的国民灵魂,认为中国人缺乏“血性”,毫无男子气概,“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也”[14];在《新民议》中揭示民弱则国弱的事实:“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泼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沈雄强毅之魄力。……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为废国。中国之弱于天下,皆此之由。”[15]1902—1906年,梁启超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20篇政论,批判中国人弱不禁风、民族武德缺失,宣扬以“力”为核心的价值观,强调新民应具备冒险进取精神[16]。其中,《论冒险进取》一文指出西方国家强于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冒险进取精神,主张以此精神重塑国民品格[17]。晚清其他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冒险进取精神事关国家兴亡,纷纷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奴性,提倡冒险进取精神。如,邹容1903年在《革命军》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人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18],革命的要义在于“养成冒险取进、赴汤蹈火、乐死不辟之气概”[19]。
“在此背景下,表达冒险、抗争、尚武等题材的小说最受时人的欢迎”[20],以弘扬男子气概、塑造少年英雄见长的冒险小说借势而入。可以说,加强男子气概是晚清的文化情绪,冒险小说的译介正是对晚清男子气概缺失的抨击和对冒险精神的呼唤。晚清进步人士纷纷译介或创作冒险小说,形成了近代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冒险小说刊行热潮。随着革命派正式与改良派划清界线并逐渐胜出,革命思潮日益盛行,“革命”一词在1906年使用多达2800余次(6)革命观念自1900年“排满革命”和“政治革命”兴起后,开始扫荡几乎一切观念领域。具体分析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65-399.,一定程度上推动了1905—1908年冒险小说译介高潮的掀起。一些冒险小说出现了“多译本的盛况”,“说明当年志在为中国少年输送精神粮食者的勤勉”[21]。总之,晚清“接受冒险小说的初衷,自然是出于时势之需,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士’的责任与抱负接受了含有科学及尚武意味的冒险小说”[22]。
二、晚清小说地位的整体提高
冒险小说兴起于晚清的直接原因在于小说地位的整体提高。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是文以载道,小说自古被视为“小道”,依附于诗歌,地位低下,难登大雅之堂。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晚清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了小说于启蒙民众、缔造强大国家的重要作用。1897年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就指出了小说的教化作用[23]。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有识之士开始真正重视小说启蒙救国的作用。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强调各国政治改革与小说启蒙关系密切[24],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将小说列为“文学之最上乘”,认为它是改良社会的利器,承担着改造社会、拯救危亡的功能[25]。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逐渐从社会边缘转移到社会中心,小说整体上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小说界革命带来了全新的小说观念,文以载道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道”强调忠君,恪守仁义礼智信,近代的“道”强调冒险、进取、进步、自由、民主等西方文明思想,“被化约为近代国家民族思想”[26],由此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从表达到接受环节都富含政治元素。大批文人出于救亡启蒙的政治需要,不断加入小说作者和读者之列,他们有意识地以小说为武器,怀抱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入世精神,书写主题也日益政治化。“在小说革命的热潮中,不少本来政治色彩较淡或甚至毫无政治色彩的外国小说,在介绍到中国来时,都被加以一种‘政治性的阅读’——译者往往在译序或后记汇总引导读者去‘阅读’其中的政治意义,且把中国的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27]。总之,晚清作家和读者都喜欢讲政治[28],“由此激发出晚清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大变动”[29]。这种变动可以从当时民营出版行业的出版物一探究竟:“印刷书籍的内容从四书五经等科举用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童蒙读物发展到戏曲小说、中西书志、教科书籍、新学书籍”[30],不论是“中西书志”“教科书籍”,还是“新学书籍”,都致力于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富有现代视野,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就翻译小说而言,“当时译书的目的主要在于输入文明而不是考虑其文学价值,或主要在于借鉴其思想意义……均是为了唤醒沉睡的国人,使其感动奋发,投袂而起,以西国少年豪杰和巾帼英雄为榜样,振兴国势,再造中华”[31]。梁启超、林纾、包天笑等大量译介科幻、侦探、冒险、教育等作品,主要介绍英雄人物或少年主人公的冒险故事,让西方少年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且,“中国早期的翻译作品中,译者按语以至评论者评语所表达的主题,十居其九是西方人那种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32],不少译作序跋明确表示其译作旨在于激发“少年”的冒险进取精神。如,1902年沈祖芬在《绝岛漂流记》自序中写道:“在西书中久已脍炙人口,莫不家置一编。……乃就英文译出,用以激励少年。”[33]近代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高梦旦在给《绝岛漂流记》撰写的序中揭示,译者译介此书是“欲借以药吾国人”,以“激发国人冒险进取之志气”[34]。1905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云中燕》书首叙言中写道:“是书亦足为振起少年精神之一助。”[35]
三、冒险小说的文类特点
冒险小说被译介到晚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冒险小说的文类特点。这类小说主要为“少年”写作,包含拯救、英雄主义、生存、勇气、职责等叙事要素,注重展现行动和男子气概。小说往往以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背景,包含危险、冲突的行动或事件,行动主人公为“少年”,他们喜欢挑战,行动果敢,展现男子气概,反映为帝国服务的爱国理念[36],又融合了自信与幻想破灭、傲慢与焦虑,最重要的是展现暴力[37]。故事的基本元素为:勇敢、文明的白人“少年”在朋友或仆人的相伴下,开启探秘寻宝之旅,他们冒险进入陌生场域,其间遭遇种种磨难,经历个人与原住民、新环境或自我等的冲突,凭借机智和勇气,借助地图或手枪等现代文明手段,最终化险为夷;甚至开拓荒蛮之地,以基督教教化蛮夷,传播西方文化精神,最后荣归本土。“少年”在不断冲突中经历成长,获得重生,重新认识自我,收获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丰收,实现男子气概的成长;故事展现了“少年”强硕的体魄,弘扬“少年”的忠诚、勇敢、智慧、正义、文明等美好品德,凸显追寻财富和自我成长的主题。
事实上,“冒险”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叙事元素,一直是西方文学作品中一个重要的叙事原型,可以说,西方文学作品对“冒险”的表现由来已久,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人传说到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日益增多的冒险传奇作品,都表现掠夺与征服的主题。作为一种重要的西方文学形式,“冒险是、而且总是男性主义的——为男性写作,庆祝男子气概……从最深层次来说,冒险是属于男人的”[38]。“冒险”有助于增进男性认同,摆脱传统男性阴柔的一面,“被视为重新激活男子气概的重要载体”[39],在塑造“少年”的男子气概中作用重大。“少年”唯有经历各种考验后,才能实现个人成长,找到一个全新的自我。从深层次来说,“冒险”是一个追寻自我身份甚至与内心自我作战的过程。“冒险”预示着进入一个陌生的异域空间,深入到内心深处与自己对话,展现男子气概;换句话说,“冒险”是输出男子气概。从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说,“冒险”提供一种有力的隐喻,喻指人类的机遇、危险、进取、意志力、对抗、胜利等,是一趟生理的、道德的、文化的旅行[40]。总的来说,冒险小说“表现了对种族、男子气概和帝国的共同关注”[41],是“使帝国充满活力的神话”[42],有助于阐释历史、帝国、勇气或权利[43],对西方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波及到世界各地,包括同时期的晚清中国。传统中国崇尚文治,反对蛮力,只有《山海经》《搜神记》《西游记》等神怪小说,从来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小说。根据晚清黄伯耀的论述,这类神怪小说虽不乏对冒险之事、冒险之人的书写,但现实生活中能称得上勇敢之人的则寥寥无几,这主要归因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即冒险之人总有神灵或邪术庇护,缺乏哥伦布式的实地探险或福尔摩斯式的科学的办案手法,其所宣扬的是忠孝仁义等儒家传统道德思想,未能有效地激发读者的勇敢之力。传统中国提倡忠孝节义,奉行以孝治国。根据儒家的伦理规范,“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被视为百行之冠,道德之本,“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44],“父母在,不远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好好爱护身体是尽孝的开始,而冒险意味着损伤身体甚至牺牲生命,是一种不孝之行。冒险甚至被视为好逸恶劳,不事生产,不供养父母妻儿,是大不孝。因此,民众不被鼓励冒险远游。传统中国缺乏冒险精神,缺乏进取、争胜的精神特质,“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45]。
在晚清外国文学译介热潮中,西方翻译小说,特别是冒险小说被选中,“以拔除学生‘畏葸之性质’”,成为“培养学生‘独立坚忍’之性格的有效利器”[46]。冒险小说的主人公多为少年英雄,他们冒险奋进,积极进取,“表现出当时国人被视为欠缺的素质——坚强的体能和智能”[47],富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其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的冒险精神对改造国民奴性、激发国民的男子气概大有裨益。用黄伯耀的话说,“惟探险小说则不然,其寄意也远,其运笔也奇,其神于所遇也,历千辛万苦,而必求达所探之勇敢之目的。聪颖之思,沈毅之力,胥于是乎具矣,故曰为现象社会增进慧力也”[48]。
此外,冒险小说经常描绘异域风情,情节跌宕起伏,富有趣味,对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中国人富有强大的吸引力。小说甚至以浪漫、审美的眼光看待死亡,将死亡修辞化,有助于鼓励国民尚武好勇。主人公要么携财富荣归故里,要么抱得美人归,这种大团圆结局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对于正在遭受苦难的晚清民众来说也是一种鼓舞与憧憬。最为重要的是,小说展现的种族歧视与压迫、亡国灭种等叙事元素,能够让晚清民众感同身受,产生亡国忧患意识,从而奋起抵抗,强国保种。
四、结语
晚清中国内外交困,国运岌岌可危,整个社会亟需男子气概。梁启超在思想界大力提倡尚武精神,以振奋衰微之民族;在文学界强调小说有助于形塑新民,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晚清有识之士积极响应梁启超的号召,纷纷译介或创作新小说,借助小说表达维新变革主张和强种爱国思想,小说一跃成为革命话语的中心,被赋予救亡启蒙、强国保种的重任。冒险小说宣扬“少年”的冒险奋进精神,有助于激发国民的男子气概,因而被大量译介到晚清中国,成为晚清文学译介中的重要一类,并引发晚清时人效仿、创作冒险小说,在近代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冒险小说在晚清的译介与传播,主要源自晚清特定的接受语境和冒险小说的文类特点,其中夹杂着进化论思潮、社会文化风气的转变、媒体境况、译者的主体性及读者阅读口味等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它契合了救亡启蒙的时代需要。小说弘扬的冒险奋进精神成为形塑“少年”、改造国民奴性、实现强国保种的利剑,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探险小说最足为中国现象社会增进勇敢之慧力”,“探险××者,就所长而引掖之,趁鼓荡之潮流,速进步之效果”[49]。
冒险小说中“少年”的冒险进取精神及其追求个人价值的理念作为塑造“少年”民族之魂、鼓励“少年”英勇救国的利器,肯定了“少年”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价值,提高了“少年”的社会地位,对几千年来的老者本位、重老轻少等思想形成了巨大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7)“儿童本位论”由周作人于1914年最早提出。具体参见:周作人.小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A]//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C].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210.的形成。此外,小说宣传的西方文明进步思想,言说的世界文明新秩序想象,对于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晚清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助于新的世界秩序观念的形成。进化论思想主导下的西方文明观念改变了传统天下观,冲击了以“礼”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以“力”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念开始流行,也促使社会权力进行再分配,有助于建构新的社会文化秩序。
冒险小说“可借以鼓励国民勇往之性质,而引起其世界之观念”[50],倡导以“力”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观念,促使晚清民众发现“少年”,由此“少年”作为“新民”代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晚清中国有了别样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