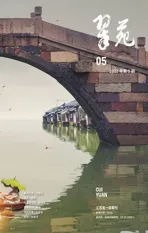在异乡与异乡飘荡
——周洁茹《在香港》读札
2022-04-06陈荣香
○ 陈荣香
游来游去的鱼——周洁茹和她的作品
从常州走出的女作家周洁茹,是一名70后。1991年,她首次在《少男少女》发表诗歌《雾》,真正“出道”于1993年,时年17岁的她在自己打暑假工的常州文学杂志《翠苑》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独居生活》。此后,一发不可收,她夜以继日“不顾一切地写”(《回忆做一个练习生的时代》),勤奋加上天赋又有野心的她,从20岁到23岁,写了有二百多万字,光发表的文字就有一百余万。作品陆续见于《雨花》《萌芽》《作家》《上海文学》《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十月》《当代》等国内文艺大刊,她称当时自己在各期刊发小说就像“集龙珠”一样,一时风头无两。
《作家》于1998年7月推出“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7位女作家的作品、创作谈集体推出,特别惹眼的还有女作家们的玉照亮相。随后“70后作家”“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等概念甚嚣尘上。巫昂称之为“把写字的人都恶心坏了”。(巫昂.那些飘零异乡的灵魂和空心人)周洁茹对这样的称号也颇不以为然,“我一直想要摆脱的一个标签是‘美女作家’,包括70后女作家、女性文学、美女作家,这些都是我最想要扔掉的标签。”(李菁.周洁茹《小故事》:她们的故事,细碎如星光)当作家贴上了一种标签,同时意味着她书写的其他可能性被遮蔽住了。对于真正的作家而言,作品是其最好的代言人或者实力说明,而不是其他的评价标准如性别、出生年代,甚至是长得美与丑这些“非文学”的因素。
此后,她的书陆续出版:二十四岁出版第一个长篇小说《小妖的网》(2000),童话《中国娃娃》(2002);小说集《我们干点什么吧》(1999),《长袖善舞》(2000年),《我知道是你》(2000),《你疼吗》(2000),《抒情时代》(2001),《梅兰梅兰我爱你》(2002);散文随笔集《天使有了欲望》(2000)等。这是她青春中最“闪亮”的高光时刻,就在她于文坛大放异彩的时候,正是在这一年,她选择了急流勇退,辞别文坛,青春离场,出走美国。
20到24岁,不喜欢吃鱼的周洁茹以“鱼”为标题写过好几篇创作谈:《头朝下游泳的鱼》《一天到晚散步的鱼》《活在沼泽里的鱼》《海里的鱼》。这些创作谈抒写了她在别人以为的安逸稳定幸福的生活中的痛苦与挣扎,“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幸福或者给了我幸福,我却痛苦。要么离开给我饭吃的地方,饿死;要么不离开给我饭吃的地方,烂死。我已经不太在乎怎么死了,死总归是难看的。长此以来,我无法写作。身体不自由,连心也是不自由的,写的东西就充满了自由。”(《岛上》)当时她是一位有编制的公务员,“六点上班,六点下班,不能迟到,不能早退。下班回家,写到凌晨四五点,直接刷牙去上班。班车上的来回半小时时间睡觉。”(《一个写作到黎明的女孩》)她的拼命三郎式的写作正是缘于不自由。她用一头近乎染成白色的头发作为反叛与挑衅,她的头发因此也成了机关里令人侧目窃窃私语的奇观。沼泽里的鱼渴望摆脱委顿不堪的环境向往江河湖海的浩大,1999年23岁成为专业作家,“终于辞职做了专职作家,开心得做梦都笑醒”(《看着天亮》),以为自己终获自由,没想到专业作家“不坐班但是开会开来开去的生活,真是太残忍了。”“鱼是厌倦了做人的人”,大海是它的归途,但不幸的是,“我只是一条淡水鱼,我比谁都要软弱。如果他们笼络我,我就被笼络;如果他们招安我,我就被招安。”(《岛上》)这条挣扎来挣扎去的“鱼”在2000年“游”过了太平洋,去了美国。她的写作和在中国的生活同时告一段落,就此封笔十五年。
从这里游到那里,从常州漂到加州移到纽约再迁到新泽西州,2009年,作为独生子女的她,为了在物理空间上离父母所在地常州更近一些,从美国漂洋过海移居香港成了新香港人。2013年担任《香港作家》副总编辑,不久就不干了;2017年任《香港文学》副总编辑,2018年接任《香港文学》执行总编辑。暌违文坛15载,2015年,她开始了全面复出。“我因为命运复出写作,我直接告诉你,命运。命运叫我重新开始写作的,命运说的,你是天才,你不写了可惜了,去写吧。那就再写一写吧。我若是失败也是命运,命运说的,那就这样吧,不写也行,你好好生活吧。”(《有一种话》)
复出后的周洁茹,笔力集中在四个方向:女性与新移民的故事,散文与创作谈。在2013年9月至2020年10月,周洁茹发表了50篇短篇小说、70篇散文以及多篇创作谈。2015年-2022年出了十五本书,一本重版,两本港版。制造了属于周洁茹的“速度与激情”。似乎20岁时那个写作疯子周洁茹再出江湖。“神奇的2017年,与我的1998年极为相似,我在这两个年份都是发表了18个中短篇小说,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安排好的。”(庄大森.周洁茹:归去来兮谈“复出”)
时光里的浪子——回不去的故乡
2019年《在香港》出版,这本散文集由四辑组成:故乡、香港、写作与问答。写故乡主要重现父母亲人、童年记忆,还有舌尖上的美味。写香港则主要落笔于日常生活及风物。写作与问答与她的精神生活——文学相关联:写作为何及如何。“她的散文新作《在香港》出版,同样呈现了一位漂泊者的观察与反思,而更令人深刻的是周洁茹所反映的精神主题——无论人在怎样的异乡,对所回望的故乡都将用上一生的目光。”(陈培浩.用文学回望故乡的漂泊者)回望故乡,封存于记忆中与童年、父母相关的片段纷至沓来。
“我回家乡的意义,一是看父母,二是吃好吃的。”《故乡》一辑中作者历数江南小城常州的吃食。主食有常州萝卜干炒饭,荠菜大馄饨,兴隆素菜馆的素面楼外楼的汤团。江苏人有“青菜豆腐保平安”的说法,各种美味豆制品:热气腾腾的胡葱豆腐、香菜生豆油拌常州豆腐、豆渣饼塞肉,横山桥百叶红汤水煮,“能下两大碗米饭”。天目湖砂锅鱼头是地方特产,喝一口汤,鲜得掉眉毛。扣肉、白芹、过年吃的炒素,再炒上一碟油汪汪的乌塌菜。具有常州地方特色的中式点心:三德素菜馆的绿豆蓉饼,米饭饼虾饼馅重皮酥的椒盐麻糕、糍饭糕绿豆糕、韭黄春卷、糖芋头……美好又日常的时光、回不去的故乡就在这冒着烟火气的一菜一蔬的记忆里。
为什么食物与故乡相关?食物蕴含的意义丰富,对人的生存来说,饮食的满足是第一位的。对于个体而言,食物差不多串起人一生成长的脉络。“味觉不会骗人,它是我们精神世界最直接、最真实的反映,让我们身在异乡,却时常在心里掂量着故乡的分量。”(严飞.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现代人的生活与情感不确定性太多,但是有一样不会变,能让我们安心地有所期待,那就是妈妈做的饭,“全世界都会变,妈妈的味道永远都不会变。”母亲精心制作的三丝鱼,“一个父亲早逝的朋友,吃到了,认为那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三丝鱼。”而她因为不爱吃鱼,一口没有尝过,后来“我在美国为找一盘唐人街的夫妻肺片,横跨了两个州的时候,突然理解了我的幸福。我想那一道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母亲做的三丝鱼卷,肯定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毫无疑问的。”(《三丝鱼卷》)食物中藏着友情。吃串串,如果没有三五好友抢着吃,“所有唾手可得的东西,都让人兴味索然吧”。(《一个人的串串》)食物也是他乡遇乡音的标志,“网油卷这三个字对我来讲,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辨别饭桌上自称老乡的老乡到底是不是正宗老乡用的。”(《故乡的食物》)
食物是表达爱的方式,它是一种情感上的慰藉,也是一种祝福。母亲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吃的留给孩子,也总会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母亲把自己爱吃的萨其马留给女儿,女儿不爱吃,原样带出去又原样带回来。等到父母暮年,女儿看望父母也带着萨其马回家,不是因为自己爱吃,而是母亲爱吃。虽然作者不擅长厨艺,但是成为母亲后,为儿女做的有限的几个菜——包菜炖豆腐、番茄炒蛋,总是先要烫去西红柿上的皮,再用心地熬煮。食物成了家族传承的基因密码,因为“好好地吃饭就代表我们对这世界的热爱,好好地吃饭就是好好地生活。”(《一定要好好地吃啊》)即便只是家常便饭,肚子吃好了,胃熨帖了,感到整个生活都会变好。就是一小瓶自家熬的酱,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也能吃出深情,就在于煮饭人的心思与爱意都在里面。当年岁日长,贪恋的不再是食物本身,而是伴随食物一起扑面而来的生活的印迹。全世界最好的三丝鱼,是母亲亲手做的。全世界最好吃的馄饨,是和朋友一起去吃的。吃的食物滋味到底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做饭的人以及和谁一起吃。
故乡与食物相关,故乡让人念兹在兹的更在于亲人。“在香港望故乡”的姿态本无意为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时间永恒而无情,消逝的不是时间,消逝的只能是时间中的人与事。“二十年前住在美国的时候,三五年回一次家乡,觉得以后的日子还长,十年前搬去香港,有了回家的便利。现实却是忙东忙西各种胡乱忙。父母后来住进了养老院,我想着更要常回家看望,想着想着,等待加等待,年纪大起来,直到坏了牙。”(《牙》)与时间赛跑一般想承欢于父母膝下尽孝,但是小的时候父亲最爱吃的鱼片干,如今“父亲和我都吃不动了。说起来真是伤感啊。”(《鱼片干》)慈爱的双亲日渐衰老多病,无忧无虑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人越长大,越到中年,越发感到对一切无能为力,人定胜天成了笑话。经历过父亲病危、抢救、插管、拔管、切管、鼻饲等无数崩溃的时刻,“也终于看到其他人类的人生,我之外的世界,所有生命的悲喜。”作者感受到鲁迅所言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人类的悲欢竟是相通的。“香港和常州来回奔波,有人问我不辛苦吗?我不想答,如果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如果我还有亲人让我为此奔波,那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怎么会辛苦?”(《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笑了》)因为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人的悲哀与遗憾往往源于熟悉的事物渐次消失,所谓斗转星移,物是而人非。一个人心境上的变老也正意味着人的存在本身在发生变化,这个“变”明显地体现在一路走一路丢失的很多东西上。这些东西包括消逝在旧时光里的一切,父母、朋友、童年。故乡就在更北的地方,两个小时的物理飞行距离,但它仿佛就是这样的遥不可及。总以为家乡一直都在,自己想回就回,长大了却总有各种不得已的理由,回家的行程一拖再拖;总以为父母一直不老,结实年轻抗打,还是自己坚强的依靠,转首眼昏牙落,垂垂老矣;总以为自己一直是个孩子,还能随时任性,但是无情的时间之轮飞速旋转,谁也无法令它停下。现实世界没有魔法,人不能更改剧情。父亲的病痛,身不能亲替,深感作为人子的无能为力。作者可以在小说中解决主人公的难题,甚至逆天改命,但是回到滚滚红尘,生活中的诸种焦虑、担忧、愧疚、烦恼……人类所遭遇的一切苦楚,爱与哀愁,悲欢离合,痛苦与煎熬,生老病死等,都得肉身承受。心想事成终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祝愿。也许一切只有通过写作能得以重现,写作是与时间相抗争的一种方式,在写作中时空可以逆转,故乡与童年也能够重返。
空间的漂泊者——在香港
周洁茹既是“港漂”也是“海归”。“现代人的宿命就是成为异乡人,在周洁茹这代作家的身后,一个剧烈全球化的世界史正在展开。”(陈培浩.在香港,望故乡)苏北人要到江南来,江南人要到上海去,上海人则要越洋过海去往异国他乡。对于空间的位移,她比常人更为敏感。她被称为城市的“漫游者”(邵栋)、“游牧者”(马兵)、“漂浮者”(常鹏飞)。她写过“到……去”系列小说:《到常州去》《到上海去》《到南京去》《到香港去》《到直岛去》《到深圳去》《到广州去》。“这是我写作上的习惯。如果我要改换我生活的地方,我会写一个《到哪里去》去提醒我的方向。比如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写了《到常州去》,因为我在常州。后来我写了《到上海去》,因为那时候我想要到上海去生活。后来我又写了《到南京去》,因为我又想到南京去生活。我只是想想,所以我没有去上海也没有去南京,我去了美国。”(《在香港写小说》)去过印度、伊朗、西非、美国南方腹地等诸多地方的奈保尔,有一个观点:“我不能去了一个地方,却不就它写点什么。我会觉得我错失了那一份经历。”(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对于周洁茹来说,她的“到……去”系列,也正是她在写作方向上的思考。她在美国时却没有写出《在美国》或者《到美国去》,原因是心理上没有准备好接受客居美国的事实,尽管她在美国住了十年,但在写作上,是空窗期,“是完全空白的十年”(《在香港写小说》),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回避与情感上的自我阻隔。
“到……去”是一个带有方向感的动词,准备,兴奋,期待,动身,启程,随时抽身,是忙里偷闲出逃的一段私生活,是游离规则之外的自在呼吸。远方一直是浪漫的想象之地,异乡有时成为自由灵魂的精神寓所,那里没有假想敌。“我后来写作就很注意方向……因为现在香港,所以又写了《到广州去》,这些地方,对于我来说,永远是去,而不是来。”“如果你看到有谁写过《在南京》或者《在北京》,那么他的现在感就真的是很强烈的。”(《在香港》)她在常州,在加州,在香港,“在”是一种日常的、在场的状态。俗事缠身、凡人庸世纷纷扰扰,是勘不破的红尘,但这就是生活,而真实的人生正是创作的源泉。
作为在香港的异乡人、新移民,《香港》这一辑以移居地香港为地理背景,文中多有对日常生活与香港人与事的书写。国泰空姐拎着隔夜面包搭机场巴士、利安邨的疯子追着自己跑了三层楼的惊险、地铁上扒住门高唱海阔天空的西装男、九龙湾翻白眼的滑冰婆婆,当然还有香港的好,丢了的东西总能接到电话让去取……她写在香港搭乘地铁巴士上班的日常,每天像时钟一样精准,记牢车次与时刻表。5:45是起床时间,做完一切家务,洗澡,刷牙,晾洗衣物,出门赶7:20或者7:35的巴士,如果都没有赶上,铁定迟到。在争分夺秒的早晨,一家只卖粉果小食的早餐店,排了三十米长的人龙,每位客人从下单到离开,绝不会超过六秒。(《我有两条路》)每一样行动的背后都仿佛有一个隐形的时钟在滴答作响,不能有任何闪失,一旦有意外,就意味着日常规则的打乱。齐美尔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中说到,“现代人的聪明才智越来越变成一种计算智慧。”“如果在约好的事情上和工作上没有准确的时间观念,那就会全都乱了套。”“大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迫使人们的生活要遵守时间,要精打细算,要准确。”(齐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正是大都会规训了城市居民的守时与精确。货币经济,还有现代的理性主义,一致要求人们遵守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时间就如一直悬于头顶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令现代人精神高度紧张,时刻绷紧了弦,一改乡村或者田园生活带给人的悠闲感。
即便作为精英的她在香港生活、工作了10年,她与香港、与香港人之间仍隔着一堵厚厚的墙。香港人的排外情绪,体现在部分香港人对周围不是原住民、不说广东话、说普通话的异己———新香港人的那种狭隘的偏见,他们怀着拘谨、冷漠、反感、轻蔑、憎恶、排斥等各种情绪。九龙湾溜冰鞋女士对着说普通话的一家人翻着白眼,滑冰场的香港人指着“我”不要碰他们的鞋:“滚!”(《九龙湾》)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马铁上坐在旁边的老头儿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低吼‘不要在公众场合说普通话!’眼珠瞪到两倍大,靠着门,气得发抖,像是经受了巨大的侮辱。”(《马铁》)哪里都是异乡,在哪里都是过客。在香港生活了多年,她仍然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仿佛时刻准备着撤退的姿势。
“强调‘在’其实是因为并未真正扎根。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很少会意识到他‘在香港’;一个地方的空间、文化、语言、饮食与祖居者如盐化水,会让人忘记了身在何方,只觉自来如此,本该如此。‘在’是一种介于主人与游人的意识,不妨说,‘在香港’其实是一种香港新移民意识。”(陈培浩.在香港,望故乡)一方面,她拥抱生活。2000年奔赴美国就是因为有人劝她要好好生活。“生活着”,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作家,她随时能抽离出来,对生活冷静旁观。作为新香港人,她与周围的人也好、事也罢,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她是一个旁观者,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游离者。现代都市里的人,均行色匆匆,与环境有些格格不入。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住在美国对美国排斥,住在香港对香港排斥,就连回故乡,发现故乡也不是自己的了,“我的城已经不是我的城……如今就住在一个《失城记》里。”(《妈妈写了两封信》)加谬在《阳光与阴影》中写道,“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与己无关。”她不愿称自己为移民作家,而更愿意称自己为流浪作家或者移居作家。在她的作品《邻居》中写出了香港人的生存状态,其实也是现代城市人的普遍状态,“冷漠到残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一点确实也是没有地域的界限的。”地理概念一直是她城市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地理对于作者本人城市漫游者的身份也带有一种确认的力量。“香港是我的现在。我在香港。”(《我们只写我们想写的》)
结 语
周洁茹的散文与她的小说,在语言风格上一脉相承。文字带着一种疏离感的质朴与简约,就像盐一样普通却有着独有的风味。任何食物可以没有糖没有油没有香料与味精,但却不能没有盐。她的散文简约直白,语言质朴无华,用的都是平常句子,寻常话语。如说东西好吃就简单粗暴“好吃死了”这样看起来没有技术含量,往往被有识之士避之不及的用语。夸朋友让自己感动,也是直接表白“世上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不加矫饰,天真素朴却不烂漫。像香葱拌豆腐般直来直去。看多了云山雾罩、重嶂叠翠、叠床架屋类重重包装的语言后,再来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有一种油然的放松感。这既和她的创作态度相关,也和她的个性相关。她对生活采取的正是一种旁观和流浪的态度。“我做一切减法,不写多余的字。”(《现在的状态》)
除了素朴的语言风格,情感上的“真”是她散文的另一特色。散文随笔写的是生活中的所遇所闻所感,它的实质是带有作者生命印迹与情感内核的“真”。它不像小说可以虚构,可以充满了戏剧性。生活不是一场假面舞会,没有观众,也不需要观众。“生活一定不要是一场表演,即使台下坐了那么多观众。我的写作也是这样,不迎合,不抗拒,没有欣喜,也不必悲伤。”(周洁茹.小对话:女性)写作对于她来说,是一件纯洁纯粹的事。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就是摆脱不了也不想摆脱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