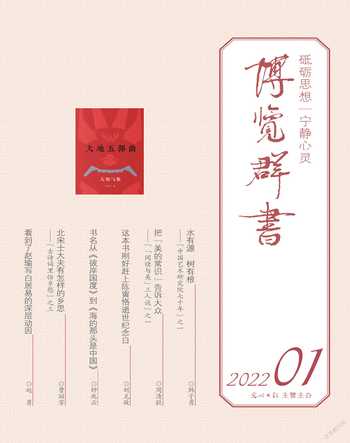乡愁曾走进汉代诗家的思绪
2022-04-02刘立志
刘立志
思乡之情与生命个体对归属感的需求密切相关,固然是人类共同具有的情感体验,但是,对于血脉中至今流淌着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而言,乡恋、乡思、乡愁则尤为重要。对故乡的精神皈依与深情呼唤是构成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生存方式的人们在心灵深处实现无障碍沟通的少数永恒情感之一,是我们民族心理结构、感情倾向、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正因如此,乡恋、乡思、乡愁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在反复咏叹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言志抒情的诗词领域,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到当代诗人们的倾情创作,表达乡情的作品从未缺席。诗人们用他们细腻善感的心灵,品味着远离故土时思乡念亲的情感體验;用他们的生花妙笔,谱写了一首首感人肺腑的故乡恋曲。那些注满了乡愁的诗词名作如同闪耀在我们民族心灵成长史上的粒粒明珠,引导着也温暖着一代代为了追寻理想,固执地离开家乡的游子的前行之路。让我们走进悠远而亲切的古人的情感世界,去了解汉代的乐府诗篇在表达乡愁时形成了哪三种互相映照的抒写模式,唐诗中的乡恋主题作品又是如何记载唐人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思考,提升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思内涵与艺术价值的,宋代词体兴盛,乡思乡恋题材由诗入词又经历了怎样的探索过程,元明清乡愁诗词又是如何在前人丰厚的创作实绩上呈现出自身的时代特点的。让我们的心灵经历一番自汉至清一路绵延而来的故土之情的浸润滋养,然后再默默地感恩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
——曹丽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人自古安土重迁,非不得已不愿意离开故乡,不愿意与自幼熟悉的自然环境和宗族体系相脱离,流落四方,去异地他乡谋生,成为游子。先秦时代,《诗经》《楚辞》里就有不少描绘游子怀念故乡的诗篇语句。《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困滞在他乡的宋国人对家乡系之念之,隔着黄河遥望故乡,固执地安慰自己:谁说宋国和我距离遥远,我踮起脚尖来分明看得清清楚楚。《小雅·采薇》述写久戍边关的征人的思归之情,“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回家吧回家吧,年头拖到年尾,一年一年过去了,有家不能回,徒然哀叹自怜,莫可奈何。《小雅·小明》中,乱世使于远方的大夫,经久不归,满怀怨愤,“岂不怀归?畏此罪罟”“曷云其还?岁聿云暮”“曷云其还?政事愈蹙”,对于自己当初入仕的选择,悔恨交加,内心焦灼不安。《唐风·杕杜》一诗为流浪者感叹无人相亲相助,“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远离父母兄弟,身处窘迫境遇,求助不得,孤独落寞,情恸鼻酸。《楚辞》中的乡愁表现得更为深沉丰富。《离骚》描写怀有美政理想的诗人在现实中遭受小人的谗毁、君王的离弃,求美人、寻知音处处碰壁,去留之际,一度矛盾彷徨,最后抛弃了“溘死以流亡”的念头,毅然决然身赴国难,终致舍身殉国。《哀郢》中“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诗人对家乡日思夜想,希望能够返回国都,施展个人的抱负,挽救时政危局。《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一语更是不期然揭橥了后世游子乡愁诗文的一大主题。
汉代人继承了前代的文学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乡愁佳作。
“游子”一词的最早出处难以查考,但是在汉代已然流行,成为常用语汇。《史记·高帝本纪》记载刘邦谓沛地父兄之语云:“游子悲故乡。”《汉书·高帝纪》沿袭不改,唐代颜师古注曰:“悲谓顾念也。”训解极为精准。东汉班彪《北征赋》曰:“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与高祖语前后一脉相承。刘邦身为亭长,文化水平有限,而班彪则为著名文士,不同阶层通用此语,足见汉人对于游子思乡之情已有明确的认知与把握,乡愁的抒写成为诗歌创作的习见题材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观传世的汉代诗歌,游子思乡之作或出于平民之手,或出于贵族之手,还有一些中下层文人之作,除了刘细君《乌孙公主歌》、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外,主要见于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氏。这些作品述及远离家乡的缘由有三,一是服劳役,主要是参军戍边,一是和亲远嫁,一是奔走谋生,个中情形不一,难以尽数。
依据核心内容的差异,汉代游子思乡诗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述写乡愁大体形成了三种模式, 一是泛言怀念家乡,渴望归返;一是将家乡具象化,代之以亲人如妻子、兄弟等,或是拈出故里亲情,隐然以为比照;一是集中笔墨描述异国异域之风俗,凸出中外之殊异,比衬诗人思乡之心切。三种模式,皆有佳构。
《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收录《悲歌》,诗云: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垒垒。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身处异地的游子远离家乡,思归不得,只好以远望来代替还乡,但是草木葱郁,山冈累累,遮住了视线,这么一点卑微的心愿都无法达成,游子内心的沉痛不难想见。
五言古诗《古八变歌》的抒情模式与《悲歌》相似,还是抬头思故乡,只不过场景变成了黄昏时分: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
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
章华台是春秋时期楚灵王建造的一座离宫,作者应该是滞留在楚地有感而发。在向晚的北风中,诗人登台望乡,秋意渐浓,入目一派衰飒景象,桑叶凋零,了无生机,莎鸡悲鸣,声声凄苦,想到当下的自己四处漂泊,有如无根的蓬草,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属呢?游子的根始终深扎在故土,故乡才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但是如今故乡却可望而不可见,变换的物候,肃杀的氛围,使得敏感的诗人倍感凄凉,彷徨且无奈。
与之类似的还有《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
座中何人,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开篇劈头便是愁云压顶,突兀而来,之后交代身处的环境——胡地、狂风、高树,继而揭明愁苦头白之缘由——离家思乡。想来主人公应该是据守边塞的戍卒,离乡万里之遥,久居胡地,家乡仿佛是暗夜里远处摇曳的一点灯火,令人欢乐,但更多的是令人忧伤,始终萦绕于心,无法割舍,无法靠近,痛苦怀思,难可名状。
上述诗篇对于游子心心念念的家乡并未作具体的描写,家乡更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与此相应,汉代有些诗篇对于乡愁意涵的界定相对较为明确。
旧题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前人多怀疑出于后人伪托,现今学界认定为汉末文士遗作。其中一首云:烁烁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凉应节至,蟋蟀夜悲鸣。晨风动乔木,枝叶日夜零。游子暮思归,塞耳不能听。远望正萧条,百里无人声。豺狼鸣后园,虎豹步前庭。远处天一隅,苦困独零丁。亲人随风散,历历如流星。三萍离不结,思心独屏营。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
在渲染了他乡深秋荒寒、远僻阴森的景象之后,主人公触景伤情,想起离散的亲人。诗中的“萍”字,逯钦立先生以为当是“荆”之误文,“三荆”乃游子故乡所在之地。曹明纲先生以为三荆与“山荆”同音,也可看作是游子称呼自己的妻子。两说比并,则诗句乃是使用双关手法。诗人天涯流落,或是为公务所羁,或是为功名之计,与挚爱的妻子离居,孑然一身,寒与暖无人关切,苦和乐莫可倾诉,长夜难捱,愁肠百结,“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时空的遥远隔不断相思的纠缠,这种乡愁真可谓是一种幸福的牵绊。
汉代乐府诗篇《艳歌行》也极具典型意义: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
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
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
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
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
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远离家乡谋生的流浪者颠沛流离,孤苦无依,有幸受到热情、善良的女主人的关爱,为他们缝补破旧衣衫,却因此受到男主人的猜疑。他们只能以清者自清开慰自己,徒自慨叹,不由得想起家乡——那里,以血缘别亲疏,父母、兄弟聚族而居,相亲相爱,彼此照顾,有求必应,不会被孤立,也不会遭抛弃,时时刻刻感觉到的,是醇厚的温暖与关怀,没有夹杂一丝的虚伪与做作,而今无端遭到猜忌,两相对照,冷暖立见,令人难以自持。“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他乡生活中的细琐不如意事触发了诗人心底的乡愁意识,胸中漾起的波纹细微而真切,浸透了人生的辛酸。这首诗的主题和内容与《诗经·唐风·杕杜》高度相似,两者应该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诗人从三百篇里汲取了营养。
显而易见,这两首诗中述及的游子思乡较之前一类来得更为真切,它们将乡愁落实到对亲人和亲情的怀念上,有意回避了时人常用的、陈旧而俗套的家乡、故乡等字眼,从而使得原本流于空泛的乡愁变得生动起来,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
家乡之外的区域也包括异国,身处异国的人萌动乡关之思,他的乡愁是对于遥远的故国的心心念想与牵挂。汉代乡愁诗的第三种模式就是述写身居异国者眷念故国,行文之中描述异国异域之风俗,而和亲政策与社会动乱是孕育此类作品的现实土壤。
《汉书·西域传》载录刘细君《乌孙公主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刘邦建汉至于汉武帝时代,四五十年时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实力雄厚,兵强马壮,不时南下侵扰,一直是汉廷的心腹大患。汉武帝时欲联络西域乌孙国一起挟制匈奴,于是采用和亲政策,两次以皇亲宗室女为公主嫁与乌孙王,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就是其中的第一位。刘细君先是嫁给乌孙国王昆莫猎骄靡,后来又嫁与昆莫猎骄靡之孙岑陬为妻,远嫁思乡,作为此歌,或称作《悲愁歌》。
诗中描述了乌孙居住、饮食方面的习俗,“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吃的、住的、用的都不是女主人公在中原时所习惯的、所熟悉的那些,更不要说其地通行的祖孙共妻习俗,尤其大悖于汉人的伦理观念,但为了达成故国的政治用心,身居举目无亲的绝域异地,刘细君只能适应,她心中的苦闷与哀愁,难以排遣,郁结在胸,回家啊,回家啊,恨不得肋生双翅飞返父母身边。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她最后终老于乌孙,未曾归汉。
有刘细君类似遭遇的还有王昭君,她作有四言诗《怨旷思惟歌》,讲述她入宫、去国、远嫁的经历,情感也是一例的凄恻哀婉,但字里行间没有提到异域风俗。
东汉末年,桓灵乱政,朝局崩颓,董卓进京,祸国殃民,为祸弥久,中原复为逐鹿之地,生灵涂炭,虽大族名士亦难幸免。著名文士蔡邕的女儿蔡琰在战乱之中为胡骑所掳掠,被南匈奴左贤王纳为妃子,陷身夷狄十二年,后来曹操将其赎回。蔡琰撰有自传体的长篇叙事诗《悲愤诗》(五言、骚体各一首)和《胡笳十八拍》,记述她在乱世中的悲惨遭遇,可谓字字血泪。
学界历来怀疑《胡笳十八拍》出于后人伪造,争讼纷纭,据许云和、石雅梅《丁廙〈蔡伯喈女赋〉与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兼论〈后汉书·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结合与蔡琰同时期的丁廙所作《蔡伯喈女赋》内容,考论以为《胡笳十八拍》信为蔡琰所作,创作时间与丁廙赋相同,都应该是在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五年之间。
蔡琰在诗篇中多次描述匈奴风俗,五言《悲愤诗》云: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
骚体《悲愤诗》曰:
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
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兽兮食臭腥。
这其中涉及风俗和气候两个方面。《胡笳十八拍》中更是不止一次提及,所述颇为充分,“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鼙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原野萧条兮烽戍万里,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遂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言及匈奴部族毛皮服饰、肉奶饮食、牛羊粪垒铸窝棚、逐水草而居、崇尚武力与壮美等习俗,确实非亲历者所能言。
异国思乡诗作,因为作者先验预设的读者就是生活在文化较为发达地区主要是中原一带的同乡人士,因此对于内地习俗一般不予赘述,而是集中笔墨刻画异国殊俗,诗人认定读者会自行作出比较和考量,从而生发出对诗人沦落的深刻理解与同情。如此行文,构思巧妙,笔墨经济,入人也深。
汉代的乡愁诗篇,或是泛言怀念家乡,或是指明怀想的是亲人或是那份浓浓的亲情,异国游子思乡则经常涉笔异族习俗,三种模式,相互映照。值得注意的是,汉人身处异地抒发思乡之情时,尚未涉及对于家乡风物的回忆与描述,刘细君与蔡琰诗作语涉胡地习尚,尽管作者心存对比之意,但毕竟是隐含的,尚未有只言片語铺写中外风景、习俗之差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批评《诗经》有物色而无景色,只是对一草、一木、一水、一石的简单描写,到了屈原时代,才开始注意结构、位置布局,由状物而进入写景。的确,《诗经》中的景象描写太过粗略,太过零散,景物只是感情触发的媒介,至于《楚辞》作品,写景功力乃有长足进步,风格也趋于多样。汉代游子在他乡有所感怀,绘景寓情,由此及彼,应该是自然之事,但传世诗作尚未见有悬想语涉家山风物者,是史阙有间,还是汉人另有思考,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