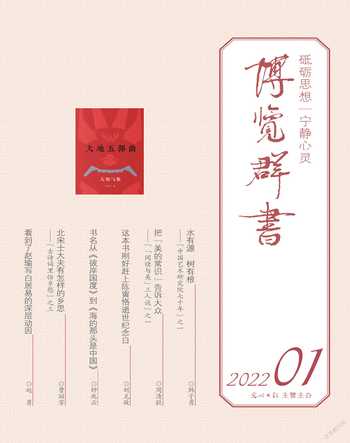这本书刚好赶上陈寅恪逝世纪念日
2022-04-02刘克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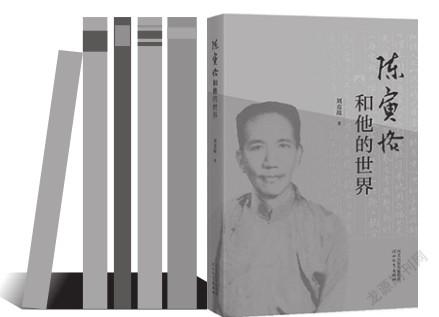
《陈寅恪和他的世界》这本小书近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称得上是几经波折方才问世,算起来是我第四本集中写陈寅恪先生的书。
第一本《陈寅恪与中国文化》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第二本《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2006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第三本《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2009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而这第四本,本来计划是在2019年陈寅恪逝世50周年出版,阴差阳错地拖到2020年,那么想正好可以改为纪念陈寅恪130周年诞辰,也很有意义。不过,新冠疫情的暴发打乱了一切,之前联系的一些出版社也不得不取消或表示看好此书但无法保证何时出版。
也就在我基本放弃出这本小书的时候,经由一位青年编辑朋友介绍,河北教育出版社看到此书的初稿后很快决定和我签约,商定尽快出版——这让我十分感动。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具体负责此书编辑工作的几位老师,河北教育出版社对拙著的厚爱一直令我感动。
说到这本小书的写作起因,似乎应该从多年前我开始接触陈寅恪学术说起,或者说从我第一本陈寅恪学术思想研究专著《陈寅恪与中国文化》说起,它其实是我第一本单独署名的书,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它是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也就有必要详细说一下我如何写博士论文。我是199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导师是王铁仙先生。说起来在报考之前我和先生并不认识,只是报名后才“临阵磨枪”抓紧看了先生的一些论文,知道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是他的舅舅,先生自然也是瞿秋白和鲁迅以及左翼文学研究方面的大家。不过我入学后,先生从来没有要求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更未要求我撰写这方面的论文,而是允许我自由阅读和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正是“陈寅恪”研究成为热点的时期,我当时既被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所折服,更为他的人生经历所感动,就想以他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但我也有担心,因为毕竟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基本都体现在中古文史研究以及语言、宗教、哲学等领域,和现代文学有关者很少,如此我以“陈寅恪研究”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题目显然有“越界”的嫌疑。
不过,当我多少有些惴惴不安地向王铁仙先生提出我的论文设想时,他不但没有异议,而且鼓励我说这个题目虽然难度很大,但他看好我,认为我能写好。我本来想了一些如果导师不同意,我如何为自己争取一下的理由,结果导师这样鼓励我反而有些担心。我问导师这样的题目是否算是“越界”,导师说现在不是鼓励跨学科研究么,你研究陈寅恪就是跨学科,没有问题。而且陈寅恪毕竟和鲁迅、胡适、许地山等人有很多往来,他的一些文章也有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的论述,这些你完全可以写。先生还说本来文史哲研究就是不分家,现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甚至研究盛唐的可以不看中唐以后的文学,这是不对的,应该打通。
听了王铁仙先生的一席话,我坚定了从事陈寅恪研究的信心,从那之后基本上一直没有中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有关陈寅恪研究的著作也出了四种——因此我能坚持到今天,第一个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王铁仙先生。
虽然在导师鼓励下确定了博士论文题目,但真正准备起来我才发现问题大了,不但我的学术准备严重不足,而且资料也极为缺乏。1995年那时还没有网络,从图书馆能够获得的主要资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那一套陈寅恪文集以及很少一些论文,至于海外和台湾、香港学术界的有关资料更是寥寥无几,有些还是放在特藏室不能出借,我只有手抄和复印,更多是手抄,因为那时复印费实在太贵。
如果说资料难以搜集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找专家学者请教就更困难,记得当时上海本地专门从事陈寅恪研究者不多——其实不是没有,是我孤陋寡闻,就想到外地拜访一些名家。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学者而是作家,就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作者陆键东先生。我是通过三联书店的一个编辑获得陆键东的电话,电话联系后就去广州拜访他。陆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有些今天看当然比较幼稚,但陆先生的回答依然对我有很大帮助。然后我第一次去了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故居,并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遗憾的是没有多少收获——虽然中山大学图书馆有一个专门的陈寅恪图书收藏室。之后我又去了北京等地,在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前凭吊,也试图查阅一些资料,但收获依然不多。现在想来,收获不多的原因其实和自己当时眼界不够开阔有关,有些史料在今天看其实很珍贵,但在当时我可能以为没有用处。不过,还是有很多著名学者对我的研究给予支持和鼓励,如周一良、傅璇琮、刘梦溪和海外的汪荣祖等,他们有的是我登门拜访,有的是写信求教,无论哪种方式,他们对后学的态度都是一样热情和真诚,以致今天再读他们的书信依然会有莫名的感动。至于本校的钱谷融、徐中玉、王晓明、殷国明和陈子善等先生,更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并极为具体地指点我的写作,令我十分感动。
大概是1996年春天,我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当时没有电脑,只能手写,为了表示对陈寅恪先生的尊重,也多少有点追求所谓的仪式感,我特意找一个朋友印了一些特大的稿紙总共是二十本,每本一百页,每页500字。我的想法是如果论文最后写十万字左右,这二十本足够我修改十次。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仅仅是引言就让我整整一个星期也没有写出来,主要是找不到感觉或者说没有灵感。有一天我正在苦恼时,随手拿过一篇写王国维自杀的文章浏览,脑海中突然有了想法,何不以王国维投水自尽于昆明湖作为引子,联想到中国古代文人对“水、河流”的描写作为开头呢?这就是现在《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开头:
中国文人,一向对时光的流逝特别敏感,而把时间与水联系在一起,更能让人们对一去不返的人生感到迷惘与惆怅。大概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开始,历代诗文对此就有了无数的咏叹……gzslib202204021141说实话,这几句今天读起来感觉有点做作,当时却让我一下找到阐释陈寅恪的途径,那就是论述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以及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复兴做出的一切努力。
论文的写作由此进入比较顺利的阶段,大致我每天写千字左右就停下,然后看一些资料,想一想接下来如何进行。当我写完论文初稿最后一行时,感觉虽然不能说写得多么深刻,但毕竟写出了我理解的陈寅恪,如此论文通过应该问题不大。初稿拿给导师看时,导师说没有想到你真的写出来了。不错,这个题目能写出来就不错。果然导师看过后给我很大鼓励,当然也指出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总之,等到论文全部修改完成提交答辩时突然发现自己才刚刚懂得一点点,如果重写一定会更好,可惜没有时间了。
论文写好后按照学校要求第一步是提交外校专家评审,记得评审专家有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南京大学的叶子铭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郭志刚先生,中山大学的黄修己先生和上海師范大学的史承钧先生等。承蒙各位先生厚爱,均对论文给予较高评价,并同意进入答辩环节。论文答辩时间则是在1997年六月,我和室友郑家建一组,他的论文研究的是鲁迅的《故事新编》。答辩委员会的组成堪称“豪华”,主席是钱谷融先生,答辩委员有复旦大学的吴中杰、潘旭澜教授,苏州大学的范伯群、朱栋霖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明、殷国明和张德林教授。各位先生在对我论文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需要提高和改进之处。为了撰写此文,我特意找出珍藏多年的钱谷融先生对我论文的评语复印件,以下就是其中主要部分:
刘克敌同志的论文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与探讨,与学术界已有成果相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与深入。论文不但对研究对象有深刻的把握与精到的分析,能发人之所未发,提出独到的见解,而且从行文中也流露出对陈寅恪这一代学人的心向往之的仰羡与一种无可奈何的感喟,确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我知道钱先生的评语多有过誉之词,其他先生的评价也是如此,现在说这些绝无炫耀之意,主要还是表示对那一代老先生的敬意。而且,答辩时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些先生在提及陈寅恪时那种由衷的赞叹以及谈论他们这代人一生命运时的感慨,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一定要把陈寅恪研究继续进行下去。
论文答辩后不久,有了一段暂时放松的时间。记得有一天接到电话,对方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卫,是我的校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他说他们出版社有意将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我当然很激动,连忙表示同意。不过他提出论文要有较大程度的修改,字数也要增加,我于是很快进入修改完善的工作之中。那时我已到山东一所高校任教,一面工作一面修改论文,因为刚写完论文不久,很多内容都很熟悉,修改比较顺利。由于李卫是责任编辑,与出版社的沟通都很顺利,而且我当时觉得只要书能出来,其他如印数什么等都不重要。我对出版社只有两个要求,一个是封面要有陈寅恪先生的画像,再一个是扉页上要有“谨以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这一行字。
既然是自己的第一本书,又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善而成,我当然要请导师王铁仙先生写序。不过,他却谦虚地说自己对陈寅恪没有多少了解,推荐复旦大学的吴中杰先生来写这个序。吴先生和我导师是多年老友,论文写作中我曾多次向他请教。我论文答辩后他还让我把其中一章修改后给他,在他主编的《海上论丛》发表,所以由吴先生写序我也是喜出望外,认为和导师写没有两样。就在一切都完成准备出版之际,意想不到的是书稿惹出一次风波,导致出版几乎夭折。原来是出版社把书稿交给几位外审专家审读,据说有一位专家认为我的书稿不该对陈寅恪大加赞美,因为陈寅恪的思想立场有问题,所以我的立场也有问题。好在出版社没有认同他的意见,此书出版才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初版就印了7000册,即便在20年前也不算少。
《陈寅恪与中国文化》出版于1999年9月,至今已有20多年,之后我又出版了《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以及《陈寅恪和他的世界》等几本“陈学”专著。我相信那位专家如果今天再看我的这些书应该没有什么意见了,如果还有,也许就是怪我没有什么进步,对陈寅恪的解读缺少更深刻、独到的见解罢。
对我的第一本书说了那么多,其实是想说我今天这本《陈寅恪和他的世界》在思想脉络上是与第一本相通的,是我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些新的思考——尽管依然肤浅。估计可能有读者已经看出我这四部“陈学”著作的联系,就是不但书名有很多重复的词语,而且都有一个“与”或“和”字。这一方面说明我不会给书起名字,也说明我可能有意无意在强调陈寅恪和他那个时代的关系。
至于此书的写法,其实是一个新的尝试。从纯学术角度看难度并不大,倒是在写法上要费一些周折。从事陈寅恪研究多年的经历,让我深感陈先生学术思想的深邃和阔大,也渐渐意识到有必要向更多普通读者介绍陈先生的一生及其学术成就,而不能满足于仅仅在纯学术领域传播。有鉴于此,才想到是否可以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和相对轻松的方式解读陈先生的一些论著或者是论著节选,意在起到一个介绍或导读作用,让读者由此对陈寅恪和他的世界产生兴趣。此外,也想把近年来所写陈寅恪与其师友交往的一些文章编进去,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些期待的变化,不至于过于沉闷。当然,既然是出于普及的目的,也就必然在引用陈寅恪著作原文的时候使用简体字,并且只能横排。为此出版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劳动,繁体转为简体很不容易。——这虽然有悖于陈先生生前的愿望,但在找到更好的处理方式前,也只能如此,还请陈氏后人和有关专家学者见谅。至于本书是否真的可以引起读者对陈寅恪学术的兴趣,也只能看此书问世后的反应了。
这本小书的最后问世刚好可以赶上10月7日——陈寅恪逝世纪念日,也就以此表示我对陈先生的缅怀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