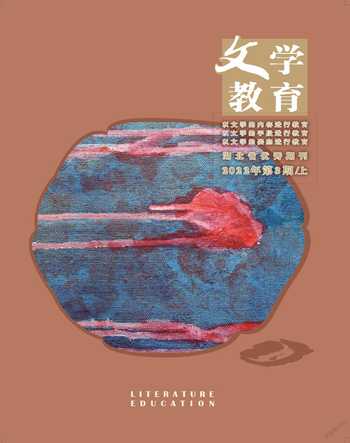香港特区文化认同意识探究
2022-04-01徐小双
徐小双
内容摘要:始于2019年上半年的香港暴力活动深受以下两个意识的推动:一是背后涌动着的“香港本土意识”及其引发的“香港民主”“香港独立”等思潮,反映了当前部分港人在后殖民文化渗透下与内地间强烈的观念冲突;二是某些港人对自己的国家没有文化认同意识。带有西方殖民主义色彩的香港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意识使得回归后的香港对同处于大中华文化圈下的中国内地和中央政府产生了离心力,进一步导致其本土意识被利用,激化了以谋求香港独立为目的的分离意识,为今日香港之困境埋下了导火索。为此有必要正视香港与内地的观念差异,发扬中华文化,尊重各自文化意识,不断加强文化自信以增进香港同胞对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感,逐渐减少冲突和对抗,实现真正的人心回归。
关键词:文化圈 香港本土意识 文化认同意识
1997年,在举世瞩目中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然而由于历史、地域、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香港与内地在融合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不足以造成2019年上半年“反修例”风波以来香港暴力活动的不断升级,亦不足以促使香港陷入危险的境地。况且从根本上而言,香港与内地同属大中华文化圈,彼此存在着天然的文化认同性。有鉴于此,有必要将相关问题,特别是港独风波背后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意识问题,置于文化圈语境中进行深入研究。
一.文化圈
1.文化圈概念的提出
文化圈(culture circles)概念最先莱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 é nius,1873-1938)提出。在文化神話学理论中,文化人类学家弗罗贝纽斯将非洲划分成不同的文化圈,发现每一个文化圈都具有一系列物质文化特质,地理环境相同的地方会产生相同的文化。文化圈理论既能运用于个别文化中,也能运用于整体文化中。1911年,德奥传播学派代表人弗里兹·格雷布纳(Robert Fritz Graebner,1877-1934)对文化圈概念做出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个地方一次性产生,向四周传播,从而形成了以该地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而一个文化圈的边缘又与另一文化圈相交叉”[5]。
2.文化圈有关空间和时间的规定
文化圈可以从空间角度强调文化特质的分布状态,即地理空间上的相同文化特质在一起构成文化丛,特定文化丛结合的特定空间构成文化圈。与此同时,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文化圈内还存在着不同文化特质出现的时间顺序,即共处于一个文化中的不同特质所显示出来的时间上的先后顺序[4]。文化圈根据时间维度可划分为原始、古代、近代等文化圈,按地区可划分为东方、西方等文化圈,东方文化圈是东方文化中最大的一个文化圈,以中国儒学文化和佛教文化为代表。“中国内地和香港同属于大中华区,具有大中华区文化圈的共同本质属性,如使用汉字、崇尚儒学等”[3]。西方文明源于两希(希伯来和希腊)文明,其主体思想基本围绕着人、欲望、宗教而展开,自由民主意识根于其中,引领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取向。殖民时期的香港就深受西方文化圈的影响,形成了与内地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次文化圈。
二.香港的特殊历史与其本土意识的形成
“‘本土意识’是指属于某个地方……”[1],从本质上来讲,本土意识作为一种地域意识存在,表现为对某一地区的热爱和归属。中山大学区鉷教授认为: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个人身上又会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主体意识[2]。可见,“香港本土意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的积淀,同时又与当今形势有一定的关系。
1.香港殖民地历史与其本土意识的产生
香港的历史可以追根溯源至5000年前,秦军南征百越,香港一带正式归入中国领土,此后一直置于中华主体的管辖之下,直至1841年鸦片战争清朝战败,才于1898年被迫割让,成为英国的殖民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发展停滞的内地相比,香港经济腾飞,本土文化逐渐兴起,香港人逐渐确立起一种具有优越感的本土意识。与此同时,香港社会兴起的诸如“六七反暴运动”“金禧事件”等一系列反殖民运动成为香港本土自我意识觉醒的有力推手,然而这些社会运动并没有撼动英国殖民文化在香港的影响力。“在‘香港本土意识’中,既有体现香港精神、能够凝聚香港社会‘爱国爱港’、‘爱乡爱土’情怀的本土意识,也有刻意突出所谓‘主体性’的本土意识”[8]。为获取香港精英阶层和市民的支持,港英当局随之采取行政吸纳政治精英、教育培养“亲英”力量、文化扶持淡化国家认同等一系列“柔性殖民”政策,后殖民主义意识不断被融入到香港的本土意识中,香港人民因此不断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熏陶,在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上与内地形成差异甚至对立,香港也从最初的“反殖民主义”本土意识逐渐转向了“反中”的本土意识。
2.香港回归20多年中本土意识的逆向崛起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的中心地位在“一国两制”的保驾护航中始终保持不变。但是,回归后的香港并没有真正地开展“去英化”“去殖民化”的教育工作,在西方殖民文化占上风的情况下,任受到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的香港青年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教育还停留在空白期,部分港人的“恋殖”现象日益突显,将内地视为文化落后的“他者”。随着内地的迅速发展壮大,部分香港人骨子里的自我认同和优越感受到冲击而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反华情绪日益高涨,对中华文化和国家的认同感日趋消减。在这种形势下,本土意识伴随着“伪主体”意识在香港崛起,香港社会日益夹杂着更强烈的“小香港”狭隘思维,缺乏“大中华文化圈”的宏观视角。
3.保守主义的抬头和本土意识的激化
201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风云变幻,英国脱欧,北爱尔兰与苏格兰站出来也想脱英,欧盟的凝聚力和一体化受到巨大冲击。2017年特朗普在第45任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中大肆宣扬“美国优先”的口号,此后美国“毁约退群”的单边主义行动层出不穷,促使西方文化逐步走向保守主义,欧洲分裂趋势也愈发明显。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保守主义的抬头和香港本土意识的崛起,促使部分香港人在国际舞台一片“退”“脱”声中跳了出来,涌现出了大量不满特区政府和反感内地的青年之声。部分情绪化、非理性化的香港青年对内地产生情感扭曲,街头游行示威和暴力抗争活动频繁密集,反政府、反权威意识泛滥。这种“新常态”的背后是躁动不安的社会和暗流涌动的西方反华势力,香港的本土意识由此激化,逐步沦为反对派谋求香港独立的分离意识和极端主义的推手。
三.香港历史与其文化认同意识
1.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
港英政府在殖民期间除了对香港进行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还通过宗教、媒体对香港实现奴化教育。这种奴化教育以权利为导向,“强调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及其统一关系,崇尚‘人权高于主权’,个人的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6]。在教育方面,出于利己动机,港英政府推行普遍的英语教育,贩卖西方生活方式,西方价值观念不断渗透香港教育,一大批香港青年的思潮悄然倒向了西方意识形态化,而中文反倒成为了“二等语文”,在教育中常常不受重视。港英政府刻意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弱化港人的国家政治认同,这导致香港与内地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隔阂甚至社会对立;为回归后的香港种下了许多“不安定”的种子。
2.特区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无所作为
增强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根本在于提升语言、文化、历史教育,然而香港特区教育局并没有推行中国国民教育。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香港企业家伍淑清一针见血的道出了香港教育局的不作为:“仿佛不知道香港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从来没有兴趣去推动国民教育”[10];而作为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也成为了反华势力的“急先锋”,热衷于煽动学生群体罢课和发起各种乱港游行活动......可见香港的暴乱就是教育失败的直接反映。2000年,香港取消作为必修教育科目的中国历史,代之以泛政治化的通识教育,在教材中不仅有意炮轰中国的“一国两制”还对西方的“占中”行为加以粉饰,激化香港与内地矛盾。相比于学生从小就接受爱国教育的中国大陆,香港地区教材中爱国教育的缺失成为当今多数香港青年缺乏文化认同意识的一大因素,香港学校没有统一教材,教师授课自由,一些思想激进的教师对中国历史进行歪曲,助长了年轻人的不满情绪,培养了一代缺乏中国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年轻人。特区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不作为,最终使香港的年轻人丢掉了文化的根。
3.香港暴乱背后的文化认同危机
一个地域的文化形成需要经过历史的沉淀。纵观香港的前世今生,香港与内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两地间文化一衣带水,共处于大中华文化圈内。但是,英国在香港一百多年的统治使香港民众深受其所灌输的价值观影响,文化也随之西化,在文化多元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文化自我意识,在思维模式、价值理念上与内地民众形成了一定的隔阂和心理界限,缺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很多冲突的起源。香港价值观念里强调最多的是西方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强调个人至上和斗争精神,与大陆传统的家国教育理念、注重伦理道德存在很大不同。部分香港人将香港看作一个特殊的区域,很少有国家的概念,强烈的本土意识使得香港民众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高于对国家主权的认同,认为香港社会自由法制优于大陆。面对内地的迅速发展他们产生了一种香港“优越感”丧失的焦虑,渴望主体性和独特性,乐此不疲地追求西方反华势力所谓的“自由斗士”“民主战士”称谓,在文化和国家认同的泥沼里无法自拔。
四.思考与建议
1.厚植和谐理念,包容文化差异
主权中国之外还架构着一个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文化中国。《左传》中记载道“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9]?当今时代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也反复强调“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是多元统一的整体,包含着“差异”和“创新”,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以和为贵、以文化人的交往理念温润人心,所以生生不息。陆港地区间的文化差异由于历史等原因而生,但这不应该成为冲突和对抗的借口,两地人民要正视差异,尊重各自的文化圈,和谐共处于中华大文化圈内,针对不同于自己所处的文化圈内的制度、法律、社会习俗等要作出适应性改变和融入。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包容性的传统,摒除傲慢与偏见,厚植和谐理念,用包容化解分歧。
2.弘揚中华文化,增进文化认同
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不断弘扬中华文化,增进文化自信,宣传和引导香港人民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加强国民教育以形成两地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积极利用文化融合来化解文化冲突,从思想上加强香港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从而增进对内地的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和社会发展认同。“塑造文化认同的前提是基于血缘记忆、地缘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共有文化和同根文化,要积极发挥中华文化感召力强、依附力大的特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让香港青年主动寻求身份依附”[7]。香港与内地文化同源,无论是大陆人民还是香港同胞,他们的血液里都留存着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港独分子和反对派的居心叵测永远改变不了内地和香港的大融合趋势。
香港与大陆文化本同源,但是西方一百多年的殖民历史人为地切断了这条天然的文化认同纽带,很多香港同胞缺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并产生了强烈的本土意识,这导致部分缺乏社会经验的香港青年在港独分子和反对派的推波助澜下为追求所谓的“香港独立”而不断参与暴力袭击事件,促使2019年下半年以来的香港暴乱活动不断升级,多次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作为一座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城市,香港如少年般在栉风沐雨中成长,彷徨与叛逆随行,成长与希望相伴,针对香港暴乱,“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全国上下最大的诉求,香港与内地要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一国两制”政策优越性,尊重各自的文化圈,携手并进,在差异中寻求融合,在融合中化解冲突,以平复香港地区日益凸起的本土意识,增进香港同胞的文化认同意识,保证香港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推动“大中华文化圈”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Snyder Gary, The Real Work [M].New York:Directions Book,1980.
[2]曹山柯.近年我国的本土意识与后殖民主义研究[J].学术研究,2005,000(007):120-124.
[3]管艳霞.“一国两制”背景下内地与香港跨文化冲突研究[J].传播与版权,2013(02):104-105.
[4]王学基;孙九霞.文化圈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J].旅游论坛,2019,v.12;No.69,17-26.
[5]吴宁.移入与根植——中国人类学学科化进程研究[D].中山大学.
[6]杨红柳.从歧见到共识: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价值观探析[J].学习与探索,2017(7):79-85.
[7]姚嘉洵,孙晓晖.香港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困境及其增进策略探析[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
[8]祝捷,章小杉“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性梳理与还原—兼论“港独”思潮的形成与演化[J].港澳研究,2016(1).
[9]跟着习主席学传统文化之文明篇:温故而知新[OL].新华网,http://union.china.com.cn/zfgl/2014-09/26/content_72655
82.htm.
[10]“修例风波”造成香港家庭撕裂,为何价值观差异巨大[OL].北晚新视觉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4921
63548545846&wfr=spider&for=pc.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