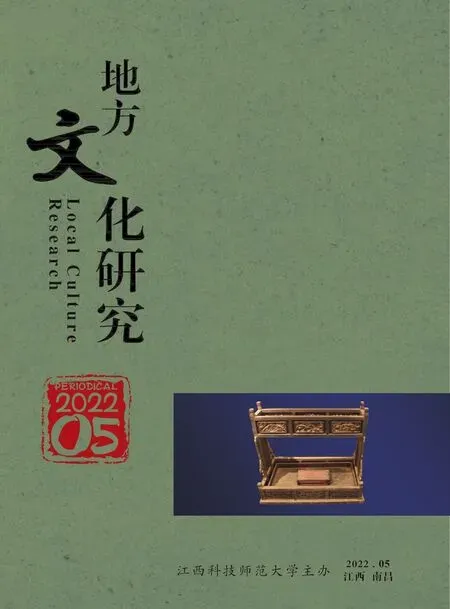《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考
2022-03-31谭经宇
谭经宇,阮 宏
(1.澳门科技大学,中国 澳门, 999078;2.肇庆学院,广东 肇庆,526061)
纯阳观是广州现存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自清季筑成以来,一直为南粤道教之显赫门庭,地位非凡,在广东具有不小的影响力。 广州纯阳观之兴建与清代十三行渊源颇深,不少学者已有论及,此亦为学界之共识①冼玉清:《天文学家李明彻与漱珠冈》,《岭南学报》1950 年第10 卷第2 期;谭元亨、宋韵琪、唐嘉鹭著:《十三行习俗与商业禁忌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年;王丽英:《浅论广州十三行商人的俗信——以潘家、伍家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11 年第3 期。。细看史学前贤的相关成果,不难发现各家所征引之材料大抵离不开一块石碑文献——《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由此足见这块石碑对于探究广州纯阳观与清代十三行之关系的重要性。然而这样一块重要的石碑文献,目前学界似乎囿于资料不足或研究兴趣之偏差,并未予以应有之关注,致使该碑之研究仍停留在征而未证的地步,缺乏系统而细致的学术探讨,其背后所反映之诸多问题也尚待进一步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不才,拟以《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所见之碑文史料为基础,结合相关的碑刻与方志资料,阐述石碑之由来、分析石碑所见之十三行史料、探讨纯阳观与十三行之真实关系,以期去伪存真,更好地还原历史真相。
一、《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及其由来
《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刻于清代道光九年(1829),原位于广州河南岛漱珠冈纯阳观内,是当初纯阳观道侣为出资捐建道场者流芳之用。 据《漱珠冈志》记载:“《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正书,存。 按,碑嵌壁间凡四张。 第一张载官员捐款数目,第二张以后载绅商捐款数目”②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7 页。。 该碑共有四块,原嵌于观内碑廊壁间,首碑载官吏捐输款项之名录,第二至第四块碑,则是刻录各乡绅商人的具体捐输数目。 从上述内容中可知碑文的内容无论是对于研究广州纯阳观的历史,抑或是探究道光时期羊城官商士绅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方面,都具有颇高的参考价值,对推进相关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 遗憾的是,纯阳观自兴建以来,历经沧桑,门庭屡废屡修,观内诸多重要古迹亦在历次变故中失之不存,而《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不幸正是其中之一。 正如纯阳观前任主持潘崇贤在《漱珠冈志序》中所述一般:“惜后历刀兵火革,羽士四散,道业凋零,观内所藏之文史档案阙失无遗,令今人考据漱珠冈与纯阳观之历史亦无资料可查。 ”①潘崇贤:《漱珠冈志序》,载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前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2 页。原碑已佚,而今人所能目睹之碑文内容则是昔日学界前贤冼玉清女士从原碑中摘录下来的成果。 冼玉清,广东著名女诗人、历史学家。 1949 年之前冼玉清女士曾多次携友造访纯阳观,对观内诸事如数家珍:“余读同治《番禺县志》,知校南有漱珠冈、纯阳观、南雪祠、清献祠诸胜。 按图索骥,因往游观。 及读壁间诸碑,得详建设始末。 ”②冼玉清:《天文学家李明彻与漱珠冈》,《岭南学报》1950 年第10 卷第2 期,第190-191 页。她在逸趣揽胜间偶然发现《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素以博闻强识称世的冼氏敏锐地发觉碑中的史学价值,认真抄录当中关于十三行行商的史料内容,随后于1950 年发表的《天文学家李明彻与漱珠冈》一文中,辟有《纯阳观与十三行》一节专述此碑之史料(《岭南学报》1950 年第10 卷第2 期)。 文中多次谈及此碑,首次为世人揭开了这块石碑的神秘面纱。此外,冼氏在其晚年所撰写之《漱珠冈志》中亦收录了这块重要石碑,并附上碑刻的简单介绍③《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载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7 页。。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流传于世的碑文内容正是冼氏所摘录之十三行史料,相关碑文内容及分析将会在下文中详细论述,此处先按下不表。 换言之,今人所能真正掌握之碑文资料仅仅是原碑内容的冰山一角。 饶是如此,亦无碍后世学人不断从中汲取学术养分。 其不仅被视作十三行与纯阳观关联研究之滥觞,还是研究行商与道教发展的重要凭证之一。
鉴于《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原碑失传,且可以参考的碑文内容颇为有限,要想理清该碑的千头万绪,则还需先从石碑的来龙去脉着手,方能减少岐见,更好地研究相关问题。
《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顾名思义是与广州纯阳观兴建之事密不可分。 广州纯阳观兴建一事,在当时的南粤可谓大事一桩,其建设之始末广见于方志及部分碑刻史料中。 譬如同治《番禺县志》载,“纯阳观,在河南漱珠冈,地近卢循故城,宋之万松冈也。 古松怪石,溪山如画。 嘉庆二十四年,羽士李青来始建为道院。观后有台,为青来礼斗处。总督阮元题额曰颐云坛。”④(清)李福泰修,史澄等修:《番禺县志》卷二十四《古迹略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第299 页。《南海百咏续编》亦有类似的记载,称“纯阳观在河南漱珠冈,地近卢循故城,宋之万松冈也。 古松怪石,溪山如画。嘉庆已卯,羽士李青来始建为道院。 观后有台,为青来礼斗处。 阮文达阁部题曰:颐云坛。 时过从之。”⑤(清)樊封:《南海百咏续编》卷二《道观》,载《南海百咏·南海杂咏·南海百咏续编》(合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211 页。纯阳观得以在南粤开宗立派,其开山祖师李明彻可谓有筚路蓝缕之功。李明彻(1751-1832),字大纲,一字飞云,道号青来,广东番禺人,生于乾隆十六年,十二岁时入罗浮山冲虚古观出家,号“明彻”,除学道外,还自学天文历法、测绘学、洋画、数学、地理等知识。 而立之年后诣京城求学,得当时钦天监监正之亲传,学成回粤,择居广州白云山。 李明彻曾任两广总督阮元之幕僚,以所学之天文地理知识助阮元修成道光《广东通志》一书,并与后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晚年积极奔走,促成漱珠冈纯阳观之兴建并任首任主持,最终于道光十三年(1833)仙逝,生前著有《圜天图说》三卷,《续编》二卷。 纯阳观内曾立有其于道光九年(1829)刻成之《鼎建纯阳观碑记》,碑文叙述了李明彻在河南漱珠冈创建纯阳观之始末,是研究纯阳观历史的又一重要碑刻。
至于广州纯阳观兴建之缘由,李明彻在其勒石碑铭中已详细指出:
漱珠冈者,因彻修省志,寻访万松山,到此见山环水曲,松石清奇,故取称“漱珠”之名也。 南临珠海之滨,北望白云藩屏之障。西来五凤,东接七星。朝云霞而印日,暮映月以辉光。周回绿水,八面青山。一遍平田青翠,嶙峋奇石玲珑。珠冈髙耸接云天,绕道苍松蔽日。奇花遍径,异草生香。左狮右象坐明堂,石蝠青羊拖后案。葫芦倒地,四面奇观。冈头虽小,景象非凡。有仙山洞府之规模,海岛蓬莱之恍样。应建道场,开玄宗正脉;创成法界,启列圣真传。蓬莱有路,仙径无差。接嗣修真高士,龙沙会上超凡,应祖师代天行化,岂不美哉! 随到五凤村访问,欲求此冈结茅耧息,祀奉纯阳帝君。 助贵乡之催官,功名显达;佑一方吉庆,福寿绵长。 此两全美举,应自天然,成斯无量功德矣①(清)李明彻:《鼎建纯阳观碑记》,载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罗国雄、郭彦汪点校:《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86 页。。
李明彻修建漱珠冈纯阳观之起因,是其助阮元修志四处访查期间发现漱珠冈山清水秀,形胜颇佳,是性命修真的洞天福地。 于是欲在此地开观立祀,以期保佑乡里,造福一方。 按照《广州府道教碑刻集释》的研究称,嘉庆二十三年(1818)两广总督阮元因慕李明彻天文地理之过人见识,招募其完善《广东通志·舆地略》六卷,及《晷度附近南极星图》《分野》《气候》一卷,遂命李氏勘查粤省各地②黎志添,李静编著:《广州府道教碑刻集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858 页。。 而据同治《番禺县志》可知,李氏首访漱珠冈则是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因恋岗上形胜而在当地结庐,其欲开玄门道场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为此,李氏在修志之余,不忘积极筹备纯阳观修建之事。《鼎建纯阳观碑记》提到他问访附近之五凤村,寻求乡绅捐助,希望能筹措建筑经费。“有林姓等语老师光降,荫我村庄,极为美事,乃本乡之幸耳。 此地是无税官山,我等住此数代看守,种植树木成林,幸蒙藉,岂不允从。 老师乃仁慈济世,必须要格外栽培,才成美举。 吾等酌量,卜吉奉送。 随具金帛礼仪,敬送陈林二姓,共同收领。 即日立成,送帖交执,任凭起造,永为世世安居,子孙代代共好。 遂卜吉日,平地筑基。 ”③(清)李明彻:《鼎建纯阳观碑记》,载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罗国雄、郭彦汪点校:《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86-187 页。至道光二年(1822)《广东通志》成书,李氏终可一心一意聚焦于纯阳观之事宜。 阮元则为了酬谢李明彻修志辛劳,于道光四年(1824)带头捐款,并发起州、府、县土绅长者捐输,资助李创建纯阳观,甚至还亲书“纯阳殿”牌匾以作表彰。“蒙宫保阮大人暨列宪大人捐签,绅士善信人等,一时共庆,随缘乐助。 先建大殿,陞座关光。 各处随后建造。 ”④(清)李明彻:《鼎建纯阳观碑记》,载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罗国雄、郭彦汪点校:《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87 页。直到道光六年(1826),纯阳观兴建之事才初告结束。是年农历四月三十日竣工之时,阮元等一众官员绅商出席开山盛典,纯阳观俨然已成南粤道教一大门户。 “于道光六年四月十三日开光升座,宫保大人会同列宪大人亲临祭祀。斯成千载威灵,继玄宗之大观也。”⑤(清)李明彻:《鼎建纯阳观碑记》,载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罗国雄、郭彦汪点校:《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87 页。李明彻为感谢粤省各界人士对纯阳观之支持与帮助,遂于道光九年(1829)勒石纪事以传后世,其中《鼎建纯阳观碑记》载门庭兴建之事,“所载实迹,遗留开山之记事矣。 开山鼎建全真道人青来李明彻笔记勒石。 ”⑥(清)李明彻:《鼎建纯阳观碑记》,载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罗国雄、郭彦汪点校:《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87 页。而《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则是载捐输助建纯阳观之人士目录及其捐输数目。 这便是《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之具体由来。
二、《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所见之十三行史料
前文已述《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现存之碑文内容,实为当初冼玉清抄录而来的十三行相关史料。 个中原委冼氏在《漱珠冈志》中讲的十分清楚:“第一张载官员捐款数目,第二张以后载绅商捐款数目,其中有可注意者为十三行。 ”⑦《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载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7 页。此即在冼氏眼中,碑文中能够引起她关注的就仅有与十三行相关的内容,是以专门摘录下来作为研究之素材。 换言之,冼玉清所摘录之十三行史料可谓是全碑的精华或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 尽管这只是冼氏有意为之的结果,但却间接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史料,为今人之研究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所见之十三行史料具体为何,今可参照《漱珠冈志》中的内容一窥其真容。 根据《漱珠冈志》记述,《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收录了九家参与捐输营建广州纯阳观的十三行行号及其各自的捐款数目。 “当时虽在中衰时期,而负捐输责任者尚有九行。 ”①《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载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7 页。具体行号及捐款数目如下:
一、伍怡和行捐款一百元。
二、卢广利捐银一百元。
三、潘同孚行捐银五十元。
四、谢东裕行捐银五十元。
五、刘东生行捐银五十元。
六、关福隆行捐银五十元。
七、梁天宝行捐银三十五元。
八、麦同泰行捐银三十五元。
九、李万源行捐银三十元②注:原碑内容中没有列出编号顺序,此为冼玉清在《漱珠冈志》中收录碑文相关内容后来添加的。。
对于碑中提及的九家十三行行号,冼氏亦作过一番研究。 冼玉清考之民国时期行商后人梁嘉彬先生所著《广东十三行考》一书,对各家行号的主持捐款者及行号之沿革,皆进行了初步考证,并将这部分内容都付之于《天文学家李明彻与漱珠冈》一文中。 因冼氏所写至考证内容颇为零散,为方便进行论证,今将相关内容整理成表格,以供参考,详情见下表1:

表1 《天文学家李明彻与漱珠冈》中关于广州十三行的考证③冼玉清:《天文学家李明彻与漱珠冈》,《岭南学报》1950 年第10 卷第2 期,第190-191 页。

(续表1)
《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所见之十三行史料文字尽管颇为有限,但却十分直观地展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其一,碑文显示了道光初期十三行行商的具体人数信息。 所谓十三行行商实为泛称,绝非字面上均是由十三家行商组成。 自清代十三行创建至覆灭,大部分时间里承充行商的数目一直在变动,少则仅有四家,多则甚至逾二十家,而符合十三家行商之数的时间仅有4 年。 从碑文可知,参与捐输纯阳观的行号共有九家,分别为怡和行、广利行、同孚行、东裕行、东生行、福隆行、天宝行、同泰行、万源行。 确切来说,尽管碑刻立于道光九年,但其碑文反映的是道光四年至道光六年间的十三行行商数目信息。 这可从李明彻的碑刻中觅得一丝端倪,他在《鼎建纯阳观碑记》中就提到道光六年纯阳观建成后不久阮元便调任云贵总督,而其它的官员乡绅度各有升迁变化,纯阳观的后续建设皆是由李明彻一人负责。 “至六月,阮大人高迁云贵,列位大人各有升迁,随后彻自一人办理。 ”①(清)李明彻:《鼎建纯阳观碑记》,载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罗国雄、郭彦汪点校:《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87 页。二则是根据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828 年(即道光八年)的时候九家商号中的福隆行因负债累累宣告歇业,其债务则由其他商家摊分②[美]马士著,中国海关史研究组译,区中华译,林树慧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五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184 页。。 三则是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之中文档案显示,道光二年(1822)七月,十三行全体行商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外船办理船牌事宜时,在文书中签名之行号足有十一家,而《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提及的九家商行均赫然在列③冷东、梁承邺、潘建芬主编:《广州十三行天宝行海外珍稀文献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174-175 页。。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碑文所反映之行商数目是道光四年至道光六年间的历史状况。
其二,是关于十三行捐款数额的信息。 在捐款助建纯阳观一事上,十三行行商们共计捐输五百九十五银元。 各家捐款数额从三十银元到两百银元不等(注:此处所述之银元为当时国际贸易流行之西班牙银元),其中怡和与广利两行捐款最多,各捐一百银元;同孚、东裕、东生、福隆四家行号次之,均捐输五十银元;天宝与同泰二行则又次之,捐输三十五银元;而万源行则位于九家行号之末,捐款数目为三十银元。 乍看之下,九家行号只是按照出资数额之高低来排序,实际上这些序列的背后反映着道光初年各商行的地位差异。 行商利用从官方手上获得的垄断清朝对外贸易的特权,享受国家的政策红利,那么行商群体也理应承担官府安排给他们的各种任务,而捐输则是诸多任务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行商与盐商同为粤东资本两大集团,每遇国家有事,彼等无不竭诚捐输”④(民国)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39-340 页。,纯阳观之修建显然就属于此列,是由两广总督阮元发起,十三行行商照例参与捐款的一次操作。 所以就如冼氏在《天文学家李明彻与漱珠冈》所述一般:“此伟大商行,虽濒于衰落,而一切公益捐输亦不能置身事外。 ”⑤冼玉清:《天文学家李明彻与漱珠冈》,《岭南学报》1950 年第10 卷第2 期,第190 页。另外,考之《广东十三行考》,可以发现行商的地位高低决定着每次捐输数目的多寡。 根据冼氏的考证,道光朝初期十三行诸商中以伍家的怡和行为魁首,而卢家的广利行则紧随其后,位于次席,二者可被视作是当时行商群体的领袖人物,因而按理应该就要承担最多的捐输数额,故而怡和与广利两行捐款最多合情合理。 至于其余七家洋行,同孚、东裕、东生三家均为于乾隆年间就承充行商的老牌行号,福隆行、天宝行、同泰行、万源行则是于嘉庆年间才始任行商的商行,而福隆行又为当中最早承充行商者,因而积累的财富也较另外三家成立于嘉庆年间的行号要厚实得多,因而将其视为与老牌行号对等的存在也无可厚非。 天宝行、同泰行、万源行三家行号承充行商时间较短,资历尚浅,地位与实力与老牌商号存在着差距,因而它们的捐输款项也相应不多。
三、碑文所见之十三行与纯阳观关系探究
《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所见之十三行史料,为今人揭示了九家商行捐助广州纯阳观兴建之情况,至于行商捐款对纯阳观鼎建之贡献如何? 是大是小? 重要与否? 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首先要从行商捐款在纯阳观捐款额以及建筑经费中的比重开始着手。 目前所见之《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史料中只记载了行商捐款共595 银元,并未列出鼎建纯阳观的总捐款以及建筑经费的数目。 欲要理清此端,还需从其它相关碑刻材料中觅得辅证,所幸的是,李明彻之《鼎建纯阳观碑记》恰能补前者史乘之阙。 据《鼎建纯阳观碑记》记载:
是我玄宗快事也,必须要堂堂大观为美。 共建大殿一座三间,东西廊房两间,正殿拱篷一座,拜亭一座,步云亭座,灵官殿一座,东客厅一所,左右巡廊二道,库房一座,内有楼阁。 后有云怡轩一所,四面巡廊。西厅二间,朝斗台座,上有亭阁,下有石室云厨二间,头门一座。四面围墙,通连接续。 连买山场,建造台椅什物,一应共计支用实银七千六百余两,共收捐签实银三千三百余两①(清)李明彻:《鼎建纯阳观碑记》,载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罗国雄、郭彦汪点校:《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87 页。。
李明彻为显玄门气象,对纯阳观营建一事极尽其所能,遂使纯阳观之规模,殿宇之气派,建筑之精美,冠绝羊城,即便放之于南粤道门中亦难有出其右者。 营建甚大的背后就是需要大量的建筑经费。 按照李明彻自己的说法,从道光四年到道光六年间,兴建纯阳观前后共花费白银7600 余两,其中接受各界人士的捐款额为3300 余两,其耗资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李明彻计算纯阳观建筑经费的货币单位是两,而《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提及的行商捐款所用之货币单位则是(西班牙)银元。 这是因为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实行“一口通商”政策以来,外商咸集广州开展对华贸易,外贸也日益兴盛起来,达到前所未有之高度。 清代中叶外国商品在对华贸易中大多缺乏竞争力,外商只好选择以中国需求量甚巨的白银作为交换物来进行贸易,久而久之,大量各式各样的外国银币从海外流入,充斥着广州市场,其中流通最广的当属当时的西班牙银元。 美国著名商人威廉·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就提及到:“自1825 年以来,有好几种银元被输入中国,在此之前最多的是西班牙的卡卢斯四世的银元。 中国人特别看重这种银元,通称‘老头’。 ”②[美]威廉·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64-65 页。由于流入的外国银币数量实在过于庞大,以致于在广东当地出现银元与银两并用不悖的情况。 《清朝外交史料》中就提及到:“按定例广东行商与外人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此事律例原甚详明。近来本国人等,喜用洋钱,行商以纹银购之。”③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1 册,北平:故宫博物院,1923 年,第14-15 页。由于外国银元大量涌入之缘故,导致了内地纹银日益减少之问题,甚至引起了清廷的高度警惕。 “外国船只以贩运货物为名,专带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以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④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3 册,北平:故宫博物院,1923 年,第21-22 页。此外,因各国银币的成色、度量衡等都与中国的银两标准存在明显差异,为消弥上述因素所带来之不良影响,甚至乎在广州十三行还诞生了一项专门以鉴别银币质量的行业——看银师。 《广州番鬼录》记载“现在我们来讲看银师,即鉴别银钱的人,或称‘银师’,他们也是外商不能缺少的任务,尤其是在收款时。 ”⑤[美]威廉·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63 页。凡此种种,尽皆说明在清代中期的广州, 西班牙银元与中国本土银两在经济活动中互相流通之现象颇为普遍,已经渗透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故而《鼎建纯阳观捐款人名碑》提及的行商捐款使用的是当时国际流通的西班牙银元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当是时西班牙银元与银两之间的换算比率为多少? 按照现今通用之说法,清朝时期1 银元可等同为0.72 两或1 两等同于1.39 银元。章文钦先生就持这一观点①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 年,第244 页。。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中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动而时常发生变化,所以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也曾提及到不同时期的银元与银两的汇率,譬如在1824-1825 年间公司曾定制了一种银元与银两的衡具,两者的换算比例是1000 银元兑换718 两②[美]马士著,中国海关史研究组译,区中华译,林树慧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五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117 页。。 而威廉·亨特则称“根据长期的经验,每1 枚银元,重量值银0.717 两,这已成当时所有结算的标准。 ”③[美]威廉·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65 页。另外,对于商人而言,汇率的变动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商业活动乃至最为重要的商业利益,所以他们往往都会在商业契约上注明货币间的换算比率。 若要清楚道光四年至道光六年间的银两与西班牙银元之间的汇率,最好的方法就是觅得相关的商业契约文书来作为明证,这样汇率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中就藏有一份道光五年(1825)注有银元换算比率的十三行商业契约文书可供参考。据资料显示,该文书是广州潘培春堂将其在十三行旁回澜桥的商馆晋孚行及其土地以番银七千元的价格永卖给东生行的正式契约④冷东、梁承邺、潘建芬主编:《广州十三行天宝行海外珍稀文献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275 页。。 《广州十三行天宝行海外珍稀文献汇编》一书对该契约文书的解读称:卖契中注明“一,实收到地价番银七千大元,每元一18,兑重五千零五两正,老司码平净元”,“验契价五千零五两正”(上面还加盖了红色官印)。 可知当时七千元外国银元,兑换为中国白银即五千零五两。 此卖契中使用的是中国特有的商业数字“花码”。 这是南宋时期从算筹中分化出来的一种进位制计数系统,使用特殊符号来代表数字,汉字计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相对应的符号分别为“丨、川、川、乂、8、一、一、三、文、十”,因其最早产生于苏州,故又称“苏州码子”。 卖契中的“一18”即“715”,说明一千元外国银元兑换中国白银七百一十五两⑤冷东、梁承邺、潘建芬主编:《广州十三行天宝行海外珍稀文献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275 页。。
按照上述之汇率来换算,当时十三行所捐之款595 银元约莫等于425.4 两。 425.4 两在当时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款项。 以李明彻购买纯阳观山场为例,李氏为此花费了白银一百两。 《漱珠冈纯阳观香灯祭祀经费奉宪暨置产业立明永远供奉碑记》载:“道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谕,本观山主青来家师于道光四年九月,备银一百两面交与善广善林仲家叔侄十六位亲同收楚。 将本山立劵送纯阳祖师建庙。 ”⑥《漱珠冈纯阳观香灯祭祀经费奉宪暨置产业立明永远供奉碑记》,载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8-89 页。照此计算,十三行所捐输之款足够买下4 个纯阳观山场。 另外,道光七年(1827)时任两广总督李鸿宾批准将南关东石角官地租金作纯阳观经费之用,金额为每年一百两。“核议缘由奉批如详,准将东石角官地每年租银一百两,由县征解司库以为拨给纯阳观香灯之用。至称此地亩数丈尺甚宽,倘将来加赠租额,亦如所议,仍留司解充别项公用,不得再请拨给。 ”⑦漱珠冈纯阳观香灯祭祀经费奉宪暨置产业立明永远供奉碑记》,载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8 页。以此观之,十三行捐款又足够纯阳观四年的经费之用。
饶是如此,但这个数字仅占纯阳观捐款额(3300 余两)的八分之一强,而比之于总建筑经费(7600 余两)则只占到5.6%而已。 这些数据直观地显示出,十三行的捐款在纯阳观鼎建过程中所起之作用并不如之前学界所想象那般重要。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纯阳观鼎建之规模实在太大,所耗费之财力亦过大,这就导致了十三行这笔客观的捐款数目在整个建筑经费中显得没那么重要。
实际上,兴建纯阳观的费用绝大部分都是出自开山师祖李明彻本人而非各界捐输。 在筹建纯阳观之初,李明彻就深知道场建筑耗资颇巨,且筑观之事只是他个人的行为,并不想烦扰他人,故而在筹措经费方面一直举步维艰,道观也迟迟未能动工。“甲申岁师于漱珠冈创建,尽用志局所酬金。顾不肯求诸贵人捐助,以故事久未观未就也。 ”①《漱珠冈纯阳观开山祖师李青来师行实》,载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0 页。经李氏自己盘点,为兴建漱珠冈纯阳观,其个人前后出资白银约4300 两,大约占到了建筑经费的56.6%,更是相当于行商捐款的十倍②(清)李明彻:《鼎建纯阳观碑记》,载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罗国雄、郭彦汪点校:《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87 页。。 至于这些资金的来源,李氏在《鼎建纯阳观碑记》中一一为世人道明:“因成员轻重不等,所有用长银两,是明彻历年所积笔墨金,及售《圜天图说》书价,并修省志修金,凑合银两,成全斯观,并无欠缺。 ”③(清)李明彻:《鼎建纯阳观碑记》,载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罗国雄、郭彦汪点校:《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87 页。碑文中提到资金来源包括李氏自己历年的稿费收入,售卖专著获得的钱财以及为阮元修省志所得之酬金三部分。 但如此重金亦未能满足纯阳观鼎建之款,与李氏结缘颇深的阮元知道内情后,急其所急,带头号召各界捐款终解李氏燃眉之急。 因此,于情于理,行商捐款仅为纯阳观建筑经费的冰山一角也就可以理解。
虽然十三行的捐款对于纯阳观的兴建作用有限,但十三行还是在其它方面显示出对纯阳观的重视。 譬如《漱珠冈志》里记载道光年间潘能敬堂曾向广州纯阳观赠送一大铁钟,重达千余斤。 “大铁钟,道光六年仲夏吉旦,潘能敬堂虔具洪钟一口,重千余斤,送至纯阳观。 ”④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3 页。潘能敬堂即行商家族潘家之家祠,故又称潘家祠,位于今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龙溪首约,至今当地仍立有《潘能敬堂碑》可供考证。 值得注意的是,此钟是潘家于道光六年仲夏吉旦送至纯阳观的。 道光六年即公元1826 年,仲夏为夏天第二个月份,即农历五月,而吉旦即是农历每月初一之义,因此潘家大铁钟是道光六年农历五月初一赠送给纯阳观的。 结合《鼎建纯阳观碑记》中提到纯阳观建成后的开山盛典是同年农历四月三十日,可以进一步得知此钟赠送之时间是在纯阳观开山的次日。 而铸造一千斤大铁钟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便可轻易完成的,由此亦可看出向纯阳观赠送之大铁钟是潘家早有筹划的产物,而绝非仓促赶制之贺礼。 同时,所赠之铁钟重达千斤,则从另一方面看出潘家或者说潘同文行对于纯阳观之重视。
潘家对纯阳观之重视还不仅于此,据冼玉清记载,道场山门上的石额上书篆体“纯阳观”三字,出自行商首领潘仕成之手笔:“纯阳观额,篆书,存。纯阳观,三字横列,道光潘仕成题。”⑤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4 页。另外,纯阳观之门联据传亦是潘仕成之杰作。 《漱珠冈志》称:“纯阳观门联,行书,存。 灵山松径古,道岸石门高。 每边五字直行。 道光丁亥八月潘仕成题。 ”⑥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4 页。据查道光丁亥按即道光七年(1827),即潘仕成所书之纯阳观门联是刻于1827 年。
然而,由于前有阮元题字“纯阳殿”之记载,不少学者误将纯阳殿与纯阳观混淆,因而对于潘仕成亦题字纯阳观一事仍旧持怀疑的态度,甚至不乏否定潘仕成题字者。 譬如《广州道教文化》一书认为潘仕成所书之纯阳观三字为伪作,倾向于是阮元所题。 书中原文称:
“石匾额右方有两行题字,记述了纯阳观山门重修的时间,一题‘道光甲辰季冬重修’,‘道光甲辰’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又一题‘民国庚辰年仲春重修’,‘民国庚辰年’即1940 年。 石匾额末署‘潘仕成书’四字,但潘仕成殁于1873 年,显然此四字非潘仕成原书,乃后人所加。 传‘纯阳观’篆书三字或为阮元所书,应有一定的根据。 ”⑦广州市道教协会编:《广州道教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 年,第75 页注释3。
显然,上述说法与历史事实相谬甚远。 因为前文已述阮元所题之字是纯阳殿而非纯阳观,这是有文献资料支撑的。 一是《漱珠冈志》中提到“纯阳观前有道光六年阮元题‘纯阳殿’三大字,正殿内悬道光辛卯长白庆保书‘万世道统’横额即庆保木刻长联。 ”⑧冼玉清撰,陈永正补校:《漱珠冈志》第四篇余事·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5 页。二是《广州府道教碑刻集释》亦持这一观点。书中在解读纯阳观碑刻时称:“道光四年(1824),李明彻于漱珠冈创建纯阳观。阮元为了酬谢明彻修志辛劳,带头捐款,并发起州、府、县土绅长者捐款,资助李创建纯阳观,还亲自书写“纯阳殿”牌匾。 而在山门挂的“纯阳观”三字和左右对联,则是广州豪商潘士成亲笔赠送的。 ”①黎志添、李静编著:《广州府道教碑刻集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858 页。三是李明彻在《鼎建纯阳观碑记》明确写出道光六年纯阳观开山时只来得及盖好大殿和部分建筑,其余建筑是在阮元离粤后陆续建成。 “先建大殿,陞座关光。 各处随后建造。 ”“至六月,阮大人高迁云贵,列位大人各有陞迁,随后彻自一人办理。 ”也就是说,开山盛典时,只是观内主体建筑大殿与部分建筑竣工,纯阳观并未营建完毕。 因而,阮元题字“纯阳殿”,潘仕成题字“纯阳观”更符合史实。
凡此诸例,皆说明了尽管十三行捐款在纯阳观营建之作用有限,但行商仍是用其它方式诸如赠送珍贵礼物和题字的形式来展示出其对纯阳观的重视。
(主持人:冷东;责任编辑: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