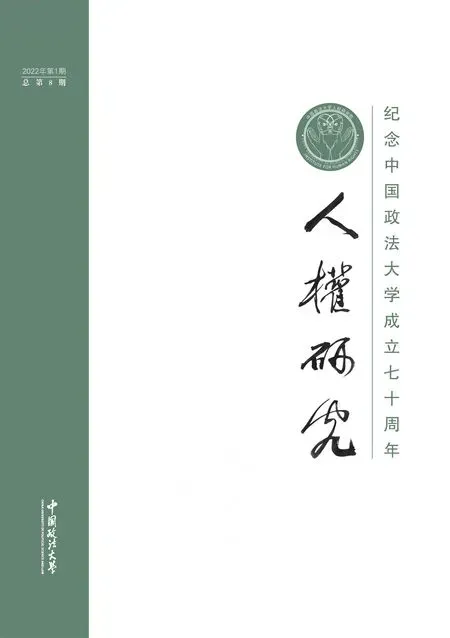何谓包容性教育?
——对残疾人受教育权的再思考
2022-03-30刘兰兰
刘兰兰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残疾人事业发展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残疾人教育是残疾人享有尊严和行使各项权利的重要途径,对推动残疾人参与、融入社会至关重要。2021年全国人大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建立完善特殊教育制度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远景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随后,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国发〔2021〕10号)明确提出“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保障残疾人在各个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
残疾人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发展和保障残疾人教育的根本目的,教育制度具有包容性是残疾人实现受教育权的关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规定“缔约国应当确保在各级教育实行包容性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制度……”,这是第一份提到“包容性教育”概念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包容性教育的理念发端于1990年在泰国宗甸举行的世界全民教育会议上所确立的“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目标1UNESCO, 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 Meeting Basic Learning Needs, 1990, http://www.undocuments.net/jomtien.htm#A.。这次会议使残疾学生被排斥在学校体系之外的问题受到重视,并倡导在全球推动均等和普遍教育机会。1994年在西班牙萨拉曼卡举行的特殊需要教育世界大会上,92国政府签署了《关于特殊需要教育的萨拉曼卡声明和行动纲要》(The Salamanca Statement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向全球发出实施“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2不同国际组织关于“inclusive education”的中文翻译不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文作准文本翻译为“包容性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中文官方文件中翻译为“全纳教育”。本文是基于对国际人权公约的规范分析,因此除了从教育学领域对我国包容性教育制度进行文献综述时使用“全纳教育”“随班就读”等概念以如实体现该制度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之外,本文其他场合采取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中文作准文本一致的表达。的呼吁,要求主流学校为包括残疾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提供优质教育,不因残疾人需要更多支助而加以歧视。3UNESCO, The Salamanca Statement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 1994, para.3, https://www.european-agency.org/sites/default/files/salamanca-statement-and-framework.pdf.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全纳教育”定义为,建立一个应对所有学习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的教育制度,减少教育系统对某些类型儿童的排斥,确保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学生在不受歧视和与他人平等的情况下享有受教育权。4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纳教育指导方针:确保全民接受教育》,2005年,第9—12页,http://www.ibe.unesco.org/fileadmin/user_upload/Curriculum/4_Guidelines_for_Inclusion-translation_CHN.pdf。2006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吸纳了包容性教育的理念,并通过第24条规范了包容性教育制度下的人权保护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包容性教育”与“全纳教育”对应相同的英文表达,但从制定机构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发布的关于“全纳教育”的文件是政治性倡导宣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国际人权公约对其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包容性教育”是国际人权法上的一个概念,具有特定的权利内容和人权保护标准。
我国是最早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应当履行公约规定的“实行包容性教育制度”的国家义务。但是,我国目前教育立法和教育政策尚未对“包容性教育”的概念和内容进行清晰的界定,关于残疾人受教育权的研究也鲜有对这一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的。包容性教育是怎样的一种教育制度?我国目前倡导的融合教育是否等同于《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所提出的“包容性教育制度”?包容性教育制度下残疾人受教育权的保护标准有哪些?保障残疾人接受包容性教育对发展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有何启示?这些问题不仅关涉残疾人受教育权的规范内涵,还关涉如何完善我国特殊教育法律制度和教育法治建设。本文尝试从价值基础和国际人权法规范的角度分析包容性教育的规范内涵和人权保护标准,并通过分析我国残疾人教育政策的变迁和面临的挑战,思考如何推动包容性教育在我国的完善和发展,从而充分实现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
二、包容性教育的核心内涵和价值基础
(一)包容性教育的核心内涵是保障包容性受教育权
1.接受包容性教育的权利是一项人权
包容性受教育权12016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包容性教育权的第4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4,2016年),认为“包容性教育……才能保证受教育权的普遍性和不歧视”。尽管该意见书的中文文本使用了“包容性教育权”的表述,但“right to education”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中文作准文本中都被翻译为“受教育权”;此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关于残疾人受教育权的专题研究》(A/HRC/25/29,2013年)中强调残疾人“受教育权是接受包容性教育的权利”。因此,本文为了保持与公约文本一致,使用“包容性受教育权”的措辞表示包容性教育制度下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是残疾人受教育权的具体表现。受教育权是一项受国际人权条约保护的具体人权,也是残疾人接受包容性教育的逻辑起点。把包容性受教育权视为一项人权是对残疾人享有受教育权的发展,其前提是对残疾模式的反思。人类过去主要从医学诊断或临床角度研究残疾,把残疾视为个人悲剧2参见[爱尔兰]杰拉德·奎因、李敬编著:《〈残疾人权利公约〉研究:海外视角(201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根据医学诊断把残疾认定为个人生理、心理的功能损伤(impairment),并把这种医学模式运用到为残障人士提供庇护、收容或安置等措施的法律和政策中,把“丧失能力即残废”的观念合法化3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6,2018年,第8段。。这种观念关注残疾的病理学根源、行为特点和矫正干预的方式,认为残疾是个人身体损害所带来的后果,提倡为残疾人专门开设特殊教育学校或机构对他们进行教育。1See Keith Ballard, Researching Disability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243, 244 (1997).这种医学模式下的“残疾印象”强烈地固化了将残疾人作为社会福利客体的刻板认知,2参见[爱尔兰]杰拉德·奎因、李敬编著:《〈残疾人权利公约〉研究:海外视角(201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没有考虑到残疾人享有社会权利的主体身份,没有认识到是社会环境对残疾人享有权利造成了各种障碍,导致残疾人长期被排斥或被孤立在教育系统之外。另一种关于残疾的认知是把残疾人置于社会环境中,认为残疾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残疾人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环境引起的,社会环境对残疾人设置的环境障碍才导致“残障”。3同上注,第11页。本文关于包容性受教育权的讨论即采取的是“残障”视角,但是为了保持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语言一致,所以沿用了现行法律中所使用的“残疾”一词。这种关于残疾认知的“社会模式”认为,导致残疾的各种社会环境障碍4See Kelley Loper, Equality and Inclusion in Education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ticle 24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Hong Kong, 40 Hong Kong Law Journal 419,425-426 (2010).,既包括物理上的障碍,例如没有提供无障碍设施,也包括观念上的障碍,例如把残疾视为限制接受教育或剥夺受教育机会的合理理由。
《残疾人权利公约》对“残疾”的定义代表了一种从医学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范式转变。《残疾人权利公约》在序言中指出,“残疾是一个演变中的概念,……是伤残者和阻碍他们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的各种态度和环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换言之,导致残疾的原因重点在于社会和环境障碍,而不是个体自身的缺陷。5参见[爱尔兰]杰拉德·奎因、李敬编著:《〈残疾人权利公约〉研究:海外视角(201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强调,“残疾是一种社会建构,不得将残障视为剥夺或限制人权的合法理由”,反对将残疾人单纯地视为福利接受者,强调残疾人是权利主体,是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各项基本人权的享有者,在制定关于残疾人教育的法律和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残疾人的多样性”。6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6,2018年,第9段。因此,从人权视角看,残疾人不仅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享有在包容性学习环境中与其他人平等获得教育的权利。
2.包容性受教育权是实现残疾人其他人权的手段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指出,受教育权是残疾人摆脱贫困、充分参与社区生活和免受剥削的主要途径。1参见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13号一般性意见:受教育的权利(〈公约〉第13条)》,E/C.12/1999/10,1999年,第1段。残疾人接受包容性教育的权利是其在经济社会中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大量研究数据显示,在劳动力市场上残疾人面临较多歧视性对待,阻碍残疾人就业或晋升的因素除了社会大众对残疾人的负面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成见,受教育程度低以及缺乏必要的职业培训机会也是一个重要障碍。2参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残疾人工作和就业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A/HRC/22/25,2013年,第8段。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低会影响残疾人的生产力,因此,残疾人在就业市场上的低就业率不是因为其自身的“残障”,而是因为教育和就业环境的“障碍”导致生产力低下。3Sebastian Buckup, The Price of Exclusi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xclud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from the World of Work,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9, p.51,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19305.pdf.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残疾人在包容性教育环境中接受教育,获得从事就业工作的各项技能,从而提高就业率,有利于减轻失业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良影响。因此,通过包容性教育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水平,不仅为残疾人实现独立生活和自主就业提供基本生存技能,而且也会促使残疾人融入社会从而实现个体经济价值。
此外,包容性教育旨在促进相互尊重和对所有学习者的重视,并在教育过程、教学课程和学校文化中努力维护包容和尊重多元的价值观。4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包容性教育权的第4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4,2016年,第10、15段。它为打击隔离和歧视提供了一个可靠平台,在不同学习者所具有的包容能力各异的情况下,残疾人的贡献可以得到重视,这有利于逐步消除对残疾人的偏见和阻碍残疾人行使其他基本权利的障碍,建立一个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包容社会。
(二)包容性教育的价值基础是包容性平等
传统的反歧视理论把平等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前者关注机会平等,法律上禁止区别对待;5参见刘小楠主编:《反歧视法讲义:文本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后者关注结果平等,承认并尊重个人尊严,禁止不合理的区别对待。6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0页。根据牛津大学教授桑德拉·弗里德曼(Sandra Fredman)提出的平等理论,实质平等是一个包含再分配维度、承认维度、参与维度和变革维度的多维度概念,不能只局限于机会平等、结果平等或者尊重个人尊严其中之一,因为它们都有无法克服的弊端,单凭三者之一都无法达到实质平等的目标。1参见[南非]桑德拉·弗里德曼:《反歧视法》(第二版),杨雅云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23—25页。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肯定这种多维度的平等观是“包容性平等”,并指出这是《残疾人权利公约》在实质平等模式上发展出来的新平等模式。2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6,2018年,第11段。包容性教育所包含的公平、非歧视、参与、尊重多元等核心价值都源于这四个维度上所追求的平等目标。
1.公平的再分配维度(fair redistributive dimension)
再分配维度要求解决资源和利益再分配对残疾人的不利条件。3同上注。实质平等观下,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应当侧重于救济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的界定不能局限在物质资源分配的不公,应当考量“权力关系”对具有某种身份的个体施加的限制和约束。4同上注,第10段。如果把我国特殊教育政策视为社会公共物品,特殊教育政策的决策和执行就是对教育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以政府公共意志来支配的。5参见王培峰:《教育政策价值选择与教育公平——以特殊教育政策为例的分析》,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80页。而残疾人是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往往在公共决策中话语权不足、社会参与程度不深,长期以来作为受助者被动地接受公共政策为其分配教育资源,形成了政策决策中的“弱权阶层”。从这个角度看,不仅仅残疾人是弱势群体,残疾儿童的家长以及特殊教育教师都可能在资源再分配过程中被边缘化,受到不公正待遇。对随班就读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普通学校还没有建立配套的特殊教育资源支持体系,随班就读的教育质量不高,融合往往流于形式,随班就读仅仅解决的是残疾人“有学上”的问题,6参见李拉:《我国随班就读政策演进30年:历程、困境与对策》,载《中国特殊教育》2015年第10期,第16页。仍然没有化解“上好学”的困境。而造成特殊教育专业化程度不高、资源支持体系不完善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残疾人和特殊教育教师代表人数稀少,在教育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公共话语权。
2.认识维度(recognition dimension)
认识维度要求尊重个人价值,打击偏见、刻板印象和暴力。7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6,2018年,第11段。这个维度尊重人的尊严,旨在促进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都能获得平等的尊重,不应因为残疾特征而被侮辱和贬低。将尊严视为平等观维度之一,意味着残疾人是独立的权利主体,法律和政策要承认残疾人在受教育上的机会平等,不得基于残疾限制或剥夺残疾人受教育机会。例如,基于医学模式的特殊教育立法依据残疾种类和残疾程度的医学鉴定对残疾儿童采取隔离教育的方式,这种基于残疾的区别对待限制了残疾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3.参与维度(participative dimension)
参与维度强调尊重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社会性,促进社会中所有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全面参与。1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6,2018年,第11段。这个维度是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关注残疾人如何与社会实现和谐统一。社会融合理论认为,如果人人都能充分参与社会活动,则他们不大可能与群体相疏远,他们也会遵守社会规则和法律,这正是实质平等观的核心和目的。2Hugh Collins, Discrimination,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66 The modern Law Review 16, 24 (2003).以社会融合为目标的教育理念必然关注残疾人参与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全纳教育是以权利为基础的教育,这是一个“通过增加学习、文化和社区参与,减少教育内外的排斥从而处理和回应所有学习者多样化需求的过程”3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纳教育指导方针:确保全民接受教育》,2005年,第9页,http://www.ibe.unesco.org/fileadmin/user_upload/Curriculum/4_Guidelines_for_Inclusion-translation_CHN.pdf。。
4.调节维度(accommodating dimension)
调节维度强调人的尊严和包容差异,为差异留出空间。4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6,2018年,第11段。与形式平等不同,实质平等观认识到残疾是个体身份的组成部分,歧视问题并不在于个体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而在于个体因为残疾的特征差异而遭受的损害。因此,这个维度旨在尊重和包容差异,并要求社会建构不是消除差异本身,而是消除由差异所导致的损害。例如,西方早期特殊教育中的“一体化”和“回归主流”运动曾经实施过把残疾儿童纳入主流学校的教育安置模式,这种模式仅仅按照主流学校的标准接纳特殊儿童,没有对主流学校进行改造并对特殊儿童提供充分的个性化资源支助,5参见黄志成、胡毅超:《全纳教育:未来之路——对UNESCO第48届(2008年)国际教育大会主题的思考》,载《全球教育展望》2008年第7期,第48页。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形式上的融合,实质上的隔离,1参见邓猛:《双流向多层次教育安置模式、全纳教育以及我国特殊教育发展格局的探讨》,载《中国特殊教育》2004年第6期,第3—4页。因此,这种模式并不是一个包容差异的教育活动。此外,调节维度与认识维度并不矛盾:一方面,从人的尊严角度看,残疾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这是基于残疾人与普通人接受教育的共性,因此要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另一方面,从教育质量的角度看,优质教育必须满足残疾人的特殊教育需求,这是基于残疾人接受教育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我国特殊教育学开创者朴永馨教授指出:认识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的共性,不是否认特殊儿童的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忽视残疾人的特殊性或不尊重残疾人的差异,不会使残疾人真正回归和被包容在社会之中。2参见朴永馨:《融合与随班就读》,载《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年第4期,第39页。因此,这个维度的实质平等要求主流教育制度要做实质性变革,改革普通学校设置、资源配置和课程设计等制度安排,以灵活和包容的手段而非消除和排斥的手段来满足残疾人的特殊教育需求。
三、包容性教育的国际人权标准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4条是目前唯一详细规定“包容性教育”的条文,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人权保护框架。该条款也是公约“包容性”精神在受教育权上的具体贯彻,包含了包容性教育的基本要素和人权保护标准。
(一)教育目标(第24条第1款)
这一条款的设置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教育宗旨”条款(第13条第1款)和《儿童权利公约》的“教育目标”条款(第29条第1款)作用一样,都是为“受教育权增加了一个实质层面”3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第1号一般性意见——第29条第1款:教育目标》,CRC/GC/2001/1,2001年,第2段。,反映了受教育权不仅是一个教育机会问题,还涉及教学内容。
这一条款明确提出包容性教育的目标有三项。第一项是“充分开发人的潜力”。包容性教育必须力求促进相互尊重和对所有人的重视,并在教学方针、学校文化和课程教学中均体现多样性价值。第二项是充分发展残疾人的个性和个体素质。这意味着,教育项目的规划应该多样化,充分发挥残疾人的个性、才能和创造力,以及促进他们的身心发展和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不能侧重残障特征,预设残疾人在学习和创造能力上不如普通人,为残疾人设置类型和内容单一的技能型课程,这种否定残疾人能力潜质的观念会限制他们的机会。第三项是参与社会。教育目标条款强调了包容性教育制度不是一个抽象和孤立的教育模式,教育必须力求让残疾人充分、有效地参与到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为促进实现以上教育目标,国家有必要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引入人权模式,在普通学校教育中积极开展人权教育和反歧视宣传,纠正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
(二)非歧视(第24条第2款)
这一条款下包含五项关于禁止歧视和排斥残疾学生的内容,要求国家既要履行尊重义务,避免制定针对残疾人的歧视性特殊教育法律和政策,又要履行保护和实现义务,以提供合理便利和个性化措施来促进残疾人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
第一项是反歧视,规定任何学生不得因残疾而被排斥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这一条款为缔约国设置了“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义务。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条,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目的和效果损害残疾人对基本权利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基于此条文,隔离式特殊学校显然损害了某些类型的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在2017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受理的第一起1鲁本案目前也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针对《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4条包容性受教育权作出决定的唯一案件。关于包容性受教育权的申诉中,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鲁本(Rubén)被西班牙政府强制送往特殊教育中心学习,鲁本的父母因拒绝将其送入特殊学校而受到西班牙政府的刑事指控。在该案中,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认为“不受歧视的权利包括有权不被隔离和获得合理便利”,这项权利“必须结合提供无障碍学习环境和合理便利的义务加以理解”。2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通过的关于第41/2017号来文的意见》,CRPD/C/23/D/41/2017,2020年,第8.4段。同时,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重申基于非歧视和机会均等的包容体制,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消除针对残疾学生的隔离式教育体制。3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西班牙第二次和第三次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RPD/C/ESP/CO/2-3,2019年,第 45段。而西班牙对特殊教育的监管依然是基于残疾的医学模式,大量残疾儿童接受的仍然是主流教育体系之外的特殊教育。因此,西班牙政府的做法被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认定为未履行公约要求的禁止歧视的义务。
第二项要求优质免费的包容性教育资源对残疾人必须是可及的。“可及性”在《残疾人权利公约》第9条体现为,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残疾人行使各项权利的无障碍环境。阻碍残疾人受教育的障碍既包括物质障碍,也包括交流障碍,消除这些障碍是实现包容性教育的前提。1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2号一般性意见——第九条:无障碍》,CRPD/C/GC/2,2014年,第39段。确保无障碍的义务通常侧重于修改学校建筑物设施,提供无障碍的交通和沟通工具,以及提供通用设计。需要注意的是,无障碍的努力不应仅局限于改造物理障碍,还应包括改造侵犯人的尊严的社会环境,因为隐藏在后者中的欺凌、恐吓以及暴力等敌意行为构成对残疾人的骚扰,不利于残疾人在包容性环境下享有受教育权。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明确指出骚扰是歧视行为,应予以禁止。2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6,2018年,第18段。也有国家已经把骚扰纳入反歧视立法中,例如挪威的《关于初等和中等教育及培训的法案》(Act Relating 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确认所有学生都享有在设施完备和具有良好社会环境的学校中学习的权利,残疾学生有权获得往返家校之间的交通和便利,学校负有义务对欺凌、暴力、歧视和骚扰等行为进行干涉以确保一个良好的校园心理环境。3See Norway, Act Relating 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999), Section 7-3 & Section 9A-4,https://lovdata.no/dokument/NLE/lov/1998-07-17-61.此外,无障碍义务还体现在克服经济障碍,国家要对残疾人提供免费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以经济援助或奖励等方式确保人人可以负担教育费用。确保无障碍也要求国家履行尊重义务,通过立法或政策确认残疾人无障碍地享有教育的权利。例如,芬兰在《基础教育法案》(Basic Education Act)中规定残疾学生为了平等参与教育活动,有权获得免费的翻译和援助服务。4See Finland, Basic Education Act (Amendments up to 1136/2010), Section 31, https://finlex.fi/en/laki/kaannokset/1998/en19980628.pdf.
第三项规定国家为实施包容性教育负有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认为提供合理便利是一项需要缔约国即刻实施的义务,5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三十五条提交的报告: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草案(西班牙)》,CRPD/C/ESP/CO/1,2011年,第44段。要求国家在立法或政策中作出提供合理便利的承诺,尊重残疾人个体的尊严和自主选择在合适的学校就读的权利。在鲁本案中,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认为西班牙政府在考虑鲁本父母选择主流学校的意愿时,没有探索为鲁本在主流学校学习提供合理便利的可能性,而是强制当事人接受隔离式特殊教育,因此侵犯了当事人的包容性受教育权。此外,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也是无障碍义务的补充。无障碍是与残疾人整个群体有关的标准化通用设计,但是没有考虑残疾个体在特定情况下的需求。而提供合理便利具有个性化特点,针对个人具体需求来设计和提供设施或资源,1参见曲相霏:《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合理便利——考量基准与保障手段》,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2期,第12页。以便在无障碍措施无法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时,可以通过提供合理便利使他们与其他人平等地享有教育权利。例如,学校建筑物的无障碍通道对于视障和听障人士而言并不能使他们便利地享有受教育权,而为他们提供盲文和手语翻译的便利才能满足他们特定的需求。
第四项和第五项规定了国家提供必要支助以及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有效支助措施。支助可以采用通用设计,也可以采用个性化方案,但都必须考虑个人的需要。与之相对应,包容性教育制度一方面可以采取通用设计方案,即在教育系统内普遍提供残疾学生所需的资源支助,包括配备经过专业培训的教学人员以及提供通用课程,确保残疾学生在教育环境中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潜力。例如,加拿大的包容性教育政策要求学校面向所有学生建立一个共同学习环境,并禁止在学校或社区中针对有学习或行为障碍的学生实行隔离性单独方案或分班。2See Canada, Policy 322 on Inclusive Education (2013), 6.1 & 6.2.2, https://www2.gnb.ca/content/dam/gnb/Departments/ed/pdf/K12/policies-politiques/e/322A.pdf.因此,许多家长把有中度以下视障、听障和智障的孩子“送到普通学校读书,这些学校再聘请有特殊教育方面经验的教师作为这些学生的辅导教师,共同参与教学,……这些学生所用的教材完全和普通儿童一样”3谢明:《融合和全纳教育是特殊教育的主题——加拿大、美国特殊教育考察报告》,载《环球特教》2003年第6期,第46页。,与普通学生共同学习。此外,特殊学校的学生在学习公共课(如音乐、体育、美术等)时可以到普通学校学习,以便让残疾学生和普通学生相互了解和学习。包容性教育制度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个性化方案,明确每个残疾学生所需要的合理便利和特定支助,包括支助工具、特殊的学习辅助设备、辅助技术和信息技术。支助措施还包括有专业的教师支助,根据学生需要,为残疾学生和家长提供学习指导和教育服务。这些资源支持措施需要进一步普及到普通教育系统,由此构建一个包容残疾学生和普通学生的共同学习环境。
(三)获得合理便利(第24条第3款)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条界定了“合理便利”的定义,并把“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分解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规定了提供合理便利是为确保残疾人平等享有或行使权利而进行的一种必要和适当的修改或调整。提供合理便利是国家承担的一般性义务,适用于《残疾人权利公约》所保障的各项基本人权,它旨在消除基于残疾的一切歧视。1See Rosemary Kayess & Philip French, Out of Darkness into Light? Introducing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8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1, 26 (2008).因此,结合《残疾人权利公约》第5条规定的“为促进平等和消除歧视,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步骤,确保提供合理便利”,拒绝提供合理便利即构成歧视。这项不得拒绝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被有的国家视为一种反歧视义务,要求以作为的方式实现实质平等保护。例如,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在埃尔德里奇(Eldridge)案中认为,有效沟通对于听障人士获得准确和有效的治疗至关重要,因此政府提供手语翻译的便利不仅面向残疾人,也面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和其他需要手语翻译的人。法院认为如果政府没有提供这样的便利就违反了宪法的平等权条款,即不履行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即构成基于残疾的歧视。2See Eldridge v.British Columbia (Attorney General), 1997 CanLII 327 (SCC), [1997] 3 S.C.R.624.
提供合理便利义务的第二个部分是关于这项义务的界限,即提供合理便利以不造成过度或不当的负担为限。但“过度或不当负担”不应当理解为不承担任何负担,而应当理解为不给提供便利方造成过分或不合理负担。3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6,2018年,第25段。在教育领域中,国家是保障受教育权的主要义务主体。提供合理便利义务要求国家“尽可能迅速和有效地争取目标”4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3号一般性意见:缔约国义务的性质(〈公约〉第二条第一款)》,E/1991/23,1990年,第9段。,使残疾人能便利地享有接受包容性教育的权利。尽管提供合理便利有时依赖可利用的教育资源支持,但是,国家不能以成本或资源有限为借口,把这项义务虚化为“逐步”或“有条件”地落实。例如,我国2017年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关于为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提供个别教学和设立专门辅导教室的条款,多次使用“有条件”的限定,使得为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上学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可能沦为一种“因地制宜”的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4条第3款与第2款第3项都是关于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但二者有两点区别。第一,前者规定的是一项特定义务,要求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为残疾人提供手语、盲文等交流方式的合理便利。而后者规定的是教育领域提供合理便利的非歧视义务,要求国家“确保提供合理便利以满足个人的需要”,意味着国家既负有积极提供合理便利的实现义务,又负有要求和督促第三方禁止拒绝提供合理便利的保护义务。第二,前者要求提供的合理便利是基于残疾人参与社会的沟通需求,是与残疾人群整体相关的共同需求。而后者规定的合理便利是基于个人的需求,具有很强的个体性。
(四)职业培训和能力建设(第24条第4款)
这一条款强调需要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以有效协助残疾学生的学习,并使之成为优质教育的一种积极资源。培训具有包容性理念的教师队伍以及学校工作人员是持续发展包容性教育的关键。正如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所指出的,“缺乏认识和能力不足仍然是包容性的重大障碍……必须确保所有教师都接受包容性教育方面的培训”1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包容性教育权的第4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4,2016年,第36段。,并引入人权模式对普通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
重视师资建设还需对残疾教师的聘用和进修提供支持,包括消除相关立法或政策障碍,放宽残疾应聘者在教师资格考试和申请教职时的健康标准,并为他们从事教师工作提供合理便利。残疾教师的存在给教学环境带来特有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有助于改变对残疾人职业发展的偏见和发挥榜样作用。
(五)终身学习(第24条第5款)
本款要求确保残疾人“在不受歧视和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普通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和终生学习”的机会。这一条款旨在强调包容性学习环境贯穿整个教育阶段、渗透教育系统的各个环节。为此,国家应当全面检视教育各阶段在理念、文化、语言、交流、投入和法律等方面存在的障碍,采取措施和提供合理便利,消除这些障碍。为便利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我国教育部2015年首次明确要求为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2017年再次对为参加高考的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作出专门规定,例如,为视障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等。2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中国根据〈公约〉第三十五条提交的第二和第三次合并定期报告》,CRPD/C/CHN/2-3,2019年,第88段。2017年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第52条将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国家教育考试”,不仅限于高考环节。但是《残疾人教育条例》关于提供合理便利的规定仅限于学校考试环节,3参见曲相霏:《〈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合理便利”理念在我国教育领域的运用》,载《人权》2017年第3期,第61页。有待立法推动合理便利在教育全过程中的普及。
四、包容性教育对我国残疾人受教育权保障的挑战和启示
(一)我国残疾人教育政策的变迁发展:从隔离到融合
现代权利观确立了受教育权是一项普遍人权之后,各国采用的不同残疾人教育模式都是在回应残疾人的特殊教育需求。随着对残疾模式认知的不断发展,特殊教育理念也在发生变化,我国残疾人教育也经历了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从隔离发展到融合发展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10月颁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将发展特殊教育学校作为特殊教育的唯一法定方式,且特殊教育主要面向盲、聋、哑三类残疾人。这种政策导向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明确了受教育权是公民一项基本权利(第46条)和国家有责任帮助安排残疾人的教育(第45条),此后,特殊教育政策开始从游离于国家教育体制的边缘状态回归国家教育政策中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发〔1985〕12号)明确提出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发展盲、聋、哑、残人和弱智儿童的特殊教育”,为特殊教育进入实质性发展轨道提供了纲领性指导。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办发〔1989〕21号),提出把随班就读作为特殊教育的一种方式。1994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将随班就读作为发展和普及特殊义务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这意味着我国残疾儿童主要依托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特殊教育机构两种方式接受义务教育。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发〔2010〕12号)对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并单独设立“特殊教育”专章,提出“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完善特殊教育体系”“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等顶层制度设计理念与思路。在该纲要的推动下,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发布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提出促进和全面推进融合教育。2017年,国务院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首次提出残疾人教育应当“积极推进融合教育”,将融合教育纳入教育法治的轨道。
从我国残疾人教育政策的变迁来看,特殊教育、随班就读和融合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不是割裂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并形成了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相结合的双轨制。1参见邓猛、苏慧:《融合教育在中国的嫁接与再生成: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分析》,载《教育学报》2012年第1期,第84—85页。有的学者认为随班就读模式是融合教育与我国特殊教育的结合,是融合教育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2参见邓猛、朱志勇:《随班就读与融合教育——中西方特殊教育模式的比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25页。是我国融合教育的主要发展方向。3参见周满生:《关于“融合教育”的几点思考》,载《教育研究》2014 年第2 期,第151—153 页。但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纳教育”理念在全球的推广,我国教育界也出现将融合教育等同于全纳教育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融合教育与全纳教育是同义词,区别仅仅是翻译不同,全纳教育或融合教育是发展特殊教育的新模式,“全纳教育使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朝着融合的方向前进”4参见邓猛:《从隔离到全纳——对美国特殊教育发展模式变革的思考》,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年第4期,第43—44页。,而且多数时候特殊教育实践中对全纳教育以及融合教育等相关概念不加区分使用。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全纳教育是随班就读的进一步发展,5参见陈云英:《在中国发展全纳性教育》,载《中国特殊教育》1997年第2期,第2—5页。它是融合理念与我国特殊教育实践的结合,是我国国情所需。6参见赵小红:《近25年中国残疾儿童教育安置形式变迁——兼论随班就读政策的发展》,载《中国特殊教育》2013年第3期,第23—29页。
但是,这种混淆融合教育与全纳教育的观点也遭到部分学者的批判。从两者面向的受教育主体来看,2017年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第58条规定:“融合教育是指将对残疾学生的教育最大程度地融入普通教育。”欧洲和美国的特殊教育在早期也采取过将残疾儿童纳入普通学校接受特殊教育的形式,并使用“integration”一词代表这种融合模式。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把“包容体制”(inclusion)作为教育改革和机构重建的一项工作,面向所有学生,包括为有重大残疾的学生提供有效教育服务。7参见朴永馨:《融合与随班就读》,载《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年第4期,第37—38页。因此,融合教育主要面向有学习需求的残疾人,而全纳教育面向的是所有学生。8参见黄志成:《试论全纳教育的价值取向》,载《外国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7页。此外,两者在研究范围上也有明显区别:融合教育概念来源于特殊教育领域,是特殊教育领域的核心词汇;全纳教育的概念指向整个教育领域,远远超出了特殊教育的范畴。9参见李拉:《“全纳教育”与“融合教育”关系辨析》,载《上海教育科研》2011年第5期,第16页。
本文认为,从发生学角度看,融合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全纳教育。虽然两者都旨在倡导建设残疾人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的教育制度,但两者采用的融合模式和实践路径具有明显差别。包容性教育与全纳教育具有相同的宗旨和目标,是全纳教育理念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具有清晰的权利内涵和明确的义务标准。而我国融合教育政策具有同包容性教育相同的目标追求。中国向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递交的第二次履约报告中特别说明,“根据《公约》倡导的包容性教育理念,中国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2017),该条例明确提出‘积极推进融合教育’”1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中国根据〈公约〉第三十五条提交的第二和第三次合并定期报告》,CRPD/C/CHN/2-3,2019年,第84段。。由此可见,我国融合教育的推广是以包容性理念推动中国特殊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但是目前无论是关于特殊教育政策研究,还是关于残疾人受教育权研究,都没有对包容性教育展开详细阐述。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包容性教育是一个法律概念,包含残疾人教育的权利义务规范内容,对其规范性分析超出了教育研究范围;第二,包容性教育被等同于融合教育,被包含在融合教育研究中,没有通过人权法研究凸显其独立的研究价值。
(二)包容性教育对我国残疾人受教育权立法保护的挑战
我国关于残疾人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主要体现在特殊教育立法上,在《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中都有涉及特殊教育和残疾学生入学的规定。国务院制定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是关于残疾人受教育权的专门行政法规。此外,涉及残疾人受教育权的还包括关于特殊教育和随班就读的地方性法规。

表1 我国现行关于残疾人受教育权的立法保护

文件名称 残疾人教育条款1996年《职业教育法》 第7、15、32条法律2008年《残疾人保障法》(2018年修正) 第21—29条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83、86条2017年《残疾人教育条例》行政法规2012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第12条地方性法规(略)
从我国残疾人受教育权的立法保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没有关于残疾人教育的单行法律,特殊教育立法层次较低,残疾人教育法律体系还不完备。2008年《残疾人保障法》第三章用9条规定了对残疾人教育方面的保障,但是仅有2条1《残疾人保障法》第25、26条。对残疾人在普通学校上学作出了规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也没有专章规定“特殊教育”。我国针对残疾人教育的专门立法只有《残疾人教育条例》,但是它仅是一部行政法规。虽然国务院、教育部也发布了许多关于特殊教育发展的政策,但只是以“办法”“通知”“意见”等形式公布,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作为《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有义务将《残疾人权利公约》要求的包容理念纳入国内立法和政策规划中。《残疾人教育条例》虽然原则性地规定了“推进融合教育”,但这一理念尚未在《残疾人保障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基本法律中得到体现。为此,我国在完善残疾人受教育权保障方面面临以下挑战。
1.教育立法中关于残疾人受教育权的保护不够全面
根据我国《宪法》第46条和第45条的规定,受教育权的权利主体是一般主体,残疾人不应因为残疾特征而丧失接受教育的权利。但是,我国现有的教育法律和《残疾人教育条例》仍然把残疾类型作为筛选残疾人随班就读的条件之一。根据2006年《义务教育法》第19条的规定,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一种是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根据《义务教育法》规定,特殊教育学校面向的残疾儿童仅为视障、听障和智障三种残疾类型,而2008年《残疾人保障法》第2条规定残疾的类型包括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多重和其他残疾等八个残疾种类。从理论和现实角度看,特殊教育的对象不宜只限定为三类,而将其他类型的适龄残疾人排除在外,这与包容性教育原则相违背,也不符合当代残疾人教育具体化、个别化、特殊化的发展趋势。尽管《义务教育法》规定了随班就读制度,而且《残疾人教育条例》也规定残疾人教育“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但是相关立法都要求残疾人“具有接受普通教育的能力”,这意味着残疾人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评估标准是基于残疾人受教育的能力,这势必会把那些既没有能力接受普通教育又不符合进入特殊教育学校的残疾人排除在学校教育体系以外。因此,这种根据残疾类别、残疾程度等条件判断残疾儿童是否适合在学校上学的规定,显然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包容性精神不符,也没有充分体现我国《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2.包容性教育制度的保障机制不足
《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包容性理念要求教育要面向所有残疾人,保障残疾人能无障碍地获得教育资源和设施,为此,国家负有为残疾人受教育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而我国教育立法中关于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和提供合理便利义务的规范比较笼统,缺乏具体内容。2017年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在第50条规定了政府应当推进“无障碍校园环境建设”,但是缺乏具体的配套规划和政策,导致这项义务容易流于形式。该条例第52条规定了政府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但这项义务仅限于残疾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而在现实生活中,残疾人就近上学所需的交通服务(如校车接送)、随班就读中的信息沟通(如手语、盲文交流)或残疾学生在校生活(如住宿问题)等问题都有赖于政府或有关部门提供相应的合理便利才能解决,从而帮助残疾人更好地实现受教育权。此外,《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中也缺乏关于为残疾人受教育提供合理便利和无障碍服务的明确规定。
3.实施随班就读的法律条款较为原则,缺乏配套保障机制
虽然《义务教育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将随班就读作为融合教育的主要实施方式,但是法律法规尚未规定实施随班就读所需的资源支持。202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2020〕4号)提出,加强随班就读的资源支持,根据残疾学生的需要配备必要的资源教师和专业人员,合理调整课程教学内容,科学转化教学方式。除此之外,随班就读的资源支持还应包括提供考试所需要的合理便利、普通学校里特殊教育资源教室的标准化建设、送教上门或远程教育的技术支持等,这些都应当上升为政府的法律义务。而资源支持的具体方式、内容和途径需要依靠教育部门出台具体的配套政策来确认,以在义务教育阶段真正落实随班就读。
(三)包容性教育制度对我国残疾人受教育权保障的启示
中国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关于残疾人权利保护的规定。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强调包容性概念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主要理念之一,应该在教育领域特别坚守。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针对中国提交的首次国家履约报告,明确建议中国“将特殊教育体系中的资源转用于促进主流学校中的包容性教育”1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会第八届会议(2012年9月17日至28日)就中国初次报告通过的结论性意见》,CRPD/C/CHN/CO/1,2012年,第36段。,这对于完善我国融合教育和包容性教育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包容性教育制度的建立需要对普通学校制度作出系统性改革,以克服教育系统里直接或间接地把残疾学生和普通学生隔离开的制度障碍。在对待残疾人的学校制度安排上,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特别强调,“必须认识到排斥、隔离、融合和包容之间的区别”2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包容性教育权的第4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4,2016年,第11段。。排斥(exclusion)是指学校的入学规定和标准以年龄、发育情况或者诊断为依据,直接或间接地阻止或拒绝残疾学生进入教育系统,将残疾学生置于社会福利或看护环境中,导致残疾学生丧失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隔离(segregation)是指将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分开,将残疾学生送往专门为某种残疾类型设计的学校,这种环境的设计或应用是为了应对特定的残疾或多种残疾,通常属于特殊教育学校系统。融合(integration)是将残疾人安置到现有主流教育机构中,但前提是他们能够适应主流学校的标准化要求,因此侧重于加强残疾学生遵守既定教育标准的能力。尽管融合教育体现了接纳残疾人回归主流的理念,但是这种“接纳”仍然是基于医学模式对残疾人进行学习能力的划分,为残疾儿童设置了一个“主流”标准,要求残疾儿童依靠自身努力,达到这样的标准,才可以在主流学校中接受教育。3参见邓猛、潘剑芳:《关于全纳教育思想的几点理论回顾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载《中国特殊教育》2003年第4期,第3页。
普通学校需增强资源支持建设,调整教育系统中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结构和发展战略,从而消除普通教育系统中存在的制度性障碍。残疾人受教育的本质不在于在哪个教室里上学,而在于这种教育是否能促进社会融合、消除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以及是否能帮助残疾人获得参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知识和技能。仅仅将残疾学生安置在主流课堂而不辅以适当和充足的教学支助,谈不上包容。如果没有改变教育系统中针对残疾人的制度性障碍,那么即使残疾人进入主流学校也会面临来自普通师生或家长的排斥、歧视和孤立,1参见王卡拉、萧辉:《自闭症孩子多数经历过被劝退 专家建议建陪读制》,载搜狐新闻网2012年10月22日,http://news.sohu.com/20121022/n355369363.shtml。这种学校环境并没有让残疾人真正融合到主流教育中。
其次,把包容性教育制度建设融入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整体规划中,才能推动特殊教育政策的法治化,提高残疾人教育立法的质量。自从《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以来,融合教育已经从我国特殊教育政策语言演化为教育法治目标之一,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还面临推进融合教育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相衔接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融合教育的制度设计要吸纳《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包容性”立法精神。包容性教育的宗旨和目标面向所有人,教育目标并非专门针对残疾。包容性教育实行的是“整个人”方针2参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包容性教育权的第4号一般性意见》,CRPD/C/GC/4,2016年,第12段。,承认人人具有学习能力,对所有学生包括残疾学生都抱有较高期望。这一方针意味着提供支助、合理便利和早期干预,在教育系统中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对策,使所有学生都能发挥潜力,而不是指望学生适应系统。尽管有的特殊教育学者倾向于从残疾儿童身心差异性和政策有效性出发,提出“适当融合”或“部分融合”的策略更能照顾到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需求,3参见彭兴蓬、雷江华:《论融合教育的困境——基于四维视角的分析》,载《教育学报》2013年第6期,第60页。然而,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残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包括选择进入主流学校或是进入特殊学校的自由。换句话说,残疾人不是因为其有能力适应主流学校从而有机会与普通学生一起学习,而是因为残疾人是受教育权的享有者从而享有进入主流学校学习的权利。而且,即使主流学校面向所有残疾人开放,也不意味着必然取消特殊教育学校,4参见彭霞光:《全纳教育:未来之路——对全纳教育理念的思考与解读》,载《中国特殊教育》2008年第12期,第4页。残疾人仍然有选择在特殊学校上学的自由,这样的教育体制才是包容的教育体制。
五、包容性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完善和发展
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4条规定的人权保护标准和国家义务,推动包容性教育制度在我国的落实,应当转变基于医学模式的立法模式,明确残疾人平等保护的反歧视义务,采取“赋能”措施推动包容性教育环境建设。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包容性教育制度。
第一,教育立法应立足于人权模式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的实现。我国现有法律关于残疾人的界定仍然是基于医学模式,关于残疾人接受教育的立法强调残疾人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残疾特点获得教育资源,而不是立足教育制度的系统改革从而消除阻碍残疾人享有教育资源的障碍。残疾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应当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要求在完善教育立法时不应以残疾种类和残疾程度为划分标准为残疾人接受教育设定条件,否则就是基于“残疾”将残疾人与其他人区别对待。尽管这种区别对待可以针对特定的残疾人提供个性化的教育,例如手语教育、盲文教育等,但是这种立法的区别对待恰恰将残疾人教育与主流教育区别开来,固化了社会大众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不利于残疾人随班就读和融入主流社会。
第二,立法保护残疾人受教育权的核心是保障平等受教育权。平等保护是受教育权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具体界定“歧视”的概念。《残疾人保障法》第3条规定“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并把“侮辱、侵害残疾人”“贬低损害残疾人人格”并列为禁止内容,这些禁止性行为都可视为对残疾人的歧视。该法也设定了一系列国家义务来实现残疾人的平等保护,包括设立专章规定政府建设“无障碍环境”的义务,但是尚未按照《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要求把“提供合理便利”作为一项反歧视的义务。因此,教育立法对残疾人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需要明确义务主体的反歧视义务,细化校园无障碍建设的标准,扩大教育领域提供合理便利的适用范围。
第三,教育政策不仅要重视提高残疾人的福利政策,还要倡导建立包容性教育环境。已实施的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采取了多项政策解决残疾人在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的问题,包括落实义务教育“一人一案”的教育安置、为残疾学生减免学费、提高残疾学生资助水平、加强特殊教育资源支持服务等措施。这些措施无疑对推动教育公平、提高特殊教育质量至关重要。202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班级中“积极倡导尊重生命、包容接纳、平等友爱、互帮互助”的价值观。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也提出,在“健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的同时,“开展残疾人融合教育示范区”,支持高等院校开展残疾人融合教育。融合教育校园应当以倡导多样性校园文化的包容性教育环境为目标,不是把残疾人仅仅当作被帮扶、被救助的对象,而是把他们视为平等的社会成员,尊重他们作为权利主体的独立性,尊重他们的潜能发挥;包容性教育环境也要求营造残疾人融入和参与主流教育制度的校园环境,帮助社会大众消除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例如,2017年清华大学录取了一名成绩优异的甘肃残疾考生魏祥,他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需要母亲长期贴身照顾生活,因此请求清华大学帮助解决母子俩的住宿问题。清华大学不仅积极公开回应他的请求,而且为母子二人安排了单间宿舍,保障了魏祥在校园里潜心修学,并顺利完成学业。1参见雷嘉:《“人生实苦,但足够相信”的清华学生魏祥本科毕业了!将回家乡直博》,载北青网2021年6月27日,https://t.ynet.cn/baijia/31028021.html。这个事例一方面反映了残疾人具有同普通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残疾人上学面临的校园环境制度建设亟需完善的问题。《残疾人教育条例》第22条规定,学校有义务“为残疾学生入学后的学习、生活提供便利和条件”,这意味着提供合理便利应当是学校制度建设的组成部分,以保障残疾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能如常进行,而不应把这种保障义务当作一种“特事特办”。未来的教育政策在倡导各级各类学校加强建设包容性学习环境的同时,要不断探索包容性校园建设的具体指标和措施,把融合教育举措和包容性指标建设纳入依法治校的规划和建设中。
六、结语
尊重和保障残疾人各项人权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8年全国人大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两期残疾人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并实施完成了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不断完善残疾人人权保障机制,不断建立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制。2021年9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强调“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并将“推动融合教育发展”“禁止任何基于残疾的教育歧视”“确保提供合理便利”等措施作为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和社会融合的目标。在新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周期,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发展应以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为核心,以建设包容性教育制度为目标,完善我国融合教育法律和政策,不断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水平,保障残疾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