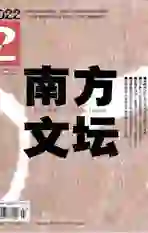杨绛小说里的同行温德和杨业治
2022-03-30于慈江
一、缘 起
古今中外的小说家不知凡几,大有成就者也比比皆是,但若论对写小说这桩事的痴迷程度,似乎就没有多少人可以比得上杨绛和王小波了。这两位小说家虽方方面面都迥乎其异——一老一少、一女一男、一寿一夭(前者得享105岁嵩寿,后者45岁即英年早逝),但都毕生对小说特别是写小说情有独钟,也都十分强调“无中生有”的写小说能力:
写小说則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①
我写的小说,除了第一篇清华作业,有两个人物是现成的,末一篇短篇小说里,也有一个人物是现成的,可对号入座,其余各篇的人物和故事,纯属虚构,不抄袭任何真人实事。锺书曾推许我写小说能无中生有。的确,我写的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②
其实,杨绛虽然如上所录,承认在她的短篇小说《事业》中,“有一个人物是现成的,可对号入座”,但到底还是没有用人物原型王季玉(杨绛母校振华女中校长)女士的真名,而是为之杜撰了一个假名周默君(或“默先生”)。这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说,还是基于她一向坚守的“无中生有”小说写作逻辑——人物和故事出乎虚构,至少人物、机构和地方的名字完全出乎虚构。
然而,小十年过去,杨绛在她2014年随《杨绛全集》一起出版的中篇小说《洗澡之后》里,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心,却一下子打破了她在包括长篇小说《洗澡》在内的虚构文字里所秉持的这一“无中生有”写作惯例——譬如,在同年出版的小说《洗澡之后》单行本第14和15页里,就有这样一段人物对话,赫然提到北大的两位知名外语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和杨业治,并恬然地、毫无违和感地让《洗澡》和《洗澡之后》里虚构的准男主人公许彦成置身于这两位真实的学者与教授之间:
馆长接着问姚宓:“你通几门外语?”
姚宓说:“学过英文、法文。”
馆长说:“不行,凡是有代表性的文字,你都得学,也别忘了咱们本国的古文。”
姚宓说:“古文,家母也教过我。”
馆长说:“中文系李主任的课,你可以去旁听。”他(又)概括说:“有一位杨业治教授,英文、德文、意大利文都好。不过,他现在只教德文,你可以旁听他的课。许彦成先生,你在文学研究社就由他指导,你可以旁听他的课。最高学府现在有哪位法文好,我不知道了。温德先生的法国文学不错,但是口音不行。俄文,你学过吗?”③
这或许主要是因为,年届百岁的杨绛在堪称自己写作生涯收官之作的这部小说《洗澡之后》里,没有像她既往那样,虚构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而是直接使用了清华、燕京和所谓新北大这样一些真实的高等学府作为小说背景,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小说里用上了真实世界中的教授、专家名——其实,除了颇为正面地推许新北大教授温德和杨业治,杨绛在小说《洗澡之后》里,还至少语涉褒扬地提到了西文图书管理大家、老燕京和新北大的图书馆负责人梁思庄(梁启超次女)。
问题的关键又或许正在于,细心的读者或研究者不难发现,杨绛在各种文类里愿意或不得不提及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时,除相对中性的、就事论事的事务性笔墨而外,基本上都是她喜欢的或至少绝不讨厌的。梁思庄女士自不待言,在如上提及的温德和杨业治两位学人身上,亦能程度不同地得到验证。说到底,杨绛虽然曾自承“我认为我为人处世也是儒家思想,我最爱《论语》”④,但骨子里毕竟首先是一个爱憎分明、敢爱敢恨的人,所以也才会毫不含糊、斩钉截铁地说:“讨厌我的人,我也讨厌他们!”⑤
二、杨绛与温德
吴学昭2017年经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一书。在该书第237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刚好清华大学吴晗到上海招聘,锺书想着换换空气,杨绛或能病好,就与杨绛商量一同应聘到母校清华外文系任教。原系主任陈福田1947年请了两个极年轻的(二十出头)美国人到清华,为高年级授《莎士比亚》,而不准教学经验丰富的Winter等授课,遭到学生强烈反对,以致外文系1948级全班罢课……”
这表明,在传主杨绛心目中,来自美国的温德先生教授西方文学驾轻就熟、经验极其丰富——这里所谓西方文学当然仅指英美文学,但前文引述的《洗澡之后》片段借指导姚宓的博文图书馆馆长之口,又等于正面肯定了温德的法国文学修养和教学水平,虽然不无调侃地不忘小小贬损一下他的法语口音(之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只是调侃,是因为温德虽是美国人,但祖籍却是法国并曾留学法国,法语口音其实不可能差到哪里去)。
盛澄华兼了一段时间系主任,又被调到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去当主任了。他比较趋时,几乎否定了绝大部分文学经典,热心地倡导用马克思主义来讲释文学,而且动员到他的老师温德头上来了。温德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早向清华学生和同事推荐和讲述英共理论家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名著《幻象和现实》(Illusion and Reality,1937)的。温德先生颇生气,他愤愤不平地对杨绛说:“我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他倒来‘教老奶奶嘬鸡蛋了!”⑥
温德有段时间不高兴,用当时的流行语说,“闹情绪啦”。清华校领导因锺书夫妇都是温德的老学生,锺书还和他一同负责指导研究生工作,就要他俩去给温德做点工作。情况很快就弄清楚,原来老温德背了“进步包袱”,不满意对某些苏联教员礼遇太过,说他们毫无学问,倒算“专家”,待遇特殊,月薪比他高出几倍。杨绛笑说:“你怎么跟他们比呢?你只能跟我们比呀!”这话,他倒也心服,他算不上什么“外国专家”,他只相当于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温德对老学生的关心显然很高兴,什么体己话都说,他甚至孩子似的发牢骚:“我都很久没吃鸡啦!”杨绛就炖了鸡,请老师到家里吃年夜饭,同时祝他生日快乐(温德12月30日生日)。⑦
如上这两段由吴学昭和杨绛转述的温德教授的话让人听了不禁莞尔,活画出这位既洋又土、眼里不揉沙子的老中国通个性的率真、耿直、火爆与不够城府。07F9C9D1-C0B6-4DF1-B196-43AE545AF27E
与老师吴宓之女吴学昭闲话当年的这些片言只语当然足见温德在杨绛心目中地位的重要,但更能突出地显示这一点的还是杨绛自己的散文《纪念温德先生》,作于1987年,温德逝世当年。在这篇纪念文章里,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一书中如上所录的两段温德轶事自然也都出现了,只是比书中所述简略。
此外,杨绛除了以她一贯不动声色的恬淡柔韧笔调,极其传神地寫出了壮年即来中国任教并毕生在中国生活的一位美国学人所能遭逢的现实与心理尴尬(“他是一个丧失了美国国籍的人,而他又不是一个中国人”⑧),更把他情趣的高雅(“一九四九年我们夫妇应清华外文系之邀,同回清华。我们拜访了温德先生。他家里陈设高雅,院子里种满了花,屋里养五六只暹罗猫,许多青年学生到他家去听音乐、吃茶点,看来他生活得富有情趣”⑨)、为人的善良正直与勇于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和张奚若先生交情也很深。我记得他向我谈起闻一多先生殉难后,他为张奚若先生的安全担忧,每天坐在离张家不远的短墙上遥遥守望。他自嘲说:‘好像我能保护他!”⑩),以及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热爱(“温德先生爱中国,爱中国的文化,爱中国的人民。他的好友里很多是知名的进步知识分子”11)展露无遗。
或者说,按老派学人张中行在《老温德》12一文中所定义的那样,杨绛此文完美地突出了温德的有“德”有大节。至于张中行也曾提及的温德的学识高、讲课好虽然并非杨绛此文的重点,但杨绛不仅一开篇就直陈自己和先生钱锺书本科或研究生期间都上过温德的课,更通过转述温德自己如何指斥某些俄裔专家毫无学问,间接地肯定了温德业务能力的强悍。
一个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或许是,与坊间认为温德20世纪20世纪初来中国任教系由闻一多举荐的流行说法不同,杨绛称:“据温先生自己说:他是吴宓先生招请到东南大学去的;后来他和吴宓先生一同到了清华,他们俩交情最老。”13揆情度理,闻一多当年应是最早与温德在美国芝加哥相识并首先为其打开了解中国之窗,而后在温德加盟南京东南大学并进而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道路上,系时在中国国内的吴宓等人合力推动了一把。
三、杨绛与杨业治
关于杨业治教授,在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一书中,至少能找到如下两则轶事:
在“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以前,人际关系比较正常,礼尚往来,说话无多顾忌,有时相互还开开玩笑……
锺书养了保康姐从城里抱回的一只小花猫,迁居中关园后,在屋前空地种了些花。杨业治笑锺书种花浇花又养猫,说他cati-culture;锺书马上回敬他daughti-culture,笑他一意培养女儿学琴。14
运动期间,为了避嫌疑,要好朋友也不便往来。杨业治在人丛中走过杨绛旁边,自说自话般念叨“Animal Farm”,连说两遍,杨绛已心里有数了,这就是她的“底”。她在课堂上介绍英国当代小说时,讲过Animal Farm是一部反动小说。检讨中杨绛做了说明,“洗澡”顺利通过;专管“洗澡”的全校学习领导小组还公布为“做得好”的检讨。15
杨绛所提供的这两个小故事表明,杨业治是钱杨夫妇共同的好朋友、要好朋友。这要好的表现在于不仅平时可以互相打打趣、彼此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临事时亦能善意地守望相助,力所能及地为对方通通风、报报信。若是细究起来,像钱杨夫妇和杨业治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教育程度、家教背景等缘故,往往崖岸自高、如封似闭,作为同事能被彼此看着顺眼,引为至交好友,还是比较稀见和难得的。
或许还值得一提的是,如上两段轶事无巧不巧地都涉及了英语,出现了英语字眼儿。这至少能说明两点:一是,杨业治作为新北大首任德语教研室主任,除德语过硬、专治德语文学而外,英语水平也很高(毕竟他清华本科一毕业,便被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德语文学并随后拿下文学硕士学位),与杨绛在小说《洗澡之后》里,借博文图书馆馆长对杨业治教授所做的“英文、德文、意大利文都好”评语相符;二是,在老一辈欧美文学学者那里,英语是基础的基础,是被作为不成文的工作语言、交流语言通用的。
而若考察杨绛在自己的文字里直接提到杨业治之处,除了本文一开篇所指出的《洗澡之后》这部小说里的几句对话,至少还有杨绛自拟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1953年2月22日,文学研究所在旧燕大“临湖轩”开成立大会,郑振铎为正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力扬为党支书。贵宾有周扬、茅盾、曾照伦及新北大杨业治等教授及图书馆主任梁思庄。16
像最初附属于新北大的文学研究所成立这样重要的大会,在文联副主席周扬、文协(即后来的作协)主席茅盾和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曾昭抡(杨绛所记“曾照伦”应是笔误,曾任新北大教务长,1953年2月后任高教部副部长)等相关的贵宾之外,新北大本校相关的教学和科研骨干或首脑一定会大部分到会道贺,可杨绛此处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地仅仅提及杨业治一位教授,以及校图书馆负责人梁思庄。即便本意或初衷是以他们一男一女两位为代表,也实在稍嫌少了点儿[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一书的第269页,又在当天与杨绛有同席和聊天之谊的杨、梁两位之外,将新北大外文系(西语系)副系主任吴兴华补充了进来,但也仍属挂一漏万,远不够充分]。
只能说,杨绛当时或后来回忆时,只对她个人比较有好感或起码更为熟悉的杨业治、梁思庄两人印象深刻一些,所以便不免任性和随意地只写了他们两位。这很像在上举《洗澡之后》这部小说里,博文图书馆馆长在温德之外,在虚构的许彦成之外,也只向姚宓推荐了杨业治、梁思庄两人一样,如出一辙。
事实上,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创始研究员王伯祥的日记中,笔者依常识或常情所做的如上揣度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印证——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大会当天其实挺热闹,“宾客同人到者(多达)六十余人”,会后“在轩中聚餐,凡五席”[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一书第269页的记述是“席设三桌”,略有出入]:07F9C9D1-C0B6-4DF1-B196-43AE545AF27E
1953年2月22日,正月初九,星期日:“十二时半乘三轮赴黄化门西谛家,平伯已在。盖约同附车出城也。时西谛适出午饭,俟至一时三刻许乃返。因共载出西直门,过海甸,迳赴北大临湖轩,已二时廿分矣。宾客同人到者六十余人。晤雁冰、周扬、汤锡予、蒋荫恩、冯至、其芳、积贤、觉明、默存、杨绛、余冠英、曹靖华、罗大冈、曾昭抡等。二时四十分开会。西谛主席,雁冰、昭抡、周扬、锡予、觉明、平伯先后讲话。六时十分始毕。即在轩中聚餐,凡五席。余与平伯、觉明、其芳、冯至、靖华、大冈及两位未及请教之人同座。饮啖至七时半散,仍偕平伯附西谛车入城。”17
如上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跃进(缓之)从王伯祥的日记入手考察俞平伯时所录。他评论说:“这是目前所见记载文学所成立最详细的史料,我已收进《文学研究所所志》中。”18而学者范旭仑对《王伯祥日记》(中华书局,2020)如下的数据挖掘虽不无出入,但大体同一,是考察钱锺书与文学所关系时的副产品: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文学所成立典礼:“与西谛、平伯共载,径赴北大临湖轩。宾客同人到者六十余人。晤雁冰、周扬、汤锡予、蒋荫恩、冯至、其芳、积贤、觉明、默存、杨绛、余冠英、曹靖华、罗大冈、曾昭抡等。二时四十分开会。西谛主席,雁冰、昭抡、周扬、锡予、觉明、平伯先后讲话。六时十分始毕。即在轩中聚餐,凡五席。余与平伯、覺明、其芳、冯至、靖华、大冈及两位未及请教之人同座。饮啖至七时半散。”19
虽然王伯祥在自己的日记中,并未也很难将当天与会的60余人全数照录出来,但至少在他自己之外,还是具体罗列了包括钱杨夫妇在内的16人,比杨绛前述记载中所提及的8人整整多出了一倍。尤其是,在王伯祥罗列的16人宾客和与会者当中,堪称重量级嘉宾的新北大俄语系主任曹靖华和西语系主任冯至赫然在座,却偏偏落下了杨绛记忆深刻、重点关注的梁思庄和杨业治!
若单从德语文学研究专家的角度来看,虽然《王伯祥日记》中提到的冯至既和杨业治年龄相仿又同系同专业,也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有过交集(杨业治1931—1935年在该校日耳曼语文系访学进修,冯至则是1935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但就事论事,冯至除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数一数二的著名作家,学位和职位也都比杨业治高一个等级(一个是博士,时任新北大西语系主任;一个则是硕士,时任新北大西语系德语教研室主任),王伯祥在日记中只提到更知名的冯至,却省略了杨业治便显得情有可原,自有其逻辑脉络可循。相形之下,杨绛显然更多是从个人好恶、情感和性别等因素(包括熟络程度)上着眼,才在还原历史时显杨业治、梁思庄而隐冯至、曹靖华。
种种迹象表明,对冯至这位当时的北大西语系系主任和后来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杨绛显然既因一开始不认识而不太熟悉,后来又因理念不一、观点分歧而不免有些敬而远之——杨绛本人如下这段看似平淡无争其实暗藏机锋的话可视为小小的佐证:“文研所刚成立的时候,外文组还没有个主脑。我记得有一天力扬带了我素不相识的冯至同志同到我中关村的新家来。锺书借调在城里工作,家里只我一人。冯至同志是新北大的西语系主任,他表示,我翻译Gil Blas的工作不合适。我说,翻译Gil Blas的事随时可以搁下,另换别的项目。他们问:‘翻译多少了?我答:‘一半。他们两人低声商量了一番,无可奈何地说:‘那就翻下去吧。大约因为半途而废也不好。我觉得一身都是错了。身属英文组,职务是‘研究,但我却在翻译法文。不过,当时‘老先生都在翻译。罗念生翻译古希腊悲剧,罗大冈翻译《波斯人信札》,老卞在翻译Hamlet……”20
说杨绛与杨业治私交不错,还可以以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为佐证,那就是,杨绛曾向杨业治签赠自己翻译的西班牙小说经典《小癞子》。笔者若干年前,曾有幸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过这一签名本的照片——应该是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年初版本,扉页左上角是繁体竖排的“業治先生指正”这6个工整、秀气又隐含一丝刚劲气的黑色钢笔字,没有注明日期,但扉页左下方偏中段处盖着一枚红色印章,是篆体的“杨绛”两字。
当时感触最深的两点印象是:其一,小说译者杨绛作为赠书者,明显对杨业治很重视,才会签得那么仔细和认真;其二,签名本所显示的杨绛的硬笔书法着实可观,既娟秀又透着功力,显然是曾认真习练过(据称,杨绛曾数次用硬笔为钱锺书抄诗,包括早期的《中书君诗》和晚近的《槐聚诗存》等),也明显比她后来写得要好(当年杨绛年方40,毕竟是青壮年,手不像后来那么抖)。
【注释】
①王小波:《小说的艺术》,载《文明与反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第362页。
②杨绛:《作者自序》,载《杨绛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2页。
③杨绛:《洗澡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4-15页。
④⑤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⑥⑦141520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243、251、250-251、256、279页。
⑧⑨⑩1113杨绛:《纪念温德先生》,载《杨绛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214、213、214、216、214页。
12张中行:《老温德》,《读书》1993年第7期。
16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载《杨绛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388页。
1718缓之(刘跃进):《〈王伯祥日记〉中的俞平伯先生》,《传记文学》2021年第1期。
19范旭仑:《钱锺书在文学研究所——〈王伯祥日记〉中的记述》,《南方都市报》2017年12月31日。
(于慈江,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07F9C9D1-C0B6-4DF1-B196-43AE545AF2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