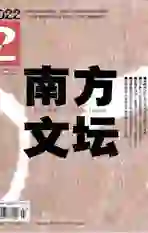女式单车、香港衣服与南方乡村认同变迁
2022-03-30刘志珍申霞艳
刘志珍 申霞艳
一、女式单车、香港衣服与时代氛围的松动
詹姆逊早就说过不存在单一的“身份”或“民族主义”,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身份总是混杂的、变化的、流动的。提起莫华杰,脑中会自动跳出东莞长安、打工作家等字样。的确,他是从广西桂东南下广东打工并通过写作改变自身命运的作家,他早期的作品也呈现“打工者”的生活场景。《临水南方》《东莞往事》等散文虽以温婉、细腻的笔致叙述了少年成长的隐秘心事,以及其在广东辗转各地打工的辛酸过往,但打工作家只是作家成长的最初印记,其作品并不能简单地冠以打工文学之名。陈启文在《一个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莫华杰中短篇小说摭谈》一文中认为:“文学创作是很个人化的,以莫华杰及其小说为例,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超越了代际同时也超然于打工身份的写作者,他很少关注打工一族的打拼与苦难,更多的是书写他远离的乡土。”①“乡土中国”已经潜入无意识深处规训我们的思维和写作,当我们面对改革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大都市时,我们依然会通过写作再现儿时的记忆和愿望。
卡尔维诺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迫切感,就是要表现他的时代”②。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南方作家莫华杰渴望表现的就是他所亲历的改革开放时代,这既是每个人的成长史,也是民族国家的现代蜕变史。莫华杰在2002年便南下东莞打工,有着相对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可他并未以广东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展开叙事,以此来凸显时代的巨大裂变,而是将笔触伸向了自己的故乡广西,以桂北小镇作为主要的叙事空间,通过冯源、陈嘉南等青年的创业和爱情故事,经由“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叙写波澜诡谲的“大时代”。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与铺陈始终是莫华杰文学创作一个颇为突出的叙事特点,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的根基。人类和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之总和,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真正体现出来”③。《春潮》是莫华杰以人物俗常的生活琐碎掘进历史的纵深处,勘探时代与个人复杂关系的一种尝试。
托尔斯泰曾说:“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乡村建构了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即使后来定居东莞,那个“邮票大小”的村庄依然是其魂牵梦萦的所在。难能可贵的是莫华杰对故乡的文学建构既不似鲁迅的批评,也不似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审美再现,也没有贾平凹式的乡土挽歌基调,而是以一种在场的情感体验描绘乡村的花鸟虫鱼、人事风物,进而展开乡村与时代的对话。《春潮》的时间跨度并不大,主要叙述了1993年到1996年之间同花镇青年的创业图景和情感纠葛。詹姆逊曾强调保持小说是“历史的”方法是对应众所周知的重要历史时间④。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最终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南方谈话让广东沿海地区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继续启航高速发展,但内陆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似乎存在一个无形的时间差,这也是莫华杰选择叙事时间的关键点。
莫华杰选取回忆的叙事视角、日常生活的叙事图景,以人物的衣食住行、娱乐、思想观念的流变来散点勾勒时代的面影。小说开篇通过欧阳娴的出场在交代了叙事时间的同时,也侧面映射出时代的幽微变化。“她骑着一辆女式单车——这还是一九九三年,农村人骑的几乎都是带大梁的男士单车,那种没有大梁、车架是一个漂亮弧形的女式单车在乡下还很少见。”⑤“春江水暖鸭先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器物是人物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建构自我认同的来源。自行车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标示性,与今天不同品牌的汽车相仿,从带大梁的男士单车到车架是漂亮弧形的女式单车,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化叙述表明了人物的身份。在闭塞僻远的同花镇,这辆自行车是欧阳娴身为小学校长的父亲托了供销社的关系才好不容易买来的,小说由此具象地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乡村的物质生活水平。除了自行车,摩托车则更具揭示人物身份的象征性。在陈嘉南购买摩托时,他已经通过贩卖“香港衣服”的方式声名鹊起,成为迥异于同花镇人的“香港仔”。就连出生于贫苦山窝子的冯源,也因开着摩托车的缘故,不仅进入教育局的宿舍楼,还不费吹灰之力得知了欧阳才华的房间号码。自行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意味着时代的加速度,意味着生活空间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女式单车超越了单车的使用价值而彰显出消费价值,成为身份的标记。嘉陵牌摩托车进入乡村则标志着流动性,稳定的乡土中国开始流动起来。
商业文明的种种症候借春潮“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改变了乡村的衣食住行,而且更新了乡民的思想观念。而价值观的变化离不开信息的刺激,手机、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大量普及带来全球信息的极度通畅,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交通、科技的制约,某种器物、时尚、潮流等要经过极为漫长的过程,才能由繁华的大城市进入偏远的乡间。20世纪90年代初期,除了少数大城市外,中国大部分内陆地区都比较落后,时尚的风潮是自上而下,从香港、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到梧州、桂林,再中转到乡村,时尚普及的速度与交通和通信的速度匹配。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指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试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进行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⑥穿衣打扮方式是我们寻求社会认同和彰显自我最明显的方式。一方面,衣服有保暖、审美的功效;另一方面,衣服也具有区分阶层和社会地位的作用。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对衣服的用色用料有严格的规定,奢靡的宫廷生活促使丝绸等昂贵的织品技艺达到非常高的水准。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阐述了人的奢侈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資本主义的发展。
频繁的商业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审美追求,虽然在此之前新式自行车、摩托车等生活用具早已出现,但这些耐用品价格昂贵,只属于富裕人家。脑袋灵活的陈嘉南从广州运回来的各种款式新颖的衣服却因价格适中,更容易得到小镇青年的青睐。尚未回归的香港引领着时尚的趣味,港产影视剧让人们对香港产生强烈的向往。陈嘉南很好地利用了大众的这种消费心理,声称自己的衣服是香港货,并挑选了一些自己去香港游玩时拍的照片贴在墙上,以证实自己所言不虚。“香港衣服”的商业噱头具有很大的轰动效应。这批“香港衣服”既新潮又让小镇青年感受到神秘的热气流。如果说陈嘉南那批衣服的香港标签只是一种商业运营手段、消费符号的话,张学友、刘德华、张国荣、beyond、谭咏麟等香港明星则是更为具体、真切的客观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觉醒,香港影视搭乘时代的快车率先崛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而其流行音乐更是火遍大江南北。八九十年代那些为人熟知的香港明星、香港歌曲,不仅对内地的娱乐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一个时代的“神话”。陈嘉南像开启潘多拉魔盒般给闭塞、偏僻的同花镇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人们原本单调乏味的乡村生活。在欧阳娴去往深圳之后,冯源正是借助这些流行音乐消磨难挨的孤寂时光,浇筑心底无地赴诉的相思之苦。除了香港明星,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和琼瑶言情小说在当时也深受广大青年男女的喜爱,是那个时代人们挥之不去的共同记忆。这些通俗文艺对内地的影响比口号要持久得多,为大家勾勒了富足而轻松的生活愿景。
二、爱情与创业的交响曲
关于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题材,南方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比如盛可以的《北妹》、王十月的《无碑》和《国家订单》、盛慧的《闯广东》、郭海鸿的《银质青春》,还有塞壬的一系列散文、郑小琼的诗歌,以及一大批出色的非虚构作品。面对这样的时代大潮,莫华杰选取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日常生活中那些极具时代印记的事物和记忆,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生活“小变化”来侧面映射巨大的时代变革。《春潮》将那些碎片化的生活细节按照记忆的逻辑镶嵌在一起,比较清晰地展现9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整体面貌。创业就像现代文学中的“革命”一样,成为开放时代的“热点”和潮流,当然,创业的青春必然伴随着爱情的交响乐。如何向阳在“大湾区文学新浪潮”广东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所说,《春潮》既是一个创业的故事,又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第一篇演讲就提到轻逸于小说的重要性。陈启文也在访谈中建议莫华杰用心体悟伊凡·克里玛“轻与重的辩证法”,“所谓轻,是如何从一个狭小的侧面揭开一角,而重呢,在克里玛笔下,那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却随着国家命运而跌宕起伏”⑦。克里玛善于捕捉生活中一些具有隐喻意味的细节,通过举重若轻的方式揭示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变化。回看过去的20世纪和最近40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在于流动性。乡土中国是建立在稳定的“熟人社会”基础上的,而改革开放让人、物、观念、资源、金钱以及整个社会都快速流动起来,交通和通信的高速发展尤具标志意味。
在改革浪潮面前,很多人怀揣着发财梦,毅然决然地“下海”。“海”意味着深邃、起伏,也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诗和远方”。城市化、商品化不仅形塑了现代中国的外部面貌,也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大量的农民离开家乡涌入城市,以谋求新的人生出路,由此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潮。农民工这个新词道出了他们新的身份:户籍制度上的农民和实质上的工人。在这场巨大的迁徙中,几乎每个人的身份及认同都更新了。
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盛可以等打工作家都凭借自身在场的情感体验,书写城市打工者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褶皱。莫华杰走在这条时代大道旁边的小径上,《春潮》避开了对珠三角的正面强攻,着重书写冯源、陈嘉南等人在同花镇的创业经历,李宝军响应改革开放号召,毅然辞去公职成为在同花镇开淀粉厂的民营企业家,梁坤健、欧阳娴等农村青年则随潮流南下深圳打工。《春潮》呈现了一代青年的选择,撷取层层涟漪来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海洋。小说的着眼点始终在乡村小镇的今昔变化,城市打工者的生活通过其与同花镇乡亲的情感纠葛来展现。更耐人寻味的是,人物创业的内驱力和最终目标并非现代人一再强调的自我实现和远大抱负,而是基于爱情的怦然心动。
鲁迅对看客文化的发掘对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后世文学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莫华杰也很好地利用了乡土中国的看客群像,但与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灵魂透析不同,《春潮》对看客的书写主要是为了制造舆论效应,并经由其思想的转变进一步体现了时代的新变。《孟子·离娄上》云:“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冯源表弟罗祥兴在富江大桥因恶作剧将欧阳娴绊倒摔晕,在桥下摸石螺的冯源情急之下穿着一件大裤衩将其送往卫生院求医,这在思想观念保守的乡间小镇是件难得一遇的新闻,又因她的男朋友是梁坤健,各种因素将二人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为了平息这场闹剧,冯源来到李宝军的淀粉厂当捞渣工,认识了因制造假化肥入狱的陈嘉南。与冯源的避难和谋生不同,陈嘉南进入淀粉厂纯粹是为了爱情,这主要源于其在劳改农场一次不经意的抬头。刚进农场的日子对陈嘉南来说如同炼狱,就在这时李素雅如一缕星光点亮了他晦暗的人生。之后为了增进两人的感情,得到李素雅父亲李宝军的认可,陈嘉南与冯源便在同花镇携手创业,并与李素雅终成眷属。冯源也因开话梅坊认识了欧阳娴的妹妹欧阳慧,以此为契机拉近了与欧阳娴的关系,欧阳娴也不顾家人的反对与性格不合的梁坤健分手,选择了幽默风趣的冯源。但冯源与欧阳娴的爱情最终难敌亲情的重负,在欧阳才华的精心策划和极力劝说下,为了智力只有八九岁的妹妹,欧阳娴忍痛答应了父亲看似荒诞的要求。瓦西列夫曾说:“爱情的悲剧是情感冲突和社会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个人的高尚追求同反对这种高尚追求的外部力量、某种重大的客观障碍之间深刻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⑧总览20世纪中国文学,爱情与家族的关系向来暧昧,家既是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前进的壁障。“五四”以降,家被视为囿羁自由、压抑人性的“罪恶渊薮”,对封建家长的反抗始终是青年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主要路径,但《春潮》中青年与父辈基于爱情的矛盾冲突并非革命、启蒙话语下的时代感召,而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的传统乡土人伦与现代人恋爱观念的碰撞。
小说以创业加爱情的叙事模式,主要讲述了冯源和陈嘉南在同花镇开设话梅坊和打火机厂的创业经历,每一次创业都对其感情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陈嘉南人物形象的身份设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宝军的淀粉厂是联结人物关系的重要纽带,冯源与陈嘉南先后进入淀粉厂当捞渣工,这与其梦中情人有着莫大的关联,但陈嘉南是爱情催发下的主动选择,冯源则是梁坤健逼迫下的无奈之举。也正是在当捞渣工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之后的共同创业埋下了伏笔。与冯源这一乡野小伙截然不同,陈嘉南来自最早沐浴改革开放朝露的广东,有着相对开阔的思想和眼界。他在同花镇贩卖衣服不到一个月便赚了一千六百块钱,这使冯源觉得做服装生意是一个不错的营生,但在陈嘉南看来,“贩卖衣服只能挣点小钱,成不了大器,一年就算赚几千块钱,也不过是一个衣服贩子”,只有打开创业之路才能出人头地。但创业需要大量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嘉南良好的家境又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哥哥陈嘉志在顺德开了家养殖场,赚了不少钱,因而陈嘉南根本不用为钱发愁,这也是他不愿贩卖衣服赚些蝇头小利的原因所在。
两万块钱创业基金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掀不起多大的浪花,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一间私人小作坊是不成问题的。李宝军的加入又是话梅坊得以顺利开设的决定性因素,李素雅的舅舅是劳改农场的监区长,母亲以前在供销社上班,借着李家的关系,他们在解决了进料问题的同时,也有了很好的销售渠道。更为重要的是,话梅坊本身就是陈嘉南针对李宝军开设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和李素雅的交往创造条件。金钱是人们日常生活绕不开的话题,“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中叙述话语中的经济话题是直接进入的,并且增进着叙述的趣味”⑨。王安忆更是强调经济叙事对于再现生活的本真状态,透视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作用。语言所指和能指的任意性本身代表着某种不确定性,不同的时代赋予语言不同的所指性意涵,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莫华杰的《春潮》,“创业”一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时代语境下的意义流变清晰可见。不同于《创业史》中由个人创业走向集体富裕的革命性蜕变,《春潮》的创业不再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话语,而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资本运作方式,遵循市場那只看不见的手,以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目的,这使得投资成本和利率尤为重要。但陈嘉南和冯源都不懂如何制造话梅,话梅坊只能请有经验的老师傅来指导,并从渡水村招了五名妇女当工人,这无疑增加了话梅的制作成本。三个月下来,“刨去原材料、人工成本、吃饭和烧煤等一切费用,大约能赚九百来块钱,然而,再除去房租六百元,就只有三百块钱的收入,三个股东分,平均每个股东才得一百块钱”。话梅又是季节性作物,话梅坊只得草草收场。
如果说话梅坊因时令、天气、产量等各种局限而经营惨淡的话,打火机厂在同花镇的开设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陈嘉南表哥唐世荣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回乡建厂则为其奠定了基础。唐世荣初中毕业便跟着父亲做皮鞋生意,由于常年奔波于广州和温州之间,他敏锐地察觉到皮鞋生意的发展空间将会日益窄化。而“广东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唐世荣看到深圳、东莞、珠海、佛山、顺德等地方四处建厂房,看样子顺德的发展不比温州差,他于是心里蠢蠢欲动,想回家乡干一番事业,省得东奔西跑”。“目前很多打火机厂的产品都是做出口贸易,还没有重视国内市场,国内很多地方的人们仍用火柴点火,包括烟民,因为买不到充气打火机只能依靠火柴点烟。打火机是消耗品,全国这么多家庭和人口,这里面潜藏着巨大的市场。”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各地经济的腾飞为唐世荣创造了良好的创业契机,国内打火机市场的供不应求也使他看到了商机。与话梅坊完全依赖外力运作不同,唐世荣经过一年的打工学艺掌握了打火机的全部技术,根据产品制作的难易程度和顾客的消费能力,将生产目标锁定在最简单的普通滑轮打火机和电子打火机上,很快使打火机作坊步入正轨,进而与陈嘉志合伙扩大生产规模,将其由小小的家庭作坊升级为企业。
莫华杰注重小说的谋篇布局,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相互映衬,环环相扣。顺德市消防部门对全市打火机厂和家庭式作坊的全面整顿,是世嘉打火机厂搬迁的直接驱动力,而陈嘉南和冯源开设话梅坊时租用的渡水村公房又为其搬至同花镇提供了可能。虽然同花镇地处偏远,缺乏招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听说广东商人要在同花镇投资建厂,下自渡水村村长,上至县委都高度重视。正是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打火机厂很快建成投产,形成了由陈嘉南和冯源负责同花镇分厂的生产管理,唐世荣和陈嘉志驻守顺德总部开拓市场的企业运作机制。而打火机厂从顺德搬迁至同花镇,不仅化解了陈嘉南和李素雅、冯源与欧阳娴异地恋的情感危机,也使同花镇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在解决了许多青年就业问题的同时,极大地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可以说,陈嘉南不仅激发了冯源创业与追求爱情的欲望和勇气,也如阿基米德杠杆般撬动了同花镇的经济板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同花镇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对两广地区经济共同体产业链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改革开放的深入与乡镇人物认同的变迁
跟职业小说家偏重叙事不同,莫华杰喜欢讲故事,他就是被讲故事的兴趣带上写作道路的,他曾经泡在网上阅读并写作,“我从写网络小说中学会了怎么编故事,怎么扯人物关系,怎么搭建整体框架,怎么把故事讲得更吸引读者,怎么把人物写得更加活灵活现。”⑩即使后来写作有所调整,对故事的强烈兴趣依然起着主导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他作品的可读性,“因为追求故事的新鲜感和吸引力,我的叙述重心往往会偏向于塑造人物和构造故事上,因此削弱了文本的思想,对人物没有更深的思考。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些,因为我认同‘形象大于思想’这个说法,也喜欢金庸先生说的‘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11新作《春潮》凸显了作家讲述故事的能力。
在勾画90年代创业剪影中,王十月的《国家订单》通过工厂小老板的一波三折和人生遭遇,“跳出了打工文学以前的局限,从单纯叙写生存之艰与内心之痛,开始转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表现个人力量在遭遇时代危机时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12,《春潮》虽然也写到因制作假化肥入狱、捞渣工工作的艰辛、开话梅坊创业的失败,以及打火机厂的生存危机,但作家只选取了其中的一些横截面,而且对于爱情的浪漫想象冲淡了沉重的现实苦痛,甜蜜爱恋的沁润也遮掩了创业的挫败感,从而使得爱情成为人物创业的原动力和最终旨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打火机厂是在顺德消防审查的外力作用下将易燃易爆的几个车间搬到同花镇的,与《古船》中的勘探队相似,其在给当地带去“福利”的同时,相应的一些隐患也随之滋生。但《春潮》并未由此展开乡村工业化所导致的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冲突,而是在侧面叙述了投资建厂极大地推动广西乡村振兴的同时,将叙事的重心始终放在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上。
莫华杰善于利用突发事件来编织情节,勾连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论是陈嘉南和李素雅,还是冯源与欧阳娴,他们的相遇都恰似一种偶然的凑巧,实在却蕴藏着某种宿命的必然。陈嘉南的追爱之旅大致分为劳改农场的偶遇、淀粉厂的相识、贩卖衣服和开话梅坊时的热恋,以及开打火机厂之后顺利结婚四个阶段。劳改场宛若月老手中的红线,将陈嘉南和李素雅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牵引在了一起。而陈嘉南不论是在淀粉厂当捞渣工,还是在同花镇贩卖衣服、开话梅坊,乃至极力说服哥哥将打火机厂搬到同花镇,都是为了成功追到李素雅,得到其家人的认可。冯源和欧阳娴的恋爱经历也与之相仿,小说以冯源救欧阳娴的误会开篇,但迥异于李素雅对陈嘉南渐进式的爱情,欧阳娴对冯源的态度经历了由愤恨到爱恋,再到忍痛分离的曲折过程。也不同于陈嘉南对李素雅奋不顾身的执着追求,冯源与欧阳娴的爱情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除了欧阳娴与梁坤健性格不合的情感缝隙,陈嘉南和李素雅的大力撮合,尤其欧阳慧的无心插柳都起到巨大作用,话梅坊在渡水村的开设更是功不可没。话梅坊本是陈嘉南为给自己和李素雅提供恋爱场地,避免他人(尤其李素雅家人)的猜忌开设的,却无意中促成了冯源和欧阳娴的爱情。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话梅坊与欧阳娴家仅隔一片小树林,为了调节脑部供血,刺激神经,在医生刘见章的建议下,欧阳慧每天都会来此地荡秋千,这为冯源接近欧阳娴提供了便利。正是由于欧阳慧这一中介,冯源不仅改变了欧阳娴对其因误会而产生的刻板印象,并最终与之相恋。
如果一味以各种巧合结构情节,自然会使小说落入俗套,从而削弱小说的文学性,降低可读性和对读者的吸引力,莫华杰对此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春潮》在诸多的因缘际会之外,也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叙事,这主要体现在梁坤健与李素雅关系的突转、欧阳才华拆散冯源与欧阳娴的原因,以及琼瑶小说对李素雅和欧阳娴的阅读影响上。劳改犯的前科和外地人的身份使得陈嘉南和李素雅的恋情遭到李宝军的坚决反对,并在李素雅家人的大力帮助下,梁坤健一改往日沉默寡言的性格,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其展开追求,李素雅也为他的诚心所打动。但小说并未以此设置三角恋的俗常戏码,而是笔锋一转,不仅将梁坤健变为陈嘉南和李素雅爱情的说客,而且爱情的受挫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梁坤健的深圳之行,这也为欧阳才华之后的棒打鸳鸯创造了条件。瓦西列夫认为“根据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就可以判断他总的文明程度”,“它使人们得以观察到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13。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时刻规训着人们的思维和言行,在向往现代开放自主爱恋的同时,很难彻底斩断传统的“脐带”。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与陈嘉南和李素雅基于客观现实的情感波折不同,欧阳才华对冯源与欧阳娴爱情的阻挠不是出于冯源贫寒家境的世俗观念,而是因为欧阳慧。冯源通过智力只有八九岁的欧阳慧成功追到欧阳娴,但也使欧阳慧对他产生了异于常人的依赖,为了让欧阳慧有个好归宿,欧阳才华狠心迫使欧阳娴离开同花镇去往深圳打工。科学研究表明,阅读可以改变大脑的物理结构和化学成分,重塑人的记忆与现实生活,小说多次写到陈嘉南为了给李素雅“洗脑”,特地在广州给她买了很多琼瑶小说,李素雅和欧阳娴也的確是琼瑶的忠实读者,这貌似为她们日后为爱情与父母反目埋下了伏笔。但李素雅虽从中深受启发,对父母对其感情的干预有所抗争,但她所受的传统教育一直规训着她,使她从未有过如琼瑶小说主人公般冲破世俗的藩篱,与陈嘉南私奔广州的想法。欧阳娴更是囿于父亲的亲情绑架而毫无招架之力,果决地将冯源让给了妹妹,带着深重的伤痛开始了迷惘的漂泊之旅。超我战胜了本我,爱情的甜蜜与激情最终难敌亲情的温情罗网,小说进而揭示出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深层文化蕴涵。
表面看来,冯源是一个酷似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人物形象,这主要源于他与孙少平有着出生于偏远乡村、因家境贫寒辍学、进入小镇(城市)打工、供弟弟(妹妹)读书等近乎相同的人生轨迹。就连爱情,其也与孙少平有某些相似之处,譬如他们都与家境优越的女性相恋,最终却悲剧收场。但孙少平对人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具有浓郁的“出走”欲望以及与命运抗争的决心和毅力,而冯源人生的反转皆因陈嘉南。受柴叔算卦的影响,冯源从认识陈嘉南那天起,便将其视为自己人生的跳板。也就是说,与孙少平凭借自身的艰苦努力与命运抗争的奋斗历程截然不同,冯源自始至终都将未来的期许寄托在陈嘉南身上,这使他不论是在创业上,还是面对爱情都缺乏一定的自主性。从某种程度而言,陈嘉南代替冯源做出了一个个足以改变命运的决定,但当陈嘉南对欧阳才华精心设计的“阴谋”无计可施时,他便彻底陷入了绝境之中。如果沒有陈嘉南,冯源也许一辈子都将是人们眼中山窝子里的穷小子,要么听从欧阳才华的安排成为同花镇中心小学的美术老师,并娶智力残障的欧阳慧为妻;要么为生计所迫,加入无数挣扎于城市底层的农民工行列;而他与欧阳娴之间的爱情便无从谈起了。
《春潮》凸显了莫华杰钩沉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代剪影的创作意图,与很多正面书写这一宏大题材的作家不同,莫华杰避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将自己的故乡广西小镇作为叙事的空间场域,采用日常化的叙事视角,以人物的衣食住行、娱乐风尚以及思想观念的新变等侧面再现了时代的现代蜕变。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农民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对于土地的依从形成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随四季时令变换的劳作和生活方式。波兹曼认为“在芒福德的著作《技术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14。这同样适用于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改革开放打破了农业文明时代乡村的“熟人”秩序和恒定结构,在商品经济和现代都市的魅惑下,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位移,空间的流动性加强,乡村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裂变。莫华杰敏锐地捕捉到了90年代初期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变化,经由冯源和陈嘉南的创业图景和情感纠葛,再现了时代热气流的猛烈冲击下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民身份的转变。
【注释】
①陈启文:《一个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莫华杰中短篇小说摭谈》,《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23期。
②[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第2页。
③[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叶齐茂、倪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90页。
④[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王逢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第270页。
⑤莫华杰:《春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第3页。除特别注明,以下《春潮》的引文均引自此版本。
⑥[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2页。
⑦莫华杰、陈启文:《访谈:在不经意之间面对自己的灵魂》,《花城》2016年第6期。
⑧13[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第376、412页。
⑨高秀芹:《张爱玲、王安忆叙述中的经济话题》,《齐鲁学刊》2003年第6期。
⑩莫华杰:《我是如何从网络作家成为纯文学作家的》,《广西文学》2021年第8期。
11莫华杰:《形象大于思考》,《滇池》2020年第10期。
12胡磊:《打工文学的叙事向度——以王十月的写作为例》,《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1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4页。
(申霞艳、刘志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