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包法利夫人》
2022-03-30李庆西
李庆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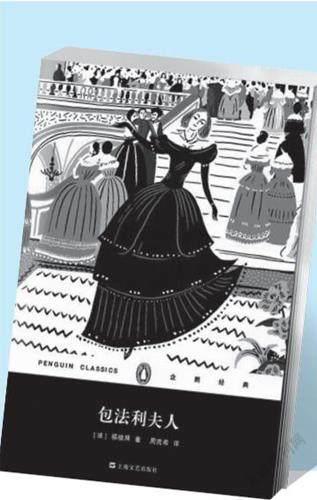
重读《包法利夫人》,是想找回过去的阅读记忆,福楼拜这部名著以前只读过两遍,许多情节都已淡忘。以前读的是李健吾译本,自己书架上找不到了,上网向图书馆借了一本,是周克希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因为两个译本并未同时在手,未做文字对比,仅凭阅读印象不觉有高低之分,毕竟两位译者都是名家。据网上信息,如今中译本已逾二十种,其中孰优孰劣,自有行内人士去评判。
周克希译本有些人物译名跟李健吾不同,如包法利先生的名字,李译作“查理”,周译是“夏尔”。爱玛的两个情人,李译是“赖昂”和“罗道耳弗”,周译为“莱昂”和“罗多尔夫”。对读者来说,译名最易先入为主,如永镇那个药剂师,留在脑子里的记忆还是“郝麦”,现在周译作“奥梅”,一眼看去感到陌生。
考虑到李健吾的旧译名较为读者熟悉,本文依然沿用郝麦、罗道耳弗这些人名。引述原著则取自周克希译文,因为手头只有这个本子。作为非专业读者,我只谈阅读感受,主要从故事本身来讨论作家的叙事意图和文本意涵。
福楼拜的现实主义或曰自然主义叙事历来为人称道,但纳博科夫认为《包法利夫人》的现实主义只是一种“相对概念”。他的《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本文以下引述的内容为龚文庠所译)专有一章讲这部小说,举述书中若干情节和细节,表明福楼拜的故事不乏违背生活真实的臆造。比如,罗道耳弗夜里招呼爱玛去幽会,朝她卧室窗口掷砂石,包法利医生居然毫无察觉。不但他从未发现妻子出轨的蛛丝马迹,就连镇上最爱管闲事的郝麦亦从未听说爱玛的风流韵事。就常理而言这不大可能。还有关于爱玛骑马的描述,以及马车夫的过于老实天真,等等,似乎也不能令人信服。
爱玛不是那种特别审慎谨细的性格,在她与查理的八年婚姻生活中,穿插着与赖昂、罗道耳弗的长期婚外情史,要瞒住自己老公实非易事,而福楼拜的手法就是一个“瞒”字。瞒得了一时谁说瞒不了一世,现实主义不排除这种可能,小说叙事本身缘从假定的逻辑。不过,在我看来,撇开纳博科夫提出的那些疑问,女主人公性格的变化(成长史)却是更值得质疑。
爱玛,包法利夫人,一个被浪漫幻想和虚荣心引入歧途的少妇,以出轨偷情来摆脱庸常而乏味的人生,最终因债台高筑而破产自杀。福楼拜详尽地描述了女主人公自我毁灭的整个过程,这是中国人老话所说“自作孽”的故事。但起初这是一个纯情少女,后来怎么变成一心追求荣华富贵的浅陋妇人(照纳博科夫说来,她性格中有一种“冷酷的粗俗”),书中尽管给出种种铺垫,依然不能勾连人物性格逻辑的草蛇灰线。
爱玛出身于富裕农户,她父亲卢欧老爹被纳博科夫认为是书中少数几个“好人”之一,可以说她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她出场时,母亲已经去世,她在家中服侍父亲和料理农庄事务。之前她在修道院的寄宿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据查理前妻打听来的消息,我们知道爱玛“会跳舞,懂地理,会画画,会绣挂毯和弹钢琴”,颇有才艺。查理最初去农庄给老爹治腿时,就注意到厅堂上挂着一幅炭笔画的密涅瓦头像,是爱玛献给父亲的作品。
书中第一部第六章是一个重要关节,这里以回叙手法介绍爱玛在修道院的读书经历,但这一段除了善意的撒谎,未见有品性污点。她读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读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和中世纪行吟诗人的作品,她想象着“自己能生活在一座古老的小城堡里,像那些身穿长腰紧身胸衣的城堡主人一样,整天待在有三叶饰的尖顶拱门下面,双肘撑着石栏,手托下巴,眺望远处平野上一位骑黑马戴白翎饰的骑士疾驰而来”。她就读的寄宿学校虽说也是一种苦修教育,却没有多少禁锢心灵的清规戒律,反倒培养了她的浪漫情怀。音乐课上学到的那些恬静的浪漫曲,打开了“情感世界的诱人幻景”,有些同学将各种画册带入学校,女生们在寝室里偷看那些带有异国情调或东方色彩的图画,这给她带来远方的想象……
这一章在于敷设初始化的浪漫底色,作者考虑到女主人公日后的变化,不忘记提示她村俗的一面—“她的性格,在热情浪漫中间透出一股讲求实际的意味。”世俗的欲念使她逐渐远离信仰的奥义,使得修道院嬤嬷们对她备感失望。可是,她回到家里又怀念起修道院了,觉得乡间生活令人生厌。作为叙事铺垫,福楼拜在爱玛性格中着意植入一种耽于想象又摇摆不定的特征。不过,这不足以提供她走向毁灭之途的动因,性格摇摆在常人身上亦常见,像爱玛那种飞蛾扑火似的疯狂却不是常人所有。

渥毕萨尔城堡侯爵府的舞会,电影《包法利夫人》(1991)剧照
追溯爱玛性格养成之思想来源,似乎主要在于文学阅读。寄宿学校使她养成了阅读习惯,婚后依然捧读不辍,查理也跟别人说起,她就爱待在房间里看书。纳博科夫认为,她接受的是“浪漫主义的陈腔滥调”和“浅俗的意象”,这未免责之过甚。其实,她经眼之书大多是经典作品,读的是巴尔扎克、乔治桑、雨果的小说,像欧仁·苏之类已属等而下之。至于她是否真正理解原著的精义,那是另一回事,自然不能以学者标准去要求她。想必成千上万的法国少女的阅读书目也跟爱玛相仿,如果说是读书有害,而为什么偏偏是她成为被浪漫文学戕害的“这一个”?将闺中阅读作为缘由,是以类型化经验捏塑人物,非走向极致不可。
纳博科夫那本书里说:“三种因素造就一个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还有未知因素X。这三种因素相比,环境因素的影响力远远弱于另两种因素,而未知因素X的力量则大大超过其他因素。”在爱玛的故事里,很难说家庭遗传因素给她带来负面影响,此项姑且不论。纳博科夫不认为环境因素有多重要,他说:“像包法利夫人这个人物一样,包法利夫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是福楼拜精心创造出来的。所以,说福楼拜式的社会影响了福楼拜式的人物,就是在作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好吧,这一项也暂且撇开,那么剩下就是未知因素X了。
未知因素X,应该就是某种不可预期的偶发事件,但纳博科夫忙于分析“多层蛋糕”式的小说结构,并未说起爱玛的那个X是什么。其实,小说第一部第八章的故事可以说就是那个X,这一章讲述包法利夫妇应邀去渥毕萨尔城堡侯爵府上做客。因为查理给侯爵做过一个小手术,侯爵举办宴会那天作为答谢也邀请了他们夫妇。这是爱玛平生唯一见识上层社会生活的一次机会,在那儿她与一帮贵族男女共度良宵,筵席的场面和各种美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还有餐后的舞会—从开场的四组舞到夜宵后的沙龙舞,他们彻夜狂欢。侯爵府上的排场和诸项吃喝玩乐,这里不便详尽复述,总之对于爱玛来说,这短暂的奢华生活着实让她大开眼界。过去是现实境遇限制了她的想象,现在她有了人生的目标—
天蒙蒙亮了。她望着城堡的扇扇窗户,目光久久在上面流连,一心想猜出昨晚见到的那些人都待在哪些房间。她向往了解他们的生活,渴望置身其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从这一刻起,爱玛就不是原先那个爱玛了。城堡的贵族生活颠覆她的三观,原本对婚姻生活心满意足的包法利夫人,开始对查理啧有烦言,“她愈看他愈觉着不顺眼”。其实,那天回家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掉了家中的女佣。书中只说她顶嘴,难道不是嫌那女佣不顺眼了?书中记下了城堡之夜给她带来的持久影响。
……沃比萨尔(渥毕萨尔)之行,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了一个窟窿,犹如暴风雨一夜之间在崇山峻岭劈出了长长的罅隙。但她还是忍了:她把那身盛装,连同鞋底被舞厅地板蜡染黄的缎鞋,小心翼翼珍藏在衣柜里。她的心宛如这缎鞋;一旦擦着华贵而过,便留下了无从拭去的痕迹。
回忆那次舞会,成了爱玛的必修课。每逢星期三,她醒来便想:“哦!一星期前……两星期前……三星期前,我还在那儿来着!”渐渐的,容貌在记忆中模糊了,四组舞的情景淡忘了;号服,府邸,不再那么清晰可见了;细节已不复可辨,怅惘却留在了心间。
纵观全书,这个事件是铸成爱玛悲剧的唯一的X因素。城堡之夜“细节已不复可辨,怅惘却留在了心间”,此后爱玛期待着侯爵还会在渥毕萨尔重开舞会,可是一直没能等来侯爵府来人召唤。城堡的声色娱乐将她带入不可想象的愉悦之境,亦将其心中朦胧的浪漫之念转化为明晰的物质之欲。福楼拜在书中写道:“一次偶然事件,有时会引发一连串的波折,会带来风云突变的结局。”爱玛沉入黑暗之际,开始徒劳地叩击锁闭的命运之门。
细细梳理爱玛性格发展的叙事逻辑,大致就是这样两点:一是文学阅读,启发了她那种诗和远方的浪漫想象;二是渥毕萨尔城堡之行,向她展示了金钱与地位构筑的另一种生活。福楼拜的叙述笔墨委婉有致,同时也提供比较多的能够说明人物心理特点的细节(这些我就不复述了,免得文章过长),但是其内在脉络还是过于简单,归纳起来,无非是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一个沉湎于文学的女人,偶尔见识了某种奢华生活场景,就足以变坏。
关于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勃兰兑斯有一个简明的概括:“在巴尔扎克时代以前,小说几乎专用一个题材—爱情;巴尔扎克同时代人的上帝是金钱,因而在他的小说里金钱成了社会运转的枢纽……”(《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第十三章)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巴尔扎克已经离世,但福楼拜依然要面对爱情主题,就像塞万提斯依然要拿骑士精神做文章。只不过在福楼拜的故事里,爱情只能与金钱联姻,呈示二者并驾齐驱的双重主题。
包法利夫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并不像纳博科夫所说完全是作者的“精心创造”,因为并不是福楼拜让金钱成为社会运转的枢纽,当时社会本身已经是这个样子。就在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期间,马克思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托克维尔写了他的《回忆录》,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法国当日的社会状况,虽然二者得出不同的政治结论(一者遗憾革命不彻底,一者因革命而感到恐惧),但他们都发现是资本的权力关系造成了社会危机。马克思进而指出,当时掌握统治权的并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他将这个集团称为“金融贵族”(包括银行家、交易所大王,以及铁路、煤矿、铁矿、森林和大土地所有者,亦即托克维尔所说的“大业主”),正是资本运作和资源垄断扼住了社会的命脉。《包法利夫人》写的是一八四○年前后的事情,这一轮革命尚未到来,但资本与寡头已经掌控大局,即便在外省乡镇,亦有税务员和公证人事務所作为体制的配套,以资本为枢纽的经济体制已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精神趣味。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与其说表现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不如说是将这样的社会环境再现于自己虚构的故事。
至于爱玛,既然已将浪漫融入奢华的梦境,其情感生活就不可避免地与金钱扯上关系。在福楼拜这个外省故事里,也有一个乡镇微缩版的“金融贵族”,那就是永镇卖服饰的商人勒乐(周译本作勒侯)。其实,他的铺子不只出售时装和家纺用品,实际上主业是放高利贷(据说他过去是开钱庄的)。这个人物出现在小说第二部,爱玛和查理从道特迁居永镇后,勒乐来登门拜访,借着推销商品来招揽他放贷的客户。他对爱玛说:“(我)是想让您知道,钱我是不放在心上的……要是您手头紧,我可以借给您。”话里话外透出的意思是,他手里资金充足,可承揽闺中贷、私情贷、抵押贷和转移支付等各种金融业务。
爱玛用钱之处,都在那两个情人身上。她先是与永镇公证处书记员赖昂发生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这一段时间不长。当赖昂去了巴黎以后,她在农展会上结识了乡绅罗道耳弗,很快就直入主题,甚至打算要一起私奔。爱玛偷情的劲头太大,让罗道耳弗扛不住。他这头撤火了,正好赖昂从巴黎回到永镇附近城市卢昂,于是两人旧情复燃,爱玛每星期进城一次去幽会。他们一起听歌剧,参加化装舞会,在豪华旅馆做爱……美食,肉欲,爱玛永无餍足。赖昂这人胆小乏味,爱玛用自己的方式改造他,照纳博科夫的话来说,“他俩的恋爱以怪诞而又哀婉的方式实现了她所有的浪漫幻想”。
她以为这就是“爱情”,其实不过是林林总总的风花雪月而已,需要不断用金钱去维护。于是,她不得不在勒乐那儿赊账和借贷,不断地从勒乐手里签出借据,她不但卖了卢欧老爹留给自己的遗产,甚至将包法利家的祖宅都抵押了出去。小说第三部不断出现这类情景,叫人看了心惊肉跳,她自己竟是债多不愁。最后,她稀里糊涂欠下八千法郎巨债,让债权人告上了法庭。她破产了,法庭限定二十四小时之内偿还,否则要查封她和查理的全部动产及日常用品。走投无路的爱玛急得到处找人借钱,找她的情人赖昂,找公证人居由曼,找税务员毕耐,都不成。公证人还想乘人之危占她便宜,此时感受到被侮辱的愤懑唤起她最后的自尊,恨不得把那男人狠揍一顿。最让她伤心的是那个罗道耳弗,当初两人说好一起私奔,这家伙事到临头却变卦了,弄得她大病一场。现在他说他还是爱着她,却是不肯掏腰包,这无疑将她逼上了死路。结果爱玛只得服毒自尽,在神甫的祷告声里,她离开了这个金钱世界。离开了金钱,爱玛的情爱世界就彻底崩塌。
一个无所顾忌的浪漫女子,适配一个窝囊、麻木、死心眼的丈夫,福楼拜正是按照这种模式来配置包法利夫妇的婚姻关系(难免让我们想到潘金莲和武大郎的夫妻配)。在包法利医生眼里,爱玛永远是那个目光怅惘而率真的少女,他每天带着满满的幸福感出门行医。不管爱玛如何折腾,他从未心生疑窦,甚至勒乐讨账都讨上门了,还是浑然不觉。为了完成爱玛那种无边的浪漫主义,查理这般死心眼的现实主义就必须傻缺到底,直到她死后,直到他自己也要死了,忧伤的心头依然充满百合花一样“朦胧的爱的气息”。
查理情商是太差,但智商应该没有大碍,就其从业经历来看算是合格的医生。他行医中也出过纰漏,那回听了郝麦忽悠,贸然给人矫正畸形足搞出医疗事故。但总的来说,他的医术乃至医德还是受到更多的认可。在整个故事中,这位查理·包法利先生,除了罗道耳弗所称“失之宽厚”的老实人性格,没有给人留下太多印象,故事情节很少聚焦在他身上。
然而,从小说叙事结构来看,从头到尾却是依据查理的人生框架,他是书中唯一贯穿始终的人物。小说第一章,从查理作为卢昂中学插班新生说起,那顶寒怆的帽子,他姓名的别扭的发音,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这一章浓缩了他整个青少年时期,捎带介绍他的原生家庭,以及他如何通过医师资格会考,开始到道特行医,并娶了一位号称富有的遗孀。第一位包法利夫人其实并没有什么钱财,当查理心里有了爱玛之后,那女人就死了(纯然出于故事安排需要)。于是,后边的主角就换成了第二位包法利夫人,查理一直在场,却没有多少戏码。而爱玛死后,福楼拜又回过头来写他,写他处理爱玛的后事,伤心欲绝中对爱玛的思念,失魂落魄地变卖家产抵债,最后他也死了。福楼拜将爱玛的故事整个嵌入查理主题的元叙事,而故事原本的主人查理·包法利却成了一个不甚重要的配角。
纳博科夫注意到,小说开头一章是用第一人称“我们”(查理班上同学的口吻)来讲述,但很快便由主观叙述转换为客观叙述(周译本正文第七页开始,叙述人“我们”就消失了),直到结尾都是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叙事。在现代小说中,换用叙事人和叙述人称的手法并不少见,但福楼拜是在读者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叙述转换,这就比较特别。纳博科夫仅仅从叙事结构方面归纳其技巧意义,称之为“柔和的波浪式运动”。但他未能意识到,这种本末倒置的叙事结构所具有的颠覆性意义。小说将次生的爱玛故事作为主题叙事,正是意味着查理所代表的那种从传统社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已黯淡无光,正当行业和一板一眼的正经人不再成为人们的话题,这俨然表明,现实的布尔乔亚生活已被浪漫主义文化所遮蔽。
对于沿循启蒙色彩的浪漫主义,作家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审美态度,借由查理对爱玛的宽容,亦表达了他自己对新思潮的理解之同情。但其中无疑带有悲观主义的审视,爱玛的命运则是他对那种偏离正常生活趣味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楼拜可谓反浪漫派的现代派。
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无关大局的重要人物,就是药剂师郝麦。在永镇这地方,此人算是有头有脸的社会达人。包法利夫妇一来到永镇,郝麦就黏上来了。作为邻居(也算是查理的半个同行),他似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的场合,郝麦都要发表言论,还经常给报纸写文章,他关注时事和科学,属于比较新潮的一路。在纳博科夫看来,这人是一个“成功的庸人”,还是一个“无赖”,因为“他的科学知识来自各种小册子,他的文化修养来自报纸,他的文学趣味低劣得可怕……”纳博科夫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类乡镇知识分子。
关于郝麦这个人物,历来评论者有不同看法。福楼拜的传记作者杰夫里·沃尔(Geoffrey Wall)则是正反两面出击,一方面认为,“郝麦是福楼拜所讽刺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代表了乡镇生活中最强大的散漫力量”“他还是一个滑稽的偏执狂,狡诈的伪君子,江湖骗子,庸医,就像莫里哀或本·琼生笔下的人文,不外乎多了些似是而非的专家的外表”;而另一方面又说,“郝麦代表了他所属阶级的进步,对现代性的追求,还有自身要忍受的历史矛盾……”同时他还提示,郝麦的反教会态度使他转向对科学的信仰,因而成为乡镇知识分子中的空想家(企鹅版《包法利夫人》导读)。
郝麦看上去只是场面上插科打诨的陪衬人物,并非构成故事行动元的角色。爱玛的一切行为,永镇的大小事件,基本上跟他没有关系(只是忽悠矫正畸形足让医生闪了个跟斗)。我所说的“无关大局”,就是这个意思。福楼拜何故在他身上花费那么多笔墨,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样一个并不依附故事主干而存在的形象,活跃在永镇的日常生活中,自然有着映衬效果,照纳博科夫的说法是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庸人风气”。但客观地说,郝麦那些浅薄而与时俱进的思想言行,反映了浪漫主义文化的某个侧面、某些精神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郝麦是爱玛的社会倒影。爱玛是忧郁的,郝麦是快乐的。他们是印刷物開启心智的一代人,爱玛耽于浪漫小说,郝麦却不止是喜欢大众科学读物,杂七杂八的文学作品也浏览过不少。他在本堂神甫面前为文学辩护,枪枪戳到要害,他还劝说查理陪夫人去卢昂城里看戏……走出中世纪的乡镇知识分子一时目迷五色,惘然之中首先抓住的是精神愉悦。郝麦的没心没肺,在爱玛身上体现为冷酷。同样的浪漫主义文化,在郝麦身上呈现为兼收并蓄的杂色,而爱玛却是一心一意追逐自己的目标。
纳博科夫对郝麦这个人物全然否定的看法未免有些偏颇,他没有理解福楼拜设置这样一个人物的真正用意。实际上郝麦是我们从历史和社会角度去认识爱玛的一把钥匙。
爱玛是一个坏女人吗?也许不一定要从现实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女性。波德莱尔就认为“她是一个很崇高的女人”,而且将她视为那个时代的英雄。诗人之言不免有些夸张。
波德莱尔是福楼拜同时代人(两人都生于1821年),他写过一篇《论〈包法利夫人〉》的论文(收入《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其中逐条分析爱玛所具有的“英雄的种种风度”,想象力,行动力,十足的男性品格,擅于享受生活,以及富于追求理想的勇气,等等。他认为,包法利夫人的不幸只是嫁给了一个笨蛋老公,她身处那个狭小的环境,只能以幻想填补心灵空缺,所以将公证处的书记员理想化了,又将穿着猎装坎肩的乡绅当成了司各特小说里的英雄好汉。到头来,她发现自己“就像是麦克白夫人搞上了一个不称意的统帅”,这是她理想失落的根本,亦是悲剧的根源。
波德莱尔是将爱玛视为一种寓言性人物,并不计较其现实的罪愆,这跟纳博科夫和许多论者的评价大相径庭。诗人不难想象那种沉闷而琐屑的乡镇生活(其实他感到巴黎比外省更加忧郁),庸人风气锁闭了一切,任何彷徨犹豫无济于事。福楼拜的故事打开一个奇异的窗口,他瞥见驿车上闪过爱玛的倩影,带着朦胧的目光急急奔向虚无之域,这让他激动不已。作为对比,他明显地发现,永镇的那些男人总是表现为各式各样的无能。

电影《包法利夫人》(1991)剧照
不能说爱玛本身是多么复杂的性格,只是这一形象投射在接受层面产生了过于复杂的意蕴。对于这个通奸女人,波德莱尔不作道德评价,却是肯定了她一心要摆脱平庸人生的正当性。这样来看待爱玛这个人物,是否更接近福楼拜的本意呢?当然,不必在意作者究竟想说什么,关键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什么,是嘲讽中产阶级的空虚无聊,还是表现某种欲求与苦难相偕而来的悲情人生?在波德莱尔看来,人性的追求往往带有自身的污点,也就是叔本华所谓“有罪的无辜者”的意思。对于爱玛的怜悯与同情,或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路。
福楼拜或是以爱玛的道德污点作为一种原罪的隐喻,悲悯是出于同情,宽宥是期待救赎。现代性本身是否携带道德进步,文明与进化如何一再遭遇困境,这是大革命以来困扰法国知识界的大问题。旧制度的崩溃也许是天意所愿,贵族思想家德·迈斯特就是这么想的(如果撇开启蒙主义和共济会的阴谋),他将人心堕落作为每一次进步的报应。在《论法国》(鲁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他对社会变革作出了这样一种反面理解。不过他提出“惩罚以便再生”的观点,无疑是一个有趣的辩证命题。
追寻浪漫主义的原罪,不妨视为更高层次上的现实主义。波德莱尔在一篇谈论雨果作品的文章里表示了这样的感慨:“唉!经过了这么多许诺了如此之久的进步,原罪依然留下了足够的痕迹,让人们看到了它数不清的现实!”(《评〈悲惨世界〉》,收入《波德萊尔美学论文选》)不必介意,福楼拜怀着何种动机将爱玛作为“数不清的现实”中的一例,故事本身并没有标准的解读方案。我想,他既然这么讲述,也许是真的看到了希望的再生。
二0二二年一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