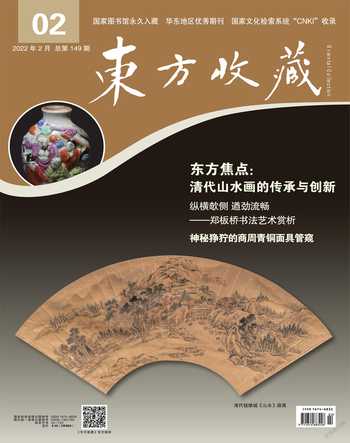汉代铜镜中四神形象设计演变初探
2022-03-29赵治俊

摘要:四神纹是汉代出土的铜镜中较为常见的一类纹饰,不同时期出土的铜镜其纹饰形象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出入。汉代铜镜的四神形象设计演变主要体现在形象、表现形式与设计思想三个方面。早期铜镜中出现的神兽纹饰形象多有变动,直到西汉末才逐渐确立了以龙、虎、凤、龟为主流的四神兽组合。而在形象的呈现上,四神纹饰与汉代铜镜纹饰的整体发展趋势一致,刻画形象由线条勾勒转向图案描摹,更为精致生动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铜镜制作工艺的进步。随着汉末道教思想的衰微,四神镜的设计及其设计思想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主题不再如往日般受欢迎,侧面体现了那一时期社会思想的变革与发展。
关键词:铜镜;四神纹饰;设计演变;道家思想
汉代作为承接秦的统一王朝,是中国铜镜发展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当时社会的繁荣带动了思想与技术上的进步,使得汉代出土的铜镜不仅制作精美且主题多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铜镜的纹饰中存在有大量动物神兽纹的使用现象,这一现象与汉代社会的宗教思想观念影响是息息相关的。纵观铜镜中的动物纹饰,会发现作为早期祭祀的礼器,其背后纹饰所表现的生物并不完全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更多的是神话传说中集合了多种动物特征的幻想生物。这些灵兽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动物,而是由人的想象力幻化而成,富有故事性和情趣性。灵兽中又有一类特定生物的组合形象——四神,曾以不同的样式活跃在汉中后期的铜镜装饰纹饰中,其具体形象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设计演化与文化积淀后,最终形成了如今人们认识中固定的组合概念。
一、四神形象的发展演变
追溯歷史,最早四神形象出现和被运用于军容军列中,成为行军打仗的保护神。《礼记·曲礼上》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那时候是将“四象”分别画在旌旗上,以此来表明前后左右之军阵,借此鼓舞士气,达到战无不胜的目的。虽早有古籍记载,铜镜中出现的四神具体形象却因汉代的社会发展与历史进程有着很大的差异。
龙可以说是中国最悠久、典型的纹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象征。汉代初期因为黄老学说的兴盛,驾龙成仙的思想相当的普及,《史记》中也提及汉高祖母亲刘媪梦见龙和她交配而怀孕生下汉高祖,后来人们普遍把皇帝神话成龙的化身。所以龙的形象之于汉代,是颇有思想渊源与象征意味的。铜镜纹饰中的龙纹表现各有不同,类似甲骨文与金文,可将其分为四种:一状如虫蛇,巨首细尾,无角无足;二状如虫蛇,有角无足;三是兽头蛇身,有足无角;四是足角具备。龙纹在铜镜纹饰中的表现较为丰富,有多种不同的衍生,广义上夔龙纹、蟠螭纹等都可以归为其中。早在新莽东汉时期,龙纹往往就作为铜镜四神形象之一而出现,可以说是四神中较早确立的形象。
虎纹可划分为动物纹的一种。不同于幻兽龙的形象,虎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动物。老虎作为百兽之王,有着其他动物不可比拟的象征地位,秦代调动兵权就已经用到了虎符这一虎形象的器件。在四神中,虎是与龙相对的生物,其二者的地位较高。东汉后期就出土有专门的龙虎纹主题铜镜,因为它经常与龙一起出现,因而也是争议较少的四神形象。
相较于龙纹,凤鸟纹的出现要晚一些,且其数量和种类都比龙纹要少。四神之中的朱雀类似于凤鸟,两者在形象上有一定的区别,但在纹饰中因为表现形式的受限,两者的区别意义不是很大。两者的判定是当鸟纹出现在特定的四神纹中认为是朱雀,其他一般被认为凤鸟。四神之中凤鸟有时会顶替掉原本是玄武的位置,但也经常单独出现。
四神之中玄武的形象是变动最多、确定最晚的,直到东汉后期道教将玄武吸纳为护法神,其存在感才有所改观。在四神形象逐步确立之前,铜镜中的纹饰中往往会出现四神形象不全的情况,且不光是存在的不确定,玄武本身的形象设计也有过一定的出入。玄武一词本指黑色的大龟,但现有的认识中往往有一条蛇盘在龟壳上。在早期出土的铜镜中是有过单个乌龟、单条蛇或者是龟蛇俱在、分而游之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在玄武形象出现以前,龟和蛇是分别具有各自意义的图腾形象,后来逐渐合并为一个意象出现在四神之列。
最后不得不提及另一种神兽——麒麟,是与玄武类似的,其形象的存在于四神组合中往往也不确定。汉镜中独角兽为麟。《礼记·礼运》中也有以“麟、凤、龟、龙”为四灵,而在纹饰中,麒麟往往占据着玄武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麒麟也是四神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后来汉代逐渐发展的趋势是将麒麟归为中间,即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中间麒麟,合称为五灵。五灵的出现表明那个时候阴阳五行说在汉代已经发展完备。古人讲究天地对应,天上所指地上必有之与其对应,而四神与四灵的概念也就是这么划分的,可以说从那时候起四神指代的神兽形象组合就已基本确立。
二、四神纹饰风格的演变
铜镜是中国青铜器文物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门类,因为其精美的背部纹饰与悠久的年代使得它既是贵重的文物,也是艺术性极高的美术品。中国铜镜的历史悠久,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时期的七星几何纹镜,而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制作精美主题鲜明的铜镜出土。在西汉至东汉延续的几百年间,随着社会的发展,铜镜制作工艺的进步,促使四神纹饰的设计也在不断地变化。
汉代早期,四神镜的纹饰以简单的线条勾勒为主,因为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工匠在铜镜背面的装饰上设计的图案不会很复杂,其刻画的纹饰的本质也更接近于符号。李砚祖的《纹样新探》中提到“两汉的四神兽纹样的符号意义最完备,最为典型”。这一时期四神的形象体现更类似于人类历史发展早期所创立的图腾符号。铜镜的刻画多呈现线条化、平面化的特点,属于刻画在不同材料上的图腾崇拜的符号。但铜镜中常多辅以云纹、几何纹饰等装饰填充,完善画面整体和谐的视觉效果的同时,也说明这时候的人们已经有了一定装饰与美化的需求。这时期的铜镜多以简单花纹线条装饰为主,在一个面上通过线条纹来填充空间,简约古朴而又充满了几何规整之美(图1)。
汉中期,即新莽时期和西汉早年,思想宣传的需要与多年来工艺的积累,铜镜装饰纹饰的制作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这时期出土的铜镜背面纹饰图案逐渐有浮雕化的表现,其细节和形态表现更为的细腻,纹饰也更加的立体(图2)。在技术与生产力的加持下,同一面积铜镜纹饰呈现的内容丰富程度直线上升,细节的繁复程度也更胜以往。西汉末年,谶纬学说广泛流行,以阴阳五行说为骨架,附会经义与儒学结合而成的神学体系,对汉代造型艺术的演变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变化呈现在当时的工艺品设计风格上,铜镜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出土的铜镜往往包含了多个道教文化设计形象,例如:仙人、凤鸟、羽人、神兽等,元素复杂繁多,刻画精美。一面铜镜之中既包含了四神形象,又充斥装饰有大量道教文化主题形象、纹样,风格脱离了初期的简约质朴,更为的精巧、细腻,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新莽时期处于西汉与东汉之交,在铜镜的发展历史研究中体现的是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时期的谶纬学说达到顶峰。铜镜也是宣传思想的产物之一,所以羽人、四神、五灵等仙人神兽逐渐成为那个时期铜镜纹饰中常见的图案。时间到了东汉,东汉早期在废制的同时恢复了西汉的政策,社会出现了富庶的景象,因此铜镜制造工艺得到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受到之前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升仙思想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以四神镜为代表的神兽纹饰依然是有相当比重的主题选择,但纹饰风格的发展鲜有提升。到了汉末因为社会的动荡,人民生活贫苦,铜镜的制作也相应的较为粗糙起来。这一时期佛教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富有佛教特色的神兽纹和莲花座纹开始盛行,以四神为主体着重刻画表现道教思想与主题的纹饰镜算是走向了下坡路。在此之后的隋唐铜镜也出现有四神形象的铜镜,不过较之汉代数量占比都是较少数的了。
总体来看,四神镜装饰纹饰的主要变化是由线描状转变为浮雕状。由受限于工艺表现的简单线条到繁荣时期的丰富浮雕刻画,再到战乱时期的粗糙制作以及最后主题的冷落,这是四神纹饰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发展变化导致工艺制作做出的选择。铜镜四神纹饰风格演变的每一步与其所处的历史社会发展环境都是息息相关的,也由此带来了对于汉代四神镜发展演变背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设计思想的思考。
三、四神镜背后社会思想的演变
汉代对于四神形象审美的起步更多地承接前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原始社会对于兽纹的野性审美的同時也结合了汉代特有的美学观念,形成了两汉丰富多彩的四神形象表达。因此四神镜的发展演变与汉代的思想发展息息相关,四神形象对于中国文化也有着深远且特殊的象征意义在其中。
西汉统治阶级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为的是了休养民力,巩固政权,而道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发展也由此开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被道教纳入其神系,作为护卫之神,成为了道教的代表与象征之物。往后的四神镜的繁荣发展,既有对于原始社会兽纹图腾的崇拜与继承,也有西汉初期推行道教思想之功。铜镜一物,虽然脱离了早期高贵礼器的身份,但因其较高的物品身价与精巧的制作工艺要求,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仍占据着很高的地位和价值。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中,镜有驱邪庇护之用,因而有“照妖镜”一说。即便到了现代,也仍有将镜子挂置于门前以作驱邪之用的习俗传承下来。这一方面是道教观念影响下产生惯性思维,另一方面也是镜子这一物件在古代所拥有的高贵象征地位的体现。铜镜这一器物地位远高于一般投入生产生活使用的普通青铜器,也正因为铜镜自诞生便被赋予了种种特殊的作用,在纹饰方面配以四神、仙人等图案,强化它的神学成分,使得它兼具实用和审美价值的同时,也被赋予了驱邪求吉等种种的精神价值。
汉代前有汉武帝为求长生不老寻成仙之道,后有王莽利用阴阳谶纬之说篡权。统治者利用谶纬之学,把社会政治的合理性建立在天、道等哲学和文化基础上。作为占测天道、操作政治、预言国家命运的方术,贯通天人,统自然与社会为一体,构成天人合一的神学世界观。道教的那一套思想吸引了不少人,使四神主题的铜镜也有着相应的发展的空间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无论是吸引人长生不老的仙人方术还是组织民众起义造反的宗教迷信,本质上还是利用道教思想的影响力来达成社会阶级统治的某一目的。汉代各种阴阳谶纬思想落实反映于生活,四神成为了主流思潮道教推广的体现。汉代有流行“青龙白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的吉语,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在风水上总是要强调建筑器皿的规划放置是否能够和这四种神兽相对应。四神镜本身也是一种装饰,当时的人们需要它们为人提供辟邪、镇宅、吉祥、延寿的作用。在两汉历经的数百年中四神镜因为其独特的定位和社会需求经历了诞生、发展与繁荣,而维系着繁荣的背后是道教思想的传播,是符合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控制工具,是民众祈福美好平安愿景的需求。
四神镜的发展因汉代道教的兴盛而成熟完善,也因道教的衰落而平淡。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同一时间佛教影响力扩大,仙学式微而衰弱,四神纹饰主题的铜镜不再受到往日的重视,其出土的主题铜镜数量较之以往减少,四神形象发展也由此定格在了这一阶段。往后随着佛道儒三教的结合,作为仙人思想的延续,汉以后铜镜中出现的四神更多的是表现祥瑞、延寿等美好寓意,并且有了其他被大众认可的形象代替,社会影响力大不如前,而这也是社会发展变迁的结果。在四神形象的发展演化中,最先是因为契合统治阶级需求的神学思想而被吸纳推广,因此繁荣发展,但也因为深度绑定宗教思想,在汉代之后随着社会主流思想的更迭而衰微,最后留存下来的只有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愿景的形象寄托与神秘的图腾宗教意味。
铜镜纹饰是装饰美化目的下诞生的产物,同时也寄托了人们的精神诉求。四神本就是由图腾发展而来的虚拟神兽组合,寄托着对于自然、对于人类本身美好的祝愿。四神镜因为顺应社会思想而诞生、发展、繁荣,也因不再融入主流社会思想而衰微。对于铜镜四神形象设计演变的研究只是管中窥豹,借助于铜镜四神纹样这一小小的窗口窥探汉代社会发展变革的一隅。当然以上对四神纹饰风格演变分析都是通过对比已出土和断代的四神纹铜镜的纹饰分析总结得出的结论,由于相应年代铜镜的出土数量不足,年代较为久远以及可供参考的相关古书典籍较少,铜镜纹饰的研究可能存在断代性、断言性,无法拿出更为严谨和可靠的材料来证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这一问题的研究讨论还需未来更多的文物资料及研究报告来补足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刘梅梅.陕西出土汉代铜镜纹饰及其文化内涵研究[D].西北大学美学硕士论文,2017:P46-47.
2.俞佳丽.汉代铜镜纹饰的当代价值研究[J].铜陵学院学报,2020,19(06):P94-97.
3.车正萍.试论汉代铜镜的纹饰[D].中央民族大学,2004:P25-28.
4.周世荣.中华历代铜镜图鉴[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P45-50,P104
5.鲁同群注评.礼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P99-105.
6.李砚祖.纹样新探.载文艺研究,1992,2:P29.
7.张嫣格.汉代造型艺术中兽纹装饰的审美意味[D].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美学硕士论文,2011:P38-41.
作者简介:
赵治俊,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思维与创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