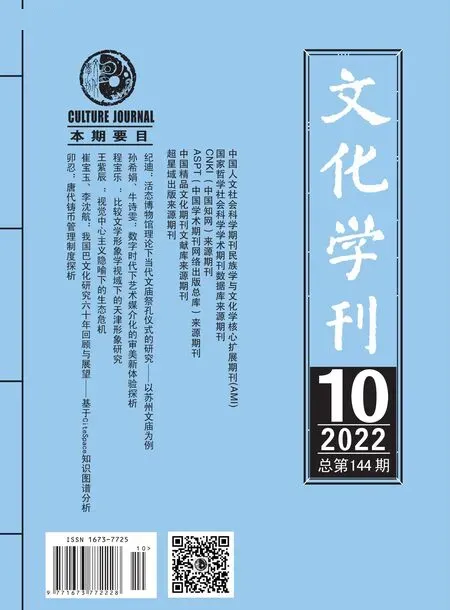略论徐渭之“大写意”
2022-03-23林一圣
林一圣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明文学家、书画家。后人评价其艺术成就多从其画的“大写意”出发,“意”多作神态言。可有他解?
一、论徐渭之“写”
“写”字始见于战国文字,由“宀”“舄”两个部分构成。从宀,义为自此迁移他处,从舄,在说文解字里的含义是“置物也,谓去此注彼也”由此意可引发三种解读,一是清除,二是倾泻,三是复刻。
“写”有清除之义,《广韵》:“除也”。“写”有倾尽之义,《增韵》:“倾也,尽也,输也”,即宣泄之义。“写”的“倾吐”之义被引申为今义的写作创作,这是因为心意是可倾吐的,由衷而成,自心而发,从笔而立,倾吐于他人得以慰藉。“去此注彼”也可解为复制之意。《晋书左思传》曰:“三都赋成,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作“书写”时“写”常作为“誊钞”之意。在书画方面,“写”也重在“临摹”之义,如《史记·秦始皇纪》:“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可见,“写”字多作“钞录”“临摹”之意解。如此看来,“写”可作心声之发微,亦可作拟古之兢兢。那么徐渭的“大写意”的“写”是哪一种含义呢?
“除”可理解为留白,不作,然此不作即作。与徐渭同一风格的八大山人画面中的大片空白就是一种除而不作。除则必有物,有物才可除,“非空”之物皆需除也。那么“空”可视为徐渭的“意”吗?徐渭会将其心中的“空”书写描画出来吗?不然也。
徐谓《自为墓志铭》自云:“余读旁书,自谓别有得于‘首楞严’……”[1]639。《首楞严经》强调被妄相扭曲遮蔽的五感,需逐一破除妄相,才能圆通自得。这里可以认为是大乘般若空宗提到的“内空”,即器官上的空无自性。但显然这与徐渭主“真心”、扬真意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徐渭的诗文仅仅体现其求佛之哲思、追佛之素养,徐渭本身是对佛道修炼的过程抱有疑义的。徐渭《四声猿》中杂剧一种《玉蝉师翠乡一梦》与《首楞严》中阿难遇摩登伽女一节的教义内核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与摩登伽女故事不同的地方是,玉通和尚在色戒之破时毫无援手,而阿难却能道交感应,引来文殊菩萨相助[1]1186。可见徐渭将空门间相互感应的概念抽离了。这一方面难免是徐渭刻意抹除外力强调自我的内心力量的重要性,徐渭根本就不在乎“空”不“空”,故此徐渭不免醒悟道:“若教牢住着,未免堕枯禅”[2]。
故若说徐渭习佛求“空”,其“空”也非佛教要求的以体认空性来复归万寂、最终得以圆脱的“空”,而是不在外不在法、求内而不求外的“空”。
那么道家的“致虚极,守静笃”的无为之举可以是徐渭的“空”吗?徐渭会“坐忘心斋”吗?
徐渭与道家的接触贯穿其人生历程[3]。他曾奢读《庄子内篇》《素问》郭璞《葬书》等颇具道家色彩的著作。晚明之际的士大夫多通融三教,讲究儒释道一体,多求思接古今,性扬万里,总各家思想之精华,为弘扬个性精神而奔走。徐渭崇庄颇深,庄子说自然之情:“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又强调朴素之美:“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而徐渭的“真心”莫不与庄子天然的“真”有异曲同工之处。徐渭一号曰“天池山人”,其《天池号篇为赵君赋》说“予耽庄叟言真诞”,可知其喜好庄子之“真”,取用庄子之真;至于“无为”,徐渭对之所言甚少[1]299。
所以徐渭重在对本心的挖掘,强调性之真我,而不是涉至彼岸抑或虚静无为,其“写意”断不会是留白心意、不宣而明。
至于“复刻”一义,徐渭在《叶子肃诗序》明辨了言与性的关系,认为模仿归模仿,其本性是难以改变的,故创作需“出于己之所自得”,认为人需要发自本性地去创作。可见,徐渭的“大写意”风格,是不会停留在抄录、拟古层面的。
晚明之际,情与理发生激烈的冲突,拟古与革新的双重变奏是为明代后期文学的主题。人本主义一派的士大夫主张高蹈扬厉的个性观念和重民益世的整体意识。“情”表现为对性灵的要求。徐渭主张“真我说”,其“四花赋”之首《牡丹赋》强调个体的主体性:“若吾子所云,将尽遗万物之浓而取其淡朴乎?将人亦倚物之浓淡以为清浊乎?且富贵非浊、贫贱非清、客者皆粗、主则为精,主常皭然而不缁,客亦胡伤乎?随寓而随更”,认为主客有别,主人的精神若是“皭然而不缁”,客人是无法溷浊其党的[1]37。从这里不难推断出徐渭是主张独立,推崇自我真性情的。他在《涉江赋》中宣明他的“真我说”的基本思想:“爰有一物,无罣无碍,在小匪细,在大匪泥,来不知始,往不知驰,得之者成,失之者败,得亦无携,失亦不脱,在方寸间,周天地所[1]35。”他认为人独立于天地,不只是肯定作为群体的“人”的存在,而且还肯定作为个体的人——“真我”的存在。因此,“写”必然是独出心裁,突显真我,直率表露,倾泻心意,一吐为快而已矣。
二、论徐渭之“意”
那么“意”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意”有多重含义,且出入之大莫能同视之也。《礼记·大学疏》记载曰:“总包万虑谓之心,情所意念谓之意”;《康熙字典》认为:“意,音异,志之发也”;《经籍纂诂》:“心无所虑也”,诸如此语;辞海定义“写意”为“通过简练的笔墨,写出物象的形神,表达作者的意境”。“意境”具有超越物象的时空感,“胸罗宇宙,思接千古”,是一种形而上的哲理性的审美感兴。显然,“意”有多重含义,大致分为两个层次:心之内与心之外。心之内则是“情所意念之意”“志之发”等说,心之外则是“意境”“心无所虑”等说。要考察徐渭的“大写意”之“意”是为何物,需结合徐渭作画之风雅、走笔之态势、行文之品趣来理解。
徐渭作墨葡萄,粗笔描墨,潇洒随意,简率纵放,追求的是“不求神似求生韵”以抒发个人的意趣。究其原因,徐渭的《选古今南北剧序》解曰:“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1]1296”《墨葡萄》[4]1表现出的是一派“天机自动”的野逸之美,不啻乎笔墨之纵放,甚至于凌法度之上。对比与其相提并论的重乎清逸的陈淳,其物象如卷狂风,上墨如倾盆,运笔却轻重有秩,细则如龙须垂露,重则如玄武开山。这葡萄也确实耐人寻味,它有着饱满的果实,但藤枝却是枯瘦不堪,如老妪之掌,但却孔武有力。显然,自然生长的葡萄是不存在这样的形态的,徐渭也无心拟其精细,所谓“枝枝叶叶自成排,嫩嫩枯枯向上栽。信手拈来非着意,是晴是雨凭人猜”。对此,谢稚柳先生这样评论:“徐的注意力,集中在情意的豁散,水墨泛滥,舞秀笔如丈八蛇矛,针对形象的描绘,也是一种可意会的神气。”(1)杜永刚.徐渭的写意花鸟[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从绘画史的角度看,徐渭的画面以抽象风格为特点,正式确立了国画大写意的特征。如果说陈淳还保留着物的神态、近乎法度的话,徐渭则是求其韵,画其气,讲究“舍形悦影”,这就不仅在于传神,而更重在画出能表现事物“人性”的一面。
所以从画的角度上来看,徐渭写的不是心之外,而是心之内。其“大写意”不在造境,而在抒发倾泻自我的本心。
徐渭的书法,视则宛如游龙惊鸿,狷狂傲世。笔法恣肆,线条如潜龙舞爪,扭曲盘绕,善用墨断而笔续之法,形成对纸张的强大抓力。最能体现徐渭书法特点之一的作品《墨花卷》[4]18充分展示了徐渭所写之“意”的满与狂。此作笔枯墨竭,却走纸如龙,毫无拖沓之感。字与字的形体之间间隔甚密,突出一种急迫、狂乱之感;且乎横不直贯,纵不厚实,冲破传统书法之法度,打破范型,呈一种涣散激荡之状,充分展现其内心风雨飘摇、孤立无援之感。对比张旭、怀素乱乎法度而又不失节制的狂草,徐渭的“大写意”风格可谓是从画到书,画线为书,书即是画——不再本乎书法之法,不再拘束自己,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狂性”,彰显自我对命运的反扑。谈及丹法,徐渭认为书丹法的关键在于“心”:“自执笔至书功,手也,自书致至书丹法,心也,书原目也,书评口也,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也。”
故考察徐渭之“意”在其书法中的体现,“意”在这里更像是一种苦痛的心灵,发现其笔走偏锋的情况居多,故而字瘦如嶙峋,骨感而无力,给予人一种沉重的痛苦感,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发泄,但字与字的架构又不够厚实,难以抵挡那排山倒海而来的窒息感与软弱感。
徐渭与唐宋派交往甚多[5]。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尖锐的,唐顺之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称复古派所作“本无精光,遂尔销歇”,指出其不足在于无关自我,没有灵魂;茅坤则更进一步,强调文章家不只是要求之于“心源”,还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盖“心源”应与徐渭的“意”可等拟同视之。徐渭一生坎坷,亲故相继离去,本以为能翻身做人的才艺却偏偏不得赏识,八次科举均落第无门。中年得到宪宗赏识,意志风发一回,终于能一展其身手时却遭受连坐,终狂性成灾,杀妻进狱。他一生顾影自怜,赋颂梅花之贞厉,赞叹它“守冷素以自恬”“风颷撼之而不动,瘴疠攻之而罔颠”,对梅花的素和雅却置若罔闻,试观以上所列心绪之烦琐,又何能“心无所虑”呢?
故此,徐渭之“意”不是心之外的“意境”抑或“心无所率”,而是心之内也,“志之发”也。
三、何“大”之有
“写意”之法自古有之,观之小则为技法,观之大则论风格。而时至徐渭,为何就称之为“大写意”?何“大”之有?一说大写意之谓大,“大”用于区分其于兼工兼写的画法,后者是为小写意。或为区分于谢赫“六法”之下的传统画法,凌“六法”之上而入圣。
振叶寻根,自汉以来,美的概念臻于清晰,朝廷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重视文字书写的规范程度和美观效果,故诗书画三绝归一流传致奇,后人争相研习三绝于一体,这就使得文人与作为艺术的书法和绘画开始真正地结缘,始作文人画。文人画提倡“以书入画”,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认为“书画同笔同法”“故工画者多善书”,后有白居易直言:“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到宋代苏轼时真正做到了结合:“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的“枯木竹石”画法有如“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黄庭坚称之“草书三昧之苗裔者欤”,是时称之为“墨戏”,譬同于米芾《潇湘白云图》。后有元赵孟兆页之“须知书画本来同”,又有元杨维桢《图绘宝鉴·序》论:“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至此书画一体,画取其形,以形传神。宽泛地说,早期的中国画都是写意的。《尔雅》:“画,形也”;南朝谢赫所作画界《圣经》《古画品录》最重“气韵生动”。观古而知,写意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形神对应,借写形传神。
徐渭的“大写意”也是写意的一种,所以徐渭的写意就是写形传神吗?不然也[6]。徐渭作《题墨牡丹》:“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多不是此花真面目。盖本窭人,性与梅相宜,至荣华富贵,风若马牛,弗相似也。”可见,徐渭不会为了形去精钩主体的形,即使自己画得并不相像。在他看来,这种行为与刻意迎合富贵差之无几。他往往醉而拟狂图:“知道行家学不来,烂涂蕉叶倒莓苔。凭伊遮盖无盐墨,免传胭脂抹瘿腮”,徐渭不认可恪守“六法”能作佳作,也不囿于传自王维的“破墨”、苏轼一众的“墨戏”文人画的画论,后者强调山水与人的和谐,突出“淡泊之意”。徐渭也在逃避现实,晚明战乱不断,朝廷不问民瘼,兴起于明中的八股文“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徐渭为之忧闷苦痛:“而予顾逡巡庠序中,庶几一飞而屡坠,既乃触网罟,卸去其巾衫,益一意于颓放,时时复从二张游[1]568。”自幼丧父、少年丧母的他从此将儒家作为其生命之中的第一精神支柱,和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能力与价值验证工具。恰值风华正茂的他进入了乡试的考试会场,迎考他一生中永远考不上的秀才考试。他前后共参加了八次乡试,一直考到四十一岁,甚至为之心染狂病而无处寻医,这般泥潭地狱使得徐渭不得不一头闷进酒坛子中:“腊酒此时熟,老夫终岁忧。壶公能醉我,跳入画中休。”(《题雪景画》)他“越觉光景无多,证果不易”。忧贫交加的困境之下的徐渭与众多画家都迈入了晚明一股崇尚怪丑乱奇的“审丑”艺术思潮之中,其崇庄之下的诡怪恢谲、汪洋恣肆的文风是其“本真”的一种最大化行为,徐渭的“大写意”正是“大”在其能突破“六法”之圭臬,打破陈法旧律,画其内心所载,笔纳造化,肖貌天下,禀性三才,拟耳目于本真之性情[7],方得万物之本色,所作之文、所书之言和所画之物无不能大写其灵也。即所谓“解衣槃礴”者“是真画者也”,是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