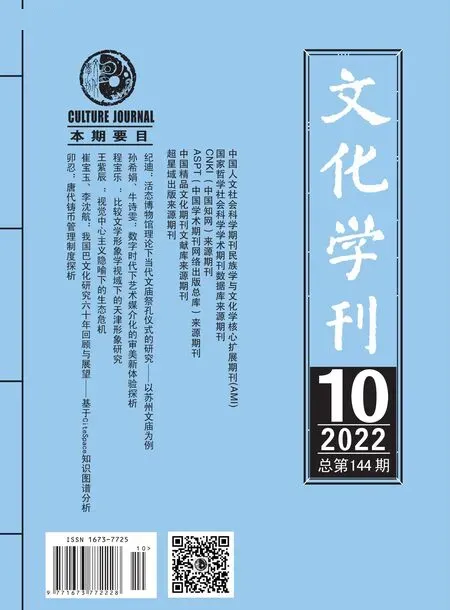论葛水平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克诺西斯”式继承
2022-03-23张林霞
张林霞
诚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批评家们在内心深处是悄悄偏爱着连续性的[1]58,这一点是将葛水平和赵树理两位作家放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联系的基本要素。本文采用布鲁姆的“克诺西斯”重复理论,深度挖掘赵树理与葛水平两位作家的创作联系,探寻当代乡土创作的可行之径。
一、人物结构之“克诺西斯”
由于赵树理与葛水平生活的年代不同,笔下人物的身份差异、思想差异以及行动力的差异较大。比如说,二位作家笔下都是以黄土高原农村的底层群众为主要抒写对象,但是对于底层的阐述明显不同。就赵树理而言,他笔下的底层群众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正的生活贫困者,这类人群的特点是憨厚老实的同时又带着愚昧或者蒙昧,比如福贵;第二种是金旺、兴旺之流,这个人群是赵树理强调过的不同的群体,从经济结构上讲他们属于贫下中农,但是他们飞扬跋扈,欺负邻里。在葛水平的农村底层群体中,女性群体是比较瞩目的,比如《喊山》中的红霞、《甩鞭》中的王引兰。相对于赵树理这一前辈强者诗人(布鲁姆将前辈的优秀作家称为强者诗人),在底层农村群体的选择上留给葛水平的空间比较狭促,将女性群体作为自身创作的关注点或许是一个偶然,葛水平是一位女性作家,她在观察农村各阶层群体时会因为自身的缘故更早地关注到女性。但这一关注的结果是比较可喜的,被辩证地提高到再创造地位的“重复”乃是新人的入门之道[1]60。这一“重复”可以说是成功的,至今为止葛水平创作的小说形象以女性形象最为典型。
赵树理和葛水平的笔下还有一类相似的群体,他们是农村生存环境中的“权力”拥有者,权力分为三类:一为政治权力,常见为村长;二为财富权力,也就是地主和富人;三为暴力持有者,恶霸。福贵就是受制于第二种“权力”的倾轧,一步一步走向了生活的不可解,成为邻里乡亲的“防备对象”。而红霞和王引兰属于第三种权力的迫害对象,苏红则遭受到政治权力的迫害。在对三种权力拥有者的刻画中,赵树理和葛水平较为“钟爱”的选择是暴力持有者,农村恶霸暴力现象在特定的年代是尤为突出的,特别是赵树理生活的社会动荡期,且这三种势力通常会杂糅勾结在一起形成农村权力网,客观意义上这张大网是束缚农村发展的力量,外在的社会动荡和内在的文明缺失共同促成了这张网状权力的形成。“文革”期间赵树理的一桩罪名就是描写中间人物,其实他是在客观呈现农村的斗争,只是因为赵树理本身对农村的情感链接,他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去看待农村的各个阶层。葛水平作为后来者作家,她对暴力权力的抒写是不留余地的,这很明显是因为时代的不同所导致的结果。
总体而言,赵树理笔下的农村群体是全面的、普遍的也是鲜活的,客观地展示出那个时代的农村群像,欢乐与苦痛并存,进步与蒙昧共生。葛水平笔下的农村群体相对是集中的,尤其是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可谓独到,但在普遍性上略显不足,有血、有肉、有理想的男性形象是比较少的。韩冲较为典型但却是作为女性形象光芒之下的男性,这大概是葛水平作为一名后来女性作家对赵树理的“克诺西斯”式重复。
二、主题结构之“克诺西斯”
自从鲁迅开创乡土题材的现代小说以来,农村和农民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笔色彩的饱和度从未下降。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乡土小说家群体,诸如东北流亡作家群中的萧红就是典型作家。赵树理的乡土小说创作与鲁迅、萧红等作家存在明显不同,那么作为与赵树理生长在同一片土地的葛水平,她的小说创作又属于两派中的哪一派?有评论家在论文中提到,鲁迅与赵树理很明显的不同在于自身的定位,鲁迅是将自己放置在农村和农民之上的“唤醒者”,尽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心忧其思想未能开化,也会在祥林嫂死去的除夕夜不能安枕,但他还是明显不同于吃住与农民混在一起的赵树理。鲁迅是精英知识分子,赵树理是农民的儿子。葛水平作为21世纪乡土题材小说家的延续者,属不属于精英知识分子,这一问题只怕是难于去下定论的。但至少葛水平的小说主题仍然是农村和农民,在这一点上同赵树理是相同的,不过具体到这一主题的阐释,两位作家仍然存在明显不同。
赵树理笔下的农村主题呈现出很明显的暖色调,而葛水平笔下的农村主题存在很明显的冷色调,但两位作家的主题内容存在明显一致。细分其主题层次主要有三种,第一层次揭露农民生活状态、展示农村发展现状;第二层次揭露农民思想落后的现实困境。这两个层次的主题是两个作家共有的,也是一致的,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层次的一致性评论家才把两位一前一后的作家放在一起做对比性研究。但这两个层次的主题是众多乡土题材作家的共性,并不能凸显出作为开创了“山药蛋派”的赵树理的个性也不能作为葛水平的创作特性。能够体现赵树理创作主题特色的是第三层次,赵树理的笔下有一批老实本分、生动鲜活又心地善良的农民,他们会受制于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但也善于接受时代进步力量给予他们的教育。这样的农民群像在搬上舞台之后,又起到了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作用,这是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最大特点,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理解“三仙姑”“二诸葛”是怎样“神性”的存在;也能感知金旺、兴旺兄弟是作为一种什么样的势力影响百姓的生活;李有才这样的人物十里八村也是有名气的。赵树理作为农民作家,他对农村的了解是彻骨的,或许鲁迅面对祥林嫂的疑问会给出模糊又清晰的回答,但赵树理面对她时会一眼看穿其内心活动,不得不说赵树理的笔尖上融入了太多对农民的关心和喜爱,但是如此生动的农民必然携带“中间人物”嫌疑,真实的农民是落后的,是蒙昧的,甚至是愚昧的,也是麻木的,甚至有时候是可恨的,但赵树理从来没有抛弃过这片黄土地。如果一定要说赵树理受到的迫害理由,所谓描写中间人物,这个理由是成立的。农民不但是可爱的,也是可怜可恨的,因为他们需要教育和改造,但是这正是文学的本质,也是赵树理的小说可以在精英文学当道的现代小说史上留下自己印迹的根本原因。
反观葛水平,她的小说主题除去以上两个层次之外也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主题,她的笔下总有一些“可怜人”,或遭命运的戏谑,或遭歹人的残害成为孤独的存在者,红霞如此,王引兰也如此,相对比赵树理的“大团圆”式欢庆结局,葛水平的小说更多的是悲凉式结尾。尽管红霞的喊山喊出了生命的力量感,但那只是存在于作者与读者内心的一种发泄,红霞还是红霞,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从未有过一丝改变;尽管王引兰报仇雪恨了,但仍然改变不了自身悲剧的命运和生活;失去女儿的苏红只能以掩耳盗铃的方式继续面对冰冷残酷但却舍不得离开的这个世界。葛水平的小说从来都是悲凉的,她笔下的农村与赵树理温情式的农村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究其缘由,究竟是农村变了还是作家变了?事实上,赵树理在写《小二黑结婚》的时候是有现实原型的,现实中的结局是男主角岳冬至因自由恋爱而被活活打死,但是经过赵树理改编后大部分青年男女受到自由恋爱的鼓舞。据当时数据显示,在案件数量中,离婚案占到了50%以上,在整个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出现一派追求新婚姻、新生活的气象,所以《小二黑结婚》成为了我国婚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赵树理的创作是源于生活的,这个故事是他自己考察到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经过赵树理高于生活的艺术化处理,这一故事带来的现实反响可谓空前。
总体而言,两位作家的主题创作是相似的,都是取材于农村和农民的现实主义创作,也都能展示出作家对农民的关怀和对乡土的眷恋。但是在创作的目的上,或者说创作意图的抉择上两位作家存在明显的分野。这一暖一冷的两种处理其实并不是赵树理与葛水平的区别,事实上赵树理之前或者之后的乡土作家都是采用冷色调的处理方式去面对农村以及农民的水深火热,鲁迅如此,葛水平也是如此,只有赵树理采用了暖阳式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整个黄土地上的农民绽放出憨实满足的笑容,这是他的小说能够在剧院演出场场爆满的根源所在,他让文学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成为百姓前进的行动指南,这一点是葛水平没有做到的,事实上鲁迅也没有做到,带血的馒头一样没有惊醒华老栓之流。至于葛水平为何会有这样后现代的处理原因是复杂的,时代的演进,个体作家的情操和艺术追求,都是原因所在。布鲁姆曾说,一个诗人对不再成为诗人的惧怕也会经常体现为一种视觉病症[1]58。葛水平面对同地域赵树理的创作成就必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感的,但是焦虑带给作家的影响却是因人而异的。笔者认为,在创作主题上葛水平的创作方式明显带有浓厚的后现代和西方小说的特色,加入了模糊处理和人性分辨,这两个主题或许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思想杂糅无意识进行的,又或许是作家有意为之,不管动因如何,葛水平作为赵树理家乡的后起之秀在讲述黄土地上的故事中脱离了“强者诗人”也就是赵树理的影响,至于这种脱离的得与失又是另外一个研究课题。
三、召唤结构之“克诺西斯”
在召唤结构中,赵树理与葛水平的结构模式差异甚大。就葛水平目前创作的小说和散文来说,读者群体较为集中的是学院派,作家的创作也基本上集中于这两种文体;除去小说之外,赵树理的剧本创作也是独具一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和葛水平都有戏剧学习的经历和生活,甚至相较于赵树理而言,葛水平最早考入的是戏剧学校,但是葛水平目前的作品集中于小说和散文。赵树理的小说成就也是瞩目的,但是相对于葛水平的小说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剧场性”特征极为明显,拿《李有才板话》来说,虽然它是一部小说,但是似乎剧场才应该是它的场所,一个张口就来的李有才可比停留在纸上的李有才生动鲜活得多。《小二黑结婚》也是如此,并且它的群众效应是在公演之后才全面取得的。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创始人,如何把这股子“土味儿”做成了现代小说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是有讲究的。赵树理作品的召唤模式是双向性的,精英知识分子把赵树理的作品当作乡土题材去看待,而农民群体把赵树理的作品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是提升自身见识的知识来源渠道,这样双重的召唤读者模式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古代与其类似的有宋代的“话本”和元杂剧,现代小说史上赵树理的召唤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再加上特定的时代背景,自然而然就有了“赵树理方向”。赵树理的作品是真正地取材于农民,服务于农民,他的群众效应并不仅仅是万人空巷,而是农民接受教育的蓝本,这样的作家倒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处。莎士比亚对自己的观众是没有任何要求的,而对于演员颇有微词[2],赵树理对于农民的热爱和帮扶由此可见。
葛水平的召唤模式是较为传统的,迄今为止,葛水平的作品影响力仅限于山西和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学者和知识分子是关注最多的群体,也就是说,葛水平的召唤结构是典型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陈列。诚然,葛水平的作品也被改编成电影,比如作品《喊山》,但是这样的作品却并不是农民喜闻乐见的,作品的悲剧感太强,中国的观众素喜团圆不喜西方社会的悲凉和人性剖析(其实这二者并无高下之分),所以带有典型后现代特色的葛水平的作品在召唤读者上比赵树理少了农民群众的参与。
当然,评价一个作家的体系不因其作品模式的异同论高低,文艺创作本应百花齐放,或许更换了赵树理的作品产生年代也一样不会有当时的反响力,至今也有很多读者对于赵树理的精英文学地位存疑。但是葛水平作为赵树理的后辈作家并没有在赵树理已经获得成功的路线上继续创作,其中原因也是复杂的。现代农民的生活环境不再是几十年前闭塞不堪的状态,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农民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在逐渐增加,手机和电脑的普及也让剧场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葛水平选择不走赵树理的老路也无可厚非。况且目前文坛上的作家创作方向中乡土题材并不多,这也是葛水平能够独树一帜的原因,按照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中所述,后来者作家想要获得超越强者诗人的途径在于能够具备创造性的重复的创作能力,从这一点上看,葛水平的召唤结构是进步的。
四、结语
作为同一片黄土地上的两位作家,赵树理与葛水平有着天然的联系,高原上的风和日丽和雨雪风霜灌溉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几十年前的赵树理作为农民群体中的一员,哀叹农民的不幸,欢呼农村的进步和改革,也同样刻画农民的蒙昧和无知,他笔下的农村是动人的,这源于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21世纪的葛水平循着前辈的足迹又开始进行黄土地上的创作,她的创作自然而然刻上了当下农村的现实问题:思想落后、污言浊行、命运悲凉、人情冷暖,这种种的抒写或许是源于最初的逃离,也或许是逃不开的乡情。有人说,葛水平笔下的乡村是藏污纳垢的,但文学评论家终究只是旁观者,作家在创作的笔端融入的情感是无法完全把控和体会的。
葛水平在作品中彰显了农村生命体的微小与磅礴,这一点是葛水平作品的精华所在,也是不同于赵树理之处,尤其是葛水平对农村女性的抒写别具一格:男权社会的女性,又是农村社会的女性,是底层中的底层的描写。作为赵树理的同乡后辈,葛水平内心存在布鲁姆所说的焦虑是必然的,但就葛水平目前的作品来说,其并未表现出雷同甚至过多的相似之处,这对于评论家来说是一件失望的事,但对于文学本身而言却是一件幸事。
春耕秋收,星沉月落,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于去罄竹抒写这片黄土地上的人和事,好在时光更迭,天地混然,两位作家作为黄土地的儿女对它的心灵寄托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