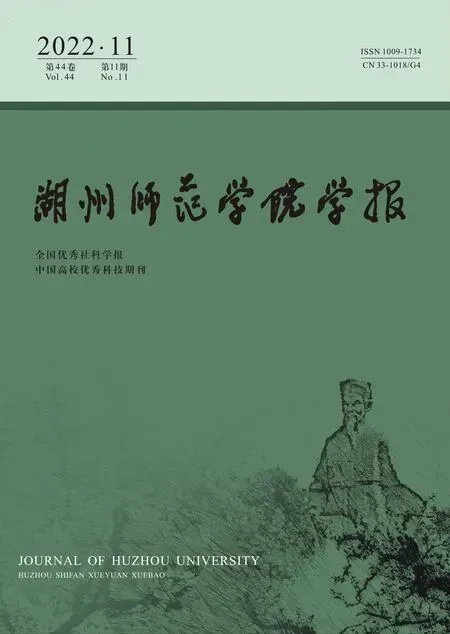“一锅粥”的固化:从数量名组合到独立成词*
2022-03-23鲍若倩
王 刚,陈 莉,鲍若倩
(1.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2.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3.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一、引言
数量结构在汉语中具有类型学的意义,在实际的使用中,其功能、性质会发生诸多变化。其中越是高频使用的结构,发生变化的概率越高,变化的形式也越多样,“一量名”就是这种高频使用的结构。从其线性组合来看,基本功能是表示数量,但是从现代汉语共时层面来看,这一结构已经有了更多的功能和意义。学界诸多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一结构,储泽祥等[1]77-80[2]1-7[3]71-77分别研究了“一个人”“一条龙”“一条心”的固化过程,曾常红[4]42-46分析了“一口气”的词汇化及其相关问题,王志英等[5]107-111探讨了“一根筋”的相关问题,郭瑜[6]157-159分析了“一阵风”的词汇化及其语用特点。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一量名”结构在演化中虽然具有一些共同的轨迹和机制,但是由于各自部件的不同,不同的具体结构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若要全面深入地分析“一量名”结构的演变,对其展开充分的个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一锅粥”为具体研究对象,探讨该构式的固化过程。“一锅粥”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有以下几种用法:
例1: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实实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接我们。(杨绛《我们仨》)
例2: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王安忆《长恨歌》)
例3:就因为这哥俩拼命地干活,所以家里乱成了一锅粥。(王小波《黑铁时代》)
例4:谭功达的心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格非《江南三部曲》)
例1中的“一锅粥”很明显指的是由米等粮食煮成的稠糊的食物;例2中的“一锅粥”已有所虚化,不再是其本义,而是“一锅粥”的比喻用法,可理解成“浓稠粘密”之意;例3、例4中的“一锅粥”本义已完全消失,结构也已经固化,表示“一团糟,极其混乱”。
固化(hard-wired)是指“两个或几个紧挨在一起的语言单位,由于频繁使用而化为一个相对稳固的、整体性的语言单位”[7]23。我们可以采用替换或添加修饰成分的方法来检验数量名结构“一锅粥”是否固化。如例1中的“一锅粥”不仅数词“一”可以被替换为“二”“三”“四”等数词,名词“粥”之前也还可以添加修饰成分,如“热”“白米”等;且替换和修饰后,句子仍然能够成立,其基本意义没有发生改变。故例1中的“一锅粥”属于可拆分的数量名短语。例2中的“一锅粥”,虽然数词“一”可以被替换,但是替换后无法再表达“灯光如豆一点一点,微弱却稠密”的意思,且名词“粥”之前已不可再插入其他修饰成分,由此可知例2的“一锅粥”已发生一定程度的固化。例3、例4中的“一锅粥”,“一”既不能用别的数词替换,“粥”前也不能添加修饰成分,说明数词、量词、名词三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已经稳固,形成了一个整体,此时的“一锅粥”可以被认定为完全固化,其意义为“混乱”。
二、“一锅粥”的固化过程
某一语法结构在其演化过程中,语义、功能的改变总会有某些诱发因素,语法形式的变化往往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从语料来看,“一锅粥”经历了无标记到有标记再到无标记的形式演化过程。
(一)作为数量名短语的“一锅粥”
“一锅粥”作为数量名短语出现时间较早。例如:
例5:里谚云:“上乡熟,不抵下乡一锅粥 。”(苏轼《苏轼集·集藏》)
例6:还有一些狡猾的租户,将米伴着水,或是洒盐卤,或是熬一锅粥汤,再洒上些粗糠,拌入米中,便称“糠拌粥”了。(陆人龙《三刻拍案惊奇》)
例7:鲁智深大骂道:“你这几个老和尚简直没道理!只说了三日没饭吃,如今却见煮好一锅粥。既已是出家人,又为什么扯谎?”(施耐庵《水浒传》)
“一锅粥”的数量名结构用法是汉语的基本规则,这是一种无标记用法。虽然我们找到的例句较早见于宋代苏轼引用的里谚(即民间谚语),但是根据规则可以推知,这种用法或许在时间上还会早于此。通过例6中的“一锅粥汤”也可知,这时的“锅”虽然是借用量词,但是“一锅粥/汤/粥汤”等的用法是一种规则用法,“锅”常常被借来用作粥/汤/粥汤等的量词。
(二)带有辅助手段的“一锅粥”
1.与比喻词同现
由于具有很强的形象性,“一锅粥”在使用中自然发展出了比喻用法,使用时往往会有表“比况”的比喻词伴随使用,例如:
例8:消息很快传到建湖厂里,上上下下的议论像是煮开了一锅粥。(1996年《人民日报》)
例9:在方形大厅里,是乱糟糟挤来挤去像一锅粥似的人群。(莫泊桑《死恋》)
例10:灯光如豆般一点一点,尽管有些微弱,却很是稠密,一锅粥似的。(王安忆《长恨歌》)
2.与引号同现
引号在“一锅粥”意义引申过程中具有显化标示作用。“一锅粥”从原义向比喻义、“混乱”义发展的过程,是逐渐变化的过程。人们使用和接受“混乱”义的“一锅粥”,也有个逐渐认可和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书面上常用引号来标明“一锅粥”不同于原义的特殊含义。例如:
例11:马威看着李子荣,大眼睛里发出点真笑:“你这几天干什么玩呢?”
“我?穷忙‘一锅粥’!”(老舍《二马》)
例12:眼下,伊拉克可以说是混乱不堪,犹如“一锅粥”。(新华社2003年11月新闻报道)
以上例8—例12中,“一锅粥”所指意义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表层的指称意义,而是转喻意义。只是在这个阶段,这种转喻意义还有比喻词、引号同现作为辅助。
(三)单独出现的固化结构“一锅粥”
在高频使用过程中,即使没有明显的比喻词出现,“一锅粥”也具有了独立的转喻意义,固化为表“混乱”义结构,例如:
例13:意思是偌大的一个哈尔滨,找不出书记和市长了,让美国人和日本人来当,搅成了一锅粥。(郑笑枫《天鹅展翅》)
例14:一件事又扯出来八件事,有件事又撞到了姜龙老婆头上,姜龙老婆也加入进来,全家吵成了一锅粥。(刘震云《一句顶万句》)
例15:我岳父家的邻居们吵成一锅粥。(莫言《蛙》)
例13—例15三个例句中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比喻词,构式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是,这里的“一锅粥”常常与“吵成”“乱成”“打成”等词语搭配使用,这些词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表示比喻的标记成分。“一锅粥”的演化还可以朝着更为无标记的方向发展。
例16:共享单车一锅粥。(虎嗅网:https://www.huxiu.com/article/172495.html)
例16中的“一锅粥”已经完全无标记化,已经高度固化了。
需要说明的是,从历时语料来看,(二)(三)两种用法并不能截然分开,中间的时间链条并非如文中描述的这般清晰明确;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一锅粥”已经出现了无标记用法,在共时层面的实际语料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标记用法。但是,这并不妨碍本文对该演化过程的描述。沈家煊[8]91-92在讨论“逻辑先后”和“历史先后”时曾经提出,共时的理论分析并不因历史事实不符合而被推翻,一方面,共时研究提出的假设除了充分的共时证据和合乎逻辑的论证,最好也有历史材料的佐证;另一方面,共时研究提出的假设并不因为缺乏历史材料的佐证或者与历史材料相悖而被推翻。
三、构件意义演化
“一锅粥”能固化且固化后具有“混乱”义,与人们对“锅”和“粥”的认知相关。这种认知引起相应的联想,使得“一锅粥”具有了隐喻性且指向清晰,因此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并最终固化下来。
“锅”和“粥”都为普通的名词。锅作为一种炊事用具的使用历史悠久,其可用于对食物进行烹、煮、煎、炸、炒等多种熟制工作,是中国人生活的必需品,自然被看作是盛装食物的容器。例如:
例17:收取好了的稻谷背到部落酋长或村长的家中,先用锅炒,炒完后由年轻姑娘用手碓舂。(宋思常《中国少数民族宗教》)
例18:逢做饭她就听女主人抱怨燃气灶冒烟,把亮亮的锅熏得黑灰。(尚绍华《悄然寻找另一个天空》)
“锅”不仅作名词,也作了量词。例如:
例19:南大洋已解冻,海洋中浮游生物大量繁殖,鱼类和磷虾特别多,南大洋如同一锅营养汤。(马天白《黑仔到南极》)
但是“锅”在一些句子中,其词性变得模糊,发生了变化。例如:
例20: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这样便把新生事物的悲剧与英雄悲剧画上等号,就无异于是将萝卜与青菜一锅煮了。(徐岱《艺术文化论》)
例21:姬得旺这遭遇,一锅端,全给透露出来了。(董富强《冰河溯行图》)
例22:变文不是所有敦煌讲唱文学的共名,尽管专治敦煌文学的学者十分清楚,但一些基础性的文学史著作却把这些文学体裁“稀里糊涂地一锅烩了”。(曹俊杰《论敦煌变文的通俗化特征》)
以上例句中的“一锅煮”“一锅端”“一锅烩”,在数词“一”后的“锅”的量词性已大大弱化,其表达的意思不再是“炊具”,而是延伸出“全部”“一起”的意思;且大都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事物被混乱放置在一起”这样的语境中。
“粥”的意义延伸,主要是由“粥”本身的状态引起的。“粥”也称“糜”,是一种由稻米、小米或玉米豆类等粮食煮成的稠糊食物。可见“粥”是一种混合物,并且具有“粘稠”“糊状”的特征。“粥”在人们的日常食物中频繁出现,具有“使用频率高、民众熟悉度高、特征明确”的特点,这就为其比喻义的产生奠定了使用基础。人们拿“粥”来作比况,形容“黏糊”“浓稠”状。例如:
例23:不下雨的时候那泥浆就好像是粥一样。(萧红《呼兰河传》)
例24:贵阳市上的细泥那浓度比小贩子卖的糖粥还要浓。(游子《贵州观感》)
周安[9]64认为,固化“一量名”结构对于构件量词和名词的选择,显然不是随意随机的,除却民族心理、文化选择等语言外部因素的制约,“一量名”内部语义匹配机制可能在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理解最终是“一锅粥”固化下来,而非“一份粥”“一碗粥”或“一锅饭”“一锅汤”等。“锅”和“粥”在这一固化结构中有着不可替代性,其本身的意义延伸使得“一锅粥”有了隐喻性,进而承载起了“混乱”的意义。
四、“一锅粥”固化前后功能演变
“一锅粥”固化前后在句法功能、语义特征、语用功能上均有变化。未固化的“一锅粥”可以用别的数词替换并插入新的修饰成分,其语义功能主要是计量和指称;固化后的“一锅粥”语义发生变化,主要表示“情况混乱,不好解决”,并且结构固定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也不可随意更改其中的部件。
(一)主语功能丧失,只能充当宾语
未固化的“一锅粥”是常见的数量名结构,属于名词性短语,在句中多充当主语或宾语,且语义关系为“述语+受事”。例如:
例25:一锅粥吃一天,菜都懒得炒,一个人太凑合,废了。(百度贴吧:https://tieba.baidu.com/p/7575023776)
例26:紧紧地攥着这张来之不易的票子,她想出去弄点杂合面来,好能煮上一锅粥。(老舍《骆驼祥子》)
固化后的“一锅粥”具有“混乱”义,在句中已经丧失了做主语的功能,只能做宾语。
例27:我心里都快乱成一锅粥啦!(王树元《杜鹃山》)
例28:等形势发展到了鼓动知青下乡的年岁,陈明家就乱成了一锅粥。(杨镰《青春只有一次》)
(二)指称义消失,隐喻义凸显
固化后的“一锅粥”凝固成一个整体,不再表示计量和指称,在语义上表示“情况混乱”。常与一些动词搭配,例如“乱”“打”“搅”“吵”等,该类动词本身也具有“场面失控才会发生”的特点,并且动词之后一般须有“成”“作”等词衔接才可以搭配使用。例如:
例29:只有张春和平时不同,非要和刘长水比赛不可,把班务会搅了个一锅粥;他说:“我和刘长水比赛抱炸药!”。(郭光《仅仅是开始》)
例30:儿媳妇和小姑子打成了一锅粥,兄弟跟兄弟也红了眼。(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一锅粥”在这两个句子中已经不具有实在的指称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处于宾语位置,但是其语义并非典型的受事或者成事,而是具有一种较为明显的描述义。故从语义角色上来看,这些句子里的“一锅粥”更像是补语,而非宾语。
(三)语用功能凸显,客观性减弱,主观性增强
如果说语篇环境、句法环境是促使构式固化的语言因素的话,那么言者主观性的凸显、言者对修辞效果的追求则可以看作是促使构式固化的交际主体因素。“一锅粥”固化以前,这些因素促使其固化,“一锅粥”固化以后,其中的修辞效果和主观性更加凸显。
1.增强日常表达的形象性、简洁性
Hopper & Traugott[10]98从语用的角度指出,在词语“语法化”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省力原则”导致的词语“固化”或者“成语化”。一般情况下,越是复杂的意义越需要复杂的语言形式,但是这些复杂的语言形式会增加交际的负担,而减轻这些负担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将这些意义整合起来打包在一个相对简化的语言形式里面。日常生活中要表达情况“混乱”的意思的词语有乱七八糟、混乱无序、七零八落等,但是这些词语虽然能够表现出混乱之意,却不能达到受话人“脑现其状、身临其境”的效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还可以极尽描写之能事,将混乱的场景一一描写清楚,但是这样又耗费很多精力。与“一锅粥”相比,这些表达形式的精炼和形象程度就略显逊色。使用“一锅粥”更容易使听话者在捕捉到有效信息的同时又增强了语言表现力,而且“一锅粥”的使用也让话语更简洁清晰,例如:
例31:而房外,则是一片沉重的涛声,这种声音带着湿透了的雪花的重量——水在搅着雪,雪又在搅着水,最后搅成了一锅粥。(王小波《青铜时代》)
例31描写“水在搅着雪,雪又在搅着水”的情景,水、雪交融的样子通过“一锅粥”的说法立刻就明白、形象起来。
例32:谭功达挨着她蹲了下来,问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汤碧云笑了笑道:“别提了,简直是一锅粥!”(格非《江南三部曲》)
例32言者在被问到现状的时候,心中有很多苦楚,却没有细说,只用“一锅粥”来进行总括式表达。提问者听到这样的言辞时也必能体会其中的心酸,可谓是“一言足以道尽人间万事”,足见“一锅粥”的经济性。
2.凸显言者主观性
沈家煊[11]268提出,语言的主观性是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明显的自我印记。主观化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语言使用产生影响:说话人的认识、说话人的视角和说话人的情感。固化后的“一锅粥”就是说话人为了突显主观情态而采取的一种表达方式,这里的主观情态主要是对当前事件的一种评价,这种评价就是说话人的一种认识。说话人用“一锅粥”来形容事件,就是为了突显情况的“糟”和“混乱”。例如:
例33:工地上到处都是蚂蚁一样的筑路大军,他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简直乱成了一锅粥。(格非《江南三部曲》)
例34:一件事又扯出来八件事,有件事又撞到了姜龙老婆头上,姜龙老婆也加入进来,全家吵成了一锅粥。(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例33中“筑路大军”赶过来的场面相当混乱,说话人对此情景进行评价,采用的语言形式就是“一锅粥”,这是说话人认识的表示形式。例34也是如此,说话人用“一锅粥”表示对“全家吵架”的一种评价。在这些例子中,说话人首先观察到一种情景和现象,然后在自己的词库中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一锅粥,对其进行描述和评价,这种描述和评价都是基于说话人自己的视角,是说话人观察客观世界的一种角度,是说话人主观性的一种体现。
五、结语与余论
从历时角度来看,“一锅粥”经历了从组合义到构式义的演化过程,其意义透明度由高到低,其功能也逐渐从指称为主到描述为主,其性质也由松散的短语结构演变为凝固的词语。
需要说明的是,“一锅粥”的固化并不意味着组合义的结构就消失了。在现代汉语中,“一锅粥”仍存在数量名结构和固化结构两种用法,它们在意义上有明显的差别,在语用功能上也是不同的。固化的“一锅粥”常用来表达说话人主观的负面评价,并且仍然受到其本义的影响,主要用来突显复杂混乱的场面或情况。另外,固化的结果通常意味着新词语的产生,而语言单位在固化后通常也会产生区别于固化前的、新的语法功能。可以说,这两者是相互伴随着发生的。尽管“一锅粥”的本原意义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固化形式出现的环境,但事实是“一锅粥”在语言表达主观性作用下,通过隐喻和引申具有了“混乱”的意义,产生了新的语用价值,已成为一个新词,并且已经被收入了权威词典[12]1534。
“一量名”形式的三音节结构在现代汉语中有很多,如前人时贤已经研究过的“一条龙”“一条心”“一窝蜂”“一阵风”“一根筋”“一个人”“一口气”等,这些结构(词)各有特点,对其开展个案研究固然必要。而如何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其展开类型研究,找出其中的共性,做出统摄性的总结,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