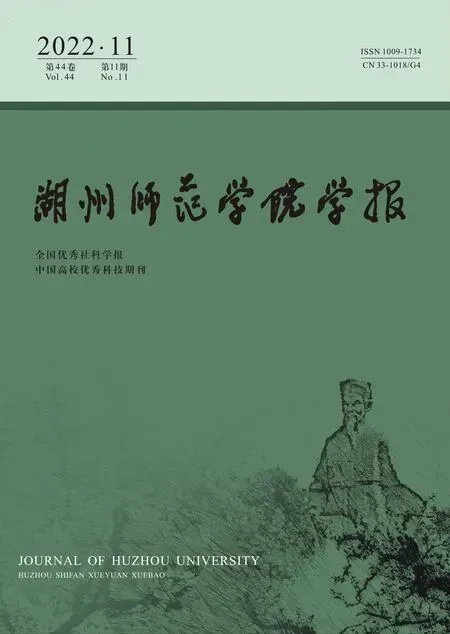人类的“心理寓言”*
——卡夫卡《审判》中“法”与“罪”的心理学哲学分析
2022-03-23吴珊珊
吴珊珊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是19至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之一,他在《审判》(TheTrial)中通过K荒凉的生命体验隐喻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K处在失衡的世界中,他的生命缺乏聚合的向心力,他并不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和应然的状态。卡夫卡不遗余力地将K内在心理世界以表象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K仿佛是突然间被抛掷在秩序性经验的裂缝中,其过往的生命体验被悬隔,各种离心力拉扯着他,使他不断地陷入突如其来的欲望场域中,读者从而能够近乎惊悚地体验到K的无力感。事实上,K的这种体验症候仍然隐匿地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中,而卡夫卡或许隐晦地为我们提供了直面这种存在的可能的解放方式。
一、K的心理迷宫
卡夫卡在关于K的审判叙事中交织地使用了两种时间维度,一种是外感知经验世界中具体出现的时间,另一种是K的内感知时间,即K的心理时间。卡夫卡废除了经验世界中时间的线性逻辑,外在的时间往往以碎片的方式在场,且每一个具体的时刻之间并无必然关联,而内在的心理时间则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在场,后者裹挟着前者。卡夫卡暗示K的审判存在于K的内感知时间意识中,一切与审判相关的时间都源于K自我的确认。他这样叙述K的初审时间状态:K接到审判电话通知“下星期天对他的案子进行简短的审理 ,……审判人员认为他会欣然接受这个时间,如果他希望改在别的时间进行,他们也会尽可能地应允他的要求,比如说,审讯可以安排在夜间进行”[1]27。K得到通知后,“没有回答便把电话挂了,他马上决定星期天去参加审讯”[1]27。这时候他身后的经理突然询问他是否有兴趣星期天上午乘帆船出去玩。K拒绝了经理的邀请后,想到“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去某个地方,却忘了告诉我什么时候去。……最好是星期天早上九点去那个地方”[1]27。读者既无法知晓K是在这个周末还是下个周末前往审讯室,也不知道对方是否知晓K关掉电话后作出的“周日九点钟前往审讯室”的决定。卡夫卡没有告诉我们K在哪一个时刻出发,而是模糊地指出K在前往审讯室时,他的时间最初看起来“似乎很充裕”,在走了“很久”之后忽然间“九点就到了”,“K又走了很久才走到那栋房子”[1]29。
卡夫卡不仅破坏了叙事时间的恒定秩序,同时也摧毁了K所处空间的稳定性。相较两种时间维度的叙述,他对K所处空间的叙述更为复杂。人类的日常生活必然是在外在的经验性空间中展开,在这一空间中人有属己的私人领域和共享的公共领域,与这种外部世界相对的是人的心理世界,外在空间的生活经验被映射在他们的心理世界中。但卡夫卡在《审判》中几乎消解了这三种空间的边界,他既取消了K外在经验世界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取消了外经验世界和内感知世界的界限。卡夫卡将这所有的空间揉成一团直接递交给读者,所以K身处的空间犹如一座迷宫,这座迷宫既丧失了稳定且清晰的边界秩序,而且整体构造扑朔迷离晦暗不明。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一天早晨当自己还躺在床上的时候,一个陌生男人进入自己的房间并宣布逮捕信息,也无法想象被告人直接生活在律师的家中,但这种私人空间被公共空间熔断且合而为一的情景出现在了K的世界里[2]43。法庭本是公共空间中的机构,但在K所处世界中,法庭所在的空间被分解成无数微小的部分粘连在K的日常生活空间中:K办公室楼下的废品储存室是法庭打手惩罚看守的场所;K求助的法庭画家告诉他,每一栋房子的阁楼上都有法庭办公室,而他的画室也是法庭办公室的一部分,那么K居所的屋顶阁楼也必然存在着类似的法庭办公室。即使是传统稳定的空间边界——窗户,在《审判》中也变得模棱两可。窗户在卡夫卡的文本中,一方面是通向外部世界的空间隐喻,另一方面,窗户的观看视角被颠倒,这一视角不再是自内向外的空间视角,而是一种自外向内的空间视角:K并非通过窗户观看外界,而是透过窗户被外界观看[3]34。
K被宣布逮捕的那一刻,他的生活只剩下审判。审判K的法庭所在的空间与K的日常生活空间之间没有任何区隔,这一事实足以使读者感到悚然和恐惧,但K本人对此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诧,他以一种平静的态度默认了事实的冷酷状态[4]179。从表面上来看,K的审判并没有显现出对他正常生活的影响,但从深层的逻辑上来看,K正是在这一“事件”出现之后,逐渐意识到空间的不安。卡夫卡以一种隐晦地方式指出K掌控着前往法庭机构的路径以及时机,法庭出现在K“想到”或者“意识到”的任意地方。卡夫卡在描述K第一次前往法庭审讯室时写道:K走了很久才到“那栋房子”,“这是一幢大得出奇的建筑,…… K转身走向楼梯,打算去审讯室。但他又站住了,因为除了这条楼梯,院子里还有三条楼梯,另外在院子的尽头还有一条窄窄的过道似乎通向另一个院子,他很生气,通知审讯的人竟然不告诉他审讯室的确切位置。……他终于登上那条楼梯,心里想着那个叫作威勒姆(Willem)的看守告诉他的话:法庭总是被罪所吸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审讯室应该就在K偶然选中的楼梯上的房间里”[1]30。
卡夫卡文本的神秘悖论在于:他越是扭曲和分割K所处世界的时空,这个世界的真实状态就越是清晰地显现出来。K的审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发生在其内感知世界中的审判,卡夫卡不遗余力地将他的内感知世界视觉化,使之成为一场“景观式”的审判[5]20。这场审判不仅仅是K个人可见的心理过程,同时读者也几乎毫无阻碍地全程介入了这一过程,这一叙述视角的转化受到了哲学家布伦塔诺的影响。(1)关于卡夫卡与布伦塔诺思想关联性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 Barry Smith, “Brentano and Kafka”, Axiomathes 8 (1), 1997, pp.83-104.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指出心理现象是意向的存在(Intentional existence),他在一些文本中也使用“意向的非实存”(Intentional in-existence)这一指称,“in”并非表达否定,而表达了一种“定位”,它表示这一现象存在于行动者的心理中。同时,K心理现象的意向对象也指涉了他的外感知经验世界。传统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清晰地界定了行动者在经验世界中的实践,以及伴随着其实践过程的心理状态,虽然读者可以通过“上帝视角”同时阅读到行动者的这两种状态,但是在叙述过程中它们具有清晰的边界。卡夫卡的文学实验颠覆了传统文本的叙述视角,模糊了这两种视角的边界,完全打乱和破坏了稳定的时间和空间秩序。他向读者展现了K整体的、不稳定的内感知心理世界,以及这一世界的心理意向来源。卡夫卡正是通过K荒凉的心理世界隐晦地叙述了现代社会官僚机制的运作,以及在这一机制中以K为代表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二、欲望场域中的K
K所处的世界丧失了古典世界的关于“整全性”的教诲,人所朝向的目的被悬隔,且放弃了对其本真状态的追寻[6]44。人的理想遗失了,K被困在各种碎片化的物理事件中;他身处的世界也背离了其本真状态,现实中的一切都仿佛被安排在错置的齿轮上,法庭机构从未显现法的正义,律师未承担过辩护的职责,画家也从未专注于绘画本身。人类的情感丧失了经验的内核,读者很容易便注意到K的叔叔对K的审判唯一的关注点是K需要摆脱审判避免破坏家族形象。善从未显现在K的心理世界中,显现的不过是善的匮乏。K的审判也绝非是仅属于他的个人生命体验,卡夫卡先于萨特和加缪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无力感和荒谬感。
卡夫卡的文本倾向于悬隔主人公以往个体性的生命体验,他们几乎是突然间进入到某种奇异的生命境遇中。除了主人公的名字,读者对他们一无所知,卡夫卡也正是通过模糊的名字将主人公隐喻为整体人类的代表,《审判》中的约瑟夫·K就指涉了圣经人物。卡夫卡暗示人的本真状态绝非是一种外界定义的社会身份,在他的很多文本中,不论是《城堡》(TheCastle)中的K、《变形计》(TheMetamorphosis)中的格里高尔(Georg),还是《审判》中的K,他们虽然具有明确的社会身份——土地测量员、推销员或者是银行高级职员,但是这些明确的社会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们知晓自我的真实存在。K在半夜来到城堡管辖的村庄,却不具有进入城堡的合法性,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进入城堡的身份,K需要证实的难道真的只是土地测量员这一身份吗?格里高尔在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害虫,他不仅丧失了自己属人的状态,同时也丧失了一切与人类沟通的渠道;K在一天早晨被宣告逮捕,他当下能够找到的自我证明材料不过是自行车执照和出生证,这些物理材料真的可以说明K的清白吗?
读者无法知晓K面临审判之前的生命经验,仿佛他这一生都在等待着这场审判。《审判》中的K与《失踪者》(TheManwhoDisappeared)中的卡尔·罗斯曼(Karl Roßmann)以及《城堡》 中的K不同,他既不是旅人也并非异乡人,他是一位在社会中已经获得成功并且具有野心的公民。但他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他们的“近亲”,他不过是在自己的“家乡”流浪,他奔波在各种审判的场所,看似追逐着一种确定性的审判结果,但实际上却不断陷入与审判无关的欲望境遇中。K在审判的初期缺乏一种关于自我生命的整全视野,也无法想象超越法庭审判之上的人的本真生命和法的状态。他的欲望隐喻了其身处世界的“欲望悖论”:欲望本是属人的、朝向某一目的或对象的欲望,但K的欲望行为之间却是断裂的,欲望对象是无目的和瞬间的。卡夫卡以近乎冷酷的笔调描绘了人类最本能的欲望,颠覆了传统文学中脉脉温情式的关于爱情的书写,并且“性”在其文本中具有强烈的荒诞意味。
卡夫卡告诉读者,K遭遇突如其来的审判的那个清晨,他还只是知晓自己有一位名为毕斯特纳(Fräulein Bürstner )的邻居,他们之间除了相互问候,并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在同一天的晚上,K向毕斯特纳小姐叙述他被逮捕的情形时,却马上陷入了对她狂热的爱恋中,“K说着跑进前厅,抱住她吻了吻她的嘴,接着又吻遍了她的脸,就像一头饥渴的野兽贪婪着喝着它终于找到的泉水”[1]26。卡夫卡用令人震惊的平静笔触指出这种欲望缺乏任何生命的内核,他写道:当K准备向毕斯特纳小姐告别时,他想“叫一声毕斯特纳小姐的名字,但却又不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1]26。而毕斯特纳小姐呢,“她疲倦地点点头,侧着身子转向了另一边,任凭他吻自己的手,仿佛对此毫无感觉”[1]26。
K在审判伊始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迷茫而支离的情绪体验,他完全被动地求助于他者,试图以此获得自己下一步应有的行动,这种求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逃避,逃避走向追寻真正的法的行动中。他毫无头绪并且缺乏接纳一切的能力,也缺乏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于是欲望成了临时的避难所,K在一次次向他者求助的过程中不断地陷入各种“性”的欲望场域中。他在初审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位误闯到审讯室的洗衣妇,在接下来自我辩护的过程中更将注意力集中到她被一个男人拽到门边的角落紧紧地搂着这一事件上。K在第二次前往审讯室时再次遇到了这个女人,他们之间关于法庭的讨论突然毫无征兆地陷入欲望的行为中,“K情不自禁地想要抓住她的手,但却抓了个空。那女人真真切切的对他产生了诱惑力,他思来想去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屈服于这种诱惑”[1]45。
卡夫卡笔下的欲望与“思”对立,是一种反本真的身体体验,这种体验不具有任何情感经验的内容。行动者和欲望的位置被倒置了,欲望成了一种外在于行动者的神秘力量,这股力量取代了行动者K的主体位置,将K和一切进入欲望场域的人作为其作用的对象,使得他们在当下的瞬间迸发了本能的情绪,却在下一个瞬间毫无留恋地分离。欲望的状态是漂浮的,它从一个对象滑向另一个对象。对于K而言,欲望推动他产生联系的女性并非唯一的,她可以是毕斯特纳小姐,可以是洗衣妇,可以是律师的助理,在卡夫卡的笔下她们唯一相似的地方在于她们的面容都是模糊的;而对于这些女性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当K和洗衣妇的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之前在审讯室里搂着这个女人的大学生出现了,他和K争夺她并带走了她,“那女人朝K挥了挥手,并耸了耸肩,暗示K她本人在这场劫持中是无辜的,但也无意于反抗”[1]47。K尝试通过欲望的关系阻断审判过程中产生的无力感,但是这一尝试是徒劳的。丧失了情感经验的欲望无法提供给K关于“法”和“罪”的存在性解答,这也是为什么监狱神父指出K过多地依赖女人,她们显然对他的审判毫无帮助。
卡夫卡只是满足于对K的欲望分析吗?果真如此,卡夫卡的伟大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大打折扣。事实上,他以极其冷静而克制的方式书写了K的生存境遇后,隐秘地阐释了K的自我觉醒和救赎之路,即他为现代人提供了一条打破“本真被遮蔽”困境的可能路径。事实上,正是基于“法”和“罪”精彩绝伦的辩证叙述,卡夫卡铺就了这条解放路径。
三、与法背离的法庭
K的“心理迷宫”隐喻了人类被无处不在的隐匿的权力所包裹的场景[7]223,同时也影射了其所身处的奥匈帝国法庭机构的极端状态。法庭机构在卡夫卡的文本中具有颠覆性的含义,法庭机构在一般意义上被理解为作出正义判决的国家组织,但是《审判》文本中却呈现为“限制公民行动”的机构[8]67。如果说卡夫卡笔下的现代人K已经丧失了古典世界的教诲,放弃了对人本真生命和法的反思,欲望成了K们不自觉的行动范式,那么这一可怖的情境在法庭的书写中被进一步强化。法庭机构消解了自身的权威,从未显现出光耀庄严的神圣地位,法庭逮捕了K,但在这一过程中法却从未现身,那么审判K的行动真的是由法庭机构做出来的吗?法庭的公职人员全然不知何为正义,而不假反思地近乎机械地服从欲望行事,法庭之外的其他人员则通过对公职人员施加影响获取利益。从这个层面来看,法庭机构也背离了其本真状态,法庭的运作方式处于法的对立面。
卡夫卡通过法庭的空间结构隐喻了其整体性的丧失。法庭结构并非以整体的建筑形式在场,其结构被分割成无数鄙陋的奇异空间,这些微小的空间粘连在被逮捕人的生活空间中。卡夫卡直接指出法庭空间结构影射了法庭机构内部的等级秩序,“光是那间狭窄低矮的办公室就能够看到法庭对这些人的轻视”[1]82。为公民审判提供辩护的律师机构也通过空间的隐喻显现其被忽视的位置,律师们工作的室内“只靠一扇小天窗采光,而天窗又很高,假如有人想看看外面,就得让某个同僚把他驮在背上。……办公室的地板上有一个已经存在多年的洞,尽管还没有大得能够掉进去一个人,但也足够陷进人的一条腿”[1]82。在前文关于空间结构的叙述中,我们知道法庭在每一幢建筑的阁楼上都有办公室,而阁楼的空间则被进一步分割,律师们工作的场所在阁楼的顶层,所以“假如有人被卡在洞里,他的腿就会悬在下一层楼的楼顶,也就是那些委托人等待被接待的走廊楼顶”[1]82。法庭的败坏不仅呈现在这种近乎荒诞可笑的空间结构中,也体现在其公职人员的身上。法庭工作人员的“内部秘密”不过是“面子工程”,因为法庭问询处是进入法庭空间的第一道屏障,所以这一区域的工作人员将得到其他人员集资提供的漂亮衣服,而对比之下其他人则穿得很寒酸,这一困窘现象也让K明白了为什么在他被逮捕时,法庭看守暗示他由他们“代为保管”他的衣物,即使他将这些东西交给仓库最后也会一无所得,因为法庭的财政困境使得其工作人员在一切可能性中榨取利益。
卡夫卡从欲望的角度质疑了欲望性政治[9]41。并非只有K深陷在非本真的欲望场域中,法庭机构人员也是如此,他们丧失了“思”的能力,全然服从于欲望工作。朝向利益的欲望使得法庭职员和与这些官员打交道的人形成共生关系,卡夫卡指出法庭机构存在着太多玩忽职守和贪赃枉法的官员,他们使得法庭机构“出现了很大的缺口”,“正是从这个缺口中,许多律师钻了进去,他们依靠贿赂探听情报,并且文件失窃的事情过去时有发生”[1]83。朝向“性”的欲望也作用在法庭机构中,洗衣妇暗示自己与法庭官员的“亲密关系”将有助于K的审判,“预审法官永远不能忘记我躺在床上的模样”,“预审法官也开始追求我了,而我恰恰在现在可以对他施加很大的影响”[1]46,而与K争夺这个女人的大学生则是预审法官的助手和心腹。K正是在这个女人的指引下看到了预审法庭审讯台上的书,“K打开最上面的书,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不堪入目的图片,……第二本书是一本小说,书名是《格雷特不得不被她的丈夫汉斯折磨》”[1]42。他愤懑于自己竟然由这样的法庭官员审判!卡夫卡用近乎讥诮的口吻隐喻了法庭机构的预审法官审判K的依据并非律法而是欲望,如果法庭人员践行的标准并非法的准则,而是欲望文本和欲望情绪,那么法庭审判的权威性和判罚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了。
法庭画家向K指出审判的三种判决方案:一是真正宣判无罪,一是表面上宣判无罪,还有一种是无限期延期审判,并指出法庭无法做出第一种“真的审判”,法庭判决的结果只能够是后两者。与前者相比,后两种审判是“非真的”审判,这也是法庭工作人员和与法庭相关的人员施展“技能”的领域。K在被逮捕之初的求助对象都向K暗示自己与法庭机构有紧密的联系,他们表示自己深谙法庭的运作机制,却无一人表示自己在法的问题上具有权威。与K陷入欲望关系中的女性都表示自己对法庭官员具有影响力;法庭画家指出自己家族世代为法庭机构服务;律师表示自己虽然不能出席审讯,但“必须要在审讯结束之后向被告打听审讯时的情况”[1]96。画家指出真正宣判无罪不在法庭机构的控制范围内,被告者自身的清白无辜则是决定性的因素。一旦K被宣判无罪,那么这个“案子”相关的一切都会消失,(2)卡夫卡所使用的“审判”的德语词“Der Prozess”,在英文中具有“The process”,即“过程”的含义,这或许是他有意为之的隐喻,他暗示K的审判处在不断持续的过程中(生命体验),而并非某次突然出现的“案件”。“不仅起诉书,而且庭审记录,甚至宣判无罪的判决书”都会消失。问题在于,画家口中的“真正宣判无罪”中的“真正”为何意?这种“真”显然无须法庭庭审和判决书等外界的证明,那么法庭又如何具有合法性?
卡夫卡通过“空气适应度”具象地暗示K的审判场所是否是法庭机构这一点是存疑的,他甚至无法适应法庭机构内的空气!法庭官员表示K之所以感到不舒服,是因为“这里空气不好的缘故”,而当K走到法庭办公室出口时,“他的力气仿佛一下子恢复了”[1]57。同样,法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却只习惯于呼吸办公室内部的空气,如果K不赶快把门关上,那么送K出门的姑娘很可能会“昏倒在地”。
卡夫卡在其文本之初就“逮捕”了K,吊诡的是K越是求助于各种他者,期待法庭给出确定的审判结果,就越是发现真正能够审判其罪业的审判者并不在法庭中!法庭在一般逻辑上表征着法的外在权威,但在《审判》文本中法庭和法却是异质的,法庭站在了法的对立面,它既不具有法的精神,也不具有权威性。整个法庭犹如盲目腐朽的机械,每一位法庭人员和靠近法庭的人都被卷入其中,成为这一机器的齿轮,他们深谙且遵守着法庭运作的逻辑,但却从未反思这一运行逻辑本身[7]57。因为对这一逻辑的反思本身就意味着一场偏离原先轨道的变革,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够追寻到法庭的本真状态,但这一行动对于法庭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四、何种法,何种罪?
实际上,卡夫卡在《审判》文本之初就已经暗示了法庭和法的异质性以及法庭和法分离的状态。逮捕 K的看守表示,前往民间寻找罪的并非法,而是法庭。K从始至终一直感到疑惑并且追问的问题是,自己究竟犯了何种罪,这种罪又触犯了何种法? 就法庭的维度来看,卡夫卡从未指认 K触犯了某种实证法,“肯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因为他没有做什么坏事,却在一天早上被逮捕了”[1]5。K与安提戈涅 (Antigone)不同,后者确实触犯了克瑞昂(Creon)在城邦中所颁布的法律。但 K又具有安提戈涅的特质,他正是在审判中逐渐认识到法本身的存在。
(一)依循何种法?
卡夫卡在其文本中嵌入了一则法的寓言,正是在这则寓言里他道出了真正的法。这则由监狱神父之口道出的“法的寓言”与“K的审判”在结构上都隐喻了“人类追寻法”这一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法的追寻”本身就已经指涉了“法的失落”这一前提。K象征着寓言中的乡下人:这个乡下人来到了“法的大门”前,他恳请守门人让自己进入这道门,这一境况正如K在被逮捕之初追问督察官,自己犯了何种罪,又触犯了何种法,他迫切地想要知晓法本身。乡下人和看门之间进行着年复一年的“斗争”,他倾其所有贿赂看门人,但后者在最后时刻才表示自己的任务不过是无限期地推迟乡下人进入“法的大门”的时间。这也正如K尝试获得法庭画家、律师以及法庭相关人员的帮助,而画家指出法庭无法给出“真的审判”,只能“表面上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地延长审判”,K也知晓律师只不过是经验丰富的老狐狸,他深知法庭的运作逻辑就是怎样把案子拖延下去。卡夫卡暗示K,他所有试图获得法庭审判的努力都如同下乡人向看门人的恳请活动一样,最终都是无结果的。乡下人在死前询问看门人,“每个人都追寻法,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之外却没有一个人要求进入法的大门?”[1]154
看门人最后道出了法的审判场所,“没有人能够来到这里,因为这个入口是专门为你一人而开的”[1]155。正是在此处,卡夫卡才指出了真正审判K的场所!K需要走进一道为他专门而开的“法的大门”,而非法庭。这也是为什么卡夫卡不遗余力地书写K一切向法庭寻求审判结果的行为都必然遭遇失败,因为除了K本人,法庭机构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审判他或为他摆脱审判。K的审判过程是一种排他性的孤独的自我确认过程。审判所依据的也并非法庭的实证法,而是一种内在的关涉整体人类的法。卡夫卡暗示法并非藉由法庭产生作用,而是通过主体性“思”的过程作用于主体,它内在于行动者的意识中,通过自我确认得以执行。
(二)“罪”的悖谬
“法”与“罪”的关系一直都是卡夫卡《审判》文本隐匿的线索,卡夫卡并未直接为这一问题提供明确的解答,但是他果真没有隐秘地解答这一问题吗?K在文本之初强调自己“无罪”时,逮捕他的看守就指出了他的矛盾:他既承认自己不懂法,又声称自己“无罪”。既然卡夫卡已经明确地排除了K违背了实证法这一可能,那么他究竟犯了何种罪?
卡夫卡《审判》文本的基调是荒凉乃至于让人绝望的,但是在这种荒凉的情绪体验中却蕴藏着潜在的变革力量,这一力量就显现在“罪”中。如果K从未遭受逮捕,“罪”的问题也从未显现,那么K将一直是他身处世界的高级经理,他也将一直处在“前反思”的状态。“罪”是一种契机,只有他追问自己所犯何罪,才具有意识到自己罪业的可能性,才可能有机会揭开本真存在被遮蔽的面纱。K的世界一直以乌云蔽日的状态存在,整个世界犹如荒野之中随时将倾的大厦,每一位介入其中的人都昏昏沉沉,他们能够体验到不安和惊恐的情绪,但却从未反思这一情绪本身,行动者的情绪体验和他能够意识到并反思这一体验是两种迥异的存在状态。
卡夫卡藉由“罪”的显现暗示了人的两种生存状态,一种状态是“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的状态[10]56。法庭中的人都尝试通过这一机构谋取利益,这种谋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丧失,越是深谙法庭机构运作逻辑并深陷在这一庞大机器中,就越是丧失了更广阔整全的“思”的视野;越是依循机构逻辑,就越丧失对这一逻辑所映射的境遇的反思。K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表示自己“知晓”法庭的运作逻辑,法庭人员、预审法官、法庭画家、律师以及与法庭官员相交甚密的女人们都表示自己具有关于法庭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却影射了他们的“遗忘”或“无知”:以K为代表的现代世界中的人遗忘了法、道德以及人性,他们无知于人生存的本真状态。苏格拉底(Socrates)强调自己的无知,但是K的“无知”是苏格拉底的“无知”的对立面,他在最初的时候将自己交托给外在法庭以及与法庭相关的人,他也无法摆脱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11]17,无法动用自己“思”的能力。
与这种生存状态相对的状态是人的本真存在?如果K一直将自己交托给外界,那么他就只能够一直处在“宕延”的状态中,其大概率的结果就是徘徊在“法的大门”前。K只有藉由对自身“罪”的“思”的能力,才能够进入这道门。卡夫卡未曾在其文本中指明何谓人存在的本真状态,而是通过“罪”的隐喻暗示了人意识到其生存的遮蔽状态,因为在K所身处的庞大而腐朽的法庭机器中,追寻生命的本真状态几乎是不可想象和不可求的。从这一点来看, “罪”具有一种变革力量,意识到自己“有罪”要优于“无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有罪之人”,也并不是每一个“有罪之人”最终都能够进入“法的大门”,只有主体清醒地意识和反思到自己的生存状态时,他才能够摆脱自己“不成熟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卡夫卡通过神父之口指出法的大门只向个人显现。法庭隐喻了丧失法的内核的“法的看门人”,他唯一的任务就是不断推迟乡下人进入大门的时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庭只能够做出“表面上的判决”或者无期限推延判决。所以,K只有突破作为“法的看门人”的法庭的阻碍,进入法的大门才能够获得“真的审判”。
读者很有可能会忽视K在律师的寓所见到的商人,他终其一生都在尝试获得法庭的判决,将希望寄托在庭审和证词上。他不断地向外寻求律师的帮助,但是也意识到律师提供的申诉书“毫无用处”。他懵懂地感知到自己的罪业——对自己被遮蔽的生存境遇的“无知之罪”,模糊地意识到法庭对于自己的罪业毫无帮助甚至是一种阻碍。商人比K更加接近乡下人的角色,他艰难地来到了“法的大门前”。但是卡夫卡暗示,即使商人未曾进入“法的大门”,他懵懂地意识到自己的“有罪”也比介入法庭机构的“无罪者”状态更善,因为卡夫卡在寓言中指出乡下人在死前看到一束光从“法的大门”内射了出来,而守门人却由于履行职责背对着大门。如此来看,朦胧地意识到自己“有罪的”商人虽然没有进入法的真正审判场所,但也瞥见了法的耀眼光芒。
(三)K真正的审判
卡夫卡通过K的真正审判隐喻了现代世界中人类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他并没有为读者提供商人的最终审判结果,商人只是来到了“法的大门前”。K比商人走得更远,他获得了审判结果,这一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K与法庭合力的结果。
就法庭的合法性这一层面来看,K逐渐成为法庭机构的“异质分子”,由开始“顺应的”态度转变为“拷问的”态度,他越是靠近法庭人员,就越看清这些人与法庭机构的共生关系,每一个介入其中的人都被法庭巨大的欲望场域吸纳。K想要获得真正的审判就必须要否定法庭的合法性,这一否定意味着通过法庭寻求审判结果这一行动的必然失败。这也是为什么当画家向K解释法庭运作时,他敏锐地意识到审判的矛盾:一方面,私人关系可以影响法庭的判决,但法庭却无法给出“真的审判”;另一方面,“真的审判”是一种私人宣判。一旦K意识到了这点,即法庭持续运作的前提就是延期和阻碍K进入“真的审判”,他的死亡也就具有了必然性。当K开始反思自己所犯何罪,逐渐意识到自己被遮蔽的生存状态时,法庭的合法性也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他也就成了法庭机构的异数,同时他便具有了走向“法的大门”的潜在机会。实际上,K在画家的画室中已经预言了法庭处理“异质分子”的行动,他向画家指出,“这恰恰证实了我对法庭的看法,只要一名刽子手就能取代整个法庭”[1]110。
从K自身的层面来看,他的“原初设置”(Default)是银行的高级职员,这一职位与法庭成员在本质上具有同构性。对于“罪”的理解使得他逐渐将目光转向自己的生存状态,他意识到自己关于罪业的追问只能够自行给出答案,这也近乎是一种孤勇的追寻行为。当他开始思考法庭的运作逻辑就已经指涉了他对法庭的否定,更加意味着对自己先前遮蔽的生存状态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K冲出了作为“法的守门人”的法庭的阻碍,进入了“法的大门”。“死亡”的判决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他作为法官为自己做出的审判,他虽然在死前询问“那个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那个永远无法企及的高级法庭又在哪里?”[1]164但他已经在接下来的话语中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即“虽然世界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它无法抗拒一个想活下去的人”[1]164。这一回答表明K已经走出了最初的那种迷茫“无知的”状态,他当下的赴死是一种真正活下去的行动。K在生命最后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疑惑,倒不如说是一种讥讽和无奈。
因此K表示自己感谢法庭派了两个半哑半傻的家伙送他上路,“并且让我向自己说出必然的结果”[1]164。对于K而言,“死亡”成了意识到自身罪业后救赎的必然方式,但是如果说K的死亡暗示了他身处的世界运行逻辑仍旧在继续,那么这一世界景象是令人悲哀的。显然,K无法替代他所处的世界中的所有人完成自身罪业这一问题的追问,每个人都必须要藉由自己“思”的能力拷问现行世界运行的逻辑,追问这一逻辑本身的合法性,才能够进入到“法的大门”成为自己的法官。卡夫卡写道:“K现在清醒地意识到,他有责任把在他头顶上传来传去的刀夺过来刺进自己的身体。(3)在卡夫卡的私人日记和公共著作中,“被刺穿”(常常通过刀子)的意象频频出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审判》中K“像狗一样”被刺死。David A.Brenner,German-Jewish Popular Culture before the holocaust:Kafka’s Kitsch,New York:Routledge,2008,p.57.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扭动了一下自己尚能自由活动的脖子环顾四周。最后考验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他无法为当局者完成所有的工作,最终失败的责任应该归咎于那些拒绝他使用这一力量的人。”[1]164
值得注意的是,K自己选择了行刑的场所,他在死亡之前看到了靠近行刑场所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窗户里出现一个模糊、细瘦的身影,他突然把身体从窗口探出,然后向远方伸展双手”[1]164。卡夫卡暗示这个模糊的身影很有可能是“K的朋友,是个好人,是个同情者”[1]164。就此而言,他还是为这个苍凉的世界提供了某种微不可察但确实存在的变革的可能性,这个人可能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清醒地意识到世界的荒谬性以及被遮蔽状态的人,K就是这种人;另一种是“整个人类”,只有整体人类都清醒地意识到人的本真存在,K才在真正意义上具有同盟者。卡夫卡的《审判》文本虽然绝望地书写了极端的世界荒原景象,但是从律师到K,再到这个“模糊身影”,又确实暗示了人类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遮蔽状态,并获得救赎的可能性。这一结局使得《审判》文本具有了某种开放性的功能,卡夫卡自此将人类情感和精神视野扩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12]36。虽然《审判》的文本充斥着悲惨和疏离的事件,K看似脆弱和挫败,但是如果读者能够理解K的“召唤者”身份,那么这或许为我们未来的可能性实践埋下一颗希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