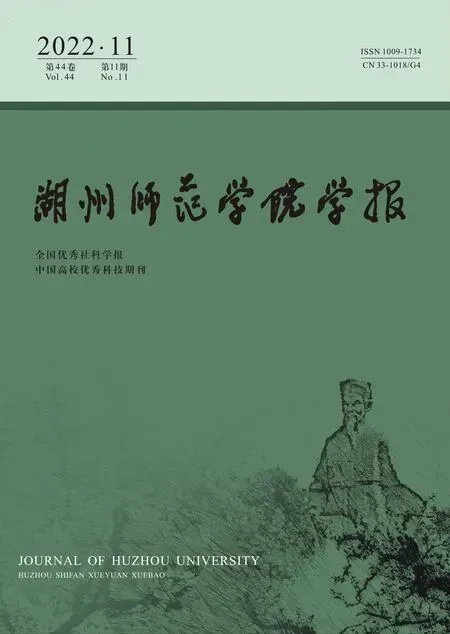乡土叙事与文学生态:论《吴兴诗话》的地域文化价值*
2022-03-23卢高媛
卢高媛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我国古代地域诗话的编撰大约始于明朝后期,江西人郭子章《豫章诗话》开启了“以地域观念建构诗歌传统的先声”[1]172。清代的地域性诗歌批评更呈方兴未艾之势,相关地域诗话据不完全统计有73种(包括地方总集附载诗话)[2]14。这个现象表明清人在诗歌创作、编选、批评时已经具备空间视野和区域意识,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学与地理在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罗伯特·F·墨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引论》说:“由于传播的作用,经过一个时期,彼此相邻的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称之为‘文化区’。”[3]251地域诗话的兴起让特定区域(通常是作者籍属地或宦游地)的文学积累得到系统的梳理,通过记叙地域文学家(包括文学世家、文学流派、文学社群、文学集团等)的事迹与创作,反映群体心理特征和文学创作观念,增进地域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从而构建具有审美趋同性的地域文学传统。地域诗话的编纂在清代整体上呈南强北弱的态势,而浙江地区的地域诗话数量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就诗话体系的内部层级而言,浙江既有以全省范围为对象的《全浙诗话》,也有小至一处名胜的《雁荡诗话》,以及涵盖府县乡镇各级的多种诗话,可见清代浙江地域诗话编纂的繁荣与完备。
《吴兴诗话》著录了顺治初年至嘉庆初年湖州地区有代表性的诗人,也是现今仅存的以清代湖州为记述对象的地域诗话著作,在地方文学文化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作者戴璐是清代中叶湖州籍文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好治文史之学,对家乡历史文献、风土文化尤为热爱。《吴兴诗话》展示了清代湖州极富特色的地方乡土民俗,呈现了繁荣多元的地方文学格局,有利于地方历史文化的补证与完善,有助于激起人们对地方文学发展的关注与反思。对此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该书的内容和价值,同时为清代的地域诗话和浙江文学生态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吴兴诗话》的基本情况
戴璐(1739-1806),字敏夫,号菔塘,又号吟梅居士,室名石鼓斋,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举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进士。戴璐居京城凡四十载,仕途稳畅,其所历官“自工部都水司主事,再擢至郎中,迁湖广道御史,礼科、吏科给事中,鸿胪、光禄、太常三寺少卿,通政副使,太仆寺卿”[4]354。晚年南归任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卒于任上,后归葬湖州。著有《六科汉给事中题名录》《吴兴科第表》《藤阴杂记》《锦江脞记》《史垣牍略》《石鼓斋杂录》《吴兴诗话》等。
戴璐的祖父、父亲皆为进士,其父戴文灯“藏书甚富,皆撮其典要,辨其异同”[5]582,这种严谨治学的家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戴璐的创作。戴璐著书严谨务实,钩沉稽古,发微抉隐,所述之事皆耳闻目见,再经芟削去重而成,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吴兴诗话》最早的版本为嘉庆二年丁巳(1797)石鼓斋刻本,后有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李中龢整理补缺的手抄本。民国元年壬子(1912)吴兴严氏随分读书斋抄本和民国五年丙辰(1916)刘承干嘉业堂刊本则都是以李氏抄本为底本。新中国成立后,以刘氏嘉业堂刊本为底本影印出版的种类较多,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吴兴诗话·诗筏·春雪亭诗话》本、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丛书集成续编》本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本。杜松柏《清诗话访佚初编》则是影印的日藏嘉庆原刻本,但是不全,只有八卷。目前尚无点校本。
《吴兴诗话》的采录范围自顺治二年乙酉(1645)至嘉庆二年丁巳(1797)付梓为止,前后逾一百五十年,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清代前中期湖州诗坛的整体风貌。戴璐为撰写此书留心乡邦文献多年,遇假归省不忘寻访探迹,积累年之功方成。所涉文献包括郡邑志乘、地方总集、诗文别集,以及各类诗话、笔记、杂说等,搜罗广泛,采摭丰富,数量可观。其中采录的诗歌来源于各类已刊刻或未付梓的总集别集、碑石壁刻、书画题识以及部分私人信函和对谈。该书在编纂体例上仿朱彝尊《明诗综》,采用以时为序、以人系事的体例。在作者分类的基础上按照生活年代先后排序,每个人物大致由小传、诗话、诗选三部分组成,但并非每个人物都具备这些内容,其详略、先后各有不同。这种模式既便于检索又标准清晰,还可以在人物条目中间评论考证,触类旁生,形成完整而开放的体系。《吴兴诗话》凡十六卷,附卷首御制卷一卷。御制卷选清代皇帝与湖州相关诗事。第一卷至第九卷为郡邑贤哲,第十卷至第十二卷为郡邑闺秀,第十三卷至十六卷为郡邑长官及游湖名士。《吴兴诗话》在写作上以陈述事实、引述文献为主,很少加入作者的主观见解和评论。少量按语主要是为了订正讹误、补充说明、考释名物、征引文献等,整体内容皆以叙事为主,而不以论述为要,遵循史家求真务实的书写原则和理性思维。
《吴兴诗话》著录的人物除了本地名贤,还把郡邑长官和游湖名士等为代表的非湖州籍人士纳入书写范围,这说明该书的地域范围不仅是一种纯地理定义上的划分,还有情感认知上的界限。也就是说,地域文化的内涵除了该空间本身的文学积累以外,还包括外界对该地的批评与创作所激发的认同感。我国不同地区都有着各自长期凝练而成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编纂地方文献意义就在于将这些宝贵的经验财富进行提炼和总结。明代学者韩昌箕说:“撰述之家,其流各别,《史通》所谓偏记、小录、逸事、琐言、家史、别传,兹不具论。他若周称之《陈留耆旧》,周裴之《汝南先贤》,陈寿之《益郡耆旧》,虞预之《会稽典录》,谓之郡书;若盛洪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谓之地理;若汉有《三辅黄图》,隋有《东都记》,于南则宋《南徐州记》《晋宫阙名》,于北则《洛阳伽蓝记》《邺读故事》,谓之都邑簿。彼皆各纪其本国之风物,以俟后之好古者有所稽讨,故虽偏而不废,杂而有征。”[6]10湖州地域文献著作最早大概出现在汉末至东晋时期,据史料记载,有韦昭《吴兴录》、山谦之《吴兴记》、王韶之《吴兴郡疏》、张玄之《吴兴山墟名》、吴均《吴兴入东记》等,然皆已亡佚,其著者亦有争议,故仅供参考。这说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地域意识的自觉和强化,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宋元以后,以省府县乡镇等行政级别为层级划分的地方志编纂开始兴起。宋代谈钥《嘉泰吴兴志》是现今可见最早最完整的湖州地方志,明清以后湖州地方志的编纂渐趋繁荣,除了以府州县镇乡等行政区划为对象的方志,还有各类山水志、地名志、人物志、职官志等,据统计多达两百五十三种[7]2,这实际上也为地方文学文献记录和保存提供了有力支持。除了史传志乘以外,地方性总集、选集、笔记诗话的编纂也是整合当地文学资源、梳理当地文学历史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可以从特定地域范围内历代文学作品的著录、编集和流传中探寻该地历史文化的内涵与特性。方志的编纂为湖州文学资源的整理和研究奠定了坚实而丰厚的史料基础,而总集类文献的编纂则进一步汇集和综合了地方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让地方文学创作及其特色更清晰地凸显出来。
以地域为标准辑录湖州文学作品最早可追溯至元代,清人郑佶说:“湖州诗自齐梁间沈约、丘迟提倡,而后代有多人。元人汇编《吴兴绝唱集》,明邱秀才《吴兴绝响录》,常熟钱大令学《吴兴诗选》久行于世。”[8]1a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明代董斯张等人共同编成的《吴兴艺文补》七十卷,收录了上古至明的历代诗文。清代陆心源《吴兴诗存》四集共四十八卷,精选六朝至明诗家近四百人;陈焯等人《国朝湖州诗录》三十四卷、《续录》十六卷收录清代湖州诗人一千一百余家,至此有清一代湖州诗坛面貌可概见。从地域历史编纂角度来说,地域诗话也是构建和呈现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形式。据笔者考证,湖州先后存在过三种地域诗话,分别是沈棠臣的《吴兴诗话》、戴璐《吴兴诗话》以及吴又禄《续吴兴诗话》。遗憾的是沈棠臣《吴兴诗话》已失传,而吴又禄《续吴兴诗话》亦不见全本,仅能从其他文献的引录中管窥一二。《吴兴诗话》作为唯一一部保存完整的湖州地域诗话,其价值不言而喻。该书通过传述人物事迹、采摭诗歌作品、记录历史事件,展现了清代湖州诗坛的发展脉络以及地方文人群体的时代风貌,为研究清代湖州地域文化提供重要的参照视角和价值尺度。
二、《吴兴诗话》与地域乡土叙事
“乡土”就是家乡和故土,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色彩、历史传统积淀和独特地理空间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地理与审美意义上的存在,乡土叙事则是对这种存在的一种观察、表达和再现的方式。通常来说,人们会对故乡这个特定地域范围产生某种基于风土、民俗、方言等的一种文化认同,并进一步形成荣誉感。乡土情结也是文学书写中常见的表现内容,《庄子·徐无鬼》说:“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9]124《小雅·小弁》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10]116对桑梓故里的热爱与推崇是人之常情,所以史家文士很多时候把记述乡域的历史、人文、风土等视为一种责任与使命。明代湖州知府劳钺《湖州府志》序说:“郡志莫切于事实,尤重于人物,姑举其概,如谢安、颜真卿辈,睹其志即思其人,思其人即慕其德。由是凡仕于湖者感之,必思所以字其民;凡诲于湖者感之,必思所以勤其教;凡生于湖者感之,必思所以修其德。匪直一世而已,推而至于千百世之下,亦莫不有感之而兴起焉者。是则郡之有志,政教攸系,于风化所属,岂独名编云乎载!”[11]429-430与方志一样,诗话作为地域历史编纂的一种形式,同样讲求切于事实、重于人物。如果撰述对象是家乡的话,在人物选择和事件处理上更体现出一种自觉的乡土意识。如清代台州学者戚学标《风雅遗闻》自叙说:“杂记乡邦事地人物,所引诗不必皆台人,亦不尽系乎论诗。总之,为风雅之事,有益于梓里文献。”[12]2地域诗话中的乡土叙事不仅可以强化人们对家乡的认同和归属,也对传播乡邦历史文化知识、培育地域文学观念产生积极影响。
就《吴兴诗话》而言,戴璐在自序中明确阐述了撰写此书的目的:“征文考献,具有苦心,庶几前贤芳躅不致湮没无传,而一邦文献借以留贻,或以补郡志旧闻之缺。”[13]175可以看出,戴璐希望通过诗话宣扬乡贤风雅、记录乡邦文献以阙补志书,在传述人物、著录作品的同时勾勒出故里诗歌的风土特征和传统。诗话采录了大量吟咏湖州地域景观的诗歌,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想象和意趣。苕溪与霅溪是湖州境内两条主要河流,细密的水网构筑起这片区域的基本面貌,而“苕霅”也成为湖州的代名词。戴璐在《吴兴诗话》御制卷中说“御制泉宗庙集远堂联‘苕霅溪山吴苑画,潇湘烟雨楚天云’。”又提到自己在内廷值班时,曾被乾隆召询问及吴兴山水之事,乾隆说:“此邦虽未临幸而山水清远。”[13]176又,乾隆有和苏轼《游道场山何山》七古一首,戴璐将此作为“桑梓光荣”记录下来。道场山是湖州胜景,文人多有流连,王叔承《道场山集序》说:“吾郡之南有道场山,峻峰回岭,树刹云霄,控五湖,引苕霅,瞰武林天目,郁郁巨丽,西吴所最胜也,名士游览品题,盖不绝云。”[14]29b古往今来诸多名篇中以苏轼“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霄下幽谷。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之句最为有名。清代宦游湖地者多访道场山,如宋琬曾偕友人同游,各赋诗一首,并作《道场山倡和题词》[15]595。此外诸如岘山、白苹洲、碧浪湖、白雀寺等景观都是文学创作中的常见意象。秀美的山水陶冶着人的性格,也濡染着人的审美批评。这些景观的艺术书写在传播过程中无意识地影响着接受者的情感与认知,反过来又对文学创作和批判产生作用。
《吴兴诗话》在叙事上注重乡贤忠义孝廉形象的塑造,以振益郡邑声名。在传主选录、诗歌选录、事件选排上以彰显人物高尚德行为目的,树立符合道德伦理的典范形象。如卷一“钟明进”条说:“守惠州,值逆藩叛,被执屡濒于危。著《两粤吟》,其《城楼抗逆》诗云:‘溅血自甘同太尉,矢心岂得睢阳会。’贼平告归。”[13]178卷十“徐师愈”条说:“父多病,谨庵侍奉汤药必躬必亲。暮年复病,两目不见物,眶周溃烂,百药罔效。谨庵晨起辄以清米饮漱口舌数百度。未几稍稍有验,睹物如云雾中,私心窃喜,每东暾欲出即候卧榻前,俟睡醒之,不懈益虔。不数月,炯然复朗矣。族党咸嗟叹曰:‘是固为人后者而事亲不异于所生且有加焉,非至性过人而能若是哉。’”[13]233若有湖人在他乡为官,也常以“有惠政”加以评价。汪曰桢有诗云:“有以气节著,有以文艺鸣。穷者为隐逸,达者为公卿。要皆三不朽,无愧乡先生。”[16]644对乡贤善行义举的赞颂与彰扬,实际上也是树立地域人文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一定程度上对乡邦士风的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也为构建地域精神文化史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吴兴诗话》体现出来的乡土意识与戴璐本人的性格与经历分不开。戴璐寓居京师四十余年,从其与友人的诗歌往来可以看出他对故乡的拳拳深情。吴锡麒有《题戴菔塘(璐)〈苕川归耨图〉三首》[17]535,苕川即苕溪,可知该图所绘的是湖州农田耕种之景。又祝德麟《题菔塘少鸿胪〈柳塘春泛图〉》诗云:“霅溪苕水弁山前,风景招人最可怜。春来处处皆图画,不独桃花近酒船。”[18]200从内容可以看出,这幅画是以湖州春景为主题,可见戴璐虽然久居京师,仍满怀对家乡风物的热爱。不仅如此,他还十分重视同乡关系建设和情感联络,多次参加在陶然亭举行的以湖州籍士人为主体的集会酬唱活动。有《陶然亭公宴诗》云:“绿衣忆步曲江滨,三世荣叨作主宾。久羡后贤腾凤采,已看几辈跃龙津。鸿才并擅无双誉,虎榜频题第一人。想得洛如花烂漫,五元联袂灿华茵。”[19]508唐代冯贽《云仙杂记》卷七“洛如花”条说:“吴兴山中有一树,类竹而有实,似荚状。乡人见之,以问陆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则生’。”[20]50戴璐在诗中以湖州特有的传闻故事为典故表达对与会俊杰的赞美,极富乡情色彩,也表现出他对湖州文化掌故的熟悉。
乡土文化实际上是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融合,是群体生存智慧和审美想象的一种表达。明末遗民诗人李令皙《同岑集》序说:“吾湖素称清远,人皆潇澹迂烈,孤清绝炤,与山水相映。”[21]377对乡邦的文学书写,总是离不开表层的地域文化景观的描绘,以及潜在的地域文化性格的阐述。《吴兴诗话》正是通过大量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展现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群体统一性和鲜明地域性的乡风民俗,在情感上表现出对乡邦故里的热爱与自豪,在叙写上体现出对乡贤先辈的尊重与推崇,在批评上呈现出对乡土文学传统的强调与肯定。
三、《吴兴诗话》与地域文学生态
中国自古以来幅员辽阔,气候环境复杂,民族众多,随之而来产生了丰富而多元的地域文化。古代思想家普遍认为,风土决定了人的气质,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晏子春秋·问上》说:“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22]122这说明不同地域的社会文化和群体气质会出现差异,对此进行比较与概括可以推动地域认识的深化,同时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湖州古称吴兴,素来有“清远”之誉。南宋湖州通判傅兆《吴兴志序》说:“吴兴东南最盛处,于今为股肱都,山水清远,人物贤贵。”[23]1明代宋雷《西吴里语》自序道:“吴兴故称江表大郡,山水清远,物产繁庶,古今著节,代不乏人。”[24]1明代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引》中说道:“吴兴在泽国上游,其俗素朴厚,绝无技巧淫糜之习。自汉以来,流寓及宋南渡诸贤类多居此,盖有自也。夫其本俗俭啬,加以君子之遗风,故至于今以尚礼节称焉。”[25]1a这段话其实已经从风土出发,对湖州民俗风尚和文人气质有大略的品评。
那么从地域概念下谈论文人群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龚鹏程先生在《区域特性与文学传统》中说道:“从秦汉到唐朝,大体上是中原文化形成、稳定并逐步扩散的时期。……这样的时期中,文化意识在中央一统结构下的分化现象,尚未发展。文学也同样还没有在建构法律系统、文体规范及评论标准之余,形成区域性次级传统的分类。”[26]289也就是说,虽然《诗经》与《楚辞》已经体现出某种地域意识,但文学的地域观念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很淡薄,并未形成普遍的批评共识。直到唐代中后期,文人结社兴起,各个地区的知识分子开始类聚起来。这之后的宋代出现了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学流派——江西诗派,标志着地域观念逐渐在文学研究中显豁起来。在地域文人群体频繁的交游酬唱中,具有共同创作趋向和审美特征的地域文学风尚才可能出现,并且进一步扩大影响。而湖州也正是在唐宋时期迎来了地域文学发展的高峰,出现了众多在文学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文学集团和重要活动。中唐时期,以郡邑长官颜真卿、本地诗僧皎然为中心的湖州诗会蓬勃开展,规模宏大,有数十首联句传世;宋代苏轼多次在湖州碧澜堂与友人酬唱,是为“前六客”之会,成为后人艳羡追慕的风流雅事。清初诗人宋琬评道:“吴兴山水,秀绝东南,而唐、宋之间复多贤太守,颜清臣、苏子瞻其最著已。两公幸当太平无事时,得以优游闲适,极登临燕赏之娱,其风流遗事宛在耳目之前。”[15]26这些声势浩大的集会活动既实现了外地来客与本土文人群体的汇聚,又推动了主流大传统与地域小传统的融合,为后世地域流派意识的凸显奠定了基础。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浙江人文蔚盛,群体集会酬唱的风气得以延续。《明史·张简传》说:“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27]2912明代以后,各类地域文学群体更成风气。仅湖州地区就有苕溪社、乐天乡社、湖南崇雅社、岘山会、逸老社、逸老续社等文学社团出现。可以说地域文人群体不可小觑的强大实力已经改变了曾经大一统的文坛格局,促进了多元文学观念的并存和交融,这也让地域文学传统的构成变得复杂起来。
清代湖州的文学家族、会社、群体的活动生态在《吴兴诗话》中多有记述,其著录的人物往往纵横关联,除了血缘、亲缘以外,通常存在同门、同年、同僚等社会关系。对此进行考察,可以对湖州地域文学生态状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以竹墩沈氏家族为例,该族系南朝武康沈氏后裔。入清以后,沈三曾、沈涵兄弟于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同榜分列二甲第二、三名进士,这标志着竹墩沈氏家族开始步入鼎盛,英才辈出,成为湖州极具影响力的名门望族。沈氏家族崇尚风雅,自沈涵开始就有组织文学集会的习惯。《吴兴诗话》卷二说:“阁学晚年家居,于屋旁辟小园,号‘东圃’,与宗族为文酒之会。”[13]187这些集会活动以沈氏族人为主体,以及少数异姓同乡文士,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双溪唱和”与“竹溪唱和”。《吴兴诗话》卷十五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康熙中叶后,吾湖诗派极盛于竹墩、前邱,两溪相望不三里,而近所传《双溪唱和诗》是也。诗为苹村宗伯所选,卷有六,得古今体诗四百六十四首,得唱和者二十九人。为沈心斋(涵)、吴芸斋(曙)、沈厚余(树本)、吴青然(大炜)、沈绎旃(炳巽)、沈幼牧(炳谦)、沈素庵(允相)、沈麟仲(楷世)、沈寅驭(炳震)、沈植庭(树槐)、沈同叔(桢国)、柯南陔(煜)、吴琳岩(斯洺)、吴眉宗(溶)、丁静山(凝)、姚孟诚(德至)、吴山补(启衮)、沈端文(揆曾)、吴易斋(隆元)、沈殿擎(柱臣)、柯贞裳(寿坤)、严古千(光夔)、茅逸群(应旦)、茅渠眉(应奎)、吴我锡(启褒)、孙立夫(炌)、董翰飞(浩)、朱樵云(廷杰)、董周池(胡骏)。……《双溪倡和集》锓刻精好,已行于世。复有《竹溪倡和诗》未刻本,起于康熙辛卯,一、二卷为何义门,三、四卷为徐澄斋,五卷为柯南陔,六卷为杨皋里,所选后附《探梅集》,厉樊榭序之。《苕颖集》柯南陔选之,则已至雍正癸丑年。后于《双溪倡和》所增之人则有董渭宣(熜)、姚玉裁(世钰)、茅用白(藉)、释彻照、沈在抡(生遴)、沈心仪(洽曾)、沈申培(树德)、沈持谦(棠臣)、沈勉之(荣仁)、沈葆之(荣光)、沈常之(荣向)、沈慎之(荣佶)、沈谦之(荣)、沈振之(荣简)、沈湘旋(生策)、沈昭子(倬)、吴书升(佺)、韩俊超、沈雨苍(作霖)、沈鹤年、沈思莪(树菁)、沈永之(荣昌)、沈补思(生甫)、沈六只(生巩)、沈葆初(生华)、沈秀君(生芝)、沈九度(生龄)二十七人。虽小有不逮,而合诸前集二十九人共得五十六人,辉映后先,亦可侈矣。[13]258-259
从唱和主体的构成可以看出,前后两次唱和活动共有56人参与,其中32人来自竹墩沈氏,所占比例接近60%。编选《双溪倡和集》的徐倬(苹村其号)为德清徐氏一脉,与沈三曾为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乡试同年。徐倬受业于明末大儒倪元璐、刘宗周,清初名家姜宸英、顾图河、查慎行、刘岩等皆出其门下。子徐元正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曾孙徐以升雍正元年癸卯(1723)进士,官广东按察使。玄孙徐松坞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进士,官户部主事。松坞兄徐天柱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戴璐评价徐氏:“五世清华,一门鼎盛,吾湖三百年来几无其匹。”[13]185又沈三曾之子沈树本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榜眼,“以白苹诗得名,与海宁杨守知(次也)、嘉善柯煜(南陔)、平湖陆奎勋(坡星)称‘浙西四子’”[13]194。沈树本长子沈荣仁与戴璐祖父戴永椿同年入翰林院,有《贺得孙诗》相赠。戴璐著录该诗并感慨:“五十四岁方读是诗以见前辈期许之殷,录以志愧。”[13]194可见戴氏与沈氏之渊源。乌程戴氏“科第传家,四世进士”[14]25b,亦是望族,其学渊源深厚,出现了不少才华出众的闺秀名媛。其姑母戴韫玉,字西斋,有《西斋遗稿》。嫁于仁和(今浙江杭州)陈淞,夫妇多有唱和,育有二女陈琼茞、陈琼圃,皆工诗善画[28]13。戴璐女佩荃,字南,嫁古文家赵佑子赵日照为妻,有《苹南遗草》。侄女佩蘅,字蕴芳,有诗早佚。除此以外,还有“苕中三钱”、德清月泉吟社、董氏南浔诗派等名重一时的地域文学社群。戴璐通过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将乡绅、寓贤、闺秀等群体串联起来,为读者呈现出真实而生动的湖州地域文学生态面貌。
地域文化是经过长时间的积淀而形成的地方特色文化,其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沉淀了厚重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对清代文学而言,地域观念已经根植于人们思想之中,成为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潜在重要因素。因此,以《吴兴诗话》为代表的清代地域诗话在书写和审视地域文学生态、补证和完善地域历史编纂的同时还参与了地域文化的建构。对此进行更广阔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让文学与地域的历史积累、风物民俗相结合,为考察地域文化体系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