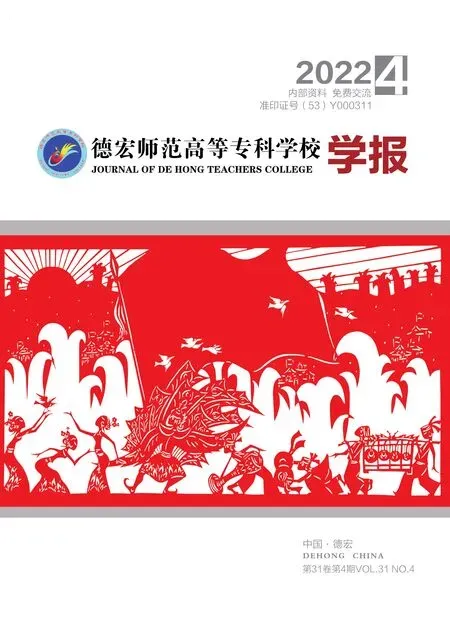民族国家考古秩序的确立
——“何日章案”与《古物保存法》的颁布
2022-03-23刘桃
刘 桃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陆陆续续许多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教是不容置喙的,但是他们中许多人还有着非常高的专业素质,所以他们往往不仅是传教士,还可能是医生、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化学家等等。由于他们来到中国后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非常感兴趣,有些人便开始在中国从事考古工作。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是没有考古这一概念的。中国人一直以来都以死者为大,挖坟掘墓是最大的忌讳。但是,中国也一直有着一群不法分子打着古墓里陪葬品的主意,这就是盗墓贼。清末民初,全中国都处于动荡之中,国家对于盗墓这一行为无暇顾及,这群盗墓贼越发猖獗,到处破坏着中国的古墓。“实际上,盗墓者均为本地人——农民、流民、摊贩,或者通常不过是些当地孩童。”[1]20世纪20年代中期,外国人在中国的考古又非常盛行,许多外国的考古工作者和学术团体来到中国考古。随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工作在全国不断发展,地方开始不满中央在本地进行的考古活动,便与中央争夺国家文化保存事权。“何日章案”便是中国的考古处于无序状态的集中体现。
那么,中国的考古是怎么从无序到有序的呢?民族国家的考古秩序是如何建立的呢?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不断发展,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和李济分别担任主管全国古物保存事权机关——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两会委员,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了保护国家出土文物的重要性。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他们认为外国人在中国从事考古工作是不利的,地下古物应该“概归国有”,中央应该拥有国家文化保存事权,于是推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即《古物保存法》。从此,中国民族国家的考古秩序逐渐确立,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得到推进。
目前,对“何日章案”的讨论只有研究《古物保存法》颁布背景的文章中有所涉及[2];关于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的研究有《古物保存法》立法始末的研究,《古物保存法》中地下文物所有权修改始末的研究,以及《古物保存法》的弊端和实行困境的研究等。[3]笔者认为首先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挖掘河南安阳殷墟与河南省府产生冲突为例,描写出民国初期中国考古的无序状态,再述及《古物保存法》确立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物权观念有关的考古秩序,更能清晰地看出中国有关文物的法律近代化过程。
一、中国考古的无序状态的集中体现:“何日章案”
“何日章案”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了地下和地上古物的所有权。在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是没有考古这一概念的,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国本土盗墓贼猖獗,肆意破坏古墓。20世纪20年代中期,外国人在中国的考古非常盛行。“一时美国、法国、瑞典等国家的考古学家和学术团体,纷纷都到中国的北方来考古”[4]。他们打着考察的旗号将中国的地下文物偷运出中国,这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因为之前颁布的法律中没有一条与考古发掘有关,没有办法对肆无忌惮搜刮中国文物的外国“探险家”和中国的盗墓贼追究责任。即使在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制定了《保存古物暂行办法》,也无法起到保护中国文物、防止文物外流的作用。因为这个文物保护的方法十分粗糙,只规定了保护文物的范围,并没有涉及到保护的具体方法和责任机构,特别是关于外国考察者、文物出境等问题更是没有提及,并且这个方法也只是暂行的临时性紧急文件。
随着中国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中央考古机构逐步建立。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带动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新学科的兴起,相继为中国学界示范了崭新的研究事业与方法”[5]。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文化保存意识不断觉醒。张永康便认为,“吾人欲发扬民族主义,则于中国民族历史,自不能漠视”,要发扬民族主义“国家应设立规模较大之博物院,以训练考古人才,并奖励从事发掘之人。”[6]为了与西方考古活动相竞争,史语所在地方上开展考古活动。但是,在军阀割据的中国,他们将地方的文物运往中央,这引起了地方的强烈不满。因为中国没有一部法律对文物的所有权和保管权加以界定,地方政府认为有机可趁。于是,河南省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向中国民族主义的现代考古发起挑战,与中央政府争夺国家文化保护事权。
随着西方考古知识的传入,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不断发展。为了与西方人在中国的考古工作相竞争,史语所在各地开展考古工作,其中就包括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商得河南省政府之保护,并由院派张锡晋先生教育厅派郭宝均先生协同视察,”[7]于是开始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后来,河南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向省政府提出将史语所挖掘的龟骨器物在开封陈列。中央研究院回答河南省政府说到“本院特派员在各地发掘古物,将来如何陈列仅限于首都及本地博物馆……贵省政府所请以掘出古物留存于开封古物陈列所一节,自可酌情商量。”[8]之后史语所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一切照旧。 但是,1928年5月,“军事突兴,驻军忽不知去向,县长亦逃,土匪并起,洹上村危在旦夕”[9]。可以看出,史语所和以何日章为代表的河南省政府有着关于文物所有权的矛盾,河南省府企图与中央争夺文物控制权。而且,在各地战火不断的情况下,考古工作受到严重阻碍,考古现场周围的土匪和强盗也对文物虎视眈眈,足以见当时中国考古的艰难和无序。
到1930年秋,张尚德、轩仲湘和邱耀亭前往安阳殷墟参观了两日。次日,史语所李济便听闻何日章来彰发掘。李济立即进城拜见何日章,对其说到“事关学术,绝无权利之可图。君即奉地方政府命令来办此事,国立中央研究院所派之考古组,可以暂停,绝不在此与君计较。但有安阳县来一公文即可,不必布告。”[10]第二日,公文到达,史语所便停止了工作。之后中研院请国民政府主持公道,国民政府又电令河南省政府继续保护史语所的考古工作,史语所再次开工。
河南省府因不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私自将安阳殷墟出土文物运往北平,导致河北省府和史语所发生冲突。何日章因对此不满,率领民众私自开挖,并阻拦史语所继续挖掘河南安阳殷墟,双方争持了近3 个月之久。[11]这就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中发生的“何日章案”。“何日章案”充分显示了没有与文物相关法律考古工作难以有序的进行,中国的考古处于无序的状态,急需一部法律来加以约束。
二、从“平分古物”到“概归国有”
(一)《采掘古物暂行条例》:采掘人和国家平分古物
如上所述,中国的考古处于无序的状态,又没有一部法律对此加以管理。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法制思想不断觉醒,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后,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严智怡即提出“限制发掘古物以保文化而维国权”的议案。他在议案中提出“嗣后无论中外人民非得省府允许,不可任意发掘古物,并转予国府拟定法律,命令限制”[12]。委员会议通过了严智怡的提案。河北省政府一面迅速将提案通知全省,一面在1929年1月份呈请国民政府“拟定法律限制发掘古物”[13]。国民政府立即将此事交立法院处理。立法委员会在1929年3月9日的第16 次会议上认为,“古物于文化学术有莫大之关系,外人任意掘取尤属妨碍领土主权,自应明定法律,严予限制”[14],同意立法;4月13日立法院第19 次会议上又讨论了此事,27日第21 次会议上,立法院交给法制委员会起草法律条文[15],由立法院委员戴修骏等人具体负责”[16];至迟在5月初,《采掘古物暂行条例》就已拟好。
《采掘古物暂行条例》中除了第四条规定古物发掘比须经过批准外,其余八条主要在规定采掘古物的所有权,本文罗列比较重要的三条:
第五条 在公私土地上采掘所得之古物,应由当地主管机关估定价格,分为价值相等之两份。一份归国有,一份归采掘人所有。以抽签法定之。
采掘人如认当地主管机关所估之价有欠公平,得呈请部指派专家三人会同该机关重行估定之。
采掘所得之古物不能分为价值相等之两份时,其不能分之部份,由当地主管机关以半价收买之。
第六条 凡采掘人依前条第一项规定应得之古物,如当地主管机关认为有一并保存之必要时,得备价收买之。
第九条 本条例第五条至第八条之规定,于偶然发见之古物适用之。[17]
根据《采掘古物暂行条例》的规定,采掘者拥有将挖掘出或者意外发现的地下古物和国家平分的权力,简单讲就是采掘者拥有一半的古物所有权。虽然《采掘古物暂行条例》中采掘者有权与国家平分古物的规定不符合民族国家的考古秩序,但也是对中国考古秩序的第一次规定,使中国考古有了规则可以依循,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二)《古物保存法》:古物“概归国有”
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地下古物应该归国家所有,因此极力反对采掘者于国家“平分古物”一规定。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将“平分古物”转为“概归国有”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古物保管委员会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熟悉它的学者,负责全国的古物古迹保存、研究及发掘等,其主要成员有翁文灏、李济、袁复礼和傅斯年等人。他们在听说《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规定采掘者和国家平分古物后,古物保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继不仅通过教育部转呈立法院暂时保留草案,并且还很快通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让中央研究院参与并提出了改进意见。蔡元培立即致函教育部,要求在采掘古物条例制定中“参加意见”。教育部回函表示“采掘古物,关系学术文化至巨”,而“其暂行条例,亦系草案,并未得最后之确定”,邀请中央研究院派人列席随后商讨采掘草案的会议。18日,中央研究院收到古保会邮寄的《草案签注意见》、《采掘古物意见书》。25日中央研究院同时给教育部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回函,寄上“对于采掘古物之意见两条”,就审批问题做了两点补充。在给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回函中,中央研究院还表示“贵会所见各节,大体赞同”,这意味着,中央研究院也认同了古保会对“地下古物概归国有”的规定。[18]最后,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古物保存法》将“平分古物”修改为“概归国有”。李济就曾说到“我们促请政府宣布古物国有的《古物保存法》是费了很多的时间,才达到这一目的的。”[19]
《古物保存法》共有14 条,规定了‘古物’的范围、保存机构、上报规、流通和所有权等。其中重要五条如下:
第六条 前条应登记之私有古物不得转移于外人,违者没收其古物,不能没收者缴其价额。
第七条 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
前项古物发现时及发现人应立即报告当地主管行政官署呈由上级机关咨明,教育内政两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收存其古物并酌给相当奖金,其有不报二隐匿者以盗窃论。
第八条 采掘古物应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之学术机关为之。
前项学术机关采掘古物应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核转请教育内政两部会同发给采掘执照。
无前项执照而采掘古物者以盗窃论。
第十条 中央地方或政府直辖之学术机关采掘古物有须外国学术团体或专门人才参加协助之必要时,应先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
第十三条古物之流通以国内限,但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之学术机关因研究之必要须派员携往国外研究时,应呈经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特请教育内政部会同发给出境护照。
携往国外之古物至迟须于二年内归还原处所。
前两项之规定于应登记之私有古物适用之。[20]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古物保存法》增加了“地下暴露地面”这个定语,使概归国有的古物涵盖面更广,将《采掘古物暂行条例》中的“平分古物”改成了古物“概归国有”,使中央政府的国家文化保存事权没有被侵夺。《古物保存法》还规定了外国人不能私自在中国采掘古物,使中国古物大量外流的情况得到了解决。这是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他们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国民族国家的考古新秩序,使中国的考古有序可循,有法可依。
三、《古物保存法》确定的民族国家的考古秩序
(一)古物“概归国有”
在《古物保存法》颁布之前,发生了“商震诉辞案”和“何日章案”,这两个事件显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争夺国家文化保存事权的竞争和中国考古秩序的混乱,也加速了《古物保存法》的颁布。《古物保存法》规定古物“概归国有”而不是归地方政府所有,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民族国家的考古秩序。
1928年12月30日,河北省府主席商震因感于境内古物遭倒卖情况严重,向国民政府提出诉愿,希望国民政府迅速厘定相关保存法律,用以限制中外人民任意发掘古墓。他提出非经省府允许,不得任意在境内挖掘古物[21],这便是“商震诉辞案”。1929年10月8日又在河南安阳发生我们前文所述了的“何日章案”。这两个案件都提出地方省府拥有对境内地上和地下文物的发掘权和管辖权,是对民族主义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挑战。
这两个案件不仅仅显示了地方团体保护在地出土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意图,还显示了地方团体对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可以说是对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挑战。首先可以看出,在当时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已经认定考古出土物件是国家文化保存法制的重要标志,一切文化保存的法制设计与行政实践都应该以考古出土物件为核心来开展。并且也认识到,文化保存工作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但是,在地方主义的影响下,在没有法律授权中央有国家文化保护事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与中央政府争夺国家文化保存事权。河北省主席商震就认为省级政府应有处分境内地上和地下的出土考古物件、考古发掘即开掘批驳等权力,何日章则把出土或未出土考古材料视为地方产权。而许多知识分子受民族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央的权力大于地方,中央应该拥有文物的保存权,地下文物应该概归国有,而是不是归地方或者私人,更不允许流出境外。在他们看来,商震的提案是对中央政府国家文化保存事权的质疑。如果一经允许,像“何日章案”一样地方阻挠中央专业团队的考古工作的事情将时有发生,国家文化保存及行政上管理将难以继续,中国的考古秩序也将持续处于混乱状态。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不愿意看见的。于是,在这群有识之士的推动之下,国民政府迅速制定了《古物保存法》。希望以此来确立民族国家的考古秩序,使中国民族国家的考古有法可依。
《古物保存法》中规定“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考古出土文物之事权归属中央政府,确保了中央的国家文化保存事权不被侵夺,初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考古秩序。
(二)外国人不能私自在中国发掘古物
自从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许多西方人便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而且,“自19世纪中业以降,西方考古探险风气大开,且盛于中国西北及中亚一带地区。”[22]他们将中国的古物运出国外,使中国的古物大量外流,英国的斯坦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国际学术界、探险界、考古学界、东西交通史学界可谓‘跨界大师’,其三次在亚洲腹地的探险考古活动及其成果与著述,皆为近代文史学界所熟知。”[23]斯坦因从1900年开始就以探险的名义在中国的西北进行考古,并将古物运出国外。1906年他在尼雅遗址进行挖掘时,收获非常丰富,发现不少祛卢文木牍、三世纪古印度文书和大量祛卢文隐文封泥印、汉代书简等古代器物。这使斯坦因体会到了考古探险的乐趣,自此掀起了一连串的文化掠夺行为。除了斯坦因之外,还有很多的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着考古活动,他们将中国许多出土文物运出国外,这导致了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这激起了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不满,他们迫切想要采取法律的方式杜绝这种情况的再发生。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才是这些文物的唯一所有者,可以说斯坦因的考古活动加速了《古物保存法》的颁布实施。[24]斯坦因在中国一共进行了四次考古探险活动,前三次都成功地将中国的大量文物运出国外,最后一次因为《古物保存法的办法》,才使他将中国古物运出国外的计划未能成功。中国成功拦截了斯坦因第四次考察中通过挖掘、购买和馈赠等方式获得100 余件文物,包括印度手卷、木简、雕塑、陶器等。[25]这是中国逐步建立民族国家考古秩序的表现之一。
而且,西方人在中国进行考古的基础上,产生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考古叙事。近代欧美的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来源都有许多新的看法。他们发表了许多新颖的议论:或谓中国文化发源于安南,或谓来自印度,或谓出于巴比伦,或谓始于土耳其,或谓由埃及东播……”[26]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来源主张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由于这种叙事不仅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建构,而且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只有民族国家才能拥有考古文物和对这些文物进行解释。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人在中国进行考古活动产生了焦虑和羞愧的情绪,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书写和中国的考古活动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进行。于是,他们将考古作为一种准确清晰讲述中华民族历史的工具,用来对抗西方话语体系下的考古叙事。郑德坤就曾说到“近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兴起,其调查、发掘、研究的重心也集中于中国文化来源问题。”[27]张忠培也说“考古学以历史研究为目的,以重建古史作为学科的最终追求,具有强烈的民族关怀。”[28]足以可见,当时受民族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将考古作为对抗西方话语体系下的考古叙事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推动了《古物保存法》的颁布,试图建立中国知识分子拥有特权的民族国家考古秩序。
《古物保存法》中规定“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中央地方或政府直辖之学术机关采掘古物有须外国学术团体或专门人才参加协助之必要时,应先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古物流通以国内限”[29]。这意味着从此外国人和普通民众都不能私自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考古权被中国的知识分子牢牢的掌握在手中,古物大量流入外国的情况也得到了解决。
(三)禁止私人古物盗窃、贩卖和私人挖掘
在《古物保存法》颁布之前,因为没有一部法律明确禁止发掘和贩卖古物,古物的偷盗、贩运非常严重。在1914年就爆发了前清热河行宫古物窃盗案。前清热河行宫(即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是由北洋政府直接管辖的,但是竟然出现热河行宫内所藏的古器物在北平古玩市场上售卖,这件事震惊了北洋政府国务院。于是,国务院立即派许世英亲自去热河行宫查办此事。后来查处是北京城内的天聚昌等商号私通宫内园丁偷盗古玩所致。于是,国务院将涉案的人都押到热河通讯办。根据查办情况得知,1890年前古物的被盗情况已经不得而知。而1890年后,热河行宫古物只要被运一次就丢一次,每次清点都有遗失。之后竟然查出前都统熊希龄督办宫内古物盘点时,因为监管不当使古物流失多件,当时担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因此下台。最后,统计热河行宫被盗窃的古物有107 种,225 件。[30]古物被盗数量之大由此可见。
除了这种震惊中央政局的大案外,偷盗和贩卖古物的小案也层出不穷。全国各地都的文物都被有意和无意的破坏着。葛维汉因“江口考古事件”写给美国领事馆的两封信中提到“四川所有的洞穴型汉墓,几乎全被当地的汉人或土人系统地盗掘过。金、银和玉器、钱币、兵器和一些陶器被盗走,不太值钱的造像和器皿在墓穴的地面上被零乱抛弃,不少都被打坏了。墓穴的门被打开过以后,不少都再未关闭; 不过,偶尔墓顶上的泥土松落,又把墓道口封闭,里面的葬品保留得相对比较完整一些。最近数十年来,这些墓穴又遭第二次劫掠,里面的塑像、陶器或残留碎片基本上荡然无存。实际上,盗墓者均为本地人——农民、流民、摊贩,或者通常不过是些当地孩童实际上。”[31]可见当时中国盗窃古物的情况多么普遍。而且,这些盗墓贼大多没有关于发掘古墓专业知识,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在偷盗古墓时往往对古物多有损坏,也破坏了古墓的本来面貌,后来的考古工作难以继续。而且,除了这种盗墓贼有意地破坏以外,因为公众考古知识和文物保护意识的缺乏,许多“古代的石碑也被损毁,石材被用来修桥、建街道,等等。士兵们挖战壕与政府修路,也破坏了各个时期的墓地”[32],大量的文物被无意间破坏了。由此可见,整个中国的古物采掘处于无序的状态,并且对古物的破坏十分严重。
《古物保存法》中规定“采掘古物应由中央或地方直辖之学术机关为之”;“私有古物,不得转移于外人”,杜绝古物了市场流通,以此来限制私人私自挖掘古物。而且,规定由专业考古人员和团队来采掘古物,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古物偷盗、贩卖和破坏的状况,使中国的民族国家的考古秩序逐步被建立起来。
四、结语
在《古物保存法》颁布之前,中国的考古一直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西方人肆无忌惮地将中国的古物偷运出境;盗墓贼明目张胆地盗窃中国的文物;土匪强盗也不断贪婪地窥视考古现场;地方政府则试图削弱中央政府的国家文化保存事权。随着中国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在安阳殷墟考古受挫之后,李济和傅斯年等人逐渐认识到了文物的重要性。于是,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们试图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考古新秩序。他们在听说《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规定采掘者和国家平分古物后,认为这是不符合民族国家的物权观念。所以立即要求将此草案搁置,并希望中央研究院参与并提出改进意见。最后,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古物保存法》将“平分古物”修改为“概归国有”,并且还规定了外国人不能私自在中国发掘,使中国的文物保护在法理上得以确立。
《古物保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央政府公布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全国性的文物保护专门法,是其后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文物保护法令的母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33]。《古物保存法》首次对“文物”进行定义,指定了古物保存的机构,确定了古物“概归国有”,对古物的采掘和流通都做了相关的规定,是中国法律的一大进步,填补了中国法律的空缺,为中国后来的文物保存法的制定提供了蓝本。“古物”这一原本属于日常生活的用语,逐渐被赋予行政层面的意义,也成为国家行政法令的专有名词。《古物保存法》的颁布,使中国的考古有序可循,有法可依;不仅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文物走向法律近代化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