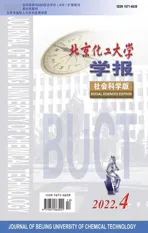《金刚经》中的“V+于+O”及“于”的隐现
2022-03-22王嘉宜
王嘉宜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一、引言
虚词“于”在古汉语中最常见的就是介词用法,常与所介引的对象组成介词短语共同充当语法成分。此外“于”还有一种非常规用法,即位于动宾之间。杨伯峻在《古汉语之罕见语法现象》中提到“关于介词的几种罕见用法”,其中之一就是“不当用介词的而用介词”[1],如:
(1)敝邑之人不敢宁处,悉索敝斌,以讨于蔡。(《左传·襄公八年》)
(2)网漏于吞舟之鱼。(《史记·酷吏列传序》)
例(1)的句义为郑人不敢安居,集齐军力讨伐蔡;例(2)则是“吞舟之鱼漏于网”,其中“讨+蔡”“漏+吞舟之鱼”是典型的动宾结构,宾语在语义上为受事,而其中插入的“于”就是杨伯峻先生所说“不当用而用”。在汉译佛经中亦有诸多及物动词后使用“于”的用例,如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中的“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等例。有关译经中“于”的这一特殊用法,前辈学者已有讨论,如许理和(1977)、梁晓虹(1985)、刘瑞明(1988)、朱庆之(1990)、袁宾(1992)、颜洽茂(1997)、董志翘(2000)、董秀芳(2006)、姜南(2008)等都针对这种特殊的“于”是否用作衬音、是否最早出现在译经中、是否只用在及物动词之后这三个问题进行过探讨,并提出了“于”作“宾语助词”“衬字”“动词后缀”“格尾标记”等多种观点。有关“V+于+O”结构中“于”的产生原因及性质问题,学界目前仍未形成定论。
《金刚经》是我国大乘佛教经典的代表之作,流传广泛,具有重要影响。据记载,《金刚经》共有六个汉译本并行流传,分别是:第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姚秦鸠摩罗什译于 402 年;第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北魏菩提流支译于509年;第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于562年;第四,《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于 592 年;第五,《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唐玄奘译于648年;第六,《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义净译于703年。这些汉译本均翻译自梵语佛经写本,保留着梵语的痕迹及译师的语言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了《金刚经》六个汉译本为语料(1)本文所有佛经语料均取自《CBETA电子佛典集成》语料库。本文有关《金刚经》同经异译及梵汉对勘材料,均取自王继红.《金刚经》同经异译与语言研究[M].上海:中西书局,2018.,对其中的“V+于+O”结构进行探讨,并尝试分析及物动词和宾语间插入“于”这一用法的形成原因。
二、《金刚经》中的“V+于+O”
《金刚经》六个汉译本中,“V+于+O”结构共有87例。根据“于”前动词的及物性,可分为两类。
(一)动词为不及物动词,名词在语义上非受事
此时“于”用作介词,引进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在《金刚经》六个译本中共有25例。根据介引处所宾语的语义又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介引的宾语为动作发生的终点。例如:
(3)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鸠摩罗什)
(4)所有一切众生类摄,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乃至众生界及假名说,如是众生,我皆安置于无余涅槃。(真谛)
(5)善现!譬如明眼士夫,过夜晓已,日光出时,见种种色,当知菩萨不堕于事,谓不堕事而行布施,亦复如是。(玄奘)
此时“于”介引的宾语大多为佛教术语,如“法”“相”“色”“涅槃”等,是抽象意义上的动作位移终点,而动词都是含有“停留”“安住”“陷入”等义的持续性动词。
第二,“于”介引的宾语为动作发生的起点。例如:
(6)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鸠摩罗什)
(7)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鸠摩罗什)
解惠全、洪波认为,“当谓语动词是含有‘获得’‘拯救’‘打发’等义的动词时,‘于’所引进的处所是动词宾语所表示的事物位移的起点”[2]。例(6)中的“取”,例(7)中的“持”(即“受持”)都有“获得”义,其后“于”介引的处所都表示动作发生的起点。
(二)动词为及物动词,名词为受事宾语
“于”插入到及物动词和受事宾语之间,这在六朝之前的文献中是较为罕见的。周一良在《论佛典翻译文学》一文中曾提到:“文法构造方面翻译佛典也曾有影响。例如助字‘于’在先秦两汉的书里没有用在他动词与宾语之间的。史记梁孝王世家‘上由此怨望于梁王’虽然像他动词,‘怨望于’似与‘责望于’用法相同,‘梁王’仍非他动词的宾语。六朝译经才有这种用法。随便举几个例,如竺法护译佛说海龙王经:‘护于法音’‘见于要’;罗什译法华经:‘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罗什译童受喻鬘论:‘得于圣道’。例子不胜枚举,大约最先是在韵文中凑字数逐渐在散文里也流行起来,虽然文人著作里没有沿用,唐代变文和讲经文里却屡见不鲜,而且变本加厉。”[3]周一良认为这种用法是受到佛经文体韵律压制的影响,最初通过添加“于”以衬音,后来译经中的这种用法逐渐影响了变文等其他文学体裁。
《金刚经》六个译本中位于动宾短语间的“于”共有32例,其中罗什本2例,流支和真谛本各6例,玄奘本和义净本数量最多,各9例。例:
(8)佛复告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是行于布施。”(菩提流支)
(9)须菩提言:“不可,世尊!不可以具足色身观于如来。”(真谛)
“行”“观”都是及物动词,“行+布施”和“观+如来”本为动宾短语,但动名间插入“于”,使之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姜南认为,“译经中动名间‘于’的真实身份是引进包含受事在内的语义格标记”[4]。作者通过《法华经》的梵汉对勘,发现动名之间的“于”并非无故增补,而是严格对译了梵语名词的格尾变化,即使是动宾之间的“于”也对应原文中表示受事的业格或属格格尾,所以“于”具有格标记的性质。若依此说,同一译本中,凡是梵语同格名词,是否使用“于”对译应该有着统一的标准。然而,《金刚经》中位于动宾之间的“于”,其使用却存在不确定性:不同的译本,相同的动宾结构,“于”的隐现情况不同;相同的译本、相同的动宾结构,在不同的译句中,“于”的使用仍有不确定性。为了考察这种不确定性是否受到梵文原典的影响,本文通过梵汉对勘,考察了在对应相同的梵语时,动宾结构中插入“于”的情况,发现“于”的使用具有隐现差异。例:
复次,须菩提!菩萨不着已类而行布施,不着所余行于布施。(真谛)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色身圆实观如来不?”(玄奘)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玄奘)
除了动宾短语,不及物动词后使用介词“于”时,即使对应相同的梵语形式,“于”的使用情况依然不同。例:
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鸠摩罗什)
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鸠摩罗什)
可以看到,在梵语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动名短语间的“于”使用情况并不一致,故不能将动名间的“于”单纯看做语义格标记。朱冠明对“于”作格标记之说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首先,梵文形态高度发达,进入梵文句子的任何一个名词都有格尾变化,因此汉译中任何位置上的汉语名词所对应的原典梵文一定都有格尾变化,按姜的逻辑则任何一个靠近名词的词(如各类介词)其‘格标记性质’都会很显著。其次,姜的对勘材料显示,处于动名之间的‘于’对应的梵文名词可以是体格、业格、从格、属格、依格,表明它几乎无所不能,那么它作为一个格标记的意义何在?如果仅仅是为了指示其原典梵文名词是有格尾变化这一点,那又无法解释为何更多的同样有格尾变化的梵文名词在汉译中并不用‘于’来指示呢?”[5]既然动名短语的“于”并非因指示梵语语义角色而存在,那么及物动词后为何用“于”介引受事成分?相同的动名结构中“于”的使用具有不确定性,影响其隐现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本文试图对这两个问题逐一进行讨论。
三、及物动词后使用“于”的原因
(一)译师汉语水平的影响
梁晓虹认为,译经中及物动词后的“于”形成原因之一就是与译僧汉语水平有关,一些译僧虽然通晓汉语,但汉语并非他们的母语,因此难以区分一些细微的语法差异,仅仅“模拟”一些词的用法,从而导致了误用[6]。《金刚经》中“行于布施”的出现就是受到译师汉语水平的影响。“行”在汉语中作动词时有“走”“从事”“实际地做”等多个义项。“布施”是佛教用语,指将自己的财物等分施给他人。本土文献中鲜少有“行+于+宾语”的用例,而在《金刚经》中却有“行于布施”这种特殊的结构。例:
【鸠】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
【菩】复次,须菩提!菩萨不住于事行于布施,无所住行于布施。
【真】复次,须菩提!菩萨不着已类而行布施,不着所余行于布施。
【笈】【玄】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不住于事应行布施,都无所住应行布施。
【义】复次,妙生!菩萨不住于事应行布施,不住随处应行布施。
翻译:又,须菩提啊!菩萨布施财物时,不应执着于事物不应住于任何处所而布施。
动宾短语“行布施”在六个译本中对应三种不同的梵语表达,其中梵语dnam dtavyam,动词为将来被动分词,罗什、流支本翻译为“行于布施”,玄奘、义净本翻译为“行布施”,真谛本则两种表达都有。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1 《金刚经》不同译本中“行+(于)+布施”的梵语对应及隐现情况
“于”在汉语中作介词时,可表被动,其后介引动作的施动者。如《诗经·大雅·松蒿》:“揉此万邦,闻于四国”,意思是“被天下四方所知晓”,“四国”是动作的施动者。但“行于布施”中,“布施”并非动作的施动,而是受动。“布施”对应的“dnam”为体格名词,梵语中当动词表示被动时,体格用作形式主语,而逻辑主语常用具格表示,因此“dnam”并非“dtavyam”的逻辑主语。故翻译为汉语时,“布施”也并非“行”的施动者,语义关系需发生一定的转换,真正的逻辑主语是“菩萨”,即“菩萨应行布施”。“行于布施”的出现,可能是译师在翻译时,用介词“于”表被动的用法来对译梵语中的被动含义,却误将“布施”置于“于”后施动者的位置,导致了“非常规”用法的“行于布施”。后玄奘在重译《金刚经》时,发现了前人的这处误译,并予以修正。玄奘与三位外籍译僧在译语选择上的差异,实则反映了母语背景对译师的影响,正如朱庆之所言,非汉语母语的译者,可能知道源头语的语义,但由于汉语水平有限,无法准确地加以表达,“甚至会将源头语的表达硬性加入译文,使译文中出现一些洋泾浜式的表达方式”[7],“行于布施”可能也是如此。这些译经中不规范的语言成分,也再次印证了佛典语言是经由间接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原典语与汉语混合的产物。
(二)“于”的未完成用法


表2 《金刚经》不同译本中“观于如来”的使用情况
杉田泰史提出“于”具有未完成用法,他认为上古汉语中一些及物动词+“于”的结构,表示动作的不完整,或是说话人在主观内对动作行为持否定或是怀疑的态度。“说话人以为,动词所表示的内容不会实现,是与现实相反的事情。因此该类用法在否定句、反问句里出现得多”[8],在这一结构中,“于”发挥了“间接格”(oblique case)的特性,使得“于”前动词的及物性被弱化。作者在文中举例:
(a)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裹31)
(b)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僖14)
“损怨”是减少对方的怨恨,a中说话人相信“损怨”一定会实现,故及物动词“损”后不用“于”;b中“虢射”相信“损怨”是不会发生的事,对观点持否定的态度,因此使用了“及物动词+于”的结构。
本文统计了真谛、玄奘、义净本中“观如来”及“观于如来”的用例情况,

表3 真谛、玄奘和义净本中“观+(于)+如来”的使用情况
真谛本中两种表达数量差距较大,玄奘和义净本中两种表达数量十分接近,这恰恰说明玄奘和义净在“观如来”中插入“于”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译本中8例“观于如来”,1例用于反问句,7例用于否定句,且其中有4处都作为问答话轮的答句,而问句则都用“观如来否”提问,上下句严格对照。例:
(13)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色身圆实观如来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色身圆实观于如来。”(玄奘)
(14)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玄奘)
(15)善现!若以诸相具足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应是如来,是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玄奘)
(16)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应以三十二大士夫相观于如来应正等觉不?”(玄奘)
义净本几乎与玄奘保持一致,有6例“观于如来”都出现在表示否定的语境中。可见,玄奘和义净本中在及物动词“观”后插入“于”,正是“于”未完成用法的体现,表示说话人认为动作行为不会发生。
(三)佛典四言文体的韵律影响
颜洽茂对六朝译经中位于动宾间的“于”进行考察时,认为动宾间“于”的使用“盖与译经的文体有涉”,“这种固定的格式对佛经翻译施加了影响,为了凑足经文与偈文字数,于是在动宾间出现了人为的扩展”[9]。王月婷也提出韵律是造成动名之间“于”的隐现度差异的重要因素[10]。汉译佛经中有大量及物动词后使用“于”的例子。如:
(17)中有神龙,性急姤恶,有入室者,每便吐火烧害于人。(东汉昙果、康孟详共译《中本起经》)
(18)我亦应彼摩罗耶山楞伽城中为罗婆那夜叉王上首说于此法。(元魏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
(19)我于彼时,为忉利天王,自在治化,受于福乐,尚说善言,以为战具,由善言故,斗战常胜。(隋阇那崛多译《起世经》)
这一用法也影响了其他类型的佛教文献(2)朱庆之将佛教文献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汉译佛典;二,中土人士的佛教撰述;三,佛教文学作品。详见朱庆之. 佛教汉语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8.,如:
(20)一切众臣如教,即竖金幢击于金鼓广布宣令腾王慈诏,远近内外咸令闻知。(《经律异相·舍利弗先佛涅盘(八)》)
(21)吾从养汝,只是怀忧。昨日游行观看,见于何物?(《敦煌变文集·太子成道经》)
汉译佛典是梵汉语言接触的产物,作为翻译类文本,会受到梵语诗学特征的影响,加之宗教传播的需要,译经语言十分注重韵律感和节奏感。为达到声律和谐,朗朗上口,译经的“四字一顿”成为了译经人和诵经人普遍认同的规律,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汉译佛典特殊的四言文体。这种文体刻意讲求节律,通常是四字一顿,组成一个大节拍;其间或与逻辑停顿不一致;每个大节拍又以二字为一个小节,基本上通篇如此[11]。由于译经的这种特殊文体对韵律要求十分严格,译师在译经过程中,为了凑足句式的四音节,往往会增添一些原典没有的成分,或是通过同义连用的方式构造双音节词,这些用例在译经中时有出现,这就为动宾短语之间添衬“于”以构成四言的用法增加了可能。
本文对《金刚经》六个汉译本中“V+于+O”进行考察,统计了相同的动宾结构含“于”及不含“于”两种情况所在句式为四言句的占比,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金刚经》六个译本中“V+(于)+O”构成四言句式的占比
六个译本中,没有插入“于”的动宾结构共有55例,其中能构成四言句式的有9例,占“V+O”结构总数的16.36%;含“于”的动宾结构共有32例,其中能构成四言句式的有7例,占“V+于+O”结构总数的21.88%,由此可知,动宾结构中插入“于”,构成四言句式的能力更强。例:
(22)虽有如是/无量众生/证于圆寂,而无有一众生证圆寂者。(义净)
(23)复次,须菩提!菩萨不着已类而行布施,不着所余/行于布施。(真谛)
例(22)中及物动词“证”和宾语之间用“于”介引,构成了四言句式,使整句形成4+4+4的节奏型,读诵时朗朗上口;而后一小句中的动宾短语“证圆寂”未插入“于”,整个句子无法被四字一顿的节奏完整切分。例(23)中,前一处动宾短语“行布施”未插入“于”,整个小句不符合四字一顿的节奏型,第二个“行布施”中增添“于”以衬音,使第二个小句更符合佛典的四言文体特征。
四、“V+于+O”中“于”的隐现
动名结构“V+于+O”中“于”的使用有一定的开放性。所谓开放性,是指相同的动名结构中,“于”可用可不用,具有一定的隐现差异。这种现象在上古汉语中就已存在,而汉译佛典中更是常见,同一部译经中,甚至是同一句内,相同动名结构间的“于”存在或用或不用的情况,例如:
(24)“唯造杂业无一善事,愿我于彼世界之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怜愍彼等诸众生故,说法教化作多利益,救护众生,慈悲拔济令离诸苦,安置乐中,为彼天人/广说于法。”(隋阇那崛多《佛本行集经》)
《金刚经》几个汉译本中亦有此现象。本文考察了《金刚经》不同译本中动名结构间“于”的隐现情况,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汉译本中动名结构对应的梵语不同。这种不同既可能是梵语同义词的换用所致,也可能是相同词根的形变不同。例:
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鸠摩罗什)
“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 (鸠摩罗什)

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鸠摩罗什)

第二个原因则是受到译师翻译策略的影响。董秀芳对上古汉语中动名间的“于”进行研究时,发现低及物性的动名之间用不用“于”具有可选择性,影响选择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由于“宾语的位置是常规焦点出现的位置,低及物性的动名关系在需要强调名词性成分时也可能将名词性成分临时作为宾语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标志非宾语的‘于/於’自然就不出现了。”[12]也就是说,强调名词性成分对是否使用“于”具有影响,而名词性成分是否需要被强调,则是由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意识决定的。第二,受到韵律影响,即通过“于”的使用起到调节句子长度的作用。文中举《韩非子·安危》的用例:“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同一句式中,低及物性的动词“在”后既有用“于”也有不用“于”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于”的作用就是凑足音节构造五言句。汉译佛典作为翻译性文本,是否需要凑足音节构造四言句式,取决于译师对于译文面貌是否需要呈现四言文体特征的主观选择性,这一现象在玄奘译本中尤为显著。
玄奘所处的初唐时期仍以骈文作为当时流行的诗学特征,以“四言句”“六言句”为多的骈体文风对玄奘的翻译策略产生了影响,加之梵语本身就具有“四音步八音节”的诗学唱诵传统,因此,在玄奘译经中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追求四言文体的翻译倾向。“玄奘译文明显地受到当时十分盛行的骈文文体影响,许多语句在音拍节奏和句型结构上都以工整对仗和平仄形式出现,其中最常见的是四四拍和四六拍”[13],在玄奘的译经中可以看到大量四字一顿的文段:
(25)时广严城/有一菩萨/离呫毗种,名曰宝性,与离呫毗/五百童子,各持一盖/七宝庄严,往庵罗林/诣如来所,各以其盖/奉上世尊,奉已顶礼/世尊双足,右绕七匝/却住一面/。佛之威神/令诸宝盖/合成一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玄奘译《说无垢称经》)
(26)如是最后/世界已前,所有东方/一一佛土,各有如来/现为大众/宣说妙法。是诸佛所/亦各有一/上首菩萨,见此大光/、大地变动/及佛身相,前诣佛所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27)行缘识者,云何为识?谓六识身,一者眼识,二者耳识,三者鼻识,四者舌识,五者身识,六者意识,是名为识。(玄奘译《缘起经》)
“为了凑成句式上的这种对称,保持骈文文体的节奏,玄奘在翻译过程中费尽了苦心,甚至做了一些增益”[14]。王继红对玄奘译《阿毗达磨俱舍论》进行考察,认为玄奘的译经有强烈地追求四言文体的倾向,而他构造四言文体的方式包括添字、复陈、省译、互文等[15]。因此,通过调节动名短语中“于”的隐现来增减句式音节,成为了玄奘构造译经四言文体的重要手段。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现举两例加以说明。《金刚经》的玄奘译本中,“住色”与“住于色”这两种表达并行使用:
是故,善现,菩萨如是都无所住应生其心,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不住非色应生其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不住非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都无所住,应生其心。(玄奘)
何以故?善现!诸有所住则为非住。是故如来说,诸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玄奘)

(30)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不住于事应行布施,都无所住应行布施,不住于色/应行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应行布施。(玄奘)
(31)是故如来说,诸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玄奘)
可见,“V+(于)+O”结构中“于”是否使用,受制于译者的主观选择,译者在动名间插入“于”,是为了调节句式音节,使其符合四言文体的韵律需要,这一点在玄奘译本中尤为明显:部分“V+于+O”结构只在玄奘译本中构成四言句式,说明玄奘相较其他译者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译经四言文体的翻译风格。
又如“堕事”与“堕于事”,二者在玄奘译本中并行使用。例:
善现!譬如明眼士夫,过夜晓已,日光出时,见种种色,当知菩萨不堕于事,谓不堕事而行布施,亦复如是。(玄奘)
梵语patito,词根为√pat,表示坠落、落下;vastu,中性名词,表示事物、财物,玄奘翻译为“堕于事”,指执著在事物或物质之中。这里“堕”的及物性低,含有“到达”之义,“事”为非受事宾语,表示动作归趋的终点,因此应用“于”介引。然而玄奘在第一个“堕事”中加入了“于”,第二个却不加,但两种表达都使所在句子符合四字一顿的节奏,“于”在这里起到了调控音节的作用,体现了玄奘喜好四言文体的翻译风格,正如吕澂所说:“他运用六代以来那种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创成一种精变凝重的风格,用来表达特别着重结构的瑜伽学说,恰恰调和。”[17]
五、结论
本文以《金刚经》六个汉译本为语料,对其中的“V+于+O”结构及“于”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以期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及物动词后为何用“于”介引受事成分;第二,相同动名结构中“于”的使用具有开放性,影响其隐现差异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金刚经》六个译本中87例“V+于+O”的用例进行考察后认为,及物动词后使用“于”的现象可能是受到译者的汉语水平差异,“于”自身的“未完成”用法,以及汉译佛典四言文体的韵律制约这三方面的影响。此外,通过对语料的考察,本文发现在《金刚经》六个汉译本中,相同动名结构之间的“于”,其使用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与动名结构所对应的梵语以及译者的主观选择有关。当译者有意识地使译文呈现“四字一顿”的文体风格时,就会通过调节动名结构中“于”的隐现以增减音节,使句式满足四言文体的韵律要求,这在玄奘的译本中尤为明显,突显了玄奘强烈追求译经四言文体的翻译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