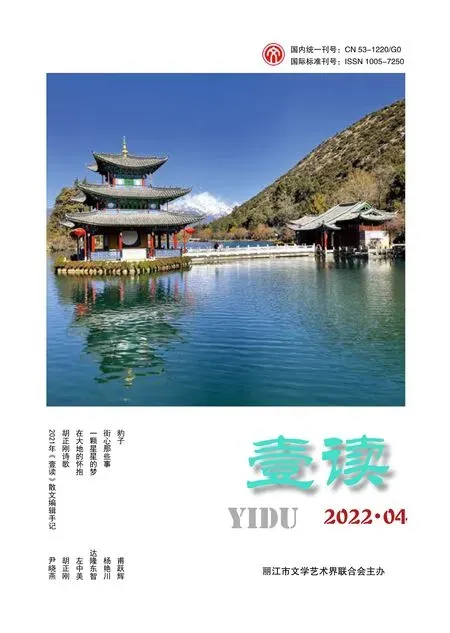又见故乡油菜花
2022-03-22张一骁
◆张一骁
人生之始,始于故乡,故乡是我生命开始且赐予我姓氏的地方。那里有犬吠鸡鸣,炊烟房舍,山川河流,菜畦地壑,以及爬满皱纹的乡里乡亲。他们注视着我长大,并逐步把我引向生活,我也在模仿他们,以求在成长的时光里获得对自身重新定义的可能。所以可以这样说,故乡在,根就在,根在,脉就在了。每逢清明节,身在异乡的我总要寻路回家,回去寻找记忆的支点和现实的依附,赶赴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重逢与团圆。
往事可追,印象中的清明总伴有成片成片盛开的油菜花。在故乡,油菜是重要的农作物,一来生长周期短,二来菜籽可以榨油,帮补家用。两个优点自然得到种植的人家的青睐。油菜大抵年前播种出苗,年后现蕾抽薹,待到枝繁花盛,清明便如约而至。小时候,清明扫墓需要穿过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现在也是,路径未曾改变。我和兄妹几人三步并两步地紧紧跟随在父辈的后头,身背竹篾编织的小背篓,背篓里装满祭品,带玩带耍,行走在乡间小道。
小道旁是连片的油菜花田,一片连着一片,从山洼子深处延伸到山脊,山脊背后依然是明晃晃的油菜花。远远望去,俨然是铺陈开来的巨幅油画,被颜料晕染成一畦畦温暖的金黄,加上有流淌线条般的地垅,或蜿蜒、或柔长,勾勒出故乡若隐若现的轮廓和肌理。“春和三月绽花黄,拂垅风来四面香”,馥郁清幽的油菜花香糅合着湿润清新的泥土气息,凝芳而来,沁人心脾。
路上我们偶尔会驻足,细看蜜蜂孜孜不倦地奔忙花丛,扇动翅膀的嗡嗡嗡声不绝于耳,蝴蝶翩跹飞舞,有些三心二意。我们几兄妹蹲下身子,在油菜花地头寻找类似于豌豆的一种开紫色花的豆科植物,有的地方叫它绿肥,它鼓囊的豆荚可以做巴乌,剥开豆荚子,把一颗一颗圆乎乎的豆子取出来,再掐去尾部,巴乌放在唇部,呼气,巴乌的呜咽声响起,幽咽的声音此起彼伏,童年的我们似乎就抓牢了整个春天。
那时我们尚不懂清明节更深层次的含义,记忆里依旧是那翠绿绵延的青山,冰凉清澈的泉水,干净透彻的蓝天,金黄如染的油菜花,平实质朴的大地,还有那置身其中的惬意。后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油菜花,大脑里就不自觉显出清明的情境。随着生活慢慢往深处走去,我不仅关注油菜花,还为了弄清楚“清明”的来由,特意去查阅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资料,懂得了“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淡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既有生之欣荣,逝去的悲凉是无可避免的,这是清明给我们带来的另一层启发和思考,也是光芒和暗影,火焰和灰烬,慰藉和残缺,疑问和困顿。祖辈们一辈子扎根在这片土地,在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枝散叶,结蔓生花,耕耘天与地,察尽人间悲喜,循环往复,过着平凡且平淡的生活,他们或许不悲伤。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年代,他们依附土地,画地为牢。以生活为圆点,就注定了人生的半径会很短很短,他们无需探寻山那边是山,是荒原,或者是海,他们甚至对海没有任何的概念,但他们是最了解蕨类植物的内心是如何同时领略光芒和阴影,如何面对灰烬和火焰的。在云贵高原,祖辈们本身信奉的只是河流,山川,草木,虫蚁和鸟兽,并如福建渔民信奉妈祖、西藏人民信奉雪山一样忠诚。
待到灯枯油尽,日薄西山,他们又把自己的生命半径再度缩减到更短更短的点,换句话说,坟冢逐渐会成为圆心。他们生前所热爱的土地,最后温暖安详地拥抱了他们,这就是祖辈在故乡最后的定格和缩影,如老照片,泛起斑驳的霉印,如锈迹,逐渐掩盖了金属的光芒。至于我熟悉的那些较为年长的乡邻乡亲,有的未能看到我长大成人,就从人间退隐,有的目送我离乡,却未能等到我回乡,陆续添作新坟,终与泥土为伴。只有故乡的土地包容着、隐忍着、沉默着,一次一次看尽人世变迁所演绎的种种仪式。
我一直在心中告诫自己,懂得了清明,才会懂得守望。“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客居他乡,我仍然会时刻眷念赐予我生命、姓氏和粮食的那片生养之地,像胎记着急找到肉身一样的惶恐和慌张。无论走多远,隔山隔水,都要记住回家的路,似乎忘记故乡的山水,肉身也会成为浮萍,成为无根野草,摇摇晃晃地在人间飘摇。工作之后,每年清明,我都要回一趟老家。每次回去,依然会选择在清明期间,跟随父辈去扫墓。有孩子后,也带着去,跋山涉水也必须要让孩子知道这样的传承和仪式,要让他以后行走人间,不忘根,不忘本,不忘山河,不忘回家。
这样的记忆已经在我脑海填充了三十多年了,不知不觉便已到而立,稍有些许中年危机。扫墓途中,我不经意间就会走到了父辈的前头。他们老了,步幅小了,步子也慢了。看着他们日渐佝偻的身姿,像一根扁担,躬出了和谐的弧度,自然就想到日薄西山,想到他们以后也会停止说人间的话,停止关注人间的风声,成为被祭祀的对象,心里不禁酸楚起来,泪水欲流,又忍了回去。是的,我们不必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尚未到来的痛苦,但当我们真正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应该表现出像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这才算得上是一个了解人生幸福和灾祸并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变故的人。他们的老去,我们只能接受,只能顺应,只能言和,阻挡不了。
我们就这样走着,谁都牢记扫墓熟悉的流程和做足祭祀的准备,依然会背着竹篾编织的背篓,背篓里装满祭品,祭品之外,还装满了一脉相承的缅怀,感恩和思念。我们依然穿过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海,行走在密集摇晃的金黄里,恰有几分与去年的自己重逢的味道,油菜花好像也“懂事”了很多,大片大片地开着,彼此不说话,不寒暄,不许诺,沉默不语。
途中偶尔也会遇见一些熟人,面孔不一,说上几句客套话。离去,赶紧追问父辈,“他是谁家人?”“与我是什么辈分关系?”“我们该如何称呼他(她)?”越来越伤感的是,我的父辈只是回答“不知道!不清楚了!”他们终于也变得模棱两可了,非同辈人,只能给出个大概,这是一个悲伤的信号。
故乡的那轮明月,已经不是那年的明月了。
按照老家清明扫墓习俗,割草,培土,挂飘,上香,摆供。倒两杯薄酒,烧几张纸钱,燃一挂鞭炮,整个过程严肃如仪。面对先祖,我们恭肃静默,以此慎终追远,缅怀先人,以尽思时之敬、悼念之情。清明是把钥匙,打开了故乡尘封的过去,填补了岁月雕刻的痕迹。我们都明白,每个人心中又何尝不是背负着一块墓碑,在行走中不停地进行着自我书写,自我记录,只是在“卒于”部分,留下空白。
面对各个大小不同、新旧不一的坟冢,我们在心里默念,但愿“里外”都有人间,烟火深处,我们还能对视,祈祷,护佑,互为彼此寻找出路和生路。
整个过程平静而深沉,如同坟头飘飞的白色“坟飘儿”,随风飘荡,自然而显眼。这兴许就是清明扫墓的意义,能够让我们在自我盘诘或与故乡的对话中,不断寻找情感的寄托和归属。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审视里,不断寻找自身的来路和归途。以烙印般的明晰让我知道生于此,根植于此,需对故乡故土故人心怀感恩与爱,并要坚韧持久,沿袭不衰。
扫墓结束,我们小辈子俯身,磕头,算是在今年与长逝的长辈作最后的告别,再把饭食一一收回背篓,像是拾起洒落一地的去岁之光。心是早已是空落落的了。沉重深郁,独自消化悲伤。“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想,清明节特意选在四月,大抵是先人考虑到后人扫墓会有太过悲切之因,所以心生恻隐,用“万物复苏”为人们心头的“清明雨”撑开油纸伞,以新生蓬勃的喜悦和希望蕴藏的期盼来稀释后人心头的悲戚,抚平揉皱的惆怅,充盈前行的力量。
返回路上,我们依旧穿过那片油菜花田。山风拂过,摇曳的油菜花在阳光下闪烁跃动,扩充起生命的张力。天空朗润通透,田畴春意盎然。路上来往的乡邻也渐次多了起来,大多是扫墓结束回家的。没有了来时的匆忙,每个人脚步逐渐放缓。沿着田埂,顺便看看油菜、蚕豆的长势,回顾一下去年那些“风调雨顺”的祷词是否在这些生灵上得到应验。或是用小镰刀掘一篮子荠菜,再采几把蕨菜,回去尝尝春天的味道。
孩子们还是无忧无虑地追逐嬉戏,乐此不疲。或追赶蝴蝶,或捕捉浅黄色的蚂蚱,或争执着谁摘得的蚕豆更多更饱满,或紧攥着一把刚采摘的小野花……恍惚又回到过去。
一代人的成长意味着一代人的老去,这是生命的自觉与传承,就像故乡的油菜花,也会凋谢,碾落成泥,结出饱满的果实,完成生命的救赎与使命。待到来年清明,这片土地,又将会有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齐刷刷地绽放,勃发出诱人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