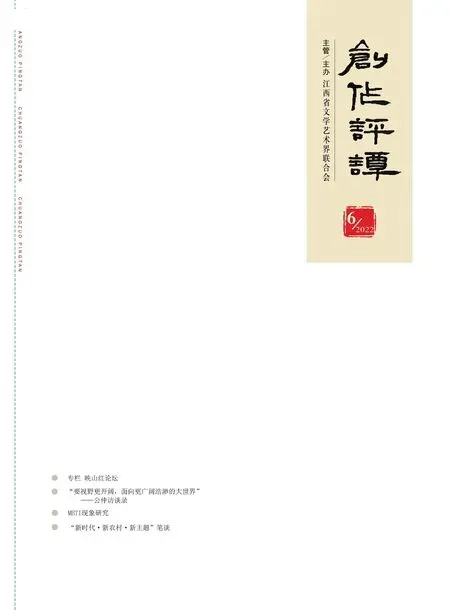“要视野更开阔,面向更广阔浩渺的大世界”
——公仲访谈录
2022-03-22访谈人李洪华
◎ 访谈人:李洪华 吴 敏
李洪华(以下简称李):陈老师您好!很高兴邀请您做这次学术访谈,今年是您的八八米寿,首先祝您身体健康、学术常青!1954年您第一次以“公千里”的笔名在《江西日报》发表文学评论,迄今已68年了,当时您在南昌三中担任政治课教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开始写文学评论的?能否请您谈谈当初从事文学评论写作的经历和感受。
陈公仲(以下简称陈):在访谈前我想先说几句话:我刚刚过了生日,已是八八老人了。现在做这命题作文,问卷回答,实在难以胜任,勉为其难了。所以,难免会说漏嘴说跑题,甚至答非所问。不过,我一定会说真话,说我想说的、我能说的话。敬请体谅,谢谢大家!
我是1952年参加工作,在江西省教育厅政治辅导员训练班(现南昌师范学院前身)培训半年,1953年春即分配到南昌五中教政治,任政治教研组组长兼共青团书记。1953年秋,五中与市立中学合并,定名为南昌三中,我即到了三中,仍教政治和做共青团的工作。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好写点文章。起初主要写些教育、语文方面的文章。第一次写文学评论是在1954年。那时正在上映一部故事片《哈森与加米拉》,青年学生们都很感兴趣。《江西日报》社记者来校采访我,谈共青团工作,他谈到学生看电影的事,突然兴起,约我写一篇评论《哈森与加米拉》的文章,说可以引导学生们欣赏影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我就欣然答应了。真没想到,我写的文章很快就发表出来了,还配有电影照片,在社会上有了些许影响。这让我产生了一点点的成就感,也鼓励了我在这方面继续发展下去。1955年干部政审,由于我海外关系复杂,被认为不宜做政治工作,建议改行从事其他教学工作,我即选择了语言文学。我的父母都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大学工作。我幼年时期家中就有专门的书房,中外各种文学名著十分齐全。从小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长大,我产生了对文学的兴趣。1955年,我被送入江西教育学院进修语文。1957年“反右”前夕,我又回到三中教语文,1959年后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一直教高中语文。我对语文写作抓得比较紧,还主编了一本《中学生习作选》,每篇都有老师的点评。此书流传很广,几年前,三中老校友还在广西某县档案馆发现了一本。当时三中名气超过师大附中,连续八年全省第一名。1963年高考作文题目是《当国际歌唱响的时候》。我们之前在学校复习练笔中,多次以“当……的时候”这样的题型让学生练笔,怎样夹叙夹议。那年三中高考语文成绩全省第一名,特别突出。
这说明当时我教语文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的语文教学特点,一是狠抓语言文字基本功;二是强调时代感,强调结合现实,强调人文关怀。到了大学之后,我选择了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现如今很多文学理论包括博士论文都与文学创作分割。文学理论从何而来?就是从大量文学作品中总结规律提升而来。可现在,文学理论是从抽象的概念而来,写出来的东西跟文学创作没有什么关系,空对空。我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强调文学理论必须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才有实际指导意义。但是现在依然是理论还是理论,创作还是创作,两者分割。现在作家极少看文学理论。我接触的许多知名作家都说,他们从不看什么文学理论,看了这些都无法创作了。
“文革”前我一直在南昌三中,“文革”中开始下放,大概1968年离开三中。开始是下放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进行劳动改造,后转到新建县生米公社。1973年我调到江西大学(现为南昌大学)中文系。当时大学刚刚复办,就读的大多是底层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不少学员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读过高中的并不多。当时开门办学,就是下农村收割插秧,在实践中学习。直到“四人帮”倒台,我才开始教写作,教写毕业论文,同时带学生们到报社、出版社、文联去实习。还带学生们沿秋收起义的路线做调查,写了一部《秋收起义史话》。真正的当代文学教学是在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之后。
李:请您谈谈从中学老师到大学老师这一身份转变对您当时以及此后学术道路所产生的影响。
陈:中学教学主要是文本教学,大学则主要是宏观、系统的文学教学,实际上内容没有改变。中学主要是一些当代文学选出来的经典散文、短篇小说,当然还有不少古文。到了大学内容和视野就更加开阔。
1977年我开始正规地研究当代文学,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研究。也接触全国范围的文学研究动态。1978年就走出去,到东北、武汉、广东、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另外《文汇报》举行了一次关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讨论。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文汇报》,很快就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外刊物发表文章。从中学到大学转变主要是视野开阔了,由文本单篇的分析上升到完整地把握全国以至于全球的当代文学动态分析。
在《文汇报》上我第一次用了“公仲”这个笔名。说起我的名字还有故事呢:我在家五兄妹排行老三,正好在中间,小名叫“中中”。发蒙读书要个学名,按辈分是“公”字辈,图简单,就把我那“中”字加个人字旁就叫“陈公仲”了。可用了一两年,父亲想想不对,古文说伯仲叔,仲是老二,孔子排行老二才叫孔老二,可我是老三呀!不能叫“公仲”,干脆谐音叫“陈公重”。于是,我这名字就用了一辈子了,户口、身份证都叫“陈公重”。写文章用笔名,我就把“重”字上下拆开,叫“公千里”。可在“文革”时期,学校校长被打成了“走资派”,我是他手下“四大金刚”的老大,我的名字就成了“牛鬼蛇神”,被批倒批臭。“文革”后期,我来到了江西大学后给《文汇报》投稿,报社在发表文章之前要对作者政审,要单位盖公章认可才行。我当时心有余悸,不敢用那曾是“牛鬼蛇神”的名字,就又想到我曾用过的“公仲”名字。江西大学就在我文稿作者“公仲”的名字上加盖了公章。文章发表了,“公仲”这笔名就此一直跟随着我,以至于许多人把我原名都忘记了,甚至我的有些稿费都因此名与身份证不符而领不到。我这名字的变迁,既反映出了我从事文学道路的里程,也折射出我们国家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印迹。
李:您最初主要是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积极参与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讨论,出版了文学评论集《当代文学纵横谈》,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能否请您谈谈20世纪80年代亲历过的文坛状况和研究工作。
陈:当时上饶师范学院缺当代文学老师,邀请我去那里教两个月,让教务处调课,把当代文学课集中到两个月内。这期间我发现他们没有教材,就带了两位高才生,一边听课一边做记录。之后整理出来,编了个小册子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纲要》。1981年在庐山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将这本书散发了。当时,代表们踊跃排队,要这本书。不久,这本书受到批评,说这本书“公然与邓小平文艺政策对抗”。当时,我比较紧张,不少文艺界朋友都不敢跟我说话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朋友来电话问我近况,我就把此事说了。没想到此事传到了中宣部。后来中宣部部长王任重的秘书致电省委宣传部,表示不要搞大批判。省委也开了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俞林代表组织与我谈话,要我正确认识此事,让我自己写一个检查,解释说明此事,把我的检查也发至全省县团级。此事就这样有惊无险过去了。
后来当代文学教材,由十几个院校联合编写,分别作为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辅导教材;又把当代文学优秀作品进行选编成书,供学生们阅读。我当时分担的是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部分,而我个人仍觉得不能畅所欲言,就决定独立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一书。这本书是当代文学第一部以个人名义编写的教材,丁玲为其写了序。这本书的初稿我给丁玲看了,她觉得有特色,就推荐给了几家出版社,可那几家出版社都担心发行量上不去,怕赔本,不敢接受。我就给了江西教育出版社,他们表示可以出版,但要我保证能发行一万册以上,我二话没说就签约保证。我找了个书商去操作,第一次印刷就发行了一万。时值全国专升本考试,急需要教材,书商有全国发行渠道,不断催着要书,一两年下来,据说竟销售了五十万册以上。书商不让我知道销售情况,怕我要分钱。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钱,书籍能出版,有人读我就心满意足了。
1980年代,我参加的学术活动有两个重要的会议。一是1980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学理论会议,后来主持人觉得名字太大,容易惹是生非,就改名为全国高等院校文学理论研讨会。那是拨乱反正后第一个全国性文学理论会议,有中国社科院、人民日报、中央党校、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以及不少高等院校校长、专家、教授参加。当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是陈荒煤(文化部副部长,当时兼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省里总管此事的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李定坤,会议秘书长是省文联副主席矢明。我是会议副秘书长,分管接待联络和简报。李定坤对我说,派两个人给你做助手,一个是文化厅办公室廖主任,一个是省文联的刘仁德。我们把庐山当时所有的宾馆饭店全包下来了,还不够住。我把一个宾馆的小会议厅改成了寝室,搬来了七八个双人床,安排一些年轻的代表来住。记得当时余秋雨气呼呼地来找我,说这里条件太差,要求换个住处。我不认识他,只见报名表上填的是教师,没有职称,又较年轻,就安排在这里住。我见他很有些情绪,还是耐心地解释说:“实在是来的人太多了,临时加了些床位,请原谅!暂时将就着住下吧。我也和你们住在一起。”说实话,当时庐山条件的确很差。刚刚开放,庐山的接待宾馆水电设备尚待更新改造。一个别墅,三五间房,住上三五个老教授专家,一人一间房,有地毯、沙发、会客厅,但只有一个卫生间。吴强说,早上上厕所要排队,真难等呀!特别是用水没保证,自来水时有时停,热水一人一天一瓶。陈白尘说,我一盆水,先洗脸,再洗脚,还要留着冲厕所。丁玲、陈明、公刘先期到达,是以疗养名义安排在军委总后五一疗养院,也是两人共用一厕所。病房还没有写字台,丁玲就用纱布绷带结成绳子,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在胸前腰间兜着一块长方形木板,成了写字台。丁玲笑着说,这是在北大荒学来的呢。尽管如此,到会代表仍络绎不绝,人满为患。
全国正式代表四百多人,其中有丁玲、陈明、王若水、王元化、吴强、徐中玉、钱谷融、侯敏泽、何洛、吴介民、江晓天、缪俊杰、阎纲、王西彦、黄秋耘、公刘、梁信、白桦、陈白尘、叶至诚、顾尔镡、陆文夫、高晓声、俞林、李定坤等人。大会会场设在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的会场旧址,讨论的分会场就分散在各个宾馆。会议提出,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改提为文学为人民服务。丁玲发言,说不提为政治服务,但必须认识到文学是脱离不了政治的。她以自身的文学创作经历,来说明此事。她还是那样火气十足,态度鲜明。而吴强是用《红日》创作实例,来印证政治干扰过多,会叫作家无所适从。他写孟良崮大捷后,战士骑着缴来的高头大马,穿着国民党的将军服,挥着指挥刀,耀武扬威地在战场上兜风吆喝。这本来是表现战士胜利后的骄傲、欢快,蔑视敌人的一种豪情,可后来被批判为“美化国民党军队、丑化解放军战士”,只好删除,再加几句胜利的口号,小说就干瘪乏味了。现在又要改回来,真叫出版印刷单位不胜其烦了。分会场讨论得更加有声有色,丰富多彩。大会上的论述都收入了简报,再散发给各个会场交流。代表们对这些简报十分满意,我也很感宽慰。出简报是我再三坚持的,我也是从北京学来的。我有幸在北京看到过八届三中全会的大量简报,叫我大开眼界,思想大为解放。文学界也应该解放思想、加强思想交流才好。
另一个重大的学术活动是1981年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召开的全国当代文学研讨会。我本不愿连年开此种大会,太劳累了,可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学会会长王庆生兴致盎然,坚持要开,认为这次会议对于“文革”以后全国当代文学研究如何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会址仍选在庐山,这次参会人员仍有三百八十人之多,比上次文学理论会略少,可对当代文学研讨来说,也是空前的。全国大专院校教当代文学的教师,几乎都有代表赶来参加,而全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简直可说是一网打尽了。《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大家有意推选他为学会会长,他也乐意接受,也决定亲自到庐山来。于是此事就这么定了。这次会议讨论也十分活跃,出了大量简报。这些简报,可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极可贵的资料。我完好保存了,到时可捐赠给文学资料馆。
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会议提出了两个“五七”的观点。一个“五七”,是指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现在改正了,重新绽放出了绚丽的鲜花,如姚雪垠、邓友梅、王蒙、张贤亮、从维熙、陆文夫、高晓声、白桦、邵燕祥、公刘、刘绍棠、流沙河等,非常值得研究;还有一个“五七”,就是根据“五七”指示,上山下乡的知青里,涌现出了大批年轻作家,如梁晓声、王安忆、张抗抗、孔捷生、卢新华等,他们写出了更多大放异彩的作品,然而也有不少的争议。社会上对这两个“五七”的作品都十分感兴趣。在庐山,游客和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当代文学会也很好奇。于是会后,我们干脆在庐山正街邮电局坡道口摆了个地摊,专卖那些“重放的鲜花”和有争议的正式出版的文学作品。我和同事卢启元两人大大方方吆喝着,这绝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彰显新时期文学的新成就、新景象。游客观众还真不少,成了当时庐山的一个新景观,被传为庐山旅游的一段趣闻:教授山上摆摊卖图书。
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您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从《台湾新文学史初编》到《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从《离散与文学:陈公仲选集》到《八零后文存》,都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请您谈谈当初进行学术转向的主要原因,以及这一转向对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陈:1973年我给工农兵教学,带了一批学生进行党史研究,到了秋收起义文家市、武汉等地,出了些关于秋收起义、湘南暴动等的小册子,直到1977年开始教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研究台湾文学,因为总觉得讲中国当代文学,不讲台湾文学似乎少了一些什么,何况,当时台湾文学在文坛已经十分火热抢眼了。艾青曾在我编写的《台湾新文学史初编》的序言中说:“中国新文学史,没有台湾,怎能算完整,怎不觉遗憾?”
当初广东、福建、北京、上海一些人已经开始研究台湾文学,几次台湾文学的学术会议促使我们开始研究台湾文学。以前不知道除了中国大陆以外还有这么一个强势的文学群体,如王鼎钧、郑愁予、洛夫、纪弦、痖弦、白先勇、陈映真、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余光中、黄春明等,他们在海外文坛名声和影响已经很大了。
1970年代后期我开始接触台港文学,觉得台港文学很有水平,价值观、艺术表现手法比较新颖。我邀请他们到江西大学来讲学,比如陈若曦、於梨华、施淑青、赵淑侠等。他们来校讲演,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讲台地下也坐满了人,礼堂窗户都爬满了人,场面非常壮观。我从77级开始,就单独开设了台港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选修课,并在全校开了跨学科的选修课。每次上大课,一个大教室都挤得满满的,后面还站了不少旁听者。我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主要是来自新鲜感。之前一直觉得很陌生,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另一点就是通过文本分析,深知他们的艺术表现能力、文学功底、文化传统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他们又多一重海外文化的熏陶。我认为,一个成功的作家必须要有多元文化的融合,靠单一的文化单枪匹马地闯荡,是很难走得坚实稳重久远的。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一个趋势,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除了有本土传统文化,还要吸收西方多元文化的营养。1990年代初,我曾写过一篇长文《走出西部文学小农意识的阴影》,当时是施战军从废纸堆里发掘出来,在《作家报》刊登了一整版。我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西部文学有了一些批评,提出要走出小农意识阴影,要有现代意识、多元文化。莫言就有一个特点,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不懂外语,但他的优点是眼界高远,读了很多海外翻译的文学作品和评论书籍,打开了视野。他是个极具个性的作家,观点独特,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我之所以欣赏海外那些优秀的华文作家,就在于他们价值取向多重丰腴,文学修养深厚,语言文学基础扎实。能出国留学创业的人才,大多有高学历,术业有专攻,凤毛麟角。我是特别关注他们的作品,也热心与海外高校学术交流,在学术研究上一直尽力保持着新锐超前的年轻状态。
李: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华文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有不同程度的担忧和质疑,而有些中国现当文学史著述则把“海外现当代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框架。您如何看待上述担忧和质疑,以及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处理方式?
陈:国内搞当代文学的一些人,对海外华文文学不读又不以为然,认为其水平是二流的,瞧不上。另一个是怕触到政治敏感问题,采取规避态度。如每年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评选,很多人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不应该参加国内排名,我却尽力争取。经过几年的努力,才取得了共识:海外作家作品只要在国内杂志上发表,在国内出版社出版,就可以参评。条件放宽以后,无记名投票,张翎、陈河、陈谦、沙石、施雨、吕红、曾晓文、张惠雯等都进入过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
刚刚讲到对待海外文学态度,一是歧视、带有色眼光,二是政治敏感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我看,一是研究机构研究部门要将海外华文文学与当代文学放在同等地位加以认识与对待,要平起平坐,要平等;二是评奖方面、科研经费方面、设置学科方面都要给予支持,对待一些敏感问题要宽容一些。值得欣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已开始有所动作了。世界华文文学已列为重点项目,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已被定为一级学术单位(序号:318号)。
李:您认为,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新生长点,它为世界华文文学注入一股新鲜血液,并正逐步形成了一支新生的主力军。能否请您谈谈这一新的生长点,它的成就超越了当年的留学生文学吗?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如今新移民文学肯定超过了当年的留学生文学。我们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其实一开始就是从留学生文学起步,但经过这四十年的发展,很多研究现在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就不行了。当年研究留学生文学的研究者不是走了就是老了,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到今天大量研究者搞来搞去还是研究陈映真、白先勇,很少听到研究他人的声音。陈映真、洛夫走了,耶鲁大学的郑愁予退休多年,可现在与过去相比似乎发展变化不大。而如今新移民文学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越了留学生文学。当年留学生文学主要思想观念是乡愁,表现的是忧伤、失望、痛苦的呻吟。而新移民文学所表现的不完全是这样,既有乡愁,也有拼搏与奋斗、信心与希望。在国内文坛一些研究者看来,新移民文学较肤浅,表现不够深刻,认为在异国土地上扎根不够,文学底蕴不深厚。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他们对新移民文学阅读甚少,知之甚微。新移民文学作家大都有高学历,语言文字功底深厚。他们既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又有海外生活的特殊经历,还有多元文化熏陶,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学世界,精彩纷呈,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感真切生动。他们对文学是写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认识会更为执着深刻。
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主要依托国内的发表平台和读者认可,能否请您谈谈这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写作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
陈:这个是绝对有影响的。不少华文作家甚至把在国内发表作品当成了个指挥棒,他们往往揣摩着国内报刊、出版社的意图喜好来选择自己创作的题材内容、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很大一部分作者以国内发表出版为荣,以国内发表出版来衡量其创作的成就。这样就改变了海外华文作家创作的初衷。能在国内发表出版,是很好的选项,但是,这不能是唯一的选项。创作的终极目的,是力求不朽,为广大读者,为子孙后代,为人类留下不朽的精神财富,也是对自己一生的经历,思想情感、梦想追求有一个交代,不要枉度此生。现在,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也有了新的出路,海外出现了不少民间的报刊、出版社,而且很有发展的势头。记住,现在面对发表、出版以至于评奖的诱惑,别忘记作家哈金的一句话:“我们应该直面于不朽!”
李:您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建设,世界华文文学已经相当成熟、完整,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大多研究未能突出海外华文文学特点。能否请您具体谈谈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相关研究应如何突出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
陈:先谈谈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外部情况。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原来挂靠在中国作家协会,属于国务院侨办直接领导,现在统归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会长、副会长由统战部委任,在经费上、人员安排上较之以前更收紧了。所以现在学科研究要有突破发展,则更需要民间力量学术支撑。正如近日我在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寄语中所讲,要突出我们学会的民间性、学术性。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发展主要从民间性、学术性出发来发展,不管外面如何,仍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李:您从事学术研究已经超过一个甲子了,至今仍然手不释卷,乐此不疲。是什么让您始终保持这样的学术热情?能否请您谈谈在治学之路上对您产生重要影响的学人和著作?回顾过往,您对自己的学术人生有哪些感到欣慰或者遗憾的地方?
陈:保持学术热情主要是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要保持自己生命的延续就是要顽强地工作下去。对我来说,就是要不断地读书、思考、写作下去。现如今有种观点是:年纪大了,需要注重保养,少管闲事。可我以为要有事干反而更能延年益寿。现在老年人一起来就有人搀着,一走路就有人扶着,这样是不可取的,就应该像训练小孩一样,让他自己走动起来。搞学术也是如此,有学术研究就有了活力,脑子也不至于痴呆。学术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无法割舍,因此才能时时新鲜,永葆青春。
我在治学道路上受到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一些传统的文艺观念,如恩格斯的论著。恩格斯对文学创作主张“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以及“作品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而不是搞什么“三突出”,不是搞“主题先行”。我认为恩格斯的观点没有过时。另外当年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妥斯陀耶夫斯基三个“斯基”的文学观念对我还是有较大影响。在论著上,对我有影响的有触动的是夏志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部书实际上是夏志清在耶鲁大学的英文博士论文。1987年我到美国,有幸与他交谈,他送了这本书给我。这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他的书突出了张爱玲,对张爱玲有些偏爱,也说明张爱玲作品有她自己的特色。其次就是沈从文、钱锺书以及张天翼。对这些人的研究与评价与国内非常不同,他的价值观以及评价手法对我影响比较大。我后来创作的几本文学史书是受了他的一些影响的。
令人欣慰的地方,首先是我觉得当代文学的几个“史”差不多都搞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台湾新文学史初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这三本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反响较好。《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销量突出。冯牧在《文艺报》上撰文认为《台湾新文学史初编》“在同类书中,属上乘之作”。《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已有了国际影响,我在韩国开会,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说,我们还在用这本书作教材呢。第二个值得欣慰的是在国内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以及新移民文学的研究做了一份应有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先后开了三个大型的国际会议,把欧美澳及东南亚的主要华文作家都聚集一堂,共商发展华文文学之大事,结集出版了三本文集,在全球有着一定的影响。第三个成就感就是参与主持了六个重要的文学会议:一是1980年的全国文学理论研讨会;二是1981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三是1993年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正式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定名为世界华文文学,是华文文学研究公认的一个转折点、里程碑;四是1997年中国小说学会全国年会(会上我被选为小说学会副会长);五是2010年在南昌举行的首届中国小说节;六是2014年首届新移民文学研讨会。
遗憾的是后继乏人。20世纪80年代,华文文学研究盛况空前,华文文学研究成为我们学生毕业论文的热门选题,但近些年来研究者日渐减少。研究不是追求热闹,而应该追求不朽。有些学者认为华文文学必死无疑.一些海外二代、三代移民慢慢失去了母语,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只能依靠老人,目前可以说是日渐式微,但还不能认为必死无疑。因为移民是一代一代前赴后继,不会中断的。有新生代移民,就必然有新移民文学。以新移民文学为主体的华文文学,前途是光明的,不必悲观。世界华文文学必定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但需要有更多人的坚持不懈。眼下困难还是蛮多的。但有亿万华人为后盾的华文文学绝不会死,只是有些时候可能会寂寥,有起有伏,有高潮期也有落潮期,这是正常的现象。
李:长期以来,您一直呼吁学界以更多的热情关注海外华文文学,鼓励年轻学者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作为前辈学人,您对将要或正在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有些什么建议?
陈:研究者要耐得住寂寞,要坚守不移。赚钱是不可能的,搞文学事业本来就是孤独、寂寞、清贫的,要有坚守的牺牲精神,要追求不朽。
李:作为一名扎根于赣鄱大地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您在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同时,也长期关注江西本土文学创作状况,撰写了大量关于江西作家创作的评论文章。能否谈谈您对近年来江西文学创作的印象及其未来发展的期待?
陈:江西文学事业自古以来是非常发达的。民国时期梁启超曾说,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两个省是江西与四川。新中国成立后,江西有突出影响的作家不多。有位江西大学的前辈胡旷,代邓洪写了个《潘虎》,全国影响不小,号称是“中国的《夏伯阳》”。戏剧创作上有石凌鹤,小说创作有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大学有“三胡一相”(胡平、胡辛、胡金岱与相南翔),我在《光明日报》上戏称为“三只老虎、一头大象”。现在年轻一代有位阿袁,是全国难得的一颗文坛新星。
江西创作要发展,就要走出二三流城市的局限,正如我写的电视剧《井冈之子》中的人物独白:“该下山了,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与巨大的海洋。”江西应该要有个“下山意识”,要视野更开阔,看看外面的风景,面向更广阔浩渺的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