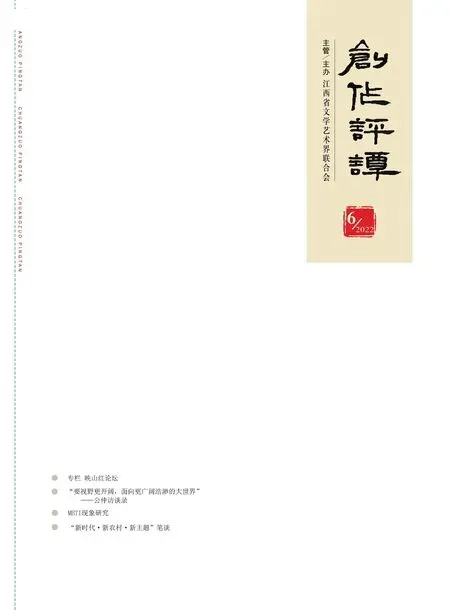新时代·新农村·新主题
——论中短篇扶贫题材小说的三个主题
2022-03-22郭诗亮
◎ 郭诗亮
2015年11月27—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会议将消除贫困提升至国家战略来推行,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更是成为社会热词。在此过程中,扶贫干部们所遇到的困难和极端贫困村落中村民的生存现状等,通过网络传播后,常使人倍感揪心。当然,不断被克服的困难和接连传来的脱贫喜讯,既证明了党和国家脱贫攻坚的决心和力度,也展示出基层扶贫干部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智慧。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实践,通过作家的中介作用,反映到小说中,形成一批扶贫题材小说。这些刻画时代发展脉络的作品,在展示贫困地区的扶贫者和被扶贫者共同致力脱贫的过程中,为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同时,由于贫困村落的地理位置、致贫原因及脱贫计划等不同,而导致扶贫工作存在相当的复杂性。现实的错综复杂决定了作家创作主题的丰富性。概括而言,中短篇扶贫题材小说主要有以下三种主题:一是讲述扶贫过程中的悲喜剧;二是书写易地搬迁前后的故事;三是塑造农村新人形象。
外来的扶贫干部与本地的贫困户,通过扶贫而被紧紧联系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上相互磨合,从而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一幕幕悲喜剧。夏天敏的《胡树和他的牛》(《当代》2020年第2期)讲述光棍儿胡树在扶贫队员的帮助和感化下,与他的牛一起找回自尊、重拾希望的故事。挥霍掉大部分扶贫资金的胡树,买了一头未老先衰的牛,然后在扶贫队员的督促下,他和牛惺惺相惜,相互成全,最终脱贫。这篇小说以自尊为线索,力图展示一个人只要有自尊,在精神上站起来,就能实现脱贫致富。与此相似的是李相华的《朱向前的皮卡车》(《福建文学》2021年第11期),扶贫干部项波按照许局长的指示,将两个定点帮扶对象促成夫妻,从而使双方人力资源和车力资源流通起来,实现脱贫。小说以“人长期不动变成懒汉”与“车长期不动容易变坏”类比,写出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是不懂得善用自己的资源。而一旦有许局长这样英明的领导,贫困户便完成了“恋爱+脱贫”,既解决了单身问题,又解决了贫困问题。显然,这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徐广慧的《麦海》(《人民文学》2021年第9期)同样具有理想主义气质。扶贫干部老张来到贫困村来福村,从为贫困户实现梦想切入,修路、招商,实现脱贫。在此过程中,村民们齐心协力,扶贫干部无私奉献,商人乐善好施,仿佛多年未解决的问题都随着老张的到来,迎刃而解。乐观理想的人物,与小说极具抒情口吻的叙述,和叙述者时常穿插其中的感叹相结合,使这篇小说具有《创业史》继承者的风度。梁弓的《外来户老莫》(《山东文学》2019年第2期)和《白马湖的春天》(《西部》2019年第4期)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前者以老莫为主要叙述对象,后者以焦三爷为叙述对象。小说通过对贫困户的刻画,以及对老莫和焦三爷命运的书写来叙述白马湖的脱贫故事。“我”改变了老莫谨小慎微的性格,并帮助他落实工作,从而使他实现精神和物质双重脱贫。而老莫的善良和智慧又对“我”的扶贫工作以及个人成长具有很大帮助。焦三爷则从最开始的趾高气扬,到最后受到贫困户们的宽容,与村民们和解。两篇小说以人物而非情节为主线,在扶贫题材小说中别具一格。
在以扶贫过程中的悲喜剧为主题的小说中,青年作家李司平的《猪嗷嗷叫》(《中国作家》2019年第5期)独树一帜。故事从贫困户发顺打算杀“建档立卡猪”过年开始,通过杀猪故事的延宕,触及脱贫户因思维局限返贫、基层干部扶贫方式简单粗暴、领导干部搞形式主义、农村男子家暴等多个社会问题。由扶贫干部赋予生存权的“建档立卡猪”和发顺等人的激烈角逐,也揭示了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并非同心协力,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矛盾。这篇小说既因故事的曲折离奇而具有相当的戏剧性,又因对多个社会问题的大胆书写而开拓了此类小说的表现范围,且能真正触及扶贫过程的艰难,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湖南作家何石在《那山那村》(《湖南文学》2019年第2期)和《将心比心》(《湖南文学》2019年第9期)中,突破了扶贫干部和贫困户交流的叙述套路,以先富村带动贫困村和先富村民带动贫困村民为叙述主线。《那山那村》中,赤泥村村支书陈松柏在使赤泥村富裕后,试图带动八里山村脱贫,他年轻时的情敌张清平则在外地与他暗中较劲。他们一个在内做工作,一个在外引资金,不自觉地达成合作,并在八里山村脱贫的过程中达成和解。《将心比心》则是村支书许仲英帮助下岗渡工刘松林成为脐橙大户的故事。何石的作品充满对湘西南人性美的书写,村民之间的矛盾往往被彼此的善意冲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云南作家潘灵的《豹子》(《青年作家》2020年第10期)展示的却是扶贫干部李小东之恶。李小东在官场受到排挤后被下放扶贫,他一心想着抱上王副县长大腿,在请人私造猎枪后,怂恿贫困的猎户黄二狗去猎杀豹子,最终黄二狗“误杀”了村民。小说将社会时事偷猎和官场斗争等结合起来,既写出以打猎为生的黄二狗一家在现代社会的无所适从,又写出扶贫干部的身不由己和不合理的欲望之害,具有警示意义。
在一些村民居住分散,且不便于铺设交通路线和水、电管道的地方,脱贫的方式常常是易地搬迁,即把村民们集中起来,另找居住之地。传统生活方式和新的居住习惯之间的矛盾,是这类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易地搬迁割断村民们的历史,使他们走向不可知的未来,这使此类小说既具有某种苍茫悲壮的气质,又具有对扶贫工作反思的深度。彝族作家北雁的《安居》(《延河》2021年第4期)将老一代坚守祖地的愿望和年轻一代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冲突,以父与子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村里最有威信的阿普,被其世侄、儿子、侄子、学生轮番游说搬迁,他坚持认为诺苏彝人的根在老房子,但最终还是为了年轻一代的希望而同意搬迁。说服阿普时,尽管双方态度温和,但却各自都摆出观点进行交锋。在此过程中,简单化的易地搬迁暴露出许多问题,使脱贫在此成为两难的选择。因此,阿普最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妥协,便既具有彝人远离祖地的悲壮之感,又有老一代为后世着想的大爱之情。此外,小说还写到人与马的感情问题,但并未深入探讨,而是以被卖的马又回到家结尾,显示出作者对彝族村民的美好祝愿。与此不同,吕翼《穿水靴的马》(《边疆文学》2021年第1期)讲述的是一个搬迁中人与牲口被迫分离的故事。陇启贵搬迁至“幸福家园”,就必须与他的马幺哥分离,但他却找不到安置幺哥的地方。陇启贵不排斥甚至有些憧憬小区生活,只是他同样无法割舍与幺哥的感情,因而陷入两难处境。小说在陇启贵与被卖掉的幺哥再次相见时结束,这既显示出人物在面对此类问题时的无力,又揭露出易地搬迁带给人的精神困境之复杂。王莉的《踏花行》(《广西文学》2021年第12期)中也有类似片段。大狗黄三因主人易地搬迁而被送人后,又拖着沉重的磨盘走到家中死去。黄三的家乡情结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易地搬迁的人们心中难舍的故土情。《踏花行》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采用儿童视角叙述,从九岁的莫巧巧眼中看村民的搬迁故事。正因此,小说得以细腻地表现母亲不得不抛下嫁妆木柜时的伤感和小学老师对农村走向没落的遗憾。此外,种地工具被变卖所传达出的农民将成为新的城市底层打工者之意,这又与懵懂纯洁的莫巧巧等人一起,营造出小说淡淡的伤感氛围。
此外,还有一部分易地搬迁主题的小说,并不着重刻画搬迁脱贫的两难处境,而是试图回答“搬迁之后如何”的问题。韩永明的《小羊咩咩》(《北京文学》2021年第5期)讲述贫困户老万独自坚守旧生活方式的故事。老万之死意味着易地搬迁彻底成功,但在小鲁队长这里,却也意味着田园生活方式的消亡。通过刻画纯洁的老万形象,作者振聋发聩地提出质疑:难道老万势利的兄弟姐妹所代表的山下生活方式,一定比山上的更好吗?如果不是,那么搬迁的意义是什么?当然,作者对山下和山上的书写有简单化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提出的问题的确值得深思。沈洋的《易地记》(《边疆文学》2019年第10期)则主要表现农村人在搬迁后适应新生活的过程。受伤且生活无保障的李有光在社区干部赵姑妈的帮助下,找到工作,重拾生活的信心。村民对干部的误解,因干部的责任心和实际贡献而消除。村民们最终理解了干部的苦心,从而过上幸福生活。有趣的是,这个表面幸福的故事底下,却潜藏着诸多不公平的因素。李有光受伤的原因和应得的保障没有得到解决;祖拱嘴五十万的新房被强拆,甚至本人也因阻拦异地搬迁工作而被判刑;李有光的工作问题得到解决,而大多数村民的问题却被搁置。两条线索一显一隐,书写易地搬迁下的幸福和不幸,传达出的是底层群众无法表述自己的困境。夏天敏的《歇云小区》(《中国作家》2020年第7期)表现的是以德恒老汉为代表的新搬迁至小区的村民对故乡的深厚感情,以及祭祖时找不到祭奠对象的无根之感。德恒老汉对羊的喜爱,体现的是他对旧生活方式的迷恋,以及对小区生活的排斥。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关注到农村老人的生存困境,对他们无法像年轻人一样迅速适应新生活,又背着沉重的传统包袱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
在书写扶贫故事的过程中,一批农村新人形象也被塑造出来。这些形象既包括扶贫干部,也包括一些中青年贫困户。他们像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新人一样,具有乐观理想的气质和坚定的信念。不过受限于中短篇小说的容量,这些新人往往只具有少许的成长性,使这类主题的扶贫题材小说存在一定的缺憾。此外,塑造新人形象离不开具体的扶贫故事,这也使得这一主题的小说常常与前两类交叉。徐霖的《鸟落下的地方》(《边疆文学》2021年第10期)是一篇女扶贫工作队员的自白。小说以城市的钩心斗角和农村生活的单纯为两条线索,讲述“我”在扶贫中接受农村“改造”,从而获得心灵上的独立,成长为自尊且能够帮助他人的人的故事。“我”在扶贫过程中,与贫困户们一起获得蜕变。有趣之处在于,小说不只是叙述贫困户在扶贫工作者的帮助下脱贫,而是将扶农村物质之贫和扶城市精神之贫,作为扶贫的两重内涵,从而完成一次城乡互帮互助的叙述,并最终将“我”塑造为没有历史包袱和精神困境的富足的新人形象。沈洋《易地记》中的赵姑妈和夏天敏《歇云小区》中的王竹笋,则是作为从农村走出但迅速适应新生活的社区干部形象出现,她们既能理解搬迁户们的精神和生活困境,从而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又能理解新生活的规则和习惯,并有效地约束搬迁者的行为。在此意义上,尽管她们不具备成长性,却也是扶贫工作所培养出的农村新人。李相华的《朱向前的皮卡车》、何石的《将心比心》和徐广慧的《麦海》则致力于塑造贫困户中的新人形象。朱向前、刘松林、老李等人,在扶贫开始后,经由扶贫干部的引导,迅速成长起来,成为脱贫的主力和示范。他们对贫困深恶痛绝,向往美好生活,因此一旦有机会走出困境,便成为贫困户中的引领者,成为农村中的新人。尽管这些塑造农村新人形象的小说仍有一些缺陷,如成长性不足、理念化严重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书写不仅有助于提升故事的可读性,也凭借方言口语等为小说带来更多的生活气息。
在以上三类主题中,讲述扶贫过程中的悲喜剧的小说,由于扶贫过程的复杂性和农村生活的丰富性,而大大拓宽了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广度;书写易地搬迁故事的小说,则以人在物质贫穷但精神富足的旧生活和物质富足但精神匮乏的新生活之间的两难处境,揭示贫困户的精神困境,从而深入挖掘了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深度;塑造农村新人形象的小说,则既是对“五四”以来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人物群像的丰富,又是对当前时代农村人物形象的精彩展示。总体来说,扶贫题材小说刻画了时代的发展脉络,反映的是时代的大主题。此类小说尽管在当下仍存在一些缺陷,如过分简单化扶贫过程和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缺乏艺术加工以及图解政治等,但它们在反映时代的发展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相信并期待扶贫题材小说会有更加优秀的作品产生。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 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理论导报》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