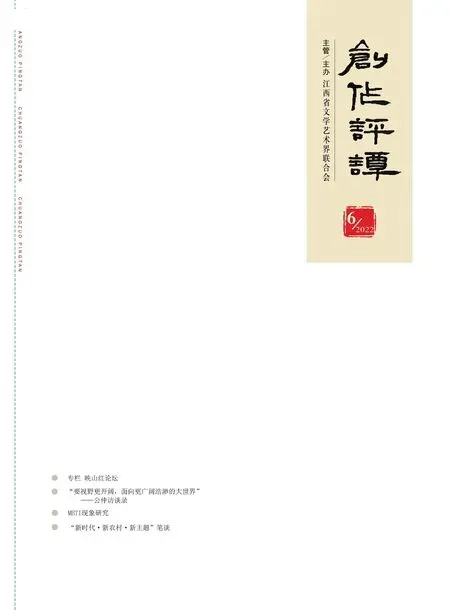中国红色文艺:多种美学基因的复杂聚合
2022-03-22◎李震
◎ 李 震
我曾经在首届“映山红文艺论坛”上讲过,“红色文化基因应该是一个国际性的概念。它应该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1]。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具体讨论中国红色文艺的美学追求问题。我想要深入认识和理解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对构成中国红色文艺的美学基因图谱进行分析。我认为中国红色文艺是多种美学基因的复杂聚合。具体而言,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中国民族民间审美趣味的文人化和西方某些艺术形式的本土化在中国红色文艺实践中的复杂聚合。这一聚合过程从延安文艺实践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起步,一直延续至今。这里结合毛泽东《讲话》精神,就其中几个核心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中国红色文艺美学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阶级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基因组合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者,毛泽东在《讲话》中从多种角度论述和强调的“人民”,当然首先是源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阶级论中的所强调的,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的人民。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论述过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历史正是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早期接受过黑格尔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来自所谓“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精神自由学说的影响,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人及其自由本质来自“自由自觉的活动”即“自由劳动”,来自人的实践过程。而这一实践过程就是历史。他曾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4]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这一历史主体的创造者,便是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无产者,便是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人民。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正是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
同时,作为一个生长于中国文化沃土,又以熟读中国古代典籍著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毛泽东对“人民”的理解和情怀势必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基。在中国三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史上,“人民至上”的民本思想根深蒂固。人们一般会将民本思想的源头追溯到儒家经典中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并认为是儒家圣贤给统治者谏言的治国安邦之策。而事实上,民本思想早在炎黄和尧舜禹时代就已经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了。无论是在典籍中还是在民间传说中,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中华民族先祖的故事,大多是在讲述先祖如何体察民情、体恤民生、教民稼穑、救民于水火的事迹。在典籍中,早在孔孟之前的五百多年前,西周初年形成的《尚书》中就有大量民本思想的记载,如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而且这句话之前是“皇祖有训”,即先祖的先祖就有此古训;《尚书•泰誓上》中又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这些说法中,民不仅贵于君,而且高于“天”,是邦国之本。这种民本思想也充分反映在历代文论中,如“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5]“写天地之光辉,晓生民之耳目”[6]等等。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和文艺观,一直是中国传统文艺的核心价值观,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学艺术史,也孕育出了诸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大量以民为本的文艺作品。
这些古老的文化思想和文艺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阶级论和人学,尽管源自不同的文化时空和思想体系,但却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文化脉络,构成了《讲话》中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坚持人民立场、向人民群众学习和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人民文艺观的思想文化根基,构成了中国红色文艺美学的人民性。
二、中国红色文艺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思想的现代化
在《讲话》中,毛泽东从文学艺术与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等多个角度,论述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这对中国红色文艺,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艺形成影响深远的文艺观,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中国当时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中,文艺属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同属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7]毛泽东早在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经将这种理论用于对中国文化的实际问题的分析,并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8]在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中,这种思想已经成熟。
同时,必须认识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毕竟是在中国的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因而这种对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艺观中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思想应该有着潜在的联系。
“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文艺观中的核心思想。早在先秦时期,“文”就与“道”构成了辩证统一体。在西周初年形成的《礼记•乐记》中就说过:“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荀子曾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9]后又有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韩愈、柳宗元的“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等历代文艺思想家的论述、倡导。及至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尽管“道”的含义因时而异,但“文”作为“道”的载体的思想一直延续至今,构成可以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相互融合的红色文艺美学观的核心内容。毋庸讳言,这种文艺观,曾被一些学者、文艺家认为是功利主义的。在《讲话》中,毛泽东不仅没有去回避“功利主义”的质疑,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10]事实上,在中国,这种所谓“功利主义”早在两千多年中形成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艺观中就已经存在了,表现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表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表现为中国传统文人心中必须要有“天下”。
依据意识形态理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文以载”道思想之于中国传统美学的主导性意义,这两种美学思想在中国红色文艺理论和实践中已经融为一体,构成了中国红色文艺美学的基本属性,尽管这两种思想,特别是“意识形态”和“道”来自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三、中国红色文艺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的反映论与“言有三表”说
在《讲话》中,毛泽东充分论述了社会生活与文艺的关系,并明确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而且说,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1]。反过来,“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2]。这些论述是中国红色文艺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形成的基础。
这种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的反映论、阶级论中国化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反映现实和历史真实有着充分而精彩的论述。恩格斯在《致玛•哈格纳斯》中延续了他近半个世纪前所写的《德国民间故事书》中要求民间故事在“适应自己的时代”基础上的“真实性和合理性”[13],他盛赞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14]。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提出了现实主义美学最经典的论述:“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5]
这些论述显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者的毛泽东对文艺与现实关系,以及文艺反映现实的“六更”之说的思想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红色文艺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也延续了中国文艺从《诗经•国风》以文艺反映现实人生、反映时代真实的美学传统。在这一传统中,除了出现了大量表现民生疾苦的文艺作品外,也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文艺思想,如墨子的“言有三表”之说就指出:“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16]其中“百姓耳目之实”是“言”之“原”,“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言”之“用”。其后有代表性的论述还有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白居易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等,与文艺家们大量反映现实历史和时代真实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
《讲话》虽然没有直接引用和论述这些来自中国传统文艺的思想资源,但却明确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17]这种来自中国本土的文艺反映现实、表现民生疾苦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实践,与《讲话》中将人民生活作为文艺唯一源泉的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作为美学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的反映论、阶级论共同构成了中国红色文艺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
四、中国红色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美学风格:基于民族民间审美趣味的文人化与西方文艺形式的本土化
从《诗经》开始,中国文艺便形成了风、雅、颂三大传统。“风”作为民间传统,始终是作为文人传统的“雅”和作为庙堂传统的“颂”的基础。从西周的“大司乐”到汉代的“乐府”,再到历朝历代的到民间“采诗”制度,中国文艺始终没有离开过民间文艺形式与民间审美趣味的肥沃土壤。这一传统到红色文艺兴起的延安时期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那就是文人文艺与民族民间文艺有组织、有理论、有纲领、大规模的自觉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红色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美学风格。
早在《讲话》之前的1938年,延安就出现了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直接支持下由专业文艺家与民间文艺家联合组成的文艺团体,并展开了大量文艺实践,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柯仲平为核心成立的用陕西地方戏曲演绎革命故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及大力开展朗诵诗、街头诗、墙报诗等群众性诗歌运动的“战歌社”等。这些团体是在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指导之下开展的民族化大众化实践。在这些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结出了中国红色文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理论。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又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文人文艺与民间文艺相融合的运动——新秧歌运动,全边区参与这一运动的达一百五十多万人次,超过了当时边区人口的总数。在《讲话》和新秧歌运动前后,延安诞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别开生面的文艺作品。如《血泪仇》《中国魂》《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等。这些作品可以说标志着中国文人文艺与民族民间文艺的全面融合,标志着风、雅、颂三大传统的合流,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审美趣味的文人化已成为中国红色文艺一个显著的美学根基,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美学追求的开端。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美学基因的注入也不容忽视,那就是来自西方的某些艺术形式所代表的审美趣味。当时奔赴延安的文艺家中绝大部分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成长起来的文艺青年,有的甚至有过国外留学的经历。这些文艺家深受西方文艺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文人文艺与民族民间文艺相融合的过程中,西方文艺基因自然也融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白毛女》和《黄河大合唱》。《白毛女》本来就是歌剧,而歌剧就是西方艺术形式。作为歌剧本土化的最早实践之一,《白毛女》并没有照搬西洋的咏叹调和宣叙调来唱中国故事,而是用河北民歌、陕北民歌来唱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贫苦女性的故事,唱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历史大势。《黄河大合唱》则是中国现实、中国旋律、中国激情,与西方交响音乐、歌队合唱的一次成功融合。这种将中国民族民间审美趣味与西方艺术形式和文人文艺的融合,构成了中国红色文艺美学风格的深厚根基,也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开了先河。特别是本土歌剧的发展,基本上延续了《白毛女》以西洋的艺术形式,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唱中国故事的传统,诞生了《江姐》《刘三姐》《阿诗玛》《洪湖赤卫队》等一大批本土化的精品歌剧。甚至在八大“样板戏”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西洋歌剧、交响音乐、芭蕾舞等西洋艺术形式的影子。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中国红色文艺美学并不是有人所说的简单的政治理念的直接美学化,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现代化、中国民族民间审美趣味文人化和西方艺术形式本土化等多种美学基因的复杂聚合。
注释:
[1]李震:《中国红色文化基因传承的历史逻辑》,《创作评谭》2022年第1期。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7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4]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页。
[5]墨子:《非命·上》,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6]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2页。
[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4页。
[9]《荀子•儒效》,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52页。
[1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4页。
[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0页。
[1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1页。
[13]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15页。
[14]恩格斯:《致玛•哈格纳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2页。
[15]恩格斯:《致玛•哈格纳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页。
[16]墨子:《非命·上》,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26页。
[1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0页。